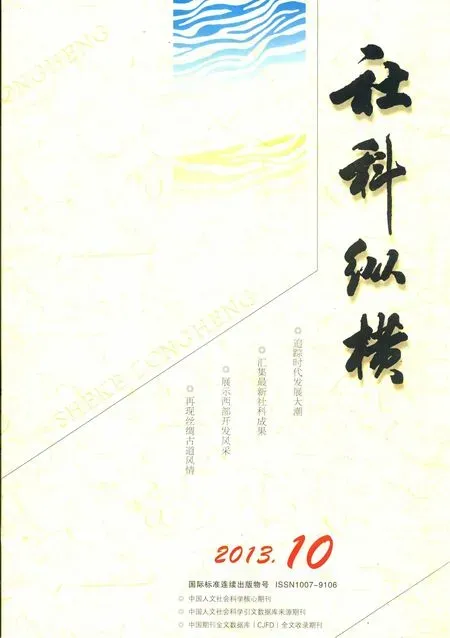试论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本真教训——缺失“重建个人所有制”商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姜中才 王 远 季云坤
(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22)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不应该是本真教训
在反思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本真教训时,主流学界一般都指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所依据的就是生产力决定论。据此原理,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建国初期,只能是“先工业化后合作化”,否则就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论证者一般都引用刘少奇的观点——“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1](P430);“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2](P 33)
对此,本文异议如下:
其一,这种教训之判断没有考虑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逻辑。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以贫雇农为主的农民阶级。最基本的动员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挖掉苦根,翻身做主”等。革命胜利后,虽然成了小块土地的个体经营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既没有骡马犁杖,又缺少启动资金,更没有经营经验,一有天灾人祸或市场竞争的挤压,便会向那些中农和富农高息借贷,低价当地,重返贫苦之渊,很难挖掉苦根,更难当家作主;而那些在革命中基本上持观望态度的中富农,既有田又有钱,既有骡马犁杖又有经营经验,很快便富上加富,进而导致“中农化”和“两极分化”的“双化”趋势。对主要依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共来说,如果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政治道德不能容许,必须将规律化的经济问题阶段性地让位于政治上的承诺问题。一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3](P243)
这种阶段性的经济让位于政治的历史选择,并不是不重视生产力,而是为生产力的发展奠定政治制度的坚实基础。1956年底,当这种政治制度基本确立之后,毛泽东便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P171)
尽管之后的历史并没有“搞”什么资本主义,但毛泽东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类似思想是坚定的——“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出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社会主义。”[5](P148)但中国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和机械化——“在我国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只有在农业已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6](P182)基于这一思想,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革命”的观点——先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再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7](P366)
其二,这种经济让位于政治的阶段性历史选择,并不违背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是,这个规律并没有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如恩格斯所指出:“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8](P70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显然是一种积极的“反作用”。
二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将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当有人将这种历史分期模式强加到他的名下时,他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P342)
这就是说,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他们的社会进程必然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发展图式。
其三,“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无须等到……”的合作化方针。
恩格斯针对法国社会党人企图保护小农的观点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0](P498-499)“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10](P500)之所以“无须等到”,是因为这种“等到”性的保护“仅仅是保护他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是延长他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10](P491)建国初期对个体小农“先工业化后合作化”的“巩固”性保护,与恩格斯当年否定过的“等到”性保护可谓异曲同工。
其四,先政治后经济的阶段性历史选择,是东方“非中心”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性选择。
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东方“非中心”国家埋葬了西方“中心”国家的殖民主义,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这种“埋葬”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让位于政治的阶段性历史选择。至于这些“非中心”的“第三世界”为什么仍旧是“第三世界”,甚至沦落为最不发达的“第四世界”,则是一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这就是第一次政治选择之后的再选择问题。
其中之“再选择”,又分两个方面:其一,由政治到经济的再选择;其二,由政治到政治的再选择。就“其一”来看,多数国家政治独立之后,因急于经济独立,而走上就经济论经济的“馅饼”到“陷阱”的道路。典型的就是“拉美现象”——唯经济而经济,单纯做大经济之“馅饼”,忽略政治之于“馅饼”的公平切割,导致两极分化,进而掉入经济、政治、社会等系列危机的“陷阱”之中。
就“其二”来看,一些国家政治独立之后,在第二次政治选择中东施效颦地走上了“中心”国家的议会民主制道路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道路。典型的就是与中国具有相当可比性的印度。当我们今天谈论新中国的第二次政治选择时,即毛泽东所说的继土地改革之“第一次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亦即合作化革命时,我们切不要忘记,正是中国有了这个“第二次革命”而印度没有这个“第二次革命”,才导致印度与中国之发展差距如此巨大。尼赫鲁的农村政策也可以说是刘少奇当年倡导过的“养肥猪政策”——蓄养富农成“肥猪”后再予以“革命剥夺”,但最终的结果是少数人“肥”得要死,绝大多数人“瘦”得要命,以致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至今仍达3亿多,且多是因“肥猪”兼并而失地的贫苦农民。
还有列宁开创的苏联,首先是通过农村合作化这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基础,再通过工业化而装备集体化,进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苏联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晚年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合作社》中——不仅认为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而且把合作社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甚至基于这种认识作出一个重要判断:“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1](P367)。
历史不能假设,但不妨做一下逻辑性假设:假设“养肥猪政策”压倒加速合作化的政策,必然会造成这些养肥的“肥猪”不仅是原来的中农和富农,更多的是握有权柄的基层干部,甚至因为其特权而成为比一般的“肥猪”还要肥大的“肥猪”。一旦如此,再予以“革命剥夺”的可能性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掌握“革命剥夺”之权力的“肥猪”不可能去剥夺自己,也不可能去剥夺与其利益攸关的其它“肥猪”;更何况,在两极分化规律的作用下,这种“肥猪”只能是数亿农民中的极少数而已。
二、本真教训——缺失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认识及实践
那么,本真教训何在呢?
其一,缺失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认识。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其基本的所有制原则不是“联合体”控制的公有制,而是自由人“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没有这种“重建”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自由人”就会失去赖以自由的经济基础,“联合体”就会由“自由人”自我主导的社会力量异化为少数人控制的超经济强制的政治力量。
遗憾的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制约,理论准备的不足,实践经验的欠缺,在反逼农业合作化加速的四次争论中,无论毛泽东代表的“正方”,还是刘少奇或邓子恢代表的“反方”,都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导致争论双方从头到尾都没有争论到“点子”上——毛泽东过于强调“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刘少奇等过于强调“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贸易自由)的“自由人”,没有一方论及“联合体”之中的“个人所有制”,导致在后来的实践中出现“联合体”与“自由人”的双向异化。
其二,缺失对“个人所有制”的“重建”。
由于认识上的根本性缺失,导致实践中过于强调“合”的作用,忽视“分”之功能——没有任何“重建”社员“个人所有制”的尝试。进而导致社员个体能动性缺失;导致社员对代表国家的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具有畏惧性的依附关系;导致只有“联合体”的强制,没有“自由人”的自由——这是合作化运动尤其人民公社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亦即本真教训。
对毛泽东那一代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来说,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人民公社之“联合体”把权力还给广大农民群众之“自由人”。但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根本缺陷,导致实践中的“跑偏”和“异化”——“联合体”异化为对“自由人”的超经济强制,“自由人”异化为被“联合体”超经济强制的对象。
不管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意义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有着怎样的争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广大社员失去了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时候,同时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自由权和发展权,进而也就失去了人民公社的主人翁地位。毛泽东发动农村的四清运动,表面看是要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让“四不清”干部“洗手洗澡”,实际上是要让广大社员成为人民公社的主人。只是由于广大社员缺失“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缺失对自己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的把握,使得这种主人地位并未得以确立。
笔者通过当年的插队,亲身感受过人民公社的方方面面;又通过近几年的调研,反思过人民公社的本真教训。一个最大的感受是:许多经历过人民公社的那一代老农,一方面对人民公社有着某种眷恋情结,一方面又对当时的大队干部说三道四。主要说当时的干部如何管制他们,如何欺压他们,如何多吃多占,而他们却不敢有半句怨言。
当时的社员普遍惧怕干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下乡时所亲历的那个大队基本如此;听其他“青年点”同学反映的也基本如此。或许这是中国农民的畏官“天性”,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仍旧惧官,惧怕自己的“公仆”,就不止是“天性”问题了。畏官之根本,就是“个人所有制”缺失,导致自己的生存条件掌握在异化了的“公仆”手中。
三、“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谛
要理解这种“公仆”与“主人”的异化,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谛。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是通过“宣布每个公民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而予劳动者以“貌似的个人自由和独立”。这种解放,远不是无产阶级所致力的“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之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2](P 473)
这种不再作为“政治力量”的“社会力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或为恩格斯所明确定义的“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12](P473)。其经济基础就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13](P832)。
其中之“协作”是以“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但“共同占有”不等于“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所有权属于资本家,所体现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或“异己的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其所有权属于“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13](P832)。这种“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便是“这样一个联合体”,通过它,把“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等“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4](P121-122),进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P325)。
马克思之所以一再这样强调“个人所有制”,只能作这样的理解:没有这种“个人所有制”,无产者就永远是无产者,就永远不得超越政治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没有这种“个人所有制”,“自由人”就失去了赖以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基础,就势必要陷入一种经济上甚或生存上对“联合体”的依附地位,进而也就无以保障对自己自由发展和运动条件的控制,甚至会导致“联合体”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异化为少数人垄断的与“自由人”相对抗的“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下的“个人所有制”之所以是一种需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因为前资本主义就存在着大量的分散孤立的以小私有制和个人自由劳动为基础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早已为资本主义所否定、所消灭。社会主义决不是要恢复这种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在资本主义之否定基础上予以再否定——“消除”资本主义之“成就”——“协作”和“共同占有”——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并“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使现成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4](P112)
至于怎样把“现成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确保“自由人”与“联合体”的有机统一,则是视各国各时期所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实现形式的问题。但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作为“个人所有制”下的个人,只有在这个联合起来的“真实的集体”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14](P118-119)其二,作为“类存在物”的“联合体”,必须是一个“真实的集体”——充分尊重“个人所有制”及其基础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以此来完善“社会协作”和“共同占有”,使其成为与“自由人”相融洽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与“自由人”相对抗的“政治力量”。
人民公社式的公有制之所以凸显超经济强制,显然强化了“其一”,弱化了甚至忽略了“其二”。当今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消极后果不可否认。最积极的意义就是开始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分”之尝试;最消极的后果就是“统合”乏力,缺失一个“真实的集体”。如何将“分”和“统”或“自由人”与“联合体”有机结合,着实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课题。这个课题能否从历史的“镜子”而不是历史的“故事”当中得以科学借鉴,关键在于能否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本真教训。这个本真教训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而是缺失“个人所有制”的有机“重建”。
[1]中共中央文献编撰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A].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1949—1976(第 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列宁.论合作社[A].列宁.列宁全集(第 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