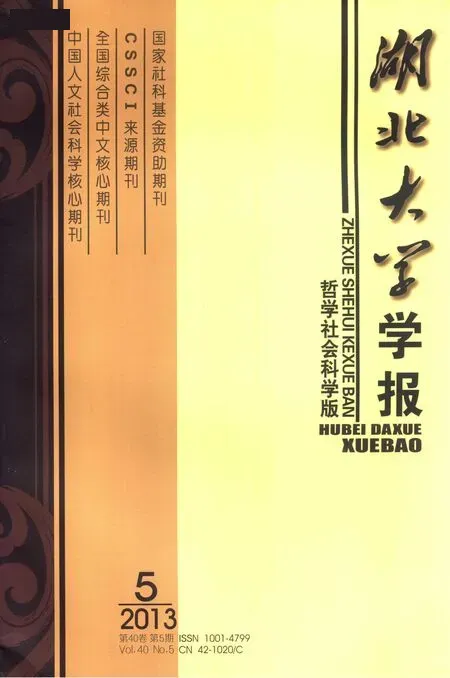孟子性善论所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问题
郭齐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孟子(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04年)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学者,一代宗师。本文拟讨论孟子的人性论与道德哲学思想,特别是性善论的真意及其中有关道德理性与情感的看法。
一、孟子的人性本善论的真意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人性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争鸣的一个焦点。《孟子·告子上》第6章记载了孟子的弟子公都子的提问。这一提问概括了当时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一是告子主张的“性①学界针对“性”是否可以翻译为“人性”这一问题曾经产生过争论。可参考:Ames,Roger T.“The Mencian Conception of ren xing:Does it mean‘Human Nature’?”In Henry Rosemont,Jr.,ed.,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Essays Dedicated to Angus C.Graham,pp.142~75.La Salle,III.:Open Court,1991.Bloom,Irene.“Mencian Arguments on Human Nature(jen-hsing).”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994):19~53;Liu Shu-hsien,“some Reflections on Mencius’s view of Mind-heart and Human Natur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2(1972):45~52。至于孟子思想中的“性”字的特殊含义,可参考唐君毅先生以“心之生”言性的解读,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1页。信广来教授把“性”译为“characteristic tendencies(特征的倾向)”。可参考:Kwong-loi Shun,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4,180~231。无善无不善”论,二是有人主张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②持第二种主张的人,据王充《论衡·本性》,接近于周之世子(世硕)。世硕的主张是性有善有恶,至于人趋向于善或恶,取决于“所养”,即后天的环境、教育的影响。据王充说,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都主张性有善有恶。,三是无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
告子主张“生之谓性”。在那时,“生”字与“性”字互训。告子代表当时流行的看法,常识的看法。告子说,人性如河水一样,引向东方则东流,引向西方则西流,都是由外在环境和条件决定的。孟子则提出了与当时流行看法迥然有别的有关人性的新看法。他指出,水可以向东向西,但水总是向下流,虽然人们可以把水引上山,但向上流却不是水的本性,而是外力使它这样的。人也是这样,人性本善,就像水向下流。而人的不善,不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孟子·告子上》第2章)。也就是说,人之为善,是他的本性的表现,人之不为善,是违背其本性的。例如牛山草木繁盛,但因人为的破坏变成了秃山,这不是说牛山的本性不能生长树木。同样,人在事实经验上的不善,并不能证明其本性不善(《孟子·告子上》第8章)。
孟子认为,犬之性与牛之性不同,牛之性与人之性不同(《孟子·告子上》第3章)。人有自然的食色之性,但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本质差异,在于人有内在的道德的知、情、意,这是人所固有的道德属性。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第6章)
按孟子的看法,恻隐、同情、内心不安、不忍之心,如不忍牛无辜被杀等,诸如此类道德的情感是善的开端、萌芽。人内在的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道德的同情心、正义感、羞耻感、崇敬感和道德是非的鉴别、判断,这些东西就是道德理性“仁”、“义”、“礼”、“智”的萌芽。这是人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的。把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扩充出去,就可以为善。
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第1 0章)仁是人最安适的住宅,义是人最正确的道路。人都有仁义之心,之所以丧失良心,是因为不善于保养。如果不加以保养,就会失掉。人们丢失了家中养的鸡犬,知道去寻找,然而丢失了良心,却不知道去找回来。因此孟子提出“求其放心”,即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的要求(《孟子·告子上》第11章)。人与非人的差别本来就小,君子保存了,一般老百姓却丢掉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第19章)。舜是按内心保存的仁义去行事,而不是在外力之下勉强地去行仁义。“由仁义行”,是由道德理性而行,是人按内在的道德命令而行,是人的道德自由;而“行仁义”,则是被动地按社会规范去做。
孟子与告子辩论,以类比法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上成功,又进一步运用反诘式、归谬法,在“生之谓性”之辩、“仁内义外”(告子一方)还是“仁义内在”(孟子一方)之辩上,最后归谬成功。按告子的思想逻辑,犬、牛之性与人之性没有根本的差异。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新的观念: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或他物的特殊性,这就是道德性。孟子不否认人有自然欲望之性,但他的意思是,如将自然欲望作为人之本性,则无法讲清人之与动物或他物的区别,只有道德本性才是人最根本、最重要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尺。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第6章)“情”,在此作“实”讲;“才”,在此与“情”一样,也即质性。这句话的意思是,“若照着人的特殊情状去做,自可以为善,而人在事实上为不善,不能赖在所禀赋的才上面。而孟子言情、才,就明白地显示,善不只存在于彼岸,实内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有了这样的心性禀赋,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性善乃专就禀赋说,与人在现实上行为的善恶并不相干”[1]149。
孟子把良心称为本心,本心是性善的基础或根据。良心本心是上天赋予的,“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第15章)。“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第15章)。孩提之童都知道爱其亲,长大也都懂得敬其兄,亲情之爱,敬长之心,就包含有仁义。这都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仁义是禀赋,是内在的。
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第21章)“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第8章)“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孟子·告子上》第8章)李明辉解释说,这表明孟子认识到“道德法则系出于道德主体”;“所谓‘仁义之心’,即是能决定仁义礼智之心,亦即能为道德立法的本心”[2]97。也就是说,心为道德法则的制定者。
孟子不仅发展了孔子的“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思想,而且发展了孔子的天道观。结合这两方面,他更强调了“诚”这个范畴,这与子思的影响有关。“诚”是真实无妄,是天道的运行规律,又是一种道德体验的状态,是对本心良知的最终根源——“天”的一种虔诚、敬畏之情。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第1 2章)以诚敬的态度对天和天道的反思和追求,就是做人之道。他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第1章)仁义礼智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充分扩张善心,就能体知这一本性,也就可以体验天道,懂得天命。保持本心,培养本性,才能事奉上天。无论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们都悉心修养身心,善待天命,这才是安身立命之道。孟子把心、性、天统一了起来。“天”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
二、孟子论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
孟子关于人性的讨论,是从人的情感——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出发的。人的道德直觉,道德当担,当下直接地正义冲动,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功利目的。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
在以上例子中,孟子指出,一个人要冲过去救一个即将落入水井的孩子,当下的刹那之间,并不是要结交孩子的父母或在乡党朋友面前显示自己,谋取虚荣。他内心有一个无条件的道德要求和绝对命令,使他不假思索地去做。人作为道德主体,自己为自己下命令,自己支配自己。这一主体既是意志主体,又是价值主体,更是实践的主体。仁、义、礼、智、信等,不完全是社会他在的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即是道德理性。孟子强调道德生活的内在性。
同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心,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既是理,又是情。这种“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没有四端之心,人就会成为非人。如果我们把这“四端之心”扩充出来,便会像刚刚烧燃的火,刚刚流出的泉水。扩充了它,就可以安定天下;而让它泯灭,便连爹娘都不能赡养。
按孟子的看法,善性良知是天赋予人的,是先于经验的,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特性、类本质,在人之类的范围内是具有普遍性的。他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听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第7章)不同的人,有诸多的差异,但口对于味道,耳对于声音,目对于颜色,又有共同的好恶,都欣赏美味、美声、美色。同样的,人的心也有其同一性,都爱好仁义礼智。我心对于理、义的愉悦,就像我口对于牛羊肉的喜好一样。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比普通的人先觉悟到人的道德的要求,懂得人的这种普遍性(“心之所同然”)。理、义是道德理性,人喜好之,如同感官对于美味、美声、美色的喜好一样。这个比喻很危险,但在孟子看来却很正常,因为道德的认识与实践,是与人的整个生命,首先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
孟子指出,仁义礼智这些道德性,源于本心,只是人们常常不能自己体认良心本心,因此常常需要反躬自问,自省自己的良心本心。他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第4章)这里所说的我所具备了一切,不是指外在的事物、功名,而是说道德的根据在自己,元无欠少,一切具备。在道德精神的层面上,探求的对象存在于我本身之内。道德的自由是最高的自由,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因为道德的行为总是自我命令的结果。反躬自问,切己自反,自己觉识到自己的行为无愧于天人,就是最大的快乐。不懈地以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达到仁德的道路没有比这更直接的了。除了反求本心,还要推扩本心,即把人的这种道德心性实现出来。“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第21章)。君子的这种本性,不因他的理想大行于天下而增加,也不因他穷困隐居而减损,因为本分已经固定了。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之心可以反映到他的神色是纯和温润的,还表现在他身体的各方面,乃至于手足四肢的动作上。本心通过推扩,通过四体,实现出来。孟子的重要论断“仁义礼智根于心”,“是不能通过外在的归纳来证明的,只能通过内在的相应来体证。人之所以能向善,正是因为他在性分禀赋中有超越的根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说性善。现实上的人欲横流、善恶混杂并不足以驳倒性善论的理据。由这一条线索看,儒家伦理的确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有相通处……”[1]147由上可知孟子的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的特征。
许多学者已经讨论过孟子思想中的理性与情感。例如,牟宗三肯定孟子仁义内在的观点近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律的观念,而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种讨论为刘述先和李明辉所继承和发展,上文已经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如David Wong在他的论文《孟子思想中有理性与情感之分吗?》中指出,孟子实际上并没有这种区分,并且论证说孟子不作这么区分有他背后的观念作为理据,并且这一理据是可以成立的[3]。尽管大家的诠释有很多不同之处,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曾经尝试把孟子思想放入西方哲学家所划出的基本区分中去讨论,然后发现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分歧其实产生于东西方对道德意识与情感的基本理解。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个很强势的区分,即理性(主动的,给予法则的)和情感或感性(被动的,为自然所决定的)之分。似乎情感仅仅是属于感性层面,而感性只是一种能力,它只是在受到刺激之后而根据人类自身的心理构造而作出自然的反应。马克斯·舍勒在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书中已经批评过这一区分。他试图揭示一个新的领域:“一种纯粹的直观、感受、一种纯粹的爱和恨、一种纯粹的追求和意愿,它们与纯粹思维一样,都不依赖于我们人种的心理物理组织,同时它们具有一种原初的合规律性,这种合规律性根本无法被回溯到经验的心灵生活的规则上去。”[4]308舍勒对传统的理性、情感的二分的挑战是一种洞见。然而他的工作尚是初步的。在这种“纯粹直观和感受”的领域,仍然有许多理论空间可以发掘。孟子以及许多支持其观点的宋明儒者,都将我们的视角引向仁义礼智等先天的价值。孟子深信,心自身具有对这些先天价值的天生的倾向。这些价值本身具有内在的条理,它并非从理论理性的原则推导而出,却同时是合理的。这令人联想起舍勒经常引用的帕斯卡的名言:心灵自有其理。
三、孟子的道德人格论
孟子十分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每每向诸侯进言,他从不把诸侯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决不被那些“大人”的权势所吓倒。他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第3 4章)的气概。他引用、重申曾子的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第2章)他有他的财富、爵位,我有我的仁义道德,我并不觉得比他少了什么。继承子思的孟子有着自由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傲气,有着“舍我其谁”的气魄、胆识。他发展了孔子关于“德”与“位”的矛盾学说,举起了“以德抗位”的旗帜,对后世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影响。
他有“天爵”、“人爵”的区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第1 6章)天爵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人爵只是世俗的功名利禄。天爵作为精神世界里的高尚道德、人格的尊严,操之在己,求则得之,不可剥夺。因此,君子所追求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孟子认为,道德原则或精神理想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依赖他人赐予的最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良贵”。别人给你的贵位不是“良贵”,“良贵”是自身具有的。
在子思子的德气论“五行”学说基础上,孟子还创造了“浩然之气”的名词。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第2章)这种盛大流行之气,充塞于宇宙之中。他又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孟子·公孙丑上》第2章)志是心之所之,是导向。志可以调动气,这是正向;反过来,气也可以影响志,这是逆向。孟子主张二者互动,持志与养气相配合。他指出要善于保养盛大流行的充满体内的气。保养浩然之气的根本在于养心,即恢复、保任四端之心。孟子主张调动气来配合道义,不仅使理义集之于心,而且使理义之心有力量,可以担当,可以实践,可以使理想变成实现。这样,面对任何安危荣辱、突然事变,就无所惧,无所疑,能当担大任而不动心。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气,也是我们生而有的气,只要不人为地伤害它,而善于保养它,就能合乎道义,辅助道义。养气在于养心,而言为心声;不正当的言论反过来会诱惑、伤害其心,故需要知言。对各种言论有独立思考,分析评判,不盲目信从,谓之知言。知言是为了辨志,知言也是养心的工夫。故以道德心为枢纽,孟子把持志、养气、知言统合了起来。《孟子·公孙丑上》篇的“知言养气”章号称难读,见仁见智,其实把握了以上所说,即把握住了它的中心思想。
孟子主张调动气来配合道义,不仅使理义集之于心,而且使理义之心有力量,可以担当,可以实践,可以使理想变成实现。这样,面对任何安危荣辱、突然事变,就无所惧,无所疑,能当担大任而不动心。孟子善于把四端之心即道德情感调动出来辅佐道德理性,成为道德实践的动力。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与康德相比,李明辉认为:“当康德将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排除于道德主体之外时,道德主体本身应有的自我实现的力量即被架空……这使得其道德主体虚歉无力。”[5]123~134
孟子之性善论肯定内在于人的生命中的超越的禀赋,是人行善的根据。但人是否真正发挥其禀赋,就在乎每个个体是否有修养的工夫。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存心”、“养气”、“存夜气”、“求放心”的存养方法。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10章)。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第2章)。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励了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孟子主张把“仁义”放在首位,提倡先义后利。孟子提倡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他主张做官要“求之有道”:“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第3章)“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第7章)在自己遭受侮辱时,怎么能匡正别人、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为,各有不同,有的疏远当时的君主,有的靠拢当时的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身居巍阙,归根到底,都得使自己廉洁正直,不沾染污泥。“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第9章)。这即是说,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场合中,选择道德还是非道德,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怎样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终究是自我作主的事。
[1]刘述先.当代中国哲学论:问题篇[M].纽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
[2]李明辉.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M].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4.
[3]David Wong.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Mencius?[J].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91,(41).
[4]马克斯·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倪梁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李明辉.儒家与康德[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