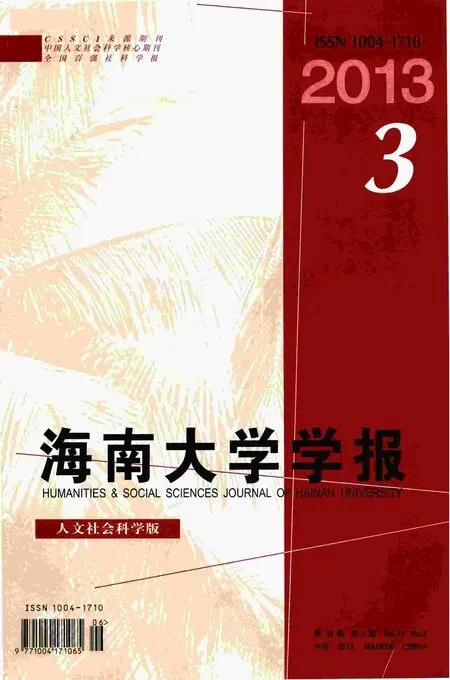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例外”与“常规”的争执——施米特与凯尔森法哲学比较研究
尹晓兵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法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神学》(1922)、《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1923)、《宪法学说》(1928)、《宪法的守护者》(1931)与《政治的概念》(1932)当中。通过它们,施米特阐释了自己的政治法学。
所谓政治法学,乃是一种对法学实证主义发展趋势的逆反或纠正,由于实证主义法学要求不断纯化法学研究对象,因而造成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也日益撕裂了法学与政治、法学与生活、法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政治法学提醒实证主义法学,在不断细化研究对象的同时,千万不可忘记一种整全性思维,一种整体的理论视域。构成这种整全性思维和视域的基础就在于政治:政治就是宪法,因而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所在。
从理论建构层面来说,施米特是以对实证主义法学——凯尔森(Hans Kelsen)的纯粹法理论为其典型代表①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本文中出现的实证主义法学,皆指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纯粹法理论之所以是实证主义法学的最典型代表,原因在于:纯粹法理论强调区别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把法律(实证法)作为一个单独和纯粹的研究对象,这比实证主义法学另外两个流派(社会学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更加纯粹和清晰。社会法学派由于强调法来源于社会,从而增加了法与习惯,法与地区,甚至法与气候的关系,而显得不够科学;历史法学派由于强调法与民族之间的天然关联,中间夹杂了民族情绪和民族感情等等非理性因素,因而显得不够客观。——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确立自己的政治法学观,具有很强的论战性。关于施米特政治法学的思想,有一种看法极富代表性:政治法学是建立在“例外”基础之上的法哲学理论,施米特的政治法学与一个国家和宪法的“危机状态”、“例外状态”紧密相连,它仅能够为“紧急状态法”(Ausnahmerechte)提供理论说明,离开了“例外状态”(Ausnahmezustand)就无法理解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思想。然而,清楚的是,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是在批判实证主义法学(特别是凯尔森的纯粹法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政治法学面对的不是一个部门法哲学,而是纯粹法理论本身。因此应当从整体上来思考以“例外”(Ausnhame)为特征的政治法学与以“常规”(Norm)②在德语中表示“例外”的单词是:Ausnahme。施米特强调法学与神学概念和结构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例外”跟上帝的“启示”密不可分,“启示”般的“例外”不能通过“理性”思维加以把握。德语中的“常规”是“Norm”,凯尔森法律思想的核心概念“基础规范”则是Grundnorm。在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当中,Norm 是指“实证法律规范”。根据施米特的研究,凯尔森最早指出法学与神学在概念和结构上的相似性,但是凯尔森却坚持法学相对于神学的独立性,认为Norm可以而且能够被人类“理性”认知而无需通过“启示”。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法学之间的关系,而不应局限于“紧急状态法”。
什么是“例外”?什么又是“常规”?施米特以“例外”为基础的政治法学理论与凯尔森以“常规”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双方于1931年发生的“谁是宪法的守护者”的争论,能否说明这两种理论水火不容?澄清双方之间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不仅仅有利于呈现政治法学、纯粹法学的轮廓,更能促进对“法”本身的思考。
一、实证主义法哲学与“常规”
实证主义法哲学,是实证主义思潮在法学学科范围之内扩展的表现。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顺应着启蒙运动以来高扬理性的时势,实证主义滥觞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自孔德(Auguste Comte)系统性地创立实证主义之后,这种研究方法迅速扩展到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孔德认为,与物理世界按照引力和其他的绝对规律运行一样,人类的社会也是如此。质言之,实证主义标榜,以实际存在的社会现实为研究出发点,要把社会现实本身自有的规律性揭示出来,发现“规律”并保证其“真理”性的力量在于人类理性。
由此,实证主义的诞生基于一个前提假定:人类社会也有规律可循。孔德自己就在《实证哲学教程》中,坦言他已经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且将其与人类认识演变的基本规律对应表述如下:“据此基本学说,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1]1在孔德眼里,实证阶段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高阶段,他所处身其中的时代就已经是实证主义的时代。显然,实证主义的兴起,与启蒙运动一样直接针对神学,甚至接受了启蒙运动以为神学是理性幼稚的产物这一前提。
当实证主义风潮渗透进现代法学研究之后,必然产生实证主义法学,即认为法学只以实际存在的并可以得到经验验证的规范为研究对象。以实际经验为出发点的实证主义法学却具有三个基本假设:
首先,实证主义法学基于“常规的(normal)”假设。在孔德的意义上,“常规”一词是指自然科学规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对应表述,是人文社会科学获得科学性的依据。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实验科学,其本质是“可重复性”,在连续的可重复性试验的基础之上,建立一定的数学模型,实现实验结果的常态化、平均化、规律化。在人类社会之中,一定的行为方式会引起相应的行为结果,一定的语言会对听者产生一定的行为影响,于是,在不断总结千千万万的行为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立法者基于对这些不断重复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关系的认知,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或者依据一定的价值要求改变这种关系,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可见,人类行为的不断重复性,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稳定性,是法律产生的基础。所以,没有“可重复性”,就没有“常规”,就没有以“常规”为基础的各种法律。“不断重复”是“常规”最为核心的特征。
其次,实证主义法学基于“法律与道德之分离”的假设。实证主义法学为了追求研究的客观性(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客观性是真理性的保证),要求研究对象的纯粹性,即严格把研究对象和视角局限在“实证”层面,因而必须撇开法律与道德、政治、习俗、惯例的关系。在实证主义者看来,道德、政治、习俗、惯例都是价值判断,法律如果要做到科学化,就必须排除它们的干扰,做到“价值中立”。客观而中立地看待法律,而不以道德的有色眼镜分析法律,就成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座右铭。
最后,实证主义法学基于“理性边界”的假设。实证主义法学对法律的分析,以人类理性作为最终保障。面对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和频繁变化,实证主义法学或者把视角局限于成文法,如同分析法学那样;或者把视角局限于法律概念,如同概念法学那样;或者把视角局限于社会群体,如同法社会学那样。所有这些视角及其法学派别,都必须建立在人类“理性边界”的基础之上。质言之,实证主义法学者,只研究理性认识范围内的法律现象,理性之外,信仰维度的规范和律法,闭口不谈。由此划清“法学”与“神学”的界限。
在实证主义法学的三个假设之中,最重要的是“常规”假设;“法律与道德分离”与“理性的边界”两大假设,都是“常规”假设的延伸和保障。这也暗示,“常规”容易遭受“道德”、“启示”的攻击和责问,于是实证主义法学要在“常规”周围,划定一条“道德”与“启示”不得靠近的界限。
实证主义者以经验为出发点的路径,这是“自下而上”的归纳总结之路。那么,是否存在从“理念”或“先验”出发的“自上而下”的综合判断之路呢?在西方思想史中,这条自上而下的道路是有的,具体表现为“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在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人们对于“什么是自然”的认识不同,自然法思想的内容也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是,作为超越于“实证法”之上的一种法而言,“自然法”的“超越性”维度始终存在。自然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十诫”,随着旧约向新约、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尤其是古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文化的推广,自然法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这个超越于人类法律之上,由上帝颁布的律法,是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绝对规则与命令,并且是人类社会保持稳定性的终极原因。上帝绝对的权威,可以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提供了自上而下的保障,这种“稳定”恰恰意味着人类社会不同于“规律”的“常规”。很显然,这个维度,被实证主义者决绝地抛弃了。
在实证主义法学内部,如何处理“常规”这个概念?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给予了很好的示范。在纯粹法理论当中,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性、科学性、严格性,法律必须有一个“等级结构”。凯尔森的推理很清楚,“若问监禁某人而剥夺其自由之强制行为何以合法并属某法律秩序,答案便是此行为乃出自司法裁判中个别规范之规定。若追问此个别规范何以有效、何以构成某法律秩序之一员,答案则为此规范符合刑法典。若再问刑法典之效力根据,则须诉诸宪法……然而,我辈若打破砂锅问到底,进而探寻宪法之效力依据,则惟有追溯先前宪法,并最终溯及某僭主或无论何种机构指定之历史上首部宪法。”[2]82-83一切社会纠纷和矛盾,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效力等级结构获得稳定的法律评价,从总体上保持了“常规”的实现。
那么,首部宪法的效力从哪里来?凯尔森的回答是:“基础规范”(Grundnorm)。对此表述,凯尔森解释道,“基础规范系实证地理解法律素材之必要预设,而非依法定程序制定或颁布,故不属实在法规范。”[2]84在这里尤其应当注意,“基础规范”,是理性的自我假设,是理性触摸到自己边缘的一种自我逆反式的防卫,正如数学当中的1 +1=2,为了整个数学大厦的奠基,而不得不假定其绝对真理性③参见笛卡尔《谈谈方法》对认识方法的规定,其中“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作真的接受”(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页)。在近代哲学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思想论争中,此处“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就是唯理论坚持的“自明真理”(如数学中的定理),它是其它一切逻辑推理、论证获得“真理性”的保证;但它仍然不能有效回应这一反对意见:所谓“自明真理”其实是理性乐观主义者“非理性”的“独断”,理性乐观主义者对它的接受与虔诚的信徒接受他们的“神”毫无二致。否则,为何迟至20 世纪,胡塞尔还要苦心构建现象学以获得“自明真理”?。“基础规范”这种在“理性限度内”无法得到说明的处境,“使得其追随者怀疑其整个理论是个神话”;因为这个假设,凯尔森被归结为新康德主义者行列——对于康德,切不可忽略他为“信仰”和“启示”所留下的“地盘”;尼采透彻地指出“康德的成功,仅仅是一个神学家的成功”。很明显,以“常规”为根本特征的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其根基最终却要用超出理性自身的“假设”来保证。难怪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断言:现代理性主义将被证明是一种虚假的理性主义(Schein-Rationalismus)[3]3。
进而言之,凯尔森如要坚持自己所声称的“实证主义道路”[2]62,就必须坚持研究方法的纯粹性和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按照他的逻辑,他就必须把基础规范作为一个类似于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事物,束之高阁,或“秘而不宣”[2]84,不能让它走下形而上学的神坛。因此,当凯尔森的实证主义法学强调其“常规”性时,就势必发生一种视角上的选择性遗忘,即忘记自己的“出身”及“来源”;否则,就会堕入要么自我欺骗进而欺骗他人,要么丧失自我无根飘泊的两难处境。对此,凯尔森仅仅增补性地指出,宪法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在现实当中具有了实效,其实效以“实际上遵从该法规的大多数人而定”[2]85——这已经是以“多数人的民主”来为相对主义的真理观作辩护了。
实际上,凯尔森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纯粹法理论自身的困惑,而是“理性”自身的限度与困惑。
于是造成了这样的尴尬局面:凯尔森以“常规”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法理论极力想要摆脱掉“例外”、“启示”、“奇迹”,但是又不得不把“基础规范”放在类似“启示”、“奇迹”的位置上。不仅凯尔森如此,他的继承人哈特(H.L.A.Hart)同样如此,后者在其思想中不得不保留一个“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把法律的来源交给一个类似于“启示性的自然法”来补充“实证主义法学”的不周延。如果继续往前追溯的话,这种理性的残缺早在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之一霍布斯那里就有清晰的展示。只是现代人往往沉浸在霍布斯以理性构建的社会契约之中,而遗忘了社会契约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人与人之间战争之时闪现于脑际的“一道理性之光”!然而,这道光何以被称之为理性的?是因为有人在背后进行计算吗?如果是计算,又是谁在计算?除了是“启示”之外,难道还有其他解释④施米特曾语:“自然状态的恐怖驱使充满恐惧的个体聚集到一起;他们的恐惧上升到了极点;这时,一道理性闪光闪现了,于是乎,新的上帝突然间就站在我们面前”(《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其实在霍布斯《利维坦》之中,神学的思想如同一条坚韧而飘渺的线,时刻拨动着研究者的心弦。引文中的闪光,可以称之为“理性”,但是称之为“启示”又未尝不可呢?而且,似乎称之为“启示”更加符合这种“奇迹”的解释。针对这个理性之光,英国哲学家休谟也曾认为,“出生于家庭之中的人处于必然需要维持社会的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同时也是出于习惯。同样的生物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为了维持规则而开始建立政治社会,因为没有它,他们之间便没有和平,没有安全,也没有相互交往”(David Hume,Of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in David Hume:Political Essay,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0)。在休谟眼里,政治和法律制度并非起源于人的理性设计,它们不过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为求方便而在无意中创造的各种规则的堆积。亦参见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二、政治法学与“例外”
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欧各国尤其是德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工业生产和经济迅速发展,思想界也日益活跃、繁荣,并且在20 世纪20—3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期:“魏玛时期”。这个时期成了自康德、黑格尔时代之后的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阶段。当时,各个人文学科纷纷逃离神学的桎梏,开始划定独立的研究对象,创造独有的研究方法,划定自己的学术领域并撇清与神学理论的联系。这样的研究趋势,几乎成了所有人文学科发展的惟一方向。然而,与此同时,也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接受不了文化传统中如此剧烈的“断裂”、激情的“弑父”,而想去寻找各个学科与神学之间的继承和联系,想要接续起西方文明发展的链条,为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人保留一条不离弃传统的“古典道路”。在这些人眼中,即便现代人文科学因为树立起理性的旗帜,把灵魂学变成心理学,把宗教当中的律法演变成法律科学,把自然哲学变成物理学、化学,也摆脱不掉自己与神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在启蒙之后有个大体相同的名字:保守主义者(Konservativ)。
在德国政治哲学家迈尔(Heinrich Meier)看来,施米特正是这样的人。“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相似性持续的减弱,正是1922年《政治神学》发起猛攻的中心所在。”[4]275为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政府主义是所有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样态,其他的政治哲学流派都可以看成是无政府主义的变种。无政府主义宣称“自我授权”和“自我管理”,但是却无法撇清自己与神学理论的牵连。须知“自我授权”和“自我管理”,只不过是人类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重新厘定,是启蒙之后人与上帝之间的“重新立约”。不但政治哲学如此,法哲学也不例外,施米特曾言,“凯尔森的贡献在于他自1920年以来便强调神学与法理学在方法上的联系。”[5]34只不过,原先的“全能的上帝”,变成了现代的“全能的立法者”。质言之,几乎现代国家理论当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施米特之所以要强调政治哲学、法哲学与神学理论的联系和关联,就是要为前者的发展,不但提供一个历史的眼光,更要提供一个可靠的地基。
具体到法哲学而言,实证主义法学由于拒绝道德、政治、习俗、惯例,因此它就只能在理性范围内,依靠概念之间的逻辑结构,形成一个密封的理论构架。外借自然科学(试验科学)的客观性,依靠“重复性”的支持,形成固定的系统流动模式,从而实现整个理论框架的稳定,维护人们“常规”的生活方式。然而人类的现实生活不但是“常规”的,更是千姿百态,万紫千红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显示出不同于“常规”的“例外”情形。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状况:法律一经制定,迫于社会的迅速变化,就面临着被修改的命运。如果固守实证主义法学的内在要求,对社会政治状况视而不见,那么势必造成实证主义法学理论愈发枯竭,法学研究的“整全视域”日益丧失。不特如此,实证主义法学由于要坚持“客观性”、“中立性”,其势必在价值层面坚持“相对主义”,而后者则意味着政治决定或政治机关可以被随意解释,更意味着:政治的无能。
面对着实证主义法学“常规”生活中“整全视域”的丧失、“政治的无能”趋势,施米特寻找到了一个工具:“例外”(Ausnahme),来呈现人类生活的完整面貌,并与“政治的无能”趋势作斗争。
“例外”是什么?施米特是从克尔凯郭尔那里找到了这个概念工具。施米特转述克尔凯郭尔的话说,“例外解释常规及其自身,如果人们想正确地研究常规,就只好先找到真正的例外。例外比常规更清楚地揭示一切。无休止地谈论常规已经令人厌倦,世界上存在着例外。如果它们无法得到解释,那么常规也无法得到解释。这个难题常常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常规不是以情感去思考而是以令人舒适的浅薄去思考。但是,例外却是以强烈的情感来思考常规”[5]14。在施米特看来,“例外”不仅仅是与“常规”并列的存在,更是比“常规”更加基础的概念。“例外”在解释力上要优先于“常规”。同时“例外”借助“强烈的情感”,把对“常规”的思考推出了“理性”的边界,为恢复或者重建“常规”与“启示”、“意志”的关联,提供了可能性。一种被实证主义法学抛弃的视角,有可能重新回到法学研究的视野中来。
针对施米特如何运用“例外”这一概念,刘小枫解读得很透彻:“施米特思想立足的专业是公法(宪法、国际法)和法理学,其法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反对实证主义的形式法学(或称纯粹法学),把公法看作是政治的体现,因此可以称为政治法学。”[6]65在刘小枫看来,施米特政治法学的思想,在于分辨出一个近代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上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主权。施米特的工作就是把主权拆穿,揭示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秘密:“国家主权说到底是人为的东西”[6]235。而要看透这一层,就必须先把凯尔森看透,把实证主义法学看透,“凯尔森把主权看做一个一般法律规范体系的观念,也就是让国家主权消融在法律秩序的规范之中……规范当然没有例外可言。施米特用一句‘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掀翻了对国家的纯粹法学的理解。”[6]164主权概念当中的“例外状态”得到重新恢复,这是施米特试图挽救被实证主义法学丢失的“整全视域”所作的理论上的突破。自此,法学研究中以“常规”为基础的“规范论”思维模式之外,又产生了以“例外”为基础的“决断论”思维模式,丰富了法学研究的视域。
针对“政治的无能”,施米特要重新厘定政治的概念。在施米特最为著名的著作《政治的概念》当中,政治是作为“国家概念的前提”而提出来的,那么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从判断政治的标准而来,而政治的标准则是:“区分敌友”[7]138。敌友的区分,需要一个场景:在“日常”或“常规”情况下只是一种杀死敌人的现实“可能性”,敌友之间的张力,还没有非要人们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程度;而在“例外”状态或者“战争”状态,区分敌友乃是横亘在生命面前的唯一“现实性”,敌友的区分,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常规”中的“可能性”往往欺骗或者隐藏了“例外”才能揭示出来的敌友之“现实性”。在施米特看来,就区分敌友的“现实性”而言,遮蔽敌友之分的“常规”就是一种“谎言”。《政治的概念》就是要刺破这一谎言,还人们以政治的真实。
造成“政治的无能”,是因为实证主义法学“常规”的“谎言”;而实证主义法学之所以拿“谎言”当“真理”,是因为它们对“理性”本身的乐观迷信——他们相信凭靠“理性”建立的“常规”。在理性的盲目中,实证主义法学丧失了西方文化传统理性与启示这一整全视野。
事实上,每个民族的立宪过程,都是一段充满“血与火”的历史;宪法是一项或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记载和结果,传承和书写了曾经波澜壮阔的生存斗争史,而且会在未来不断继续这种书写地“修宪”。宪法不但是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作为族群意义上的对抗之结果,也是民族国家内战之结果。可以说,宪法与革命、战争有着同源同种的特质。宪法当中的每字每句都渗透着鲜血与智谋,斗争与妥协的硝烟。特别宪法当中的序言部分,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之注脚。实证主义者为了维护“常规”这一“和平”的法律和社会状态,使用“多元论”、“相对价值论”、“中立论”等冷冰冰的“理性”来驱散弥漫在法律当中的硝烟之时,在施米特看来,这无异于否定人类的历史,丧失对真理的追求,否定人类价值的高贵性:理性要求人们放下武器,在圆桌前商谈;理性要求人们放下民族的尊严,把人道主义视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理性要求人们把仇恨埋在心中,把脖颈伸到“中立的”法官面前。“政治”被终结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相互之间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针对这种“理性”的教导,施米特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以“理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背后,恰恰隐藏了一条最为重要的“信仰”:人惟有自身能够反对自身(人是上帝)。这是对人的无限“信仰”,对“理性”的无限“崇拜”。至此,“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信仰启示的探照下,整个“理性”反而成了一个最大的“例外”。正如施特劳斯指出的:“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只是现代理性主义的一个变种,后者本身已经够非理性的了。”“启蒙运动把传统中的例外,变成了一种立场之基础。”[3]4-7
实证主义法学,试图用理性的“铁笼”画地为牢,把自己圈在理性的界限之内,保持客观性和“科学性”,试图用冷冰冰的“理性”困死宪法当中民族情绪这只“巨兽”;试图用“常规”来为“铁笼”加上“链条”;试图用中立化、世俗化、相对主义彻底拒绝来自上帝的启示(人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而施米特想要用“例外”砸碎“常规”的铁链;要用“启示”来为陷于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泥淖的人们指路;纠缠于“常规”周围的幽灵,与政治浪漫主义的“机缘”亦有颇多相似;那随时都可能出现于天际的“奇迹”,如何能够被“常规”的“理性”思维模式认知。在施米特看来,实证主义者似乎忘记了:人就是上帝“奇迹般”的创造出来的。
三、区别与联系
施米特和凯尔森关于法哲学之间具体而微的差别,最为具体的表现在于两人1931年的论战。这一年,施米特发表了《宪法的守护者》(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同年,凯尔森针锋相对发表了著作《谁应该是宪法的守护者?》(Wer soll der Hüter der Verfassung sein?)。
施米特以“例外”的思想背景为宪法寻找一个守护者的时候,分别评价了司法者和议会成为守护者的可能性。就司法者而言,宪法的守护者这项议题,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如何防止最强的规范受到较弱规范的侵害。”[8]42而是司法者本身就存在问题,“只要司法权本质上仍然是司法权,那么就无法避免它在政治上永远会来得太迟的结果,而且司法程序规定得愈彻底、愈缜密、愈符合法治国的要求、愈符合司法权的形式,司法者来得就会愈迟。”[8]36另一方面,就议会来说,“议会由于其内在的多元主义而无法形成多数或不具行动力;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则是,在各个不同情况中形成的多数力量,会把所有法律上的可能途径当成其把持权力状态的工具与确保手段,并且机关算尽地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的期间,也试图限制最强大与最危险的对手寻求同样可能性的机会。”[8]119而帝国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乃是与魏玛宪法本身最为合体的选择。毕竟魏玛宪法第48 条⑤魏玛宪法第48 条:“联邦大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联邦大总统对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理,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联邦大总统得临时将本法114、115、117、118、123、124 及153 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得由联邦大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其详细,另由联邦法律规定之。”但是关于限制总统这个权利的规定根本就没有出台过,帝国总统成了法律秩序中的“例外”。为这道路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对于天主教有极深渊源的施米特来说,这些都顺理成章,但是,却要遭受来自理性的拷问,施米特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保证决断主义不致沦为不受约束的独裁主义?谁来保证这个游离于法律秩序当中的“例外”、“独裁者”,给人类“启示”的是“真理”而不是“兽欲”?
凯尔森认为“理性”可以做到,而且在奥地利建立了一个理性设计出来的机构——宪法法院。在凯尔森看来,宪法法院才是宪法的守护者。在凯尔森眼中,帝国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只不过是“19 世纪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而已。而君主一般与品行不良、骄奢淫逸、荒淫无度、偏听偏信的时代新画像相符合,是个不折不扣的“非理性”因子,而这个因子与新时代的民主氛围相差太远,太不入流。究其实质,宪法法院之所以能够守护宪法,在于其包含“多元民主的基本要素。”而民主就是理性辩论,乞灵于在辩论和协商当中,能够不期而遇“真理”。“真理”成了某种“机缘”,可遇而不可求。况且,宪法法院本身的运作,乃是在宪法之上仍有一个更高裁判者,凌驾于宪法之上,握有终极裁判权,显得更像是“专政”而非民主,凯尔森的困难恰恰在于,他要为一个民主系统当中的非民主成分辩解。不但对于宪法法院来说,凯尔森面对着一个理性的悖谬,而且就其思想倾向来说,如果真像凯尔森所希望的,把法律和道德相分离,那么极难避免的是,人们会把基本规范当成决断或没有外在正当理由的命令。于是,在理论的根基处,凯尔森面临着向施米特寻求理论帮助的困境。即以“常规”为特征的“理性”,要向以“例外”为特征的“启示”“意志”寻求帮助。
作为个人来讲,凯尔森一直标榜无神论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就其理论精神气质而言,凯尔森并未脱离神学影响,几乎可以说,这种影响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宿命。实际上,从启示神学的角度来看,施米特与凯尔森之间的理论纠葛可以表现在两个不同的信仰教条:“常规”创造或再现了一种和平的局面,乃是基于对宗教信条的信仰:“不要与恶人作对!”而且要做到“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9)。此信条被尼采誉为“福音书中最深刻的话语,某种个意义上,也是理解福音书的钥匙”。“与邻为善”乃是凯尔森所在的实证主义,祈求世界和平的最终神学根据。倘若离开了这个信条,和平还有可能吗?
施米特认为,有可能。不过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督信条之下:“人类的世仇”(《创世纪》3:15)和“该隐杀死亚伯”(《创世纪》4:8)。即“与邻为恶”、“骨肉相残”,胜利者保有和维护一种和平和统一。因此,需要建立以“同质性”为基础的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为战,建立帝国。以“战争”这样的“例外”所保证的和平时代,要比以凯尔森从“与邻为善”导致的和平时间长得多。这在埃里克·彼得森(Erik Peterson Grandjean)看来是再清楚不过了:“民族国家意味着战争,而罗马帝国则意味着和平。”况且还有天主教制度持续了长达1 500 多年的历史为证。
早在1927年出版的《宪法学说》(Verfassungslehre)中,施米特就提出了“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在谈到绝对意义上宪法的两种形式的时候,施米特指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首先可以指具体的、与每个现存政治统一体一道被自动给定的生存方式……也可以指一种根本法规定,亦即一个由最高的终极规范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系统(宪法=诸规范的规范[Norm der Norm])”[9]4-9在绝对意义宪法的第二种含义上,施米特提到了凯尔森,“在凯尔森那里,惟有实在的规范才有效,也就是说,惟有能够产生实际效力的规范才有效。这些规范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们依照正当的理由应该有效,而只是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根本不用考虑合理性、公正性之类的品质。在这里,应然突然消失了,规范性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粗陋的事实性同义反复:如果某个规范有效,并且因为它有效,它就是有效的。这就是实证主义……实际上,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权(即权力或权威),并且凭着它的意志而被制定出来。”[9]12
施米特试图将凯尔森的实证主义法学理论支撑下的宪法学理论,容纳进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来构建一个针对“魏玛宪法”的独一无二的“宪法学体系”。为此施米特找到了绝对意义上宪法效力的来源:意志、权力、权威(人民制宪权和政治意志),重新恢复了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es)的“制宪权”理论。而针对这一发现,直到8年之后的1935年,凯尔森才在其《纯粹法理论》当中指出,“法律规范无法自基础规范逻辑演绎而生,而只能由特定行为制定或发布,后者并非智识活动而系意志行为。”[2]82对一部宪法而言,“制宪权”就是一个民族政治意志的反映,在一个民族具体的宪法传统中,制宪权从民族意志中首次创生,而且是其历史上的“仅有的一次”。其后的制宪权,就其能够被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次的行使而言,每次都是全新的。归根结底,“制宪权”类似于“上帝的意志”:要有“光”,只是这里的意志乃是要有“一部宪法”。相对于实证主义宪法学体系强调“常规”而言,这种“制宪权”的“意志”无疑是一种“例外”,但这种“例外”恰恰解决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疑问:“第一部宪法从哪里来?”
显而易见,施米特的宪法理论并未直接向凯尔森的实证主义宪法观发起进攻,而是采取迂回包抄的路线,挖了实证主义宪法观的根,并且把它融入到自己的宪法学说(尤其是“绝对意义上的宪法”)当中。施米特比凯尔森的高明之处,体现在他把凯尔森的实证主义宪法观变成自己宪法学说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言之,施米特通过把“制宪权”与“宪定权”加以细致的区分,使得宪法研究的视角和概念更加丰富,这样原先宪法理论当中只有宪定权的概念,现在由于政治宪法学中制宪权的出现,把宪法理论的讨论推到了政治的边沿,扩展了法学研究的视野,增强了法学研究的质感。更主要的方面在于,施米特以“区分敌我”的“例外”弥补了凯尔森“常规”的不足,施米特的宪法学说是“例外”与“常规”的结合。
由此可见,施米特和凯尔森的根本分歧在于:在凯尔森眼里,实证法的来源在于先验的假设——基础规范;对此,施米特则指出,凯尔森是在“原地打转”、“同义反复”(Tautologie)、在“理性的牢笼”里纠结,始终无法在纯粹理性限度内找到一个可以依凭的地基。施米特自己的政治法学,则通过“制宪权”,把一种“启示”的意志(“人们要成为一种政治性的存在”这样的“天命”⑥关于这个天命,参见Heinrich Meier,Die Lehre Carl Schmitts Dritte Auflage,J.B.Metzler,Stuttgart,2009.S.30.迈尔指出“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3:15)”是施米特政治神学思想的核心和秘密所在。由此,依据圣经,敌人是注定的,而政治的标准是划分敌人与朋友,因此政治也是注定的。政治是《圣经》给人类的天命。关于此点的更详细的分析,参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特别是脚注2,以及施特劳斯在《<政治的概念>评注》中第9、10 两节。)给现实化了。由此施米特不但把凯尔森的宪法理论容纳进自己的宪法学体系当中来,而且为政治法学提供了除了理性之外的“启示”、“意志”根基。昭示现代人,“启示”在面对“理性”的挑战之时,并未被击溃,而是相反,越来越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小 结
施米特的政治法学思想,倘若离开了凯尔森的参照,则很难得到理解。通过以“例外”和“常规”所形成的张力,两人的思想论争把人们带到西方思想的根本处:“启示”与“理性”的张力;而从两人的思想论争来看,“启示”仿佛具有相对于“理性”的优越性。否则,施米特创建政治宪法学以“制宪权”为基础,把凯尔森的“宪定权”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让自己被凯尔森所包裹。当然,这一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凯尔森在理论气质和视野上稍逊施米特所致。
另外,上文曾经将施米特与凯尔森的思想论争,追溯到圣经的启示之争:即“与邻为善”和“人类世仇”这对看上去水火不容的两个信条。尽管这两个信条现实性的统一在一部“圣经”之中,但是,不应忘记“与邻为恶”是圣经旧约的教诲,而“与邻为善”则是圣经新约的教诲。相对于新约门派林立,一派“喧闹”“娱乐”的场面,旧约则显得异常“严肃”和“庄严”。旧约里“奇迹”不断,上帝亲临的时刻数不胜数,“例外”状态频繁发生;而新约里,上帝隐身,再不亲临天下,一切都是属人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波澜不惊,山不会动,地不会摇,海水也不会再分开,一切都被“自然规律”所慑服,所规制,一切都是那么的“常规”。
尼采在《敌基督》(Der Antichrist)第27章中说得很清楚,耶稣是一场反抗犹太教会运动的领导者,他反抗的是以色列的社会等级、特权和秩序,是对所有高等人的不信任,是对教士和神学家的否定,而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得以延续,并且艰难地赢得最后生存的可能性,恰恰就在于犹太教的等级制度和严密的秩序。根据尼采,“新约”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造反派。所谓的“与邻为善”,不仅降低了政治的高贵和人类的价值等级体系,而且使人遗忘了人类生存的本质状况:人与人的战争、族群与族群的战争。相比较“旧约”而言,新约在促使人遗忘人类生存的这一本质状况。旧约创造了很多的“悲剧”故事,而新约里到处是“福音”,但就其是否反映了人类的真实生存状况而言,旧约在讲实话、真话,而新约则是在粉饰太平,在“撒谎”,尽管有一个美妙而温柔的名字——“福音”。
在这篇短文中,呈现施米特与凯尔森的思想论争,其结论并非是施米特的政治法学高于凯尔森的实证主义法学;而是要意识到,西方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一片光明,在根本处就有着“启示”与“理性”的张力或纷争——而这场纷争,远非“耶路撒冷与雅典”就能涵盖得了!
[1]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凯尔森.纯粹法理论[M].张书友,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3]施特劳斯.哲学与律法[M].黄瑞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4]MEIER Heinrich.Die Lehre Carl Schmitts[M].Stuttgart:J.B.Metzler,2009.
[5]施米特.政治的神学[M].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7]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M].李君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9]施米特.宪法学说[M].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