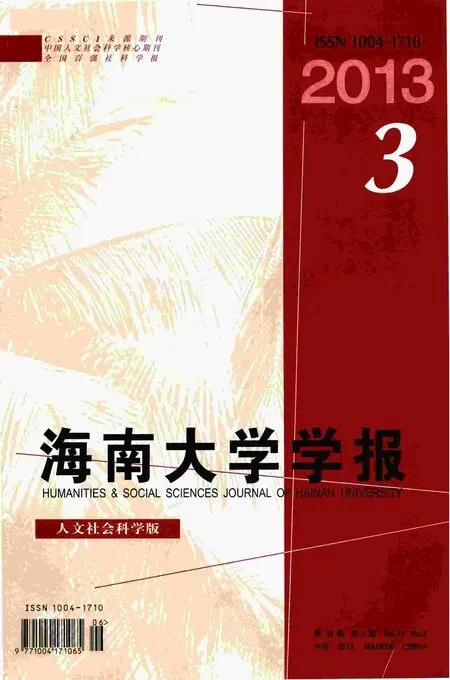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黄汉林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州 510275)
《风雨》是《诗经·郑风》中的第十六首,其中尤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两句最为脍炙人口,身处乱世或困境者常援引此句自勉,以表明坚定的君子气节。除此以外,也有许多人用其中的“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表达得见心上人时的喜悦之情,又用来表示与同道好友相聚时的畅快之情,而这些心情的表达或传达,最终都归结到“既见君子”上。为此,如何解释诗的主旨,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
《风雨》是典型的重章叠句,全诗总共3章,每章4 句: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关于诗的字词释义,“凄凄”,三家诗作“湝湝”。《说文》:“凄,云雨起也。”湝,水流动的样子,亦指寒凉,“夷”,喜悦,也指心平;“潇潇”即“潚潚”,风雨暴疾之貌,《说文》:“潚,水清深也”;“胶胶”,三家诗作“嘐嘐”,“瘳”,愈①俞樾辨“云胡不瘳”条(《群经平议》卷8):《毛传》解“云胡不夷”、“云胡不喜”,皆作喜悦之意,解“瘳”为“愈”,其义与“夷”和“喜”不对应。俞氏认为,“瘳”当为“憀”,“憀”与“聊”义同,“聊”,赖也,乐也;人无聊赖则不乐,因此“聊”也有“乐”的意思。俞氏引经据典,解“云胡不瘳”为“云胡不乐”,亦可通。详见刘毓庆等撰,《诗义稽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021页。,“晦”,昏暗,“不已”,不止。
《风雨》3章只不过各换5 字,含意却层层递进。从写景角度看,首章言“风雨凄凄”,应是风雨初起,让人觉得凄厉而寒凉;次章言“风雨潇潇”,似有风雨渐大之象,风雨声疾而势猛;终章言“风雨如晦”,变更词式,不再以迭词来描述和形容,此刻的风雨似乎更为猛烈,铺天盖地,天昏地暗。“晦”指黎明前最黑暗之际,欲浊欲曙,天将明则反而晦。《说文》:“晦,月尽也。”指月已沉而日未露之状,但“晦”过之后,将有一线曙光的渐临和随之而来的天光明亮景象。
与景色应和的鸡鸣,初为“喈”,姚际恒认为:“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之后“胶胶”,同声高大也;鸡三鸣后,天将晓,(鸡鸣)相续不已[1]221。“喈喈”、“胶胶”、“不已”,三种鸡鸣之声分别对应着三种雨势“凄凄”、“潇潇”、“如晦”,啼声像从小至大,从一两声到数声相应以至群鸣不绝,仿佛要唤出个黎明来。其中末章的风雨“如晦”与鸡鸣“不已”的对应,以一反前二章的叠词造句,揭示了所描绘的情形在渐变中发生的质之变化。
在这种晦暗凄寒的背景下,诗中人却因得见君子,而心有所安(夷)、郁有所解(瘳)、喜悦不已(喜)。李晋卿以病愈的过程来解释此诗层次递进之意:“夷如病初退,瘳如病既愈,喜则无病而且喜乐也。”[2]87
对诗中的情景与人物,《毛传》认为是“兴”,朱子认为是“赋”。“兴”为虚写,“赋”为实写,诗中的风雨、鸡鸣、君子,可实可虚,虚实难辨。扬之水说:“诗之好,正在于不论究竟为实为虚,风雨在《风雨》之中,已经是实实在在的风雨,君子更是《风雨》中‘既见’而令人跃然欣然之君子。”[2]87
历代对这首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一为政事说,源于《毛传》,着意于政治时势与君子气节,解作“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二为情事说,斟酌于男女之情,如朱子《诗集传》解为“淫奔”之诗,后世尤其今人则摒弃朱子说法的道德维度,转而解为男女自然而然欣喜相见的情诗;三为怀友说,如方玉润所言,“风雨晦暝,独处无聊,此时最易怀人”[1]220。这三种说法在诗学辨析中的有何具体意义?
一
《毛传·小序》云:“《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风雨鸡鸣”为“兴”,“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郑康成笺:“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3]。所谓君子“不改节度”,并非不谙通变之术,而是在其位谋其职,或行或止,应机立断。欧阳修解《艮·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时,引“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证:
《艮》者,君子止而不为之时也。时不可为矣则止,而以待其可为而为者也,故其《彖》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于斯时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则位之所职,不敢废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之谓也。[4]
清末学者汪之昌则举《易系辞》的“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佐证《风雨》,以“鸡为知时之禽”,“君子之俟时与鸡之伺晨而鸣,正可罕譬而喻”[5]1018-1019。因此,君子不改节度之德,是既不废职位之所在,又能辨识时务、伺机行事的审慎德性,有这种德性的君子出以定国安邦、经纶济世,入则立身行己、始终如一,所以为诗中人所思慕。后世有许多解释者遵从《毛传》、《郑笺》的说法,大同而稍异,可举数家以证《毛传》说。宋代的严粲把《风雨》中的“风雨”理解为郑国的动乱:“郑公子之乱,时事反复,士之怵于利害,随势变迁,失其常度者,多矣,诗人思见君子焉”[6]312。钱澄之追随严粲,以更具体的史事进一步坐实严粲的说法:“郑国当时无片刻安宁,而国人望治,幸而有孔叔持政,随后又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臣用事,国渐以宁,诗人所见之‘君子’,是不是指这几人?”[6]312-313黄节认为,钱氏的说法只不过是“推度之辞,非释经义也”[6]313,而顾广誉的解释似乎更合乎诗的意旨:
当极乱之时,人皆迁于习俗,而有君子不改其常度,是天心所赖以不坠也。且君子在世,无论得志与否,不有补于时,必有裨于后,又世运所恃可以转也。今而未见天心、世运,殆有不可知者矣。诗人愿见如病得瘳而喜且悦者,以此。[6]313
君子,是天心之所赖而不坠、世运之所恃而可转者,故此处的“君子”不是专指一时一地贤良方正之梓材,而指后世养成君子气节者。明代陈耀文《经典稽疑》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条钞录各家说法共有7条,其中意思与《毛传》解释相同或相近的就占了5 条,称颂君子临难不夺、为善不止之德。例如,《南史·袁粲传》:“粲初名愍孙,俊于仪范,废帝裸之,迫之行走。愍孙雅步如常,顾而言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如,《辨命论》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焉有息哉”[5]1017。然而,即便风和日丽而非风雨飘摇时,雄鸡也一如既往地司晨如命、啼鸣不已,诗中为何强调乱世思君子?即为何突出治世需要这种君子?“如此事实,载之可感,言之可思”[7],乱世之变的凄惶,让多少人因历史之轮的碾压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和为人坐标,但这种无常与变数却突显了君子之德有常而不改的节度。此可感可思者,正是诗教之功,由此后世君子方可层出不穷。围绕诗教而成的诗学传统,是华夏民族“自觉地教育本民族中虽为数不多但总归会有的抱负者的根底所在”[8]。
二
朱子《诗集传》中的说法似乎不同于《毛传》的解释传统,独以《风雨》为“淫奔”之诗:“风雨晦冥,盖淫奔之时。君子指外期之男子也……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所期之人而心悦也。”[9]63朱子又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9]65朱子径直指诗中主角为女子,于是,诗中的“君子”自然可解释为“男人-良人”,这种解释不免削减了此诗更为深广的意义和可能性,而“淫奔”说亦颇遭后人批驳。毛奇龄认为:“自淫诗之说出,不特春秋事实皆无可按,即汉后史事,其于经典有关合者一概扫尽。”[7]方玉润斥朱子之说“无良甚矣”,认为“郑本国贤士大夫互相传习,燕享之会,至赋以言志。使真其淫,似不必待晦翁而始知其为淫矣”[1]220。田汝成虽然觉得毛公与朱子“皆未得诗人之面命”,然《毛传·序》说“犹足以存礼义于衰乱,昭贤达于忧勤”,朱子之过则在于“欲捐成说而任独见”②见陈耀文《经典稽疑》之钞录,转自刘毓庆等撰,《诗义稽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017页。。在今人看来,朱子之说着实迂腐无趣,对男女自由恋爱有道德偏见,假如能够摘除“淫奔”的有色眼镜,则可解释为此诗写两情相悦之男女相期如约的喜悦之情。然而,究其实质,今人的自由恋爱说与朱子的看法似乎有着共同的基础:男女之间自然而生的相恋之情。如程俊英、蒋见元便认为,此诗写妻子与丈夫久别重逢,欣喜不已③汪之昌驳朱子时已经谈到此种解释:“即不信《小序》者,未尝指为淫诗,不过易思君子为喜见夫,亦以经文之显有可凭也”。见刘毓庆等撰,《诗义稽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017页。[10],男女淫奔之情于是合法化为夫妇之情。扬之水《诗经别裁》的看法是,《小序》的解释“诗意虽好,情意却平”,诗之原意“也许只是表达了一种最平凡最普通的情感,即两情之好”,“淫奔”一词则仿如代号,朱子恐怕也未必情愿用④夫妻重逢或情人相见之说,自现代以来随处可见,见于各种《诗经》注译或选读之中。如余冠英的《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90页;高亨的《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2]86。扬之水的说法,似乎为朱子搭设了一个下台之阶。
不过,或许还可以追问:朱子说法的理据何在?兴许源出于孔子“郑声淫”之说。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⑤参见《论语·卫灵公》。又,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⑥参见《论语·阳货》。陈启源认为,朱子误以“郑声淫”断尽《郑风》二十一篇:其一,孔子所说的“郑声淫”,并不是说郑诗淫或郑风淫,“郑声”指的是音乐,非指诗词,“郑声靡漫幻眇,无中正平和之致”,因此谓之淫;其二,淫者,过分之意,并没有专指男女之欲。陈启源反问,“孔子删诗以垂教立训,何反广收淫词艳语,传示来学乎?”⑦参见《毛诗稽古篇》,转自程树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8页。因此,孔子厌恶的应该是“郑声”,而不是“郑风”。
然而,现代的两情相悦说与朱子“淫奔”说是否真的有共同之处?男女相爱之情真的是两种说法共通的基础?需要细加辨察。朱子“淫奔”之说固然有所偏颇,但其所据之理在于正声雅乐,亦即立足于德政之风动教化;毛奇龄、方玉润、田叔和、陈启源等人驳斥朱子,无不立足于君子之贤良达德。君子乃德政之根本,朱子与这几位反朱者对“德”的见解,并未迥异于《毛传》“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大旨。因此,《毛传》的解释既含夫妇男女乐以相配之美,也有思贤进德之善。现代的解释虽然摘除了朱子扣于此诗的“淫奔”帽子,但其旨限于男女相配之乐,似乎已无《毛传》“忧在进贤,不淫其色”的含意,君子之德隐而不见。古今之异,于此可见一斑。
三
方玉润既不满朱子“淫奔”说,同时也认为“《序》以风雨喻乱世,遂使诗味索然”,因此把这首诗解为怀友之作。“风雨晦暝,独处无聊,此时最易怀人。况故友良朋,一朝聚会,则尤可以促膝谈心……其乐如之”,但如果“必以风雨喻乱世,则必待乱世而始思君子,不遇乱世则不足以见君子,义旨非不正大,意趣反觉索然”[1]220。怀友说似乎是方玉润首倡,但在方氏之前,这种解释已有所本。《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为韩宣子设宴饯行,韩宣子请郑国诸卿赋诗言志,其中子游赋《风雨》,杜预注:“取其既见君子,云胡不喜”[11]。子游之赋为外交辞令,但取诗中君子惜友离别的意思。汪之昌的说法既突显了《毛传》的解释,但也含有君子之间惺惺相慕之意:
所谓“思君子者”,非必以君子不并世而慨想也,非必以君子在异地而遥慕也。金锡圭璧之行,固已相知有素,惟是卷怀寂处,抱负大有为之经纶,或小试其一二,或曾未效其设施,而不得见之于行,遂至仅托诸言,正犹“喈喈”、“胶胶”之应时而鸣,极之晦冥昏默之交。当其时,容或不辨昏晓而鸣之不已,以惊昏惰,闻其声而怀不能置,故宜。[5]1019
汪之昌举子游赋《风雨》为韩宣子饯行一事为例,并加按语曰:“饯训送行,赋此者殆惜其去而不留,尤足以证成思君子之说,然则古义洵不可易已。”[5]1019汪氏所谓古义,既指《毛传》的古义,也含君子之谊。
按照怀友诗的解释路向,“既见君子”之乐接近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⑧参见《论语·学而》。。玩索孔子这句话的语境,前一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后一句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以说,这三句是夫子自道,即“不愠”之君子气度,与“有朋”、“时习”之乐一样,共予人以愉悦的温润感,这种愉悦温润之源在《风雨》中。《易·象传》释兑卦:“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兑,悦也。君子相见,促膝谈学,乐趣无穷,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其实“君子”一词含义广泛,很难具体指认,但《庄子·天下篇》对君子的定义却足够明确:“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⑨《天下篇》稍后提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刘小枫认为,“志事道行与仁义礼乐匹配无间”,君子除以这四经滋养一生之外,仍需学习《易》和《春秋》,以求通达“临事不乱”之德,养成“面对含混的实际政治应该具备的法名参稽能力”。“临事不乱”之德就是“君子虽处乱世,不变改其节度”之德,因此与《毛传》的解释若合符节。参刘小枫著,《共和与经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69、272-273页。这里,君子的恩、理、行、和四种情态,分别与仁、义、礼、乐为内容,而且融于仁慈的自然熏习濡染之中,在当时而言,即以六经陶养君子性情,形塑君子常德。故“既见君子”之乐,可能是君子之间共学同修、以蓄养君子仁德之乐。如此一来,怀友说与《毛传》思君子不改常度的解释庶几耦合。
《风雨》一诗的政事说、情事说、怀友说,各有其理致,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诗中的“君子”,可以是修齐治平的德才兼备者,也可以是丈夫或情人,还可以是学问上的朋友和同道。但是,究竟什么人在思君子?诗人?王者?庶民?情人?君子?都有可能。政事说立足于善,乱世之时,无常与飘零的沧桑感弥漫于世,不论王者还是平民,都祈盼贤良方正、处变不惊的君子现世,因此见而乐之;情事说立足于美,透过《风雨》的恋情仿佛可见将于爱意中欣然而至的翩翩君子,两情相悦的浓情,酿造着相见怡然之乐;怀友说则把诗旨之真之挚设置于君子之间,让同道之思与友人之念,凸现在风雨中,不论是高山流水的知音,还是共度时艰的知交,这份风雨中的造访与等待都是人间罕事,因此不论是待者还是来人,内心都充盈期待相见倾谈之乐⑩兴许有人会问:假如说政事诗的解释立足于善,情事诗的解释立足于美,两者合起来看,此诗就是美而善之作,怀友说是否可以视为立足于真?朋友之间的讲习共学,难道不是着意于求真吗?《风雨》一诗的确有其真之处:素朴动人、情真意切之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此诗为真善美之作。然而,君子之所学,并非不求真,但并没有在孤立于善的层面上求真,这种脱离道德之善意义上的求真就是所谓的价值与事实之别。真善美是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划分,尤见于康德,但并不见于西方古希腊罗马传统。我国学问传统似乎也没有这种单独的求真之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因此,孔夫子门下的诸贤者和君子共学“夫子之文章”,只不过是讲学夫子所作的六经而已。至于什么是性与天道,历代可谓众说纷纭,但无疑包含纯粹的求真之学(现代人称之为科学)。夫子既然不谈论性与天道,君子自然不得而闻之。。在古人那里,善与美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体两面之物,善的美感与美的善意往往互相转换,在此处体现为善的东西,在彼处则可能是美的化身。此诗之妙,在于既虚且实之间而教人为善的感美。《诗》之制作,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持人性情,乐而不淫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也曾经说过:“诗人的作品希望给人们带来善与乐”(《诗艺》333),善是指有裨益于生活,乐就是如今所谓的审美愉悦。。或许,真正长思君子的,是《诗经》的编订者孔子(假如孔子果真曾经删诗)。这样理解也合乎情理。即便此诗初衷只是思君子(无论庶民、情人、友人之思),但夫子编订之意,已使此诗的涵义和阐释呈现多解之义,教人为善不息、不改常度,这样立意中的君子,方能同时为王者、万民、情人、友人所思。如此一来,政事说、情事说、怀友说,似乎并没有截然可分的界线,“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1]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扬之水.诗经别裁[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3]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13.
[4]欧阳修.庐陵学案[M]∥黄宗羲.宋元学案: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6:192.
[5]刘毓庆,等.诗义稽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6]黄节.诗旨纂辞[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卷1[M]∥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经部):6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09.
[8]刘小枫.《德语诗学文选》编者前言[M]∥刘小枫.拣尽寒枝.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56.
[9]朱子.诗集传:卷4[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250.
[1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