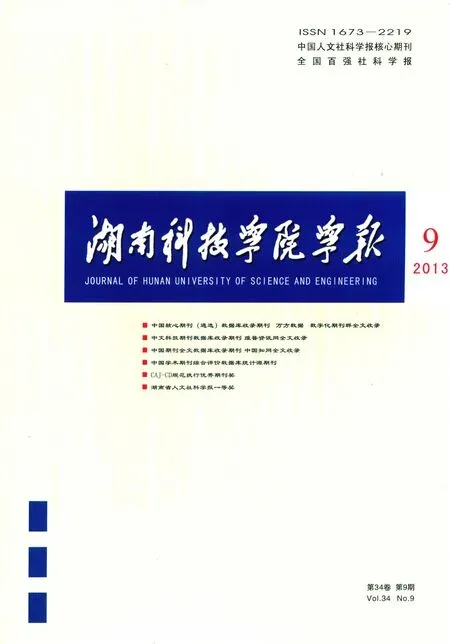陈鼓应的《彖传》观批评
张丽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易传与道家思想》(1993)、《道家易学建构》(2003)是陈鼓应著述的关于道家与《周易》之间的联系的两本专著。前者对《易传》各篇逐篇论证,力证《易传》各篇的主体思想属道家学派,后者从阴阳、道论(如道气说、太极说)以及对待与流行等思想观念,重构道家易学。[1]P1这两本专著打破了《周易》经传属儒家经典的传统旧说,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易学的研究有很大启迪。但将《易传》全篇归于道家学派的观点,无疑带有牵强附会之嫌。
一 万物始生观
(一)天地生万物
乾象征天,天伟大至极,开创万物,使云气流行,雨泽施布,太阳运转,四季更替。坤象征地,它美德至极,深厚无疆,配合天普载万物,使万物得到滋养与孕育。《彖》展示的是天地生养万物,天地乃万物之始。陈鼓应认为:“《彖传》对万物起源的看法完全是自然主义的,而丝毫不带有神秘的色彩。这乃是受到老子自然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而与儒家思想无涉。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在自然的意义上使用‘天’这个概念的人,而且,尽管老子在天地之前安置了一个道,但是天和地仍然是万物的直接生成者,结合《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和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可以看出这一点。”[2]P9
陈鼓应肯定了《彖》的天地生万物,但却忽视道家在天地之前还存在着一个“道”的概念,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这是一个超越物质的思维体系,《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万物》也直接表述了道化生万物的整个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与,《彖》的天地直接化生万物的唯物观点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吕绍刚在他的《周易阐微》中也认为《易大传》的宇宙论讲到太极为止,太极是物质性实体,而老庄在太极之前还讲道,道是老子虚构的超物质规律,是观念性实在。陈鼓应忽略“道”的概念,断章取义地认为《彖传》的天地生万物是受老庄自然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着实缺乏说服力。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春秋以前,‘天’就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著名先秦古籍《山海经》中有女娲补天的故事。周代之前,人们对“天”的认识,还没有和万能的“帝”联系起来,天就是大自然的天,虽然神秘,但并不神圣。[3]P36先秦时期并没有哲学这个概念,说“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在自然的意义上使用‘天’这个概念的人”,丝毫无助于证明《彖传》受到老子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彖传》中的自然主义应该是长期以来历史积淀的产物。
(二)阴阳化万物
无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都是由阴阳两爻组合成的。“阴”、“阳”概念的形成,是古代人们通过对宇宙万物矛盾现象的直接观察得出的。“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在古人心目中,天地、男女、昼夜、炎凉、上下、胜负……几乎生活环境中的一切现象都体现着普遍的、相互对立的矛盾。根据这种直感的、朴素的观察,前人把宇宙间变化万端、纷纭复杂的事物分为阴阳两大类,用两种符号表示。[4]P2《周易》卦爻符号的创立就是阴阳概念的显现。而在乾坤二卦中,乾象征开创万物的阳气,坤象征孕育万物的阴气。万物必须在天地阴阳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化生出来。故坤卦《彖传》有“乃顺承天”、“ 柔顺利贞”之说,意在乾坤阴阳相互作用时坤应顺乾,阴应顺阳之道。还有泰卦《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否卦《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都体现了只有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养才能畅通之理。
陈鼓应认为《论语》、《孟子》、《中庸》这些儒家典籍中并无阴阳说。而作为周室守藏史,老子继承一阴阳解释自然现象的史官传统,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更是明确地讲:“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老庄的这种阴阳气化的思想应该说正是《易传》以阴阳解《易》的理论来源。[2]P12高亨说:“《说文》:‘冲,涌摇也。’《广雅·释诂》:‘为,成也。’冲气以为和者,言阴阳二气交荡以成和气也。”[5]P101诚然,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为和”的确与《彖传》的阴阳化万物有相似之处,但陈鼓应忽略了《周易》卦爻符号的创立正是阴阳概念符号化的一种显现,《易经》卦爻中蕴含着阴阳,且《易经》先于《老子》而存在,《易传》以阴阳解易是由《易经》所饱含的阴阳特性决定的。同时,《泰》、《否》二卦的彖辞“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强调的是阴阳交合的必要性,而“冲气以为和”表现的是阴阳交合的结果,可见《彖传》和《老子》虽都涉及阴阳,但是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阴阳并非老庄独创,纵使儒家典籍中鲜有阴阳之语,也无法证明《易传》以阴阳解《易》的理论来源是老庄的阴阳气化思想。
二 循环发展观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这在《周易》许多卦的彖辞中都有所体现。乾卦《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是喻示阳气变化循环不已,犹如冬尽春来,新的阳气又开始萌生万物。损卦《彖》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则是喻指事物的增加减少都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的。复卦《彖》曰:“复,亨”,刚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丰卦《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鬼神乎?这都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盈则虚,损则益,生则死又将复归生,无限循环下去。
“反者道之动”出自《老子》四十章,意为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乃是道的运动规律。“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意为道是循环运动而不停顿的。陈鼓应根据“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认为老子把循环运动看作是道运动的根本形态,这种道的循环运动对《彖传》的“损益盈虚”、“反复其道”观念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不可否认“反者道之动”、 “周行而不殆”、“损益盈虚”、“反复其道”都体现了循环发展的规律。但前二者强调的是“道”,“道”是事物循环往复的动力所在,“道”具有循环不殆的性质,这是一种由对自然观察的物质层面上升到思维层面的深层次的哲学命题,而“损益盈虚”、“反复其道”则是最简单的对天地自然直接观察得出的结果,是古代任何一个平民百姓都能观察到认识到的一种自然规律,农业作为古代人民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人民必然给予大自然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种共有的对大自然的普遍认识没有必要说它是儒家的或者是道家的。纵使以伦理见长的孔孟之道没有提及“损益盈虚”、“反复其道”,也无法让人认同老子对《彖传》的“损益盈虚”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
三 人法天地观
(一)三才之道
《周易》的三才即天地人,三才的概念在《彖传》中并没有系统的语言表述。对三才的描述出现在《周易》的《系辞下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周易》中,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世上有天道、地道和人道,这和《老子》所强调的天地人外还有一个“道”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此外,道家的“道”是统一的“一”,由此产生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易传”的道则相反,是多样的,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6]P198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颐卦《彖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谦卦《彖传》:天道亏盈而好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从这些彖辞可以看出,《周易》强调人的行为需效法天地,如效法天地的变革、效法天地的颐养、效法天地的尊谦卑盈。《老子》认为宇宙之中有四大,这四大的关系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则顺应自然,这是一个层层推进的关系。
陈鼓应认为第一:损盈益谦的天道、地道、人道也是老子之道的内容。第二,人、地、天都要统一于自然之道,这是老子的观点,《彖传》更具体地讲到天道、地道、人道的一致性。天地人一体是以人效法天地为基础的。老子如此,《彖传》亦然。[2]P14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彖传》以人法天地为准则,在天地外并没有一个需要效法的“道”存在,并且天和地是并列为人所效法的,《老子》则不然,它是递进的效法关系,同时,老子的“道”和《易传》的“道”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单纯地因为《老子》与《彖传》都出现天、地、人这些字眼而将二者同一处理,是有失偏颇的。
(二)人事之道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夫易者,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周易》强调人的行为需效法天地,如效法天地变革、效法天地亏盈而好谦。《老子》则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是效法,但在本质上还是存在差异的。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殷纣,面对统治者残暴的统治,有德者可以群起将其推翻,上顺天命,下应民心。袁振保在《周易与中国美学》中说道:“追求事物之阳刚美、动美,事业盛大之美,变革之美,乃是《周易》一种极为突出的美学精神。”[7]而老庄强调的是守静无为,《庄子·人间世》中顔回将之卫,因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但仲尼却建议他顺其自然,最好的办法是“心斋”,即“入则鸣,不入则止”,随遇而安,“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尽力求得内心的虚寂静止。[8]P47宅,居处也。处心至一之道,不得已而应之,非预谋也,则庶几矣。[9]P36这与《革》卦的有计划有预谋地用武力结束残暴统治有着很大差别。屯卦《彖传》:宜建侯而不宁。意为事物初生之时,王者应当建立诸侯治理天下而不可安居无事。《老子》则重视“太上,不知有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境界。
陈鼓应在《〈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中列举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老子》全书的种种例子,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这里的圣人、侯王虽都效法天地、效法道,但它强调的是无为和自化,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需要很大地发挥出来。与《彖传》的“汤武革命”、 “宜建侯而不宁”的有为相比,是有本质差别的。
四 刚柔崇抑观
“刚柔”字眼多次在《彖传》中出现,有时只出现“刚”或“柔”,有时并列出现。如坤《彖》:柔顺利贞。复《彖》:“利有攸往”,刚长也。屯《彖》: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彖传》的刚柔有时象征阴阳之气,有时指卦象或爻象,有时意在表现刚健柔顺的性质。陈鼓应认为《彖传》以刚柔解《易》,同以阴阳解《易》一样,应该说不是出于儒家,而是出于道家传统。老子从普遍意义上来阐述刚柔,《老子》第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对于刚柔对立方面的论述显然啓发了《易传》的作者以刚柔系统概括对立的卦象和爻象。[2]P13诚然,《彖传》与《老子》都出现了刚柔这组对立的字眼,这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但《彖传》和《老子》在对待刚柔的态度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一)崇刚尚阳
《彖传》崇刚尚阳,如否卦《彖传》: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彖传》作者将阳、刚比喻成德行高尚的君子,而将阴、柔喻意成卑贱险恶的小人。又如豫卦《彖传》: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卦象征欢乐,卦体为下坤上震,“刚应而志行,顺以动”指的是九四的阳刚与下坤的群阴相应而心志畅行,下坤柔顺应阳刚而动,故至欢乐境界。由此可见,除了崇刚尚阳外,《彖传》还强调柔对刚,阴对阳的顺应。《彖传》中还有“柔顺利贞”(坤),“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升),“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睽)等都体现了它的崇刚尚阳,阴柔顺阳刚的思想。
(二)崇柔抑刚
《老子》强调柔的重要性,认为柔能克刚,如“柔弱胜刚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同时他反对以刚强处事,认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坚强象征着死亡,只有柔弱才是生存之道,他还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争即是刚强,唯有不争,柔顺似水,才能不致灾祸。这种崇柔抑刚思想与《彖传》的崇刚尚阳明显是不同的。张岱年也说过:“老子贵柔,意在以柔克刚。柔只是一种手段,胜刚才是目的,贵柔乃是求胜之道。孔子重刚,老子重柔,其实是相反相成的。”[10]
陈鼓应为证道家思想与《彖传》崇刚尚阳思想有想通处,特别举了黄老学派的《文子》及稷下道家《管子·枢言》等篇,认为《文子》书中《上德》篇“阳灭阴,万物肥,阴灭阳,万物衰;故王公尚阳道则万物昌,尚阴道则天下亡”、《管子·枢言》中的“尽以阳者王”、“尽以阴者亡”的崇阳思想与《彖传》的崇刚尚阳思想是相同的。[2]P38陈鼓应的这种创新确实值得肯定,但黄老学派只是道家学派的一个支脉,它产生于战国中期,它的思想仍然是以老子为宗的,学说的核心是“无为而治”。而《管子》则是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融合了众家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方面。它的学派归属问题一直颇具争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则将其改列法家类。《管子》、《文子》的尚阳思想,不排除是受当时百家争鸣、各家思想相互影响的结果,也与黄老学派发源地齐国当时的发展需求有一定关系。此外,《管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至秦汉时期,《文子》成书晚于《管子》,在秦初即遭到禁毁,到汉代才重新流传,《彖传》成于战国中期以后,孟子和荀子之间,在时间上也无法断定《彖传》与《管子》、《文子》谁先影响谁。因此,以黄老学派的《文子》及稷下道家《管子》诸篇中存在的尚阳思想作为《彖传》属道家流派的论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1]陈鼓应.道家易学建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郑慧生.甲骨卜辞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冯达甫.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袁振保.《周易》与中国美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5):36-44.
[8]曹础基.庄子浅注(修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清]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齐鲁学刊,2003,(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