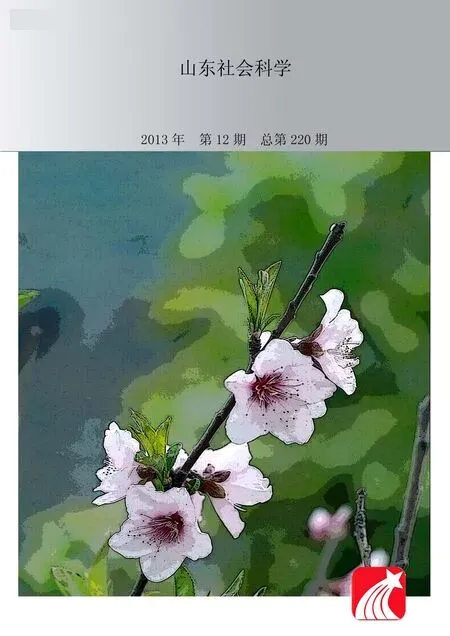本雅明:“讽喻是现代人的盔甲”
刘 林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是“为讽喻恢复名誉”①[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的世纪,最早开启这一理论进程的现代批评家是德国学者沃尔特·本雅明。②本雅明的现代继承者包括弗莱、加达默尔、C. S. 路易斯、艾柯、保罗·德曼、杰姆逊等人,对此提出异议的重要批评家为克罗齐。他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以人类语言的世俗性质为基础,以16—17世纪的德国巴洛克戏剧为研究对象,提出并详尽论述了“辩证讽喻”(dialectic allegory),这一重要概念是本雅明20余年理论生涯的关键词,在其后期著作《巴黎廊柱计划》、《中央公园》③《中央公园》是本雅明为“巴黎廊柱计划”写下的修改札记。本雅明在和阿多尔诺的通信中得知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当时正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寻找房舍,即以此为名。等论著中都多有阐述,本雅明以此为核心重构19世纪法国文学发展史,对波德莱尔诗歌创作提出全新解读。《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将“巴洛克讽喻”作为“辩证讽喻”的代表,而将“浪漫派象征”作为其反面。本雅明批评浪漫主义理论家“过于生硬地”综合部分与整体、艺术和理念,“由于缺乏辩证的活力,他们对内容的形式分析和对形式的美学内容所做的分析都是不公正的”。与之相反,“巴洛克的讽喻典范则是辩证的讽喻”④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s of German Tragic Drama (Verso Edition),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New Left Books, 2003, p. 160.。实现政治转向后的本雅明强调“辩证讽喻”中蕴含的激进的政治功能,试图在基督教信仰、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弥赛亚救赎”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艺术对人的解放”之间找到契合之处。
一、“浪漫派象征”与“辩证讽喻”
本雅明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序言”首先回应和延续了其论文《论总体语言和人的语言》(1916)的主要观点。在他看来,总体语言是上帝创世的语言,它具有普遍性,无处不在,覆盖万物;它具有统一性,精神实体和语言实体融合其中;它又具有超验性,是一切具体的人的语言的蓝本和根基。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曾经为万物命名,但在亚当因犯下原罪而堕落之后,人类语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亚当的堕落首先是语言的变质和腐坏:语言从精神实体变成表现事物的工具,此前的单一语言变成了多样性的语言,此前的实体语言变成象征和符号,这意味着人们借助语言而获得的有关事物的知识不再是全面的、直接的,人们只能通过语言符号来部分地、间接地获得知识。这些看似抽象玄妙的神学思辨是本雅明研究德国悲苦剧这一特殊戏剧形式的理论基础。
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指出:“讽喻世界观来自充满罪感的身体和更纯洁的诸神本质的冲突,前者由基督教作为例证,后者具体表现在万神殿中。”[注]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Verso Edition),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98, p. 226. 下文引用该书时不再一一注释,均在正文注明页码。“充满罪感”集中体现在人类的语言运用上。堕落前的亚当在伊甸园中命名万物,名称与事物本身是统一的,而堕落后的亚当获得了抽象的关于善恶的知识,语言只能是符号;另一方面,万神殿中的诸神雕像用艺术的手法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人们对诸神的敬拜和祭祀流露出对那个无法进入的理念世界的眷恋与期待。简言之,随着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人类进入一个词与物、经验与理念、现象与真理相互断裂的时代。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总结说:“亚当为事物命名一点都不是游戏之举或任意而为,它实际上确认了伊甸园的这种状态,即根本都不用为词语的表达意义努力。在命名中,并无倾向性的介入,理念就显露于外。”(p. 37)在“后亚当”的堕落世界中,基督教神学用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一本体论的鸿沟(ontological gap)。耶稣基督是个人与集体、人性与神性、现象与真理、世俗与神圣、经验性与超验性的完美融合。中世纪的人维持了统一的宗教信仰,通过解读耶稣基督的神迹满足自己追求形而上真理的热情,认为在各种具体事物背后都潜藏着自己信仰的宗教真理。本雅明引用一位德国学者的话说,当文明草创、民智未开时,“智者们只好将敬畏上帝、美德、善行的教育内容埋藏或隐含在诗歌或寓言中,这样芸芸众生才能懂得”(p. 172)。但在中世纪结束后,在人文主义、基督教改革宗、理性主义的冲击下,传统的统一世界观日益解体,人们再也不能无视本体论的鸿沟。德国悲苦剧作为巴洛克文学的代表形式,是这一现实困境的艺术表达,在这种艺术形式兴起的16世纪,“传统形式被剥夺了宗教上的圆满实现,要求它们在自身之上发明一种世俗的解决方案来取而代之”(p. 79)。当然,本雅明以前的理论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仅将德国悲苦剧当作古典悲剧的简单回归或复兴。随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诗学以“美”的概念为中心,认为“美可以和神圣联接成一个毫无裂缝的整体”(p. 160),象征把经验材料与超验真理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生活表象与本质的关系,打通本来相互隔绝的现象世界和真理世界。针对这些看法,本雅明的《德国悲苦剧的起源》力图拨乱反正,颠覆“浪漫主义的象征”这一“暴虐的篡位者”。但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在论述中并没有简单地将象征完全视作讽喻的反面,似乎讽喻就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一方面象征与讽喻相对立,另一方面象征又是讽喻建构的基础,讽喻有必要吸收象征的合理因素,确立象征和讽喻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做到这些,讽喻才能从一般讽喻发展成“辩证讽喻”。
19世纪“象征优于讽喻”论的主要根据可以概括为象征和所象征之物之间是有机的自然的联系,这方面最流行的例子出自英国批评家柯勒律治,他认为“船帆来了”象征着“船来了”,船帆是船的整体的一部分,从属于整体又暗示着主体,部分的存在也就是整体的存在。本雅明并不否认真理的在场,他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的“序言”中引用柏拉图的《会饮篇》,论证存在着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但他同时强调真理的不在场性质。真理和知识不同,真理不能被占有、被质疑,“在理念的舞蹈中被再现出来(represented)的真理,拒绝以任何形式被投射进知识的领域”(pp. 29-30)。真理是“理念的舞蹈”,它总是变动不居,一个动作是对前一个动作的否定,既表现什么又逃避或否定这种表现。即使存在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世界,那么如何接近这一世界也大成问题。本雅明强调,感性经验或理性能力都不能帮助我们跨越“本体论的鸿沟”。耶稣基督的奇迹是神学奥秘,不能简单挪用于世俗生活。由此看来,与暗示整体、无限、自由等理念在场或存在的“浪漫派象征”相比,主张“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说的却是另一回事”的讽喻就具备了一个突出的优点:它一方面说到某一件事,另一方面又否定自己说到这件事而很快转向另一件事。如果一件事物被讽喻地表现出来,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再是原有之物,“它表明原来所代表事物的不存在(non-being)”(p. 233);而且,这也就意味着它除了可以被讽喻地表现出来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性质或者存在。如此说来,理念被讽喻地表现出来,它既不是在场的,也不是不在场的;也可以反过来说,它既是在场的又尽力逃避这种在场。讽喻,是理念在场和不在场的综合统一。
理念的在场与缺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讽喻与时间、讽喻与自然—历史的辩证关系。“浪漫派象征”认为象征意味着理念的瞬间显现,正如本雅明总结的,“在对象征的体验中,时间的度量是神秘的瞬间,其间,象征假定其意义深入到它那最为隐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那被重重包围的内部。”(p. 165)“浪漫派象征”的缺陷在于,它只看到理念在场的一面而忽略其不在场一面,后者被本雅明称之为“延续”, 这一点可以巴洛克文学为例:“连续不断地将各种碎片堆积起来,但心中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只是满怀着对于奇迹的不可挫败的期待。”(p. 178)悲苦剧作者们虽然期待着理念显现的奇迹瞬间,但其实心中并不清楚这一瞬间何时到来,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中体验到的仍然是对这一时刻的无穷无尽的延宕与推迟,只能“连续不断地”创造各种讽喻形象来暗示那个时刻。在全书的结尾处,本雅明对这一点还举例说明:“正如坠落的人从高处跌下时会翻跟头,讽喻的意愿从一个象征跌到另一个象征上,在无底的深渊中感到头晕目眩。”(p. 232)从高处到“无底的深渊”必将是一个相当长久的过程,其间虽有理念的瞬间显现,但难以持久,这一瞬间过后,讽喻还会继续跌落,“从一个象征跌到另一个象征上”。如果说“浪漫派象征”意味着在时间上是瞬间显现和体验,那么讽喻则强调这种显现既是瞬间完成的,又将会持续不断地继续进行下去,是瞬间和延续的统一。
上文中“讽喻跌落”的比喻暗示了本雅明“辩证讽喻”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跌落”只能是由上而下的不断沉沦,这对应着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处境。本雅明认为中世纪注意到世上万物皆无用处、人生易逝等,但把这些特征看作“拯救之路上的座座驿站”,而德国悲苦剧“则完全渗透着世俗生活毫无指望的特征”(p. 81),把拯救之路上的驿站改造成“衰落途中的座座驿站”(p. 166),其历史观不是进步的、上升的,而是退步的、下降的,展现了一幅日益凋敝、败坏的画面。当然,不同的人在自然中看到的景色千差万别,或许有人眼中的自然生机勃勃,鲜花遍地,但对讽喻作者们来说,“他们在自然看到了持续不断的转瞬即逝,而且唯有在这里,这一代人的视觉能力才能认得出历史”(p. 179)。“在自然的脸庞上写着‘历史’这个字,其意义乃是转瞬即逝。”(p. 177)历史和自然共同分享着一个日益败坏的进程,前者的终点是是死亡,后者则是“废墟”。德国悲苦剧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满怀忧郁的主人公面对着死神的头颅或者骷髅大发感慨,陷入沉思,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墓园”场景正与此类似,表明戏剧人物只有从死亡意象中才能了解历史意义。悲苦剧中另一典型意象是建筑物的废墟,它经常被用作戏剧行动的背景,“在废墟中,历史才确确实实地沉入背景之中。在这一变形中历史没有采取一种永恒生命进程的形式,而是采取不可抗拒的衰败的形式”(p. 178)。废墟是建筑物倾颓、坍塌、衰败的结果,它暗示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废墟曾是完整建筑物的一部分,但现在却作为整体的片段、碎片而存在,“废墟这一意蕴丰富的碎片,这一遗留之物,是巴洛克所有创造中最优秀的材料”(p. 178)。以废墟这一看似无用的、无意义的意象为例证,本雅明认为在讽喻作家笔下的自然既有意义又没有意义。说它没有意义,是因为在讽喻创造的过程中,自然被人为地剥夺了以前上帝创世时所赋予的意义、在亚当语言中所具有的意义:“它再也不能投射出它自己的意义或深意”(p. 183)。说自然有意义,是因为它在讽喻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用来指涉他物的事物,从这一行为本身来看,都来自这种能力,就是使它们不再和世俗事物等量齐观,这就把它们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也的确可以将其神圣化。”(p. 175)本雅明总结上述两方面说,“用讽喻术语说来,世俗世界既被提升了,又被贬低了。”(p. 175)
在本雅明看来,讽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使世俗事物“神圣化”、“被提升”、重新获得意义的一种方式,正像当代研究者指出的:“在一个看上去远离意义的时代里,巴洛克时期的作家们通过讽喻技巧来构建和意义的关系。”无论是依赖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早期本雅明,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后期本雅明,“都坚持立足于世俗世界来拯救这一世界”[注]Richard Wolin,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26.。这一点在和“浪漫派象征”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浪漫派象征中,象征始终是整体性、无限、神圣的一部分,然而在亚当之后的世界中,这种“部分从属于整体”的观念是一种假定,整体性既然不能存在,部分和整体的从属关系也就不会存在。讽喻不是部分,而是碎片(fragment),其功能是消除“整体性的虚假外表”(p. 176)。“思想领域中的讽喻是什么,各种事物领域中废墟就是什么。”(p. 178)废墟不是原有建筑物的一部分,只有经过时间的流逝才能形成废墟;作为“碎片”的讽喻同样和此前的整体性拉开了时间的距离,不再是原先整体性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正像废墟使人想起原来的建筑物,碎片也让人想起整体性,或者说它指向了整体性。这就使讽喻脱离原来的语境而置身于一个新的语境,是对原有语境的彻底毁坏,宣布原有语境不再有效,讽喻自身就可以孕育甚至诞生意义,这就等于宣布讽喻蕴含着潜在的激进功能,“这是对世俗世界发出的一个破坏性的、然而又是公正的判决”(p. 175)。至少,讽喻为创造新的有意义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人们通过讽喻来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人为的、任意的行为。“任何人、任何客体、任何关系都可以绝对地意味着其他任何事情。”(p. 175)讽喻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在表现模式上也是人为的,充满了主观性。不言而喻,这种行为像其他行为或自然界中的事物一样也会转瞬即逝,以死亡或废墟来结束。死亡为讽喻标识出边界,它在世俗世界中将不能超越这个界限;达到这一极端的讽喻将无事可做,它不会再回到世俗世界而只能转向去指涉永恒的世界,用传统的神学术语来说,那是耶稣基督复活所代表的上帝世界,“与其说转瞬即逝被表达出来或者被讽喻性地表现出来,不如说它被展现为讽喻,复活的讽喻。最终,在巴洛克死亡标志中,讽喻反思被扭转了方向;在它宽大弧形的第二部分,它返回来拯救世界。”(p. 232)只有在弥赛亚再临、拯救实现的世界中,讽喻才能终止或被放弃,因为人们将重新直接面对真理或理念,“在上帝的国度里,讽喻创造者们才会醒来”(p. 232)。
讽喻从指涉世俗世界转向永恒的理念世界,这被本雅明称为“朝向复活理念的不忠实的一跳”,它之所以不忠实,是因为讽喻抛弃或否定了那个孕育自己的世俗世界。这表明,辩证讽喻实现其激进潜能的具体途径是它既能设立对立因素,又能消解这一因素。比如德国悲苦剧中有大量表现阴谋篡位、血腥复仇的情节,这些罪恶都用讽喻的情节表现出来,但上帝创世时说过,自己创造的世界是好的,所以不会存在绝对之恶。德国悲苦剧用讽喻手法表明这一点,“讽喻恰恰意味着它所代表的事物的不存在。由暴君和阴谋家代表的绝对之恶不过是讽喻。他们不是真实的,他们所代表的、所拥有的只有在忧郁的主观性视角下才能存在;他们就是这一视角,因为他们只能代表盲目性,他们的子孙就会摧毁这一视角。”(p. 233)显然,讽喻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没有人可以规定必须使用某一事物来代表另一事物,舞台上的罪恶都表现出明显的主观色彩,他们只能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只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二、“波德莱尔的才能是讽喻制作者的才能”
在本雅明笔下,“辩证讽喻”也被称为“巴洛克讽喻”,集中体现在17世纪德国悲苦剧中。如果说古代希腊悲剧的主题是描写主人公因为个人道德缺陷而导致的灾难,它挑战了神话中规定的社会秩序或人的使命等传统观念,那么德国悲苦剧的主题则是描写人类作为被造之物在世上经历的各种磨难,它展现了人类在一个“讽喻的时代”里的基本生存状态,其主人公展现的不是个人的个性,而是人类分享的共同命运,“作为悲剧生命形式的死亡,是一种个人的命运;而在悲苦剧中,它经常采取一种集体命运的形式,似乎将所有的参与者都召唤到最高法庭的面前”(p. 146)。在舞台设计上,悲苦剧也表现出更多的虚拟性和象征性,“在全体欧洲悲苦剧中,舞台都不能作为一个实际地点严格地固定下来,因为它也是被辩证地分裂了”(p. 119)。所谓“辩证地分裂”可以有两层含义:首先舞台道具按照其象征性排列,而不是照搬实际宫廷里的生活场面;其次,和古典主义戏剧强调“地点的整一”不同,悲苦剧虽然大多发生在宫廷上,但这一地点并不固定不变,悲苦剧是流动的戏剧,从一个地方很快转向另一个地方,将世界本身当成自己的舞台。毫无疑问,以上这些特征都会对观众产生完全不同于古典悲剧的美学效果。观众不再认同一个具体时空中某一悲剧英雄的个人故事,而是发现舞台上人物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舞台上的虚拟空间只能产生在自己的想象中或自己的内心中,德国悲苦剧初步具备了“向内转”的特征。
“巴洛克讽喻”中尚处于萌芽状态中的向内转倾向在数百年后被称为波德莱尔诗歌的鲜明特征。本雅明《中央公园》(第32节a部分)指出,“讽喻在19世纪离开了外在世界,为的是落脚于内在世界。”[注]Walter Benjamin, “Central Park”, trans. Lloyd Spencer and Mark Harringt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4 (Winter, 1985), pp. 32-58.显然,19世纪的讽喻不可能仅是17世纪讽喻的简单复制,二者之间的差异应该追溯到它们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巴黎廊柱计划》在对比17世纪和19世纪的讽喻时说:“在巴洛克时代,商品的异化特征还相对来说没有发展起来。商品还没有深深地将其印记——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印刻在生产过程中。17世纪的讽喻可以某种方式构成一种风格,在19世纪就再也不能这样做了。作为讽喻制作者的波德莱尔是完全孤立的。”[注]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47.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中央公园”的最后一节:“讽喻式的观察方式在17世纪塑造了风格,在19世纪就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如果19世纪讽喻的风格形成力量变得衰弱了,那么创作程式的诱惑力量也是如此,这一诱惑在17世纪诗歌中留下了众多痕迹。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程式存在于讽喻的破坏性趋势中,其重点在于艺术作品的碎片化特征。”这里提到的19世纪诗歌在讽喻中脱离了原有抒情诗的创作规范、对原有语境的质疑和破坏等特征和波德莱尔诗歌中对震惊经验、对现代社会异化性质的体验和表现密切相关,是波德莱尔诗歌“辩证讽喻”的基本内容。
在本雅明看来,传统的乡村生活是重复的、可预知的,而现代城市生活则不同,可以“震惊”经验来概括:人们走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上,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扑面而来,人们无法预知将来会碰到什么。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定理,“意识到某事和记住某事是同一个系统中不能彼此兼容的两个进程。”也就是说,人们的意识系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意识到某事和记住某事,做了这件事就不能做另一件,或者说一件事做得多了,挤占了意识的空间,那么另一件事就必然做得少。现代人在纷至沓来的匆匆行人的陌生面孔中体验到一次次瞬间诞生又稍纵即逝的震惊:他能意识到这些面孔,却无法记住它们;而传统社会中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则标志着生活的经验,里面蕴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现代人相对来说没有记忆,也就没有经验,或者说只有“经验的贫乏”:“除了天上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这一风景的中央,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力场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体。”[注][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打个比方说,人们的意识就像图书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容量,就会崩溃;现在想放进去更多的书籍,应该怎么办呢?方法之一是仅将每一部书的“摘要”放进去,这样图书馆的容量扩大了,但人们在图书馆中再也无法找到任何一部完整的书籍,人们只能看到书的“片段”:“在个别印象中震惊因素越多,作为抵御刺激的屏幕的意识就越需要保持警觉;它这样做得越有效,这些印象进入经验的数量就越少,在人的生活中只能停留一个小时的间隔。或许,震惊抵御的特殊成就可以从这一机能上看出:给每一突发事件在意识的时间中分配一个节点,但以牺牲内容的整体性为代价。”[注]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9, p. 159.现代人面临着生活印象、震惊经历的无限堆积,为了防止意识崩溃只能放弃“内容的完整性”,就会选择储存单个的印象或者单个印象的一部分,这样获得的经验是片段化的或者碎片化的,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彼此之间相互孤立。这样看来,意识系统只起到对震惊经历的“登记注册”作用,那么,这一经历的其他部分去了哪里呢?或者说,当一部书的“摘要”登记在图书馆时,这部书的其他部分储存在何处呢?本雅明引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只能放在“被认为是和意识不同的系统中”,或者像普鲁斯特说的,放在“不情愿记忆”中。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一开始就描写从一块玛德莲点心引发的无尽回忆,但如果事先没有被记住的话,那事后又如何可能被想起呢?从反面看,“如果震惊被直接整合进有意识记忆的登记系统中,引发诗歌经验的偶然事件就会变得贫乏,”(Illuminations, p. 158)但从正面看,震惊经历可以通过“不情愿的记忆”,间接而非直接地进入人们意识,成为现代诗歌的创作材料,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等人都由此开拓出文学创作的新领域。
以震惊为核心的现代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最大感受是经验的片段化、短暂性和意义的缺席,这种新的生活体验通过波德莱尔笔下的人群中的行人、吸毒者、娼妓、腐尸、机器旁的工人、赌徒、捡拾垃圾者等形象表现出来。波德莱尔在《天鹅》一诗中环顾巴黎市景,不禁感叹:“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讽喻。”这表明波德莱尔要在都市风景的背后探寻深藏不露的现代人的命运,这一探索过程可以和击剑士练习剑术相比较,“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炼,∕在各个角落里寻觅韵的偶然,∕绊在字眼上,就像绊着了石头,∕有时会碰上诗句,梦想了许久。”[注][法]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击剑士在练习时不断劈开周围的虚空,其对手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看不见的空气;同样,诗人也只能在冥想中从生活现象入手讽喻地想象出生活的本质,这样才能获得灵感。波德莱尔在描写娼妓、工人时触及现代社会普遍盛行的等价交换的商品原则,这一原则甚至将人与人的关系改造成物与物的关系的异化现象。波德莱尔用讽喻的手法描绘出现代社会精神价值和意义极度匮乏的画面,《中央公园》第27节也说:“如果波德莱尔坚信他的天主教信仰,他对世界的经验与尼采发明的那句话可以准确呼应:上帝死了。”
《恶之花》中塑造的现代人的讽喻形象如何改造成“辩证讽喻”呢?波德莱尔诗歌在讽喻中既描写了地狱般的场景,也触及消除地狱的力量。他的名诗《应和》第一节就说“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话音;∕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森林用舒适的目光将他注视。”(《恶之花》,第11页)本雅明的理解和传统象征主义不同,“波德莱尔用‘应和’所意味的,或许是一种经验,它在抵御危机(crisis-proof)的形式中试图确认自身。”(Illuminations, p. 178)他将“应和”视为现代人消除感受危机或经验贫乏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的特征在于“森林用舒适的目光将他注视”,森林不是被动地接受人的目光,而是回应了这一目光。自然的“回看”问题如果置于现代社会语境中就更加明显了,本雅明曾引用恩格斯早期著作的说法,街道上的行人“没有人甚至想到对其他人瞥上一瞥”,这里所缺乏的“回看”是波尔莱尔诗歌的主题之一。《给一位过路的女子》写路人的“回看”使诗人登上天堂,“美人已去,∕你的目光一瞥突然使我复活,∕难道我从此只能会你于来世?”(《恶之花》,第80页)《我没有忘记,……》则把落日余晖写成自然的好奇的“回看”说,“傍晚时分,阳光灿烂,流金溢彩∕一束束在玻璃窗上摔成碎块,∕仿佛在好奇的天上睁开双眼,∕看着我们慢慢地、默默地晚餐。”(《恶之花》,第84页)在爱情的回忆和眷恋中掺杂进人与自然的彼此眷顾、互动和谐的图景。
上面《给一位过路的女子》写到了与邂逅的美人相会于来世,而《我没有忘记,……》则是对爱情的回忆,波德莱尔的诗歌讽喻大多融进时间因素,既诉说过去也梦想未来。象征强调部分和整体、有限和无限、世俗和神圣的瞬间融合,时间因素忽略不计,但讽喻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其间的时间间隔清晰可见。“辩证讽喻”将这种时间间隔明显地提示出来,在过去和将来这两个维度上扩展现在的含义,现在和过去的关系他称为“记忆”,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则为“希望”。《应和》第一句就将自然比喻成一座供人们敬拜和祭祀的庙宇,而且它会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来回应偶然路过的行人。这使读者想到自然的历史无比久远,在人类历史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人类历史仅是自然历史的很小一部分,“‘应和’是记忆的材料——不是历史的材料,而是史前史(prehistory)的材料。”在史前史的时期,人们还不可能面临着经验贫乏的问题,所以回忆这一时期乃是解决现代问题的药方之一,“经验是有关传统的问题,在集体存在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是如此。”(Illuminations, p. 153)当然,波德莱尔的回忆是多方面的,既缅怀早已逝去的黄金时代,也回忆人类受到统治者压迫的历史,“文明记录中没有一部不同时也是残暴的记录”(Illuminations, p. 248),典型的如《天鹅》一诗,波德莱尔从受伤而踯躅在街道上的天鹅想到“一去不归的人”,“被遗忘在岛上的水手”,“想起囚徒、俘虏……和其他许多人”。
当然,以上所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读者带回原始社会,辩证讽喻还蕴含着对未来的乌托邦的展望。就辩证讽喻本身来说,辩证法既包含了矛盾,也潜含着矛盾消解的前景。“多义含糊是辩证法的图画似的意象,是处于静止之中的辩证法的法律,这一静止是乌托邦,是辩证形象,因为也是梦境。”(Reflections, 157)在矛盾消解时辩证思考本身似乎凝固不动,但其间蕴含着新的希望。另一方面,对未来的想象也是必不可少的经验,“希望也是一种经验。……满足了的希望才是经验的王冠。”(Illuminations, p. 175)没有未来展望的经验毕竟会残缺不全,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但任何未来想象都是人类乌托邦的集体记忆和当前社会现象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在每一时代的眼前,接踵而来的时代都以形象呈现出来,在这一梦想中,这些形象看上去和史前史的因素连接在一起,也就是和一个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连接起来。这一现象的线索保存在集体无意识中,它和新事物结合以产生乌托邦,从坚固耐久的建筑物到时生时灭的时尚,都可以看到乌托邦在生活的数以千计的变形中留下的各种迹象。”(Reflections, p. 148)任何时代都存在未来幻想,都有自己的乌托邦,乌托邦既融合了对史前史、对无阶级社会的记忆,又融合了现代社会中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鲜事物。本雅明随后举出的例子倒不是服装时尚,而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在现代机器生产条件下对未来人类居住之地的设计,傅立叶将机械制造定律和神秘激情融为一体,他的乌托邦看似一台机器,但又是高度复杂的有机体。类似描写也见诸波德莱尔的诗歌,如“让你的目光深深直视进∕森林之神和水边仙女的固定目光中”,显然森林之神、水边仙女等都不属于人类成员,他们都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些描写暗示人们可以在目光交流中展开乌托邦幻想。换言之,尽管现代人处于经验缺乏的不利状态,对抗危机的方法是防御性的,但并没有放弃对遥远未来的想象。
在本雅明以前的圣保罗、圣奥古斯丁、但丁、笛福、柯勒律治等人的各种讽喻理论中,讽喻总是和时间意象密不可分,本雅明的“辩证讽喻”也不例外。“辩证讽喻”虽然发生在现在,但这一“现在”总会自觉地向史前史的记忆、乌托邦的想象这两个维度拓展。表面上,现在似乎和过去、未来等这些“非现在”的因素处于矛盾中,但实际上,现在将过去、未来都集于一身,和过去、未来的联接更为厚重而紧密,这一具备了更多含义的特殊“现在”被称为“当下”,它承载着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展望。因此,“当下”这一时刻是危机的时刻,也是消除危机的革命时刻。身处这一时刻的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想到古代;这一时刻过后,人们将用各种纪念日来记住这个时刻。本雅明说:“就像我们之前的每一代人,我们已被赋予微弱的弥赛亚力量。”(Illuminations, p. 246)实现了救赎的“当下”展现乌托邦场景,它是“经验的王冠”,乌托邦并不需要在将来某一时刻来临,“时间的每一秒钟都是弥赛亚可能步入的窄门。”“当下”是对绵延不断的时间的彻底中断,它摧毁了过去也摧毁了未来,因为它实现了乌托邦;其外在标志是历史上的宗教节日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新设立的各种纪念日,这些节日都区别于一般的时间,使人们回想起人类经历过的弥赛亚拯救或乌托邦时刻。在本雅明看来,“当下”意味着和过去的决裂,这是无产阶级最后一个被压迫者阶级所应该具有的革命意识,“在毒害德国工人阶级方面,没有什么东西比相信自己沿着时间潮流前进更深的”(Illuminations, p. 250)。如果相信自己代表了时代潮流,那么就会忘记今天的革命实际上是对过去传统的否定,它不可能来自过去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弥赛亚拯救相类似,就像弥赛亚降临之后将不再有历史,革命也不是历史的目标,而是历史的终结。这里既透露出本雅明在激进岁月中按捺不住的政治热情,也不免将革命本身简单化。
本雅明指出:“17世纪的辩证形象的规范演变成讽喻,而在19世纪这一规范则是创新。”(Illuminations, p. 158)本雅明所说的创新既包括形式上的,也包括内容上的。以波德莱尔诗歌为例,他善于将本来毫不相关的词语并列起来,类似于蒙太奇技巧,使词语在新语境中产生意蕴,在波德莱尔诗歌中,“一个讽喻突然出现,并没有先前的准备。”[注]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 p. 100.波德莱尔的讽喻表现上是矛盾的,但不断追求新语境下的新意义,具有中断时间之流,创造危机时刻的激进含义。
本雅明在描述自己的政治转向时曾说,他的立场是“永远激进的但从来都不是逻辑的”(always radically but never logically)[注]Walter Benja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0),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trans. Manfred R. Jacobson and Evelyn M. Jacobs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300.,这一说法也可以用来形容“辩证讽喻”:它总是激进的,蕴含着革命的潜能,但又不是完全可以依靠逻辑连贯地从过去推导出来,因为它对过去的记忆要和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追溯到或者延伸到一个遥远的“无阶级的社会”;正因如此,“讽喻是现代人的盔甲”[注]“Allegory is the armature of the modern”,语出本雅明《中央公园》第32节。,是现代人抵御经验贫乏危机的武器,又是创造新天地的艺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