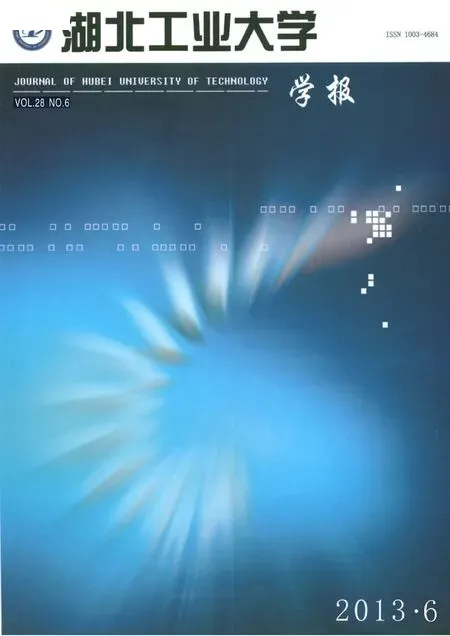汉赋主题与汉代《诗经》学
金前文
(湖北工业大学语言文化传播系, 湖北 武汉 430068)
汉赋是在汉代《诗经》学的控制和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汉代,“《诗》‘经’精神”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1]48;对“《诗》‘经’精神的……贯彻”[1]51,是汉赋创作的基本要求。“赋者,古诗之流也”[2]23这一思想的表述,就是两汉赋家对汉赋这一基本创作精神的具体体认。因此,汉赋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汉代《诗经》学的烙印。徐师曾云:“《上林》、《甘泉》,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炫曜,终折以法度, 而雅颂之义未泯;《长门》、《自悼》等,缘情发义,托物兴词,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泯”(《文体明辨序说·赋》)。从汉赋创作情况看,汉代《诗经》学对汉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汉赋表现的主题、汉赋采用的题材、汉赋的写作技法,都无不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因此,在汉赋研究上,应该有关于汉赋与汉代《诗经》学关系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并无实质性的成果出现。故而,本人拟做一点尝试。囿于篇幅,本文只讨论汉赋主题与汉代《诗经》学的关系。
1 汉赋表现的主题
所谓主题,就是“作者通过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3]126。汉赋主题,多与君有关,主要围绕君的道德行为规范,讨论了为君者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如傅毅《舞赋》云:“天王燕胥,乐而不泆。娱神遗老,永年之术。优哉游哉,聊以永日”,认为君应“乐而不泆”;孔臧《谏格虎赋》云:“今君荒于游猎,莫恤国政,驱民入山林,格虎于其廷。……以此为至乐,所未闻也”,认为君不应“荒于游猎,莫恤国政”;等等。
1.1 君行孝道问题
君的孝道,在汉赋创作中是很受重视的;汉赋家作赋经常触及到君的孝道问题。如张衡《东京赋》云:“天子……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声教布濩,盈溢天区”,《文选》薛综注云:“感物,谓感四时之物,即春韭卵,夏麦鱼,秋黍肫,冬稻鴈。孝子感此新物,则思祭先祖也”。显然,赋文写的是天子行孝之事。孝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祭。《礼记·祭统》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中庸》云:“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汉赋家作赋时,经常写到人君行祭之事,显然是对君行孝道的一种宣扬。两汉时期,当政者比较重视孝,并强调“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书·宣帝纪》),“以孝的精神为治理社会的根本”[4]337。应该说,在孝的问题上,两汉统治者做得是比较好的。因此,汉赋对君行孝道的关注也就主要表现为对人君行孝的褒颂。上文张衡赋中,作者就借“声教布濩,盈溢天区”对天子的孝行进行了褒赞。又如班固《东都赋》云:“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文选》注引应劭《汉官仪》云:“天子父事三老”。天子之孝的内涵,不仅仅止于事亲。《孝经·天子章》云:“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赋文对天子率行孝道的行为进行了赞颂。
1.2 君能否节俭戒骄淫
“骄”,是“不恭”的意思。《汉书·傅喜传》云:“丁、傅骄奢,皆嫉喜之恭俭”。“恭俭”,就是指节俭戒骄。两汉赋家作赋时,对人君能否节俭戒骄淫是比较关注的。班固《东都赋》云:“于是圣皇…………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把不骄能恭看作“帝王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赞扬了“圣皇”(即光武帝)“允恭乎孝文”的行为。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云:“二君之论,……徒事争於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把奢淫看作贬损人君的一种表现,传达了人君当节俭戒淫的思想。扬雄《校猎赋》云“孝成帝时羽猎,雄从。以为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扬、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恐后世复修前好,……故聊因《校猎赋》以风”,直接表达作者作赋的目的是为了讽谏人君的奢靡。班固《东都赋》云:“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又沐浴於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颂曰:盛哉乎斯世”,对人君能自我返奢归俭的做法进行了颂扬。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赋家关于人君应节俭戒骄淫的思想。
1.3 君能否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的内涵比较丰富,有爱民、安民、务农重本、轻贡赋惜民力等等。两汉赋家作赋时对这些内容也比较关注。如班固《东都赋》云:“于是圣上……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于是百姓……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赞扬了抑工商、兴农桑的做法,传达了君应务农重本的思想。又如张衡《东京赋》云:“天子……恤民事之劳疚。……因休力以息勤”,表达了君应轻贡赋惜民力的思想。又如扬雄《羽猎赋》云:“上……土事不饰,木功不雕,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收罝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于是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加劳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赞扬了君不饰土事、不雕木功、承民乎农桑,开禁苑与百姓共之的做法,传达了君应爱民、安民、务农重本、轻贡赋惜民力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赋家关于人君应以民为本思想的反映。
1.4 君能否致任贤能
致任贤能,是君为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尸子》曰:“治国有四术:一忠爱,二无私,三用贤,四简能”(《文选·东京赋》薛综注)。两汉赋家作赋对人君为政能否致任贤能也是比较关注的。张衡《东京赋》云:“表贤简能……所贵惟贤……于斯之时,海内同悦”,对人君能表贤简能给予了肯定。边让《章华台赋》云:“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诸侯慕义,不召同期。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虽齐桓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 对人君能任官处能进行了颂扬。这些都体现了赋家关于人君为政应致任贤能的思想。
1.5 君能否省刑罚兴教化
汉赋家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以明,习俗以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汉书·礼乐志》)。两汉赋家作赋时表达了这种思想。张衡《东京赋》云:“秦……威以参夷之刑。……乃救死於其颈”,说明严刑重罚并不能治世。赵壹《刺世疾邪赋》云:“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说明靠刑罚也不能救世。这些都体现了赋家关于人君为政应省刑罚的思想。张衡《东京赋》云:“乃营三宫,布教颁常……春日载阳,合射辟雍。设业设虡,宫悬金镛。鼖鼓路鼗,树羽幢幢。……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阕,《驺虞》奏……仁风衍而外流,谊方激而遐骛”,盛赞了东京文事之盛,说明人君治世当兴教化。班固《东都赋》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颂曰‘盛哉乎斯世’”,也对人君治世能兴教化的做法进行了赞颂,传达了人君治世当兴教化的思想。
1.6 君能否正确对待战争
正确对待战争,就是要讲义战,反对穷兵黩武。两汉赋家写赋对人君能否正确对待战争也是比较关注的。冯衍《显志赋》云:“疾兵革之寝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体现了对不义之战的厌疾和指斥;而扬雄《长杨赋》云:“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王廷。驱橐它,烧蠡,分单于,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兖鋋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则体现了对义战的赞赏和肯定。这些都体现了赋家关于人君应正确对待战争的思想。等等。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两汉赋家作赋表现的主题与人君联系比较紧密,多是围绕人君阐发的。
2 汉赋主题与汉代《诗经》学
汉赋对主题的表现,与汉代《诗经》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汉代《诗经》学具体包括齐、鲁、韩、毛四家。四家对《诗经》的解读是以“礼”为中心的;也就是“以礼解《诗》”[1]33,主要通过《诗经》阐发儒家的礼治思想[5]。
儒家礼治,极为重视君臣伦常;《新书·礼》云:“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因此,四家对《诗》的解读主要是围绕“主主臣臣”进行的,解读的主要是儒家的“君臣”伦常[5]。
在“君臣”伦常中,四家诗认为,为君者必须有德。有德,就是有“仁”,就是为君者要“以仁治”。“君以仁治”,首先是以“孝”治,其次是“行仁政”。“行仁政”,内涵极为丰富,又包括节俭戒骄淫、以民为本、致任贤能、省刑罚兴教化,正确对待战争不穷兵黩武、守义战等等[5]。
联系上文可以看出,汉赋对人君道德行为规范的阐发与四家诗对君德的解读基本相合,其内容基本是承四家诗而来的。四家诗对汉赋创作主题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实际上,汉赋在讨论君的道德行为规范时也有对君德的直接论述。如在《天子游猎赋》中,司马相如借乌有之口驳斥子虚侈谈楚王田猎之盛时说:“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等,都体现了作者对君德的重视和宣扬。
在论述过程中,汉赋还对能行“仁”的有德之君和君的有德之行进行了褒赞,对君的失德或不合德之处,进行了谏,这从以上所举实例就可看出来。汉赋的这种或褒或谏,实际上也是受了《诗经》学的影响。
在“君臣”伦常中,礼对臣的要求是“忠”。四家诗论臣,是以“忠”作为讨论“臣”的标准的。所谓“忠”,就是要勤于王事,诚尽职任;既要“彰主”,褒扬君的功德,又要“谏主”,进谏君主之过[5]。汉赋多为“奏御”之作(班固《两都赋序》),汉赋家作赋是为了“奏御”,当然要履行臣道。用赋褒谏,就是赋家履行臣道的具体体现。
不过,在谏时,汉赋采用的都是“讽谏”的方式,极为委婉,往往是以君自我反省、主动改正不德的形式进行的。如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云: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閒,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以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
“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乡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
等等。
这种进谏方式也是受了四家《诗》学的影响。四家诗认为,“忠”臣“谏主”要有正确的方法,要“谏而不露”,“欲其由君出”;既要使君改过,又要远罪避害,成君之美,采用“讽谏”的方式[5]。汉赋的进谏方式显然是由四家这种《诗》学思想而来的,是四家这种《诗》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总之,汉赋在主题表现上,以“君”为中心,阐述了君德,褒扬了合德之君,对君的失德进行了谏,谏时又极为委婉,采用了“讽谏”的方式。这些特点,都明显地打上了汉代《诗》学的烙印,体现着与汉代《诗经》学的深切关联,是汉代《诗经》学影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萧华荣. 中国诗学思想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 李 善. 六臣注文选(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刘安海,等.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孙 筱.两汉经学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 金前文. 四家《诗》说大义浅探[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2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