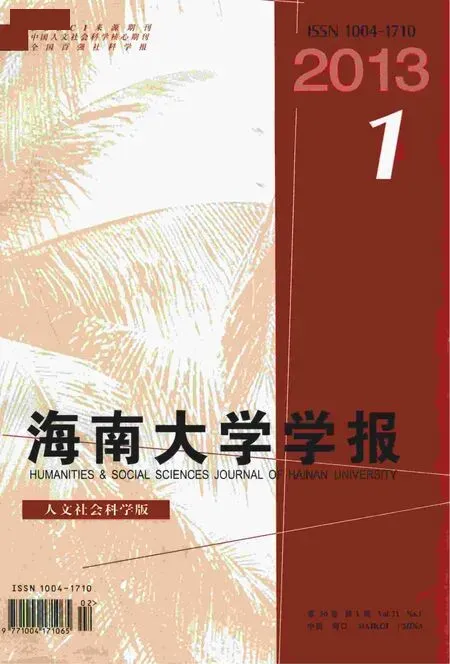羁旅山水与家园体验——论羁旅行役诗中家园感呈现的意象形态研究之一
程 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羁旅行役是士人普遍经历的一种生存样态,作为古典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抒情主题,它集中表达了因不可抗拒的现实事务目的而漂泊无定的人生感受;尤其是士人志在推仁行道的文化使命而自觉谋求政治践履,羁旅行役突出了游于家、国之间而陷入的生命无处安顿的困境体验;此种切身体验的生存境遇凸显出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剧性真相,更激发了诗人对人生价值的反复探问和追询,由此产生对精神家园的强烈企盼。体味人生漂泊、反思价值困境、向往精神家园这3个方面,展示了士人羁旅行役由浅到深的文化意蕴层次。羁旅行役诗虽出于各不相同的个体经验的自我抒写,却有一个共通的主题联结点,即寻找家园感的安顿。人生其实是一场茫茫追寻而永无歇止的行旅,家园感是士人在天地逆旅、人生如寄的生命感悟中对精神归依的终极追求,它并没有宗教信仰的具体形式,而是一种虚灵的心理体验;尽管它也常遭到质询,但对于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观念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经过生命历练的反复体味而在心中自然呈现的家园感,仍旧为游子诗人提供着止泊生命、建构价值的坚实依据和最后归宿。家园感的呈现绝非廉价的、一触即得的,而源于士人羁旅之中价值困境、家园何在的追问,是执着现实人生而不断积淀起来的文化心理的自然选择,对它追询的过程本身即构成精神家园的意义。家园感常在与人亲切相依的自然或生活中通过对应的物化形态而得以呈现,山水、佳人是两种最常见和重要的意象形态,包蕴于其中的丰富文化信息又是有所差异的。本文集中讨论羁旅山水与家园体验。
一、家园意识与士人羁旅行役的文化精神
从字源学上考察,“旅”和“游”同出于“方人”字,小徐本《说文解字》释作“象旌旗之游及方人之形”[1]。“游”古字作“遊”,是执旌旗行走的意思,早期的涵义与巫术宗教相关,意谓像神明一样体验着自由超越的游的状态。“旅”,“俱也”,有多人结伴随旗外出之义,描述的是古代氏族奉族神徽号或图腾标志而群体迁移游居的文化现象,也带有原始巫术宗教的意味[2]。“旅”、“游”同源而又有差别,《周易正义》释“旅”卦云:“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3]268,又《序卦》云:“旅而无所容”[3]398、《杂卦》云:“亲寡,旅是也”[3]401,意指一种抛绝亲故、客游在外、失本无根的生存境遇。故“旅”常为现实生活所牵掣,为世俗事务所萦绊,它虽然如“游”一样也呈现为一种游离流动的状态,但与“游”寓意着对现实世界一切羁绊的精神解脱涵义不同,它的本质是不自由的,它一端拴系着温暖家园的召唤,一端又不得不体验着生命的漂泊而难以回归,这是羁旅行役文化意蕴最直接显著的特征之一。《昭明文选》的诗文分类将纪行、行旅、军戎区别于游仙、招隐、游览,就是着眼于这种内在的精神分野,盖游览诗常寄意于山水风光和仙、隐境界,在神游心赏中乐以忘忧、脱去桎梏,其主题是解脱和自由;而行旅则被世务所役使,总是满含悲戚的情绪和不自由的痛苦,如李周翰注:“旅,舍也。言行客多忧,故作诗自慰”[4]。“旅”所负载的不可抗拒的现实目的性,以及行旅之中理性所无可解释的生存困境,暗伏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悲剧,由此引发生命不得安顿、家园失落的种种人生悲吟。
这类主题在诗歌中的表现可以追溯到《诗经》。如《王风·扬之水》、《豳风·东山》、《小雅·采薇》写戍卒士兵的思乡哀叹,《小雅·四牡》、《北山》、《小明》写士子大夫行役的怨苦悲伤,《唐风·鸨羽》、《小雅·杕杜》、《何草不黄》写征夫对行役不息的怨愤和控诉,还有朱熹所屡称的“妇人以其君子从役于外”[5]而作的思妇怀人之诗,如《召南·殷其雷》、《邶风·雄雉》、《卫风·伯兮》等,也都是借拟思妇口吻来逆叙征夫行役思归之情的。“王事靡盬”、“我戍未定”等种种不自由的现实目的性活动的驱使,造成人生行旅迁流的巨大缺憾和哀伤,于是才有望乡怀土、念远思归的深刻情感体验。这些先民歌咏透露出羁旅行役之中家园意识的两重特质,其一是重视家族血缘之间伦常联系的脉脉温情,如方玉润评《魏风·陟岵》云:“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日远离父母者乎?”[6],道出了寻求人伦亲情之抚慰、归根宗族乡土之渴念的文化情结。其二是向往和平无争、守土不迁的田园牧歌式的现世生活,如《王风·君子于役》以黄昏这一动人的意象,将中国人心灵深处根植于农业人生的家园感真实昭显出来,表现了对和谐安宁之生活的永恒祈求,“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所折射的绵绵诗意,就成为一种千载相通的文化原型,深深烙印在游子诗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这两重特质与中国农业文明所塑造的民族性格密切相关,稳定、循环、恒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以家族为基本单元、以宗法制为政治礼俗制度的社会结构,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宗族封建国家到家族专制王朝,都未有大的质的改变,在此稳固封闭的文化系统内,个体生命对血缘宗族始终葆有一份伦理情感的向心力,家园与羁旅行役的内在文化关联,才会在千百年游子的反复咏叹中得到加强而融进民族文化心理的血脉。
儒家的仁学更为伦理情味浓厚的家园意识注入了全新的人文精神,使中国人对家园的诚挚渴念之情由企盼宁谧和谐的农业人生提升为家国情怀和天下意识,同时也为士人设定了修齐治平的自我实现之路,使士人羁旅行役楔入了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处。“仁”以“亲亲”、“孝悌”为核心而向外扩展,注重礼融于情的凝聚内化和人性心理的自觉培养,将尊祖敬宗、收族爱人的宗法伦理规范转变为士君子人格主体上的修德与求仁。儒家文化理想的内在逻辑是在伦理中心的基石上视家国一体同构,从正心诚意的内在道德秩序的建立,到将家庭伦理秩序推而为国家政治秩序,“仁”的追求通过对伦理精神的情感认同(“我欲仁,斯仁至矣”)和现实践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把个体与家国天下紧密绾结在一起。胡晓明先生说:
家国通一精神,一方面,将中国人的乡关之恋政治化、理性化。思家的魂梦飞萦,不仅是一己小我的温煦之情,而是与国家民族文化理想循循相通的庄严圣洁之情。另一方面,……又将中国人的政治情结生命化、人伦化。政治之治乱兴衰,不再是外在于生命人伦之事,而是由生命中延伸开展而出的真实需求。[7]
以屈、杜为代表的游子诗人对家园的千年歌吟,展示了一种仁心辐辏、通于家国的文化情怀和价值模式:一、士人的羁旅行役背后始终萦绕着一层由志道意识伸展而来的政治追求,学而优则仕、由家到国的政治实践以实现儒家的文化理想是士人的道德宿命。尤其是士人依托取士用人的制度化保障而对仕途政治的普遍参与,羁旅行役被更明确地定位在集权专制的政治格局之下,家与国构成了游子行役中生命两端游履的价值支点,家与国之间的距离(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距离,更是文化、心理上的距离)则隐伏着家园失落的悲剧意识。二、“旅之时义大矣哉”又体现着一种坚定不渝的入世情怀和执著此际人生的准宗教信念。其实人生恒久漂泊,实无根本的归歇之处,“中国人生来便被道德本体放逐”[8],永远在经历着灵魂的浪游,而文化系统体用不二的特性又使士人别无他途可走,只有以乐感的态度重新执着现实来直面人生本原的悲剧。尽管行旅之人总有适彼乐土逍遥神游的解脱欲念和超越祈想,但并不厌弃现实、超离世间而皈依彼岸,反而总是在现实困境的无所归依之际寻求向道德本体和宇宙情怀的回归,于绝望中造出希望,“旅”的不自由中正展现着价值建构的曲折流程。三、寻找家园感是精神反复游履不懈追询的心理过程,家园感的获得意味着一种冥证的心灵境界的提升,每一次向精神家园的回归都使心灵获得一次新鲜的感受和洗礼,这情理交融的洗礼历程本身就构成了精神家园的意义。家抚慰着游子感性的生命欲念,国昭示着求仁行道的价值追求,游于家国之间的羁旅行役使体味和建构精神家园充满了情理间作的内在张力,同时也使思家、恋阙的主题变奏成为士人精神的一体两面,家园感正是在这积淀起来的心灵本位中反复呈现而历久弥新的。在没有反抗对象、没有外在超越的价值归宿的中国文化中,建构精神家园是一种以百倍悲情为底色、尽心而知命的自我价值设定,概括了中国人特殊的文化悲剧意识和自我救赎之路,也成为消解行旅失路之悲、安顿漂泊生命的重要文化动因。
二、士人羁旅山水的诗歌传统
家园意识始终牵引着游子行旅的精神指向,家园感产生于生命历程的切身体味中,它是精神浪游的止宿而非归附于物质实体,是一种虚灵的心理体验,常需要借助特定的情境意象而加以呈现。羁旅行役诗中那些鲜明集中的意象,凝聚了游子感性生命代代相通的情感内容,就成为补偿家园失落、提供精神归宿的独特符号,如月、雁、酒、梦、远村、孤舟,等等。山水与羁旅行役的漂泊体验最为贴近,游子的家园感往往在晓行夜宿的山程水驿中最显迫切,山水跋涉加剧了“旅”的不自主和无所归,但同时特定的山水意象也构成了温暖安宁的家园体验,成为生命安顿的典型形式。
早期羁旅行役诗中的自然是作为家园的对立面出现的,自然环境的凄凉险恶、节序物候的迁逝瞬变,都凸显出行旅置身异域之中无主无依的生命漂泊感。《楚辞》中的《涉江》、《悲回风》诸篇,就以陌生异己的荒野山水,皴染了“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的失土无根之悲。汪瑗解《哀郢》“将运舟而下浮兮”以下数句云:“故都平乐之风土,日邈以远,而漂泊于此大江之介,感风景之殊,使吾之心益哀而悲焉”[9]176、“乘此陵阳之波,淼然南渡大江矣,果将何所归而何所往耶?实反言以深见迁客之流离,故都之日远也”[9]177,风景之殊乃作为远离故土无所归依的反衬媒介,还未能直接作为家园呈现的情感形式。自然景象与人情物感有内在的同构关系,羁旅之中忧心愁悴的情绪往往选择集中固定的物象来加以表现,伤春悲秋就是最常见的情感意象模式,宋玉《九辩》所树立的贫士悲秋传统,被称为“千古言秋之祖”而被后世羁旅行役诗所反复摹写。其背后实暗藏着中国文化悲剧意识的基本结构,即在人事政治与自然天道同构共通的模式里去感受和追问人的价值。朱熹《楚辞集注》云:
秋者,一岁之运,盛极而衰,肃杀寒凉,阴气用事,草木零落,百物凋悴之时。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乱,贤智屏绌,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是以忠臣志士,遭谗放逐者,感事兴怀,尤切悲叹也。萧瑟,寒凉之意。憭栗,犹凄怆也。在远行羁旅之中,而登高望远,临流叹逝,以送将归之人,因离别之怀,动家乡之念,可悲之甚也。[10]
悲秋意识里包含了时间迁逝所催迫的生命短促之悲,有主昏政乱贤愚倒置的政治理想之悲,也有孤旅离别迁贬放流的家园失落之悲,这一原型里包罗了后世悲秋的基本类型,又总而表现为被天道抛弃的文化之悲。天道与人的悬隔是由与人生命节律同构的自然物象呈现出来的,秋景的盛极而衰、肃杀萧条对应了人的悲感,种种现实境遇的人生悲情就有了固定的意象化形态;天道又并非外在于人的绝对理念而是与人息息相通的,天道循环无往不复的整体系统保证了人重获价值依据的可能,而不是越出天人合一的封闭轨道走向虚无。自然秋景的描摹具象化了人与天道的疏离感,同时也使心灵在往复求索的洗礼中重新校正了亲合天道的追求方向,中国人的悲秋并不是寂灭绝望,而是在体证与天道疏离和亲合的过程中使精神得以历练而获得丰富和新生。伤春意识的心理机制也同于此,只是物象的选择稍异,而生命的感受更偏于柔性。总之,自然构成了沟通天人价值转换的绝佳载体,沿着楚辞所开创的源头,后世的羁旅行役诗中就多有山水物色之辞,以及类似生命漂泊的楚调之叹。“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王粲《七哀诗》)、“殷怀从中发,悲感激清音”(陈琳《游览》)、“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陆机《赴洛道中作》),这些漂泊感受都通过萧索悲凉的山水物象得以宣泄,与《九辩》的悲秋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自然山水要进一步成为家园感的直接呈现形态,还有待于诗人自然审美意识的觉醒,只有视自然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非异己存在的行旅背景或宣泄情感的触媒,向往安顿的家园意念才能真正落实在山水审美的愉悦和净化中。汉魏行旅、祖饯诗中已有粗略片段的自然景物描写,但仍由纪行咏怀的线索加以串接,情事相生的抒情思路仍未开发出独立写景的空间和意象化的诗思方式。东晋湛方生《还都帆诗》用四分之三的篇幅刻画行舟山水,且在山水赏悦的审美体验中“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已转变了感物兴悲以突出漂泊感的楚调模式。王夫之评:“纯净无枝叶。杜审言‘独有宦游人’一律脱胎于此”[11],即行旅诗已变情事咏叹为情景观照,山水审美意识与行旅漂泊的精神联系开始明确浮现。谢灵运真正首开了羁旅山水的抒情传统,论者指出“谢客山水诗由宴游、特别是行旅诗中蜕出当无可疑”[12],行旅作为山水诗创作动力的源头之一,即归因于在行旅途中借自觉的山水审美以满足涤洗烦累、寻求安顿的精神需要,“由‘疚心’之嗟,变而为‘赏心’之娱,生命漂泊的喟叹,终究转成了安顿生命的欣慰”[13]。谢诗常标明行旅时地而恣意独游,一方面“寻山陟岭,必造幽峻”,着力于发现远离人寰的荒僻幽奇的自然美,暗示自身陷入了与家国离而未合的愤激和伤感的情感漩涡:“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七里濑》)、“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迢迢万里帆,茫茫终何之”(《初发石首城》);一方面又在体物精微的迥秀之句中获得审美关注的短暂停留,山水作为畅神之具就暂时消弭了其行旅失意之叹:“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富春渚》)。前人谓谢诗“模写行役江山历历如画”[14],已开南朝及唐人以山水写羁旅行役之情的固定模式。
南朝的山水行旅已更多将游于家国之间的漂泊感融入山容水色的工笔刻画中,达到情景的交流互诉,如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沈约《登玄畅楼》、江淹《赤亭渚》、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等,都以山水物象的画面感形象呈现出仕宦迁谪的无奈飘零,在山水阻隔的境遇中突出对家园的想望:“故乡邈已夐,山川修且广”(谢朓《京路夜发》)、“去家未千里,断绝怨离群”(江洪《旅泊》)、“夜泪坐淫淫,是夕偏怀土”(何逊《宿南洲浦》)。以下诗例中则表现出一种更加纯净的审美心态:
昧旦乘轻风,江湖忽来往。或与归波送,乍逐翻流上。近岸无暇目,远峰更兴想。(任昉《济浙江》)
森森荒树齐,析析寒沙涨。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信是永幽栖,岂徒暂清旷。(丘迟《旦发渔浦潭》)
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何逊《慈姥矶》)
暮潮还入浦,夕鸟飞向家。寓目皆乡思,何时见狭斜?(何逊《渡连圻》)
任、丘二诗的羁旅行役之思被山水游赏的兴致所化解,山水所代表的自然世界是世俗世界之外足以摆脱俗务拘挛、安放自由生命的家园;何诗则以行旅日暮中宁谧安详的江景抚慰着游子的乡愁,《君子于役》以来的黄昏意象勾起了一代代诗人对于精神家园的悠悠追忆。在唐人“以情意对山水”[15]的审美观照中,这种家园感的诗意呈现更与山水的审美境界情景交融,浑化无迹。仅以孟浩然为例,如《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早寒江上有怀》(“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等,山水成为旅思乡愁的直接情感形式而不再有理障的阻滞,后人透过这些山水意象也能立即感受到共通的生命的缺憾与安顿。清人黄叔灿评《建德江宿》云:“‘野旷’一联,人但赏其写景之妙,不知其即景而言旅情,有诗外味”[16],刘永济评:“诗家有情在景中之说,此诗是也。不可但赏其写景之工,而不见其客愁何在”[17],行旅之叹与家园之思已在山水中得以完全交融映发。这里透显出羁旅行役诗中家园感与山水的一个重要联结点:家国之间的羁旅之游转变为山水之间的审美之游,游于家国之间的价值追询和家园失落感在当下诗意的、审美的心理体验中即获得生命的安顿。士人羁旅山水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即多是以山水审美作为渡引人生超越的梯航,特定的山水意象给游子带来生命安顿的欣慰感和满足感,凝聚了诗人关于家园忆念的集体无意识,每一次对这些熟悉意象的感性经验,都会激起家园感在心中瀰瀰漾开。
三、羁旅山水中生命的漂泊与安顿
羁旅之游向审美之游的内在转变,积淀出充满诗意的山水之心和家园体验,在山水行旅的特定情境中,暴露价值困境之际往往即是家园感油然而生之时,中国山水诗本就具备生命漂泊与家园安顿合二为一的文化品格。山水意象如何具体参与到山水审美的心理体验和价值转换中而传达出家园感,可分以下几种类型来探讨。
(一)山水作为横隔于家国之间、暴露价值困境的具体显现
空间地域上的距离感首先在直观上就展示了行旅的无目的感和无归宿感,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朱止谿评:“悲歌,不得志于时之所作也”[18],表明这无名的歌者谋求有用于世却进(欲渡河无船)、退(欲归家无人)失据的矛盾境遇,游子望乡悲歌多是起兴于空间距离的无法逾越。士人因义无反顾的游宦仕进活动而离乡去国,山水阻隔、征途迢递最为形象地呈现出游离于家国之间两端无可依止的漂泊状态,如潘岳《在怀县作》:“信美非我土,秪搅怀归志。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愿言旋旧乡,畏此简书忌”,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羁旅山水更将家国价值实践上的梗塞难通,抽象为一种文化心理上的疏离感受,如何逊《初发新林》:
伊昔负薪暇,慕义游梁楚。短翮忘连翩,追飞散容与。优游沐道教,渐渍淹寒暑。大德本无酬,轻生窃自许。舟归属海运,风积如鹏举。浮水暗舟舻,合岸喧徒侣。癝癝穷秋暮,初寒入洲渚。铙吹响清江,悬旗出长屿。危樯迥不进,沓浪高难拒。回首泣亲宾,中天望宛许。帝城犹隐约,家园无处所。去矣方悠悠,含意将何语。
诗人首先自陈感激君主知遇之恩的报国之志,接着描写羁旅行舟中的艰难险阻,秋暮寒洲、危樯沓浪暗示了仕途的蹭蹬曲折。“帝城”、“家园”一联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引领企望,而是在进退两难之际陷入了价值实现的困境,极典型地刻画出士人羁旅之中寻找家园的文化心态:士人求仁行道如果无法进入到国的层次,就会汲汲奔走努力向政治理想趋近,在羁旅中产生恋阙思君的怨悱失意和怅望企盼;即使进入到国的层次,又会因功名未就而难于归家,因公务迁谪而淹留旅途,从而导致人生飘零的忧伤和对家园的强烈渴慕。这种游于家国之间的困境体验是士人在政治系统内游宦行役的普遍遭遇,亦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道德宿命。
由此种共通的人生体验而引发的羁旅之叹,在唐诗中尤其普遍。唐人政治本体意识空前强化,开放的时代精神使士人的功业意识激昂高涨,致身科举、漫游干谒、出塞入幕、征戍迁谪的大范围流动,使羁旅之中的家园意识与体认道德秩序的政治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使感性生命与羁旅山水发生频繁密切的接触,融入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家国之间情(浪漫张扬的个体感性)理(政治传统的历史理性)冲突的张力,形成了唐人浓郁的乡愁情结。以陈子昂《晚次乐乡县》为例,首联写故乡杳远,日暮孤征,正是士人行役向国的价值的勉力追求,同时也兴起家园之思;前人评颔联:“故乡、旧国,语若重复,细玩味之,当自有别。迷者,非行而迷失也。川原回异,念旧国所经若迷耳”[19],其实所迷者乃是由于个体生命无法融入道德本体、历史天道而怅惘失据;故颈联以“野戍荒凉,烟火断绝,深山穷僻,林木云平”[20]加深了人生漂泊无可依托的悲感,向往家园安顿的欲念就在野景暮愁中萦绕愈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谁堪登望云烟里,向晚茫茫发旅愁”(王昌龄),唐人乡愁的深层文化意蕴在于体现着对政治本体的深情体认,烟波茫茫具象化了价值追求发生梗阻、反思家园何在的巨大迷惘。唐诗中的途次旅泊最常见此种抒情姿态:
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常建《泊舟盱眙》)
旅望因高尽,乡心遇物悲。故林遥不见,况在落花时。(崔曙《途中晓发》)
帝乡劳想望,万里心来去。白发生扁舟,沧波满归路。(刘长卿《晚次湖口有怀》)
霜蘋留楚水,寒雁到吴城。宿浦有归梦,愁猿莫夜鸣。(钱起《早下江宁》)
水远山遥的具体情境突出了与家国疏离的生命状态,羁旅乡愁每在此时便倍显迫切。山水由地理空间上的阻隔形式折射出人生并无外在终极依据的悲剧性存在,价值追询在困境体验中发生断裂,家园感失落了,由此产生价值的虚空感。但价值空没并非导向人生的消极沉沦,而是重新寻找家园安顿的心理起点。
(二)山水作为人与自然亲和、体认宇宙情怀的具体显现
与家国疏离的困境体验,是建构精神家园的心理流程中最初的必经阶段,家园感的失落激起了重新建构价值的冲动,将人生引向对悲剧性现实的反思和抗争。当士人在厚重乡愁的洗礼下重回现实寻找意义时,心灵已获得一种净化后的感动,家园不必外求,而在内心的情感体认中获得着落。表现于羁旅山水,就不再强化着阻隔与疏离,而是直接作为安顿生命的补偿形式。如王绩《野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这是黄昏时分万物归息的平凡生活场景给人带来的安宁感;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是雪夜人归之时落魄游子获得止泊的一份温馨感。意象的选取剪裁突出了自然与人的感性生命韵律的和谐,勾起游子向往幸福宁静的家园体验,山水承载着一种共通的心境,即在此情境中人与自然不再是拒斥疏离,而是走向亲和,视山水为家园的所在。
这种亲和更深透一层就是寥廓深邃的宇宙意识。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结句:“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饱含了中国人肯定宇宙生命的美质以表达家园企盼的那一份执着的深情和恒久的感动:人生在百折千回的艰难寻觅后,尽管寻找不到答案,但依然有斜月脉脉照人心头,有江树摇摇指人归路,生命中一切美好的情愫在宇宙意识的激发下获得提升和敞亮,个体生命便不再孤单悬隔、被偶然抛掷世间无所凭依,而是在与宇宙亲和的审美境界中找到了根本的归宿。中国人与自然宇宙的亲和心理,即彰显了山水审美意识中最具文化根蕴的宇宙情怀:它根源于“一个人生”的文化背景,由于没有超越的上帝或先验的理性可供皈依,人只有依靠自己去寻找和建立价值凭据,将活的意义构筑于活本身;于是才会有对宇宙的情感灌注,“有意赋予宇宙以暖调情感来作为‘本体’的依凭”[21]110、“来支撑‘人活着’”[21]181,儒道皆以宇宙作为人的价值和道德的依据;体认这一“假设”和“约定”的“本体”,并非理性思辨的服膺或宗教信仰的盲从,而仍归于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情”本身。在宇宙的情感化中人意识到宇宙无限而人渺如尘,永恒不可达到,便产生悲剧意识;返归自然、亲和宇宙亦使生命宇宙化了,在审美体认中充实和丰富此在的“情本体”,便是悲剧意识的消解;宇宙诚美好,人生实可贵,于是执着现实重新向道德本体融入,提升人格境界而获得价值感。自然宇宙给予人之“大德”,就是提供安顿生命的最终归宿,使人珍惜、留恋人生之实有。表现诗人心灵深处的宇宙情怀的重要形式就是赏悟山水,山水诗则是感受、领悟、把握此种本体之情的艺术呈现。仍以孟浩然《建德江宿》为例来分析这种审美体认的具体心理流程:“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前两句是孤舟旅泊,日暮烟渚凸显价值困境,家园寻找不到,陷入悲剧感;后两句转入了对山水的审美观照,旷野之中天水相合,远树微茫,江水映月,似与人相亲相近,个体向宇宙无限融入,具体时空中的羁愁旅恨被涤洗尽净,理性追询的执迷也已消淡,只剩下心境的审美沉入,家园感便在心中袅袅生成。由此亦可深掘“以山水写羁旅行役之情”这一模式背后的深刻文化意蕴,如以下诗例:
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马周《凌朝浮江旅思》)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陈子昂《度荆门望楚》)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王湾《江南意》)
三首诗抒情写景的结构十分类似,都由羁旅行程发端进入到情境化的山水描写,最后又以旅思乡愁作结。中间两联的山水景象皆渺远阔大,展现了昂扬时代精神所激发的精神张势,如王夫之评前二首云:“神采天香,古今鲜匹”、“平大苍直”[22],王湾诗第三联更被胡应麟誉为盛唐气象的代表[23]。初盛唐山水诗中常常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张势,就是将微渺的个体抬置、融入苍茫无限的宇宙之中,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庄严地思考人生意义,从而感悟有限生命、激发用世豪情、获得价值感,山水成为诗人情感的直接投射,心灵也因此自足充盈而获得家园感。李白山水诗中雄奇阔大的宇宙意识,代表了唐人情意化山水的最高典范,如《峨眉山月歌》中山月江流依依相送,有情至极,令旅思飘逸飞扬,毫无乡愁的沾滞和凝重;《早发白帝城》中万叠重山之间大江轻舟的流转飞动之美,实映衬着主体精神趋于自由超越的生命体验;《渡荆门送别》颔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以流动的视角将精神视野扩充至水天浑合之际,渺小的个体已消溶在自然的怀抱,物我不分,有情的宇宙真正成为了诗人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杜甫漂泊西南的羁旅纪行诗则总在山水跋涉当中突出向道德本体的回归,试读自陇入蜀的羁旅组诗之终篇《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诗人的情感哀回百转,悲凉激壮,崎岖山水饱含了身世飘零与时代丧乱的沉痛体验。李子德评:“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24],其诗史意义已超出纪行言志的狭义范围,而是以诗来承载仁心通于万物直与天地同体的道德信念,此信念源自与天道亲合所产生的强烈认同感,因此激起对礼乐传统和历史本体的终极关怀。在老杜的诗歌生命中,君臣大义、家国通一之情怀“都从一副血诚流出”[25],又经由诗歌完成一己之仁的扩充和人生超越,“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这是仁者观物与宇宙生机最深层次的契合。于风尘漂泊中积淀起来的“元气浑沦”(杨德周评语)的人格境界,成为新的人生价值的基石,在这里,诗人的政治生命已属次要,道德融于天道而获永恒的价值实践不必依托在政治秩序中,而毋宁在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格践履中。《登楼》、《秋兴八首》、《阁夜》、《登高》等诗里雄沉深灏的家国情怀即是此种人格境界的反复体验,而“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乾坤一腐儒”(《江汉》)、“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置身寥廓宇宙背景中的微渺孤独的形象,则已不再是漂泊无依的简单象征,而是人格生命独立苍茫的坚定信念,是道德本体和宇宙情怀给予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安顿。
(三)山水作为诗词内部“化时间为空间”审美机制中家园感的具体呈现
这一点仍由中国人特殊的时空观念和宇宙意识生发而来,并进而影响着对诗词的审美体验。冷成金先生指出:“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外向超越的价值追求,不太认同超验的理念设定,而是追求内向而超越,热衷于在可感知、可把握的现实经验世界中寻找价值与意义。将无限的不可把握的时间性因素化为有限的可把握的时间性因素,将不可回避的可能导向‘超验’的时间因素化为‘经验’性的空间因素,正契合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执著而超越’的文化精神”、“时间的作用就是将无限的、不可把握的空间划定为有限的、具体的、可感可控的空间,空间从而成为时间的显现形式。……也使得蕴涵在时间中的生命意识向蕴涵在空间中的秩序观念趋近,从而建立起生命的价值感”[26]。羁旅中最鲜明的时间感受就是晨昏行宿、春秋代序所产生的迁逝感,黄昏体验、伤春悲秋意识等都在强烈迁逝感的刺激下产生生命无处着落的失家之悲。汉魏抒情诗中的“感物”传统即常常引发生命忧思和人生玄理,但空间性的“景”仍作为时间性的“情”的起兴媒介和抒情陪衬,未能突出山水意象的独立自足性。唐诗中已有普遍的自然意象优势和成熟的山水诗境,不论是物境、情境还是意境,总之都是凭藉山水形成一个独立的心灵空间,家园感尽管虚灵,却可以落实在情感化、心境化的客观空间中而呈现。山水审美中的一大心理转换机制,就是“化时间为空间”,即将时间无情流驶中生命惶惶无可定止的家园欲念,既非归附冥冥上帝向往彼岸,也非坠入虚无走向荒诞,而仍是落实在可感知可把握的山水境界中,在这个特定情境化的山水空间里来体认家园感。如温庭筠《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全诗围绕“早行”展开,旅愁与乡思又随着景物片段的空间转换而“呈现为动态发展之过程”[27]。首联以晨发(时间因素)牵动乡愁,这时家园茫茫尚无着落;颔联以旅途即目之景组成羁旅早行的真切画面,“意象具足”而羁愁旅思已见于言外;颈联仍以槲叶、枳花的画面相切换,在情景运动的时间过程中乡思之悲已淡化而为欣悦;尾联追思梦境,家园感定格在“凫雁满回塘”这一亲切温馨的特定空间中。又如《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第一句面对时间迁逝、归期不定的无奈产生家园失落感,接着凝入“巴山夜雨”的山水空间中;第三句是审美主体的心理时间指向未来以祈想家园感,仍以“巴山夜雨”这一特定空间加以收摄,空间的重叠造成时间的回环,迁逝感便不是把握不住,而是在这个经过充分情感体验而突出的山水意象中找到了家园的一丝暖意。人与宇宙自然亲合的心理使这种化时间为空间的审美转换,常落脚为具体实在的山水情境,如停车驻马、夜泊阻风途中的寓目之景,也形成相当集中典型的山水意象群,如烟江落木、秋风雁阵、明月孤帆,等等,构成了羁旅山水中的一种审美定式。反之,如果空间无法作为时间的归宿,即迁逝感未能转入环闭可感的空间中获得消释,士人就会在时空疏离中无所着落,或在时空无限中感受到自身的渺小而陷入价值虚空,人生如孤舟飘荡,临水茫茫,这样就回到第一点所归纳的情形了。从诗词内部的时空因素来分析山水审美与家园感呈现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来领略羁旅山水所包蕴的文化信息和审美特征。
“一切人生的不能在其自己,都是生命的漂泊。生命的漂泊的诗意,就在于它是与生命的安顿一体而两面的”[28]。中国山水诗始终有乡愁这一文化底色,它又与羁旅行役有共同的精神源头。乡愁的诗意,即在生命漂泊与安顿的体味中积淀出深沉丰富的人生之情,家园感说到底就是此种人生之情的实有感和着落感,代表着中国人立足现实不忧不惧的乐感态度。山水则充当了有情的媒介,既与人有着生命的共感交流,又启示着在体认天道中追求天人合一,实现超越。相比之下,佳人意象更多体现着在伦理温情中寻求家园安慰,其中仍有政治祈求与感性欲念相缠杂的复杂内涵,这须另撰一文加以讨论了。
[1]王贵元.说文解字校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78.
[2]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53.
[3]孔颖达.周易正义[M]∥李学勤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李善等.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9.
[5]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
[6]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6.
[7]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91.
[8]冷成金.唐诗宋词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9]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0]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19.
[11]王夫之.古诗评选[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23.
[12]赵昌平.赵昌平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05.
[13]胡晓明.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7.
[14]安磐.颐山诗话[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2册.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463.
[15]程磊.山水诗中审美主体自我呈现方式的变迁[J].云南社会科学,2010(6):158-160.
[16]黄叔灿.唐诗笺注[M]∥陈铁民.王维孟浩然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217.
[17]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M].北京:中华书局,2010:52.
[18]黄节.汉魏乐府风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256.
[19]唐汝询.唐诗解[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842.
[20]王尧衢.唐诗合解笺注[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305.
[21]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2]王夫之.唐诗评选[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03.
[2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9.
[24]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11.
[25]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3.
[26]冷成金.论化时间为空间的诗词之美[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42-143.
[27]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654.
[28]胡晓明.文化的认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