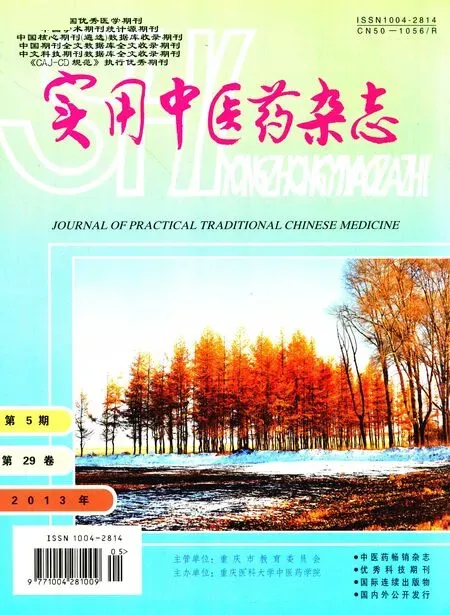缺血性中风中医治疗进展
穆珍珍
(广西中医药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广西 南宁530001)
缺血性中风是指由于脑供血障碍引起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发生坏死、软化形成梗死的脑血管疾病,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偏瘫和意识障碍,约占中风的60%~80%[1]。现将中医治疗缺血性中风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内经》中虽无“中风”的病名,但类似中风病证的记载较多,如卒中昏迷期归为“仆击”“大厥”“薄厥”等,半身不遂归为“偏风”、“偏枯”等[2]。关于“中风”病机分析,在唐宋以前多从“外风”立论,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风历竹病脉证并治》篇首次提出“中风”病名并加以专篇论述。巢元方、严用和、陈无择等均在其著作中就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详细论述。金元时期,各医家据临证体会对中风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3]。明清阶段,出现百家争鸣现象,各持己见,如张景岳认为中风与外邪无关,其主要病机为“内伤积损”,叶天士倡导“阳化风动”说,认为中风为本虚标实之证,王清任就中风病机提出了“气虚血瘀”新理论,并据此创制补阳还五汤。
现代医家综合各家学说,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如赵孔华等[4]认为,缺血性脑中风病理基础以痰瘀为主,脏虚为本,痰瘀为标。严浩成等[5]认为肾气虚弱,元气不足,五脏之气化乏源,可致气虚无力行血而瘀阻。陶根鱼等[6]认为气虚血瘀是缺血性中风发病的基本病理因素。朱天民等[7]认为正气耗损,脑脉闭阻是脑梗塞的病理环节。韩萍等[8]认为血浊是缺血性中风发病的初始病理产物,易上袭脑神,伤及五脏。其中最为标新立异的是王永炎院士针对中风病提出了“毒损脑络”病机假说,认为中风发病是由于毒邪损伤脑络,络脉破损,或络脉拘挛瘀闭,气血渗灌失常,致脑神失养,神机失守,形成神昏闭厥、半身不遂的病理状态[9]。
2 辨证论治
活血化瘀法。陈雨恒[10]采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缺血性中风68例效果满意。王建新等[11]根据临床治疗经验,提出中风病本质为血瘀,治疗以祛瘀为要,活血化瘀法贯穿于治疗的始终。王志欣等[12]也强调了缺血性中风治疗要重视活血化瘀法的运用。
化痰祛瘀法。痰瘀同源,痰浊可致瘀血,瘀血停留可生痰湿,应用化痰祛瘀法对提高缺血性中风患者的临床疗效至关重要[13]。李玉芳等[14]以化痰祛瘀为治法自拟开窍化痰通瘀方(麝香、冰片、石菖蒲、郁金、水蛭、地龙、川芎、人参、胆南星、三七)治疗脑梗死217例,总有效率94.01%。李京等[15]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化痰祛瘀汤可显著改善脑梗死急性期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明显提高t-PA水平,降低PAI水平,降低脑损伤,起到脑保护作用,从而改善神经功能缺损,促进机体的恢复。
益气活血法。雷鹏等[16]用蛭蛇通栓胶囊治疗缺血性中风病(气虚血瘀证)疗效肯定。更有许多学者宗王清任气虚血瘀是中风重要病机,认为气虚是本病之本,血瘀乃本病发生发展的核心,而在治疗中采用益气活血法治疗,选方多用补阳还五汤或自拟益气活血方。张德景[17]将102例随机分为治疗组72例及对照组30例,分别采用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和维脑路通治疗,结果总显效率治疗组70.83%、对照组44.33%(P<0.05),总有效率治疗组94.44%、对照组76.67%(P<0.05)。
补肾益气法。武继涛[18]认为补肾益气法是缺血性中风的基本治法。补肾方药可使脑髓得充,气旺血生,可扶正温阳,振奋阳气,促进肺、脾、肾三脏功能恢复,气化复常,痰饮自消,并促进血液流通,使脑部的局部循环得到改善。张树泉等[19]以补肾活血为治法,用补肾活血方(制何首乌、山萸肉、炒山药、麦冬、肉苁蓉、石斛、五味子、当归、川芎、地龙、石菖蒲、郁金、茯苓、炙甘草),并用大鼠脑缺血模型进行研究,证明该方能明显降低大鼠缺血边缘区神经细胞的凋亡数目,有良好的抗凋亡作用。
清热解毒法。王永炎院士提出了“毒损脑络”的病机学说,认为痰瘀互结,蕴结于脑,化生内毒,损伤脑络[20]。因其引起的临床症状多呈一派火热之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热毒是中风发病的关键因素。李继英等[21]认为脑血管内血栓形成属于中医有形之瘀血,同时全身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属于无形之瘀血,故清化血分瘀热是缺血性中风急性期主要治法。
3 中成药治疗
中成药能从对抗氧化、细胞凋亡、血管损伤及脑细胞水肿与坏死等多方面改善缺血再灌注造成的脑组织损伤[22],从而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
血塞通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是由中药三七提取的有效成分三七皂甙精制而成。药理研究表明,三七皂甙能够抑制血小板黏附和聚集,降低血黏度,促进瘀血消散,对急性缺血后的脑细胞有保护作用,还能够促进巨噬细胞吞噬作用,消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等。郭泽云等[23]通过脑缺血再灌注模型,检测血塞通对沙土鼠脑组织钙、水含量的影响,以及对海马CA1区神经元迟发性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提示血塞通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灯盏花素注射液。灯盏花生药及其制剂的主要药理作用是改善微循环,降低血液黏度,抗血栓形成等。胡志祥[24]报道用灯盏花注射液治疗老年动脉硬化脑梗死32例,对照组31例用低分子右旋糖酐500mL,两组总有效率分别为87.5%、64.5%;血小板聚集率及三酰甘油组均明显下降(P<0.01与P<0.05),全血及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纤维蛋白原、总胆固醇各项指标,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
川芎嗪注射液。王芳[25]利用大鼠脑血栓栓塞模型进行动态实验,发现正常大鼠血浆溶血磷脂酸(lysophosphatidic,LPA)的水平较低,脑血栓形成后,血浆LPA显著升高,6h达高峰,是对照组的3.1倍。川芎嗪可降低LPA,其机制可能与其抗血小板聚集作用有关。
此外,黄立武等[26]观察疏血通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结果疏血组与依达组显效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但二者与疏依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3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治疗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低于治疗前。治疗后3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提示疏血通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满意。
4 其它治疗
针灸疗法。石学敏等[27]认为中风的病机是“窍闭神匿,神不导气”以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3207例不同病理阶段中风者。主穴取内关、人中、三阴交,辅穴取极泉、委中、尺泽。吞咽障碍加风池、翳风、完骨,手指握固加合谷,语言不利加金津、玉液放血。每日针刺2次,10天为一疗程,治疗3~5个疗程。结果首次发病组总有效率98.97%;多次发病组总有效率96.64%,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吴伟凡等[28]采用祛风醒脑针刺法(主穴取百会、风池、风府、合谷、太冲,气血不足者加足三里、血海,阴虚阳亢者加太溪、三阴交,风痰阻络者加丰隆、阴陵泉。得气后留针30min,1日1次,连续治疗4周)治疗中风先兆证60例,与对照组60例(口服肠溶阿司匹林片,每次0.3g,饭后30min服用,1日1次)比较,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与血浆内皮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联、血浆一氧化氮含量及血液流变学指标改善均优于对照组。
5 小 结
中医治疗缺血性中风有独特的优势,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辨证缺乏一定的规范性、疗效重复性差、样本量偏小等。因此,应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规范化诊断、疗效标准。使中医于治疗缺血性中风有更好疗效。
[1]Fergu son A,Sircus W,Eastw ood MA.Frequency of function algas trointestinal disorders[J].Lancet,1977,2:613-614.
[2]胡翠平,鲍远程,韩辉.缺血性脑卒中中医研究进展[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0,22(11):1021-1023.
[3]续洁琨,赵琰,屈会化,等.中医药防治缺血性中风临床及实验研究进展[A].现代化中药制剂发展与中药药理学研究交流会论文集[C].2009.
[4]赵孔华,张沁园.缺血性脑中风的发病机理探讨[J].河南中医,2006,26(7):7.
[5]严浩成,李国青,王行宽.补肾益气活血法治疗缺血性中风的研究概况[J].新中医,2005,37(2):89.
[6]陶根鱼,杜晓泉.益气活血法在缺血性中风病中的地位[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8,21(3):5.
[7]朱天民,孙宏.中西医结合治疗脑梗塞的思路和方法[J].中医杂志,2004,45(5):3.
[8]韩萍,周永红,王新陆.缺血性中风从血浊论治[J].新中医,2008,40(9):1.
[9]李澎涛,王永炎,黄启福.毒损脑络病机假说的形成及其理论与实践意义[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24(1):1-7.
[10]陈雨恒.活血化瘀治疗缺血性中风68例[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1993,13(10):631.
[11]王建新,刘芳,魏稼.中风之本与活血化瘀之用[J].江西中医药,1995,26(4):17-18.
[12]王志欣,王群.缺血性中风活血化瘀治疗及研究进展[J].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1994,7(11):677-678.
[13]鲁启洪,刘红艳,韩忠顾,等.缺血性中风的中医药疗法[J].中医药学刊,2006,24(8):1534-1537.
[14]李玉芳,陈立平,范玲.开窍化痰通瘀法治疗脑梗死的临床观察[J].中华医学实践杂志,2007,6(1):41-42.
[15]李京,曹锐,胡文忠,等.化痰祛瘀汤对脑梗死急性期组织型纤溶酶元激活物及其抑制物影响的临床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7,14(6):333-336.
[16]雷鹏,吉海旺,罗强,等.蛭蛇通栓胶囊治疗缺血性中风病(气虚血瘀证)临床研究[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30(5):30-31.
[17]张德景.益气活血通络法治疗脑梗塞72例疗效观察[J].中医研究,1996,9(3):19.
[18]武继涛.从肾虚论治缺血性中风[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5(3):223-224.
[19]张树泉,徐西元.补肾活血化痰方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5,3(6):515-516.
[20]常富业,王永炎.中风病毒邪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7(1):3-6.
[21]李继英,汪琴,彭宇竹,等.脉络宁注射液和复方丹参注射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疗效观察[J].中西医结合临床急救,1998,5(8):345-348.
[22]张学艳.中药对脑缺血损伤时细胞凋亡相关基因调控的作用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07,13(2):145-147.
[23]郭泽云,武云平,李素华,等.血塞通注射液对沙土鼠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J].昆明医学院学报,1999,20(2):1-3.
[24]胡志祥.灯盏花注射液治疗老年动脉硬化性脑梗死32例[J].西北药学杂志,1999,14(2):71-72.
[25]王芳.川芎嗪对脑栓塞血浆,溶血磷脂酸水平的影响[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07,10(4):12-13.
[26]黄彬森,黄立武,林飞.疏血通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60例疗效观察[J].新中医,2009,11(41):23-25.
[27]石学敏.针刺治疗中风病的临床研究[J].上海针灸杂志,1992,11(4):4.
[28]吴伟凡,赵玉池,吴伟,等.针刺治疗中风先兆证的临床研究[J].湖北中医杂志,2006,28(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