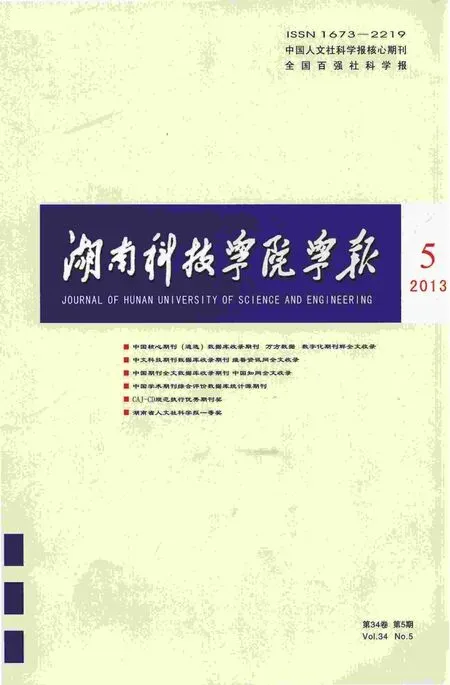论韩少功小说中的神秘倾向
王 蓉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综观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他在1985年集中推出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代表了他的创作向神秘风格靠近,尽管后来的《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显示了作者很强的理性思维,但不能掩盖理性思维下的神秘暗流。目前,国内外尚无研究韩少功小说神秘倾向的专论,与之相关的论述主要有三:一是从整体和源流上探讨20世纪神秘主义文学思潮的演变,或是关注与神秘主义文学有关的楚文化神话系统。谭桂林在论述80年代的神秘主义文学倾向时,着重提出了韩少功直接运用神秘意象来突出作品的中心题旨。[1]凌宇提到东方神秘主义——不可认知,只可感悟的“道”影响了韩少功的创作,韩的创作面对时空的辽阔和悠久呈现了无法破译的迷惘和痛苦,突出了幻想情绪,呈现出迷离浪漫神秘的风格。[2]二是从表现手法、思维模式、审美风格等方面分析了韩少功1985年以来的探索型小说。南帆敏锐地发现韩少功1985年后的创作中断和抛弃了以往作品的诗意,走向惊惧、猥琐与畸形,乐于制造异样的气氛,塑造了一批批畸形和猥琐的人物[3];汪政,晓华认为韩少功《爸爸爸》以来的作品运用神话模式和梦幻等非理性方式,吸取楚文化浪漫浓艳、神奇诡谲的美学风格,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4]。三是有关专著中部分章节探讨了韩少功创作的神秘倾向。如张学军在《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5]第七章“文化寻根派小说”中分析了民间文化和地域特色对寻根作家的影响,寻根作家表现出对神话传统和巫术文化的偏爱,造就了艺术世界的神秘感,而神秘作为审美范畴给人朦胧、含蓄、深邃的美学感受,韩少功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楚文化的流向,文学创作中表现了楚辞的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张学军系统研究文化寻根派小说,发现了韩少功创作神秘的审美风格,但不够深入和具体,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拟以神秘倾向为切入点,分析韩少功小说创作中的神秘倾向。
一 神、神秘主义与神秘倾向
在论述前,先看看神、神秘主义的含义。西周金文最早记载“神”字:“惟用绥神怀唬前文人。”[6]“神”字从“示”从“申”,“示”指祖先,“申”像“电”,指“闪电”。因此“神”字有两层涵义:一是初民将“闪电”等难以琢磨和解释的、神秘的,昭示大自然强大威力的现象,称为“神”,二是初民将保佑子孙的、能代为向主宰一切的“天帝”申言的故去祖先,也称为“神”。“神”与不可预测的神秘宇宙自然力量相联,更与象征生命延续、民族历史传承的人神相通的人的力量密切相关。“神”意味着伟大的生命力量,自古以来人对“神”就有着与生俱来的敬畏与崇敬之心,这是从“神”的原初意义来说的。刘勰将“神”引入文学,他认为神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文之思也,其神远矣”[7]、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等阐明了他认为的“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神秘主义”,《汉语大辞典》解释为“1.宗教唯心主义的一种世界观。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界直接交往,并从这种交往中去领悟宇宙的秘密;2.指文学艺术上的神秘主义,即强调表现个人难以捉摸的感受、幻想等。”[8]《20世纪英美文学辞典》解释为“Mysticism—神秘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神秘主义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中世纪宗教故事,或出自创作家的幻想,宣扬上帝、神性、宗教虔诚,在冥思中达到宗教的净化等等神秘观点,或者鄙视尘世,否定现实生活,追求寂静与空灵等宗教态度。”[9]神秘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鬼神信仰、万物有灵,与宗教渊源深厚,同时有着深厚的民间积淀,并反映到文学创作之中。
孔见指出:“对于‘神秘’一词的运用,韩少功颇为讲究而且别有用心,他认为神秘有两种:一种是把不可理喻的东西转变为常识可以理喻的,如把雷喻为雷公;另一种是把被理喻了的东西转变为不可理喻的或难以理喻的,把常识转化为奥秘。韩少功所感兴趣的正是最后一种。他认为人类是残疾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极为有限,他们的知识常常是把未能理解或未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加以武断的定义。这种肤浅做法的结果就是在常识下面渗漏了、遮蔽了大量未理解的深邃的东西,这就是神秘的所在。揭示这种神秘,破译感官未能感知的东西,便能促进人类知性的健全。”[10]韩少功在神秘思维的导向下,发掘了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湘西残存的原始或半原始的巫性文化,他谈及自己对巫楚文化的一种理解:“巫楚文化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以及东南亚的少数民族中间,历史上随着南方民族的屡屡战败,曾经被以孔孟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所吸收,又受其排斥,因此是一种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至今也没有典籍化和学者化,主要蓄藏于民间。这是一种半原始文化,宗教、哲学、科学、文艺还没有充分化,理性与非理性基本上混沌一体。”[1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强调的或者说感兴趣的乃是巫楚文化,对占统治地位的中原儒家文化的反拨。将这种“混沌一体”用文学创作来表现出来,必将生成其小说的神秘风格。
二 巫鬼气息、幽灵隐现下的神秘氛围
韩少功小说的神秘倾向建构在乡风民俗的整体性和人们精神气质的同构基础上,一方面他擅长风物地貌和习俗民情的细腻生动刻画,另一方面他对神秘因素的把握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民间文化的认同,对自然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的浅层次描绘上,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了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性格、精神和气质,展示了乡间各式人物富于神秘色彩的人生。
巫鬼气息的乡风民俗既是韩少功小说中神秘倾向的原因;反之,也是其重要表现。湖南地域历史上被称为荆蛮之地,高山阻隔,烟波浩渺,瘴疟丛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楚人“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12]。韩少功的小说扎根湘楚大地,偏爱选择乡村山寨作为故事的发生地,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呈现了各种原始的巫术和仪式场景,《爸爸爸》、《女女女》、《诱惑》等小说展示了一个个神秘怪诞,充满巫术文化的艺术世界。
《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坐落于大山里,“白云上,人们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你一走,前面的云就退,后面的云就跟,白茫茫的云海总是不远不近地团团围着你,留给你脚下一块永远也走不完的小孤岛”,但这里不是人间仙境,白云下的大山深处密林丛生,蛇虫瘴疟横行,腐臭黑汁肆虐,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野蛮的乡风民俗融为一体,形成了鸡头寨这个远离教化、远离文明,靠祖传习俗自在自为、自生自灭的生存场景,这里弥漫着贫困、荒诞、保守、肮脏、冷漠、残酷的气息,活脱脱一幅人间地狱般的画面。那里的人们不相信史官讲述的正史,而相信歌谣传唱的半巫半神、真假莫辨的历史,他们传唱祖先从姜凉唱到府生,火牛,优耐,刑天,刑天在东海边繁衍生息的后代,传说与现实在这里交融与互动,人类的源头及未来在歌谣中显得扑朔迷离,没有定论。他们祭神的传统源远流长,诸如祭祖先,祭谷神等,《爸爸爸》中丙崽本是用来祭谷神的,由于天公不作美,雷声阻止了大家的行为,从而演变成了一出闹剧。他们崇尚庄严的仪式,比如炸鸡头峰引起的“打冤”是典型的带有仪式性的场面:火光越烧越高。人圈子中央,临时砌了个高高的炉台,架着一口大铁锅。锅口太高,看不见,只听见里面沸腾着,有着咕咕嘟嘟的声音,腾腾热气,冲得屋梁上的蝙蝠四处乱窜。大人们都知道,那里煮了一头猪,还有冤家的一具尸体。一个汉子走上粗重的梯架,抄起长过扁担的大竹钎,往看不见的锅口里戳去,戳到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分发给男女老幼。人人都得吃但无须知道吃的是什么。不吃的话,就有人把你架到铁锅前跪下,用竹钎戳你的嘴。这种场面是何等动人心魄!这个“同仇敌忾,生死相托”的仪式,混合掺杂了民间的悲壮和残酷。它是不容冒犯的誓师,是一种旧式的崇高的正义的伸张;但它又是以一种残忍的形式出现,具有浓厚的狭隘的初民意识,它阻碍了鸡头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人们麻木不仁、年复一年的生活于此。还有诸如红白喜事的唱简、请巫师施法术、砍牛头预测胜负、集体服毒等奇特的习俗,似真似幻,怪异荒诞,颇见楚辞中特有的巫风气韵。《爸爸爸》隐去了鸡头寨具体存在的年代,鸡头寨的乡风民俗具有浓郁的原始初民气息,《归去来》、《女女女》、《诱惑》、《北门口预言》中则是现代的乡村景象。《归去来》黄治先返回的知青落户点有着崎岖蜿蜒的山路、烟熏火燎的炮楼、被雷劈的树木,保留着木桶洗澡的古老风俗,《女女女》中地震来袭、鼠疫横行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诱惑》里的鬼斧神工的自然山川对人的压迫感让人窒息,《北门口预言》中的北门口则始终萦绕着杀人的阴郁气氛。总之,小说中的自然景观与民风习俗都被赋予了象征功能,丰富和拓展了小说的内涵,为其叙事奠定了神秘色彩,体现了人类封闭却顽强、保守却执著、敬畏却始终无畏的神秘思维特点。
和重视巫鬼的乡风民俗相关的是,韩少功小说中“幽灵”忽隐忽现,活灵活现,更让小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牛津英语词典》给幽灵下的定义的第一和第四条分别是“作为生命原则的灵魂或精神”和“一个人物”。从这里看,幽灵与人有交叉点,幽灵是抽象的人,但是幽灵与人也有重要的差别。“但是更普遍的现代意义上的‘幽灵’包含了一种幽灵的观念,一种死者的幻影,一个从阴间归来的亡灵,死者回到某种幻象般的存在——一种不是活着但也没有完全、最终死去的实体。”[13]幽灵是介于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实体,打破了生者和死者的界限,生死不分的状态混淆视听,幽灵因此着上了神秘之色甚至让人产生恐惧之感。
《鼻血》讲述的是幽灵杨家二小姐陪伴公社火伕熊知仁的故事。实际上,作为电影演员的杨家二小姐生活在首都,演电影,也进过牛棚挨过批斗,但是在她家乡马坪寨的青砖楼里,活生生的杨二小姐化成幽灵时时出现在熊知仁的视听嗅觉范围内,成了熊知仁生活的支柱和理想中的结婚对象。作为先遣兵的熊知仁驻扎进青砖楼就闻到了香味,其他人如黄秘书等人却对香味无动于衷。闻香识女人,熊知仁在青砖楼的角角落落里找到了玻璃镜片、银簪子等女性用品,似乎听到了女人娇滴滴的嗯声,还有女人洗头泼水的声音,在无人进入的柴房里发现了一摊水渍印证了柴房里曾有人洗过头。种种蛛丝马迹让熊知仁胆战心惊,他隐隐的感觉到这屋子里有一个女人,但不能确定是谁。一张女人的照片,也就是杨二小姐的照片让熊知仁如梦初醒,开始了与杨二小姐幽灵共患难的日夜相处。照片里杨二小姐流泪时,熊知仁找到了症结,将杨的断臂粘到照片上,“杨小姐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润嘴角似藏蓄着感激的微笑”。有了杨小姐的陪伴,熊知仁注重个人卫生,一改往日的邋遢形象,也许,他期待着这位杨小姐成为他相伴一生的人。多年过去后,杨二小姐回到家乡路过熊知仁的小饭店,熊发现杨的肩胛处有一处两寸多长的疤痕,而这正是当年照片撕破的地方,熊知仁也突然感到一阵吐不过气来,现实离他很近,也离他很远,当年的杨二小姐已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杨小姐离去的背影意味着熊知仁青砖楼里的想像灰飞烟灭。杨二小姐的幽灵形象也从知仁的头脑里消失殆尽,他决定娶婆娘了。《山上的声音》中一位麻风患者救了岌岌可危即将落水的“我”,“我”千方百计地探寻发现这位麻风患者二老倌竟然已经去世十多年。“我”与村民修路搬迁二老倌的坟墓,在坟前的桐树旁发现了一根完整无损的红橘牌香烟,“我”清楚的记得香烟是为感谢二老倌的搭救而向他致谢的,“我”感到很茫然,香烟可能是陌生人无意遗落的,也有可能是幽灵二老倌的,因为“我”递给他的烟他没抽而是插进了衣袋。“我”的疑团的焦点在于二老倌是生还是死,哈佬确证二佬倌被“开款”(乡间刑罚),众目睽睽之下用火油烧死,“我”现实的遭际是二老倌把我从木头桥上拉上岸,这里,生与死的距离显然已模糊,“我”感觉到他是活生生的,以哈佬为代表的老一辈认为他已去世,双方在矛盾的拉锯中生出了神秘和恐惧之感。
三 各色人物呈现出来的神秘色彩
韩少功说:“人本身是很神秘的。人的神性是指一种无限性与永恒性。我想把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做一种沟通。我想重创一个世界。我写的虽然是回忆,但最能激动我的不是复制一个世界,而是创造建构一个世界。”[14]因为有了人与神沟通的理想,韩少功小说中的乡民都有向巫靠近的倾向,有知识有素养的知青在梦魇中在找寻真实的自我,多种畸形变异者退化到人的最初形态,人与灵之间混淆生与死的界限,各式人物都与正常人保持着距离,他们在自我的世界里演绎着神话与传奇。
有着神秘色彩的乡民是韩少功小说中神秘倾向的主要表现主体。巫是原始人沟通人与自然的使者,原始人通过巫认识自然、社会和自我。巫为众人祈福,人人都应膜拜和感谢神巫。巫作为凡人时在人们心目中是可亲可近的,而当巫行法术时,人们则对他充满了敬畏,如同敬畏神一样。韩少功笔下的乡民具有巫的特性,比如周老二、杨某具有特异功能,巫婆和巫师也是人们在科学无法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选择。
《北门口预言》中的屠夫周老二,操持一把拐子刀,拥有一手与众不同的杀人绝技。他的杀人方法被幻化,“他不用板刀而用拐子刀,刀口向外贴在手臂后,每次从死囚身后上去,横肘一抹,人头便滚落在地,动作轻捷而利落,旁人几乎来不及看清楚刀下奥秘。”“他还可以双刀斩双头,动作一次性完成,被称为左右开工,此绝技不轻易示人。”“一抹”与“双刀”的绝技在看不清楚与不轻易示人的描述下多了令人猜想的空间,周二究竟是怎样杀人的?他的杀人方法因此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神秘感。周二的行为处世以及现实遭际也有别于他人,他在杀人后提着拐子刀寒光一现,“见羊斩羊、见狗剁狗”,“揩刀肉”就此而成,谁也奈何不了他;他斩了王癞子,背上长了毒疔,半个镇子的人都可以听到他彻夜的嚎叫,众人都说他遭到了报应,因为王癞子是冤死的,报应说没有兑现,周老二的毒疔后来脓净封疤;周二到了牙齿掉光的年纪,“据说他看人还是职业性地往颈跟上看,说人还是职业性往颈根上说”,他根据颈根的粗细、厚薄预测某人的未来,甚至未曾与他谋面的人,也能描述其颈根的特点,比如他说邮电局彭家老三颈后边的肉足够有寸多厚,是能干大事的人,实际上他没见过彭家老三。与刽子手相对的是囚犯,囚犯也并非常人,演绎着各自的传奇。土匪头子烈性不改,临刑前骂骂咧咧,周老二“一抹”绝技也失去了威力,周老二砍他第一刀,他扬着脖子差点站起来,第二刀总算是把他脖子给砍了,但他的骂声仍然在继续,最后他仰面倒下颈腔喷溅的血浇了周老二一身,土匪头子的匪气和霸气令人惊悚之余,一股神秘之感随之扑面而来。《史遗三录》其中一录写猎户杨某,其人长相奇怪,错杂黄牙暴露于唇圈,唇圈永难围合,年过六旬身体硬朗,常赤足行于村路。他是猎人,又比一般猎人技高一筹,他见迹捕猎物,看到虎粪即能推测老虎的出没时间和轨迹,随后安装虎夹即可捕获老虎。杨某有如此的洞察力,他的铁铳亦有神灵,比如门外有野物,铁铳就会躁动不安,等待主人立即行动去捕杀猎物。杨某通医道,能治蛇伤,如果他连呼三声伤者姓名,伤者能答应则能治好。杨某的特殊才能还在于有别于同乡人的思维,如他对被誉为乡村神童的小孩的评价就与众不同,别人认为此小孩将来必成大器,而他则预测这小孩将来会坐班房,似乎印证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古话;他坚持认定贪污的会计不应受罚,让他继续从事会计工作,原因是会计已收了两房儿媳,儿子带了手表去县城做事,冤枉已经吃了七八成,贪欲不会再膨胀,而再选新任会计会更多地吃冤枉,众人幡然醒悟,会计被留任。韩少功小说中出现的专门从事巫术的乡间巫婆和巫师,堪称是对湘楚文化遗留的保存,也是作者沟通人与神的表现形式。比如《老梦》中请民间享有盛誉的巫婆三阿婆照油碗。场长在饭碗连续失窃后不得不请三阿婆照油碗查出窃贼,三阿婆在场长房里神秘地施巫术个把时辰,成效虽然不大,却反映了人们在科学无法查明真凶的情况下,潜意识里是重视和信赖巫术的。德龙也许是《爸爸爸》里可有可无的人物,因为作者没有对他进行正面描述,只是着重叙说了他唱简的历史。但他作为山寨中有着特异功能与先天预知能力的神巫,预感到在外来文化冲击下鸡头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没落的命运,他信赖的庄严厚重之感的牧歌式的人文环境终将消失殆尽。于是,他选择了没有任何理由的出走,不管他的出走是否成功,他是否寻找到了人类别处的美好家园,他没有将生命毫无意义地消耗在死气沉沉的鸡头寨,这是他的高明和有远见之处,而巫对现实的超常感知能力和对未来动向的把握是他做出出走决定的重要因素。
迷失自我的返乡知青是韩少功小说中体现神秘倾向的另一类重要群体。知青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插队的乡村,他们返回城市再次回乡,试图找寻过去的自己,但这种找寻是徒然无力的,比如黄治先(《归去来》)、福生(《余烬》),他们往往分不清现实与往事,迷失在他人或自己营造的不可解释的漩涡中,甚至失去和消解了自我。
《归去来》中的知青黄治先迷失在插队的村寨里,也迷失在“我是谁”的困境中。黄治先来到小村寨,他陷入了现实与记忆的谜团。他眼前的景物似曾相识,土路凹凸不平,山民的房子一户挨着一户,窗户开得高且小用来防盗贼,泡在水潭的小牛长着苍老的皱纹,甚至被雷劈过的空心老树依然挺立,这些都是现实中的镜像,不时闪现于他的记忆,冲击他的头脑,“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神经病,脑子还管用。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听朋友们谈过?或是在梦中……我慌慌地回忆着。”种种的不确定缠绕着黄治先,他在迷惑、挣扎中走向更大的神秘漩涡。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村民,村民都一致认定黄治先就是十年前在此插队的知青马眼镜,将黄治先带进了十年前的语境。村民与黄治先聊着往事,据说黄曾经当过民师,曾与村民一起修路,村民更感兴趣的是曾经与马眼镜一起插队知青的去向,黄治先在村民的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变得意志脆弱,半推半就中他试着走进马眼镜的世界,说谎与圆谎的对话中,黄受到良心的谴责,最后在“行不得也哥哥”的鸟叫声中,逃离了村寨,但他不能逃离心魔,他究竟是黄治先还是马眼镜?回到旅社,他打电话给朋友确认自己的身份,朋友的肯定没有消除他的疑虑,而是加重了他的负担,他不停地对自己的身份发出疑问?“我累了,妈妈”作为小说的结尾,意味着黄治先没有找出“我是谁”的准确答案。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笼上了一层神秘之感。黄治先的回访过程实际上是自我的追寻与确认过程,在故地,我无意间遭遇到一些似能确证“我”的人证物证,似曾相识却又无法确信,最终拼凑出来的是一个面目模糊的“我”。《余烬》里的知青福生插队时上山背竹子,晚上曾经到一窑洞躲雨,一陌生妇女找到他,请求他写一张条子借用他的汽车送她的女儿——即将生产的妇女去医院,实际上,福生当时只是知青,汽车对他来说太遥不可及,无奈下他写了条子给这位妇女,也没记住这段插曲,只是对躲雨时大家共同喝过的汤念念不忘。若干年后,福生已是银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前往山里考察矿泉水项目。被虱子折腾的他想半夜逃回城里,却被告知车已被借走,他觉得不可思议,白天根本没有写条子借车给任何人,而周科长拿出的条子显示签名是他的笔迹,只是有点模糊。这张条子引发了福生的联想,他的记忆追溯到了知青时代扛竹子的那天。为了解除现实与记忆的迷惑,他走出旅馆,寻找曾经写纸条的地点——窑洞。他如愿找到了窑洞,里面架着一口锅,锅里残留的白菜汤冒着热气,显然此处有人来过,他依稀记起过桥时似乎有五个人从山坡上走下去,但他没有勇气追寻这些人,这一切似乎让他又闻到当年的气息,同样的是五人背竹子,同样的是煮着白菜的锅,难道是巧合?福生经历了一次神奇之旅。过往之事今日重现,一张曾经写过的条子救了今日一位难产妇女的性命,福生迷失在此次返乡之旅中。《归去来》、《余烬》两作品有意打破人和现实、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同一状态,摒弃那种简单化的、直线式的描摹生活的方法,而付之以浓郁的情感,包孕以复杂的意味,显示出复杂生活的途径,给予我们迥异于那种单纯的审美冲动。这种有意的错位和背离,如同一幅意境深远的泼墨画,托情于幽邃深渺之中,引起我们求索的好奇心,从而把更宽阔的思索留给大家。
变化莫测的畸形变异者是韩少功小说中神秘倾向的另一重要表现群体。韩少功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与人类相异的畸形变异者,他们外貌奇特,甚至正常人也逐步退化为猴、熊等动物的模样,他们的思维简单,呈模糊混沌状态,他们的行为越出常轨,愚昧无知,横蛮不讲理。可以说,变异者是熟悉的事物陌生化,从内到外对人类的颠覆中让人生出神秘之感。
丙崽“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丙崽与众不同的出生方式注定了他是畸形变异者。七八年后,“他还是只能说这两句话,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很多年过去后,“丙崽还是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档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了好几年,但他的相明显地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丙崽是一个长相丑陋的侏儒,身高永远是孩童的身高,智商也停留在孩童阶段,永远只会说“爸爸”和“×妈妈”两句话表达高兴与愤怒之情。丙崽娘为何会生下这么一个变异者?是因为丙崽娘在灶房码柴时弄死了一只蜘蛛,据说“蜘蛛绿眼赤身,有瓦罐大,织的网如一匹布,拿到火塘里一烧,臭满一山,三日不绝。”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丙崽娘触犯了蜘蛛精,也就是冒犯了神明,因果报应降临于她儿子丙崽,这种简单的因果思维使丙崽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再看丙崽历经的两次劫难,都是化险为夷。第一次要拿丙崽的头祭谷神,因为他是一个废物,正要行刑时,天上轰轰的雷声救了丙崽一命,大家认为神对这个瘦瘪瘪的祭品不满而放了丙崽;第二次是丙崽服了毒汁后仍旧顽强地活下来,连头上的脓疮也褪红结壳,而服毒的众山民已化成断魂鬼。不言而喻,丙崽顽强的生命力往往是神的护佑,神谕的指示换来了丙崽不死之身。丙崽是畸形的变异者,鸡头寨的人大多如此。无论丙崽是卜卦时的神谕还是可怜的出气筒,他的精神畸变恰恰暗示了鸡头寨人另一种意义上的精神畸变。丙崽和他的乡亲们,思想和行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他们对世界显露出冷淡、陌生的面孔,现实世界最终也将他们无情地抛弃。丙崽生下来就是变异者,《女女女》中的幺姑,《人迹》中的大脑壳,却是经历曲折后变异,幺姑变成猴后又变得像鱼,大脑壳则变成了熊罴。幺姑中风后送到乡下,性格一改往日的勤劳善良和任劳任怨,变得乖张敏感不可理喻,与中风前判若两人。中风前她处处为他人着想,力行节约,是一位典型的奉献者;中风后,她处处给珍姑一家造成麻烦,变得自私贪婪,转变成一位索取者,似乎将过去的种种委屈和牢骚全部发泄出来,这是幺姑心性上的大转变,她歇斯底里的刁难和捉弄之态,看上去信佛实际上成了一个顽劣的痴童。珍姑一家在万般无奈之下,打造了一个笼子将她关起来,这也成了幺姑由人变猴变鱼的转折点,她的外貌之变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幺姑住进笼子后,“听老大老二说过:她后来简直神了,不怕饿也不怕冷,冬天里不着棉袄,光着四肢在笼子里爬来爬去,巴掌比后生们的手还更为暖乎一些。”后来,她的皮肤变硬变粗,鼻孔向外扩张,人中拉得很长很长,人们觉得她变回人类始祖猿猴的样子,更惊奇的是,她的身体不断萎缩,只剩下光溜溜的身子和一双眼皮松泡的呆呆双眼,神似水中无精打采的鱼类,幺姑也彻底由人变物。
总之,韩少功小说神秘倾向的确立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拓了属于个人的小说独特的审美境界,标志着他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标志着他创作上的成熟,另一方面也给他的小说带来为神秘而神秘的倾向,有些篇目让人不乏晦涩之感,对读者的顺利阅读设置了很大的障碍,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者更深入、更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梦案》、《暂行条例》、《很久以后》大量运用梦境、幻觉拼接画面,造成小说为形式而神秘的空洞感,丧失了《爸爸爸》等作品所具有的厚重感。当然,韩少功小说的神秘倾向给读者阅读带来了想像和思考的空间,“神秘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它能给人一种朦胧、含蓄、深邃的美学感受。”[5]读者出没于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之间,体会韩少功小说的神秘魅力,所获得的是一种语言过于直白、主题过于单一的文学所无法提供的审美经验。
[1]谭桂林.从脱魅到迷魅——20c中国神秘主义文学思潮的演变[J].社会科学辑刊,1994,(4).
[2]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J].上海文学,1986,(6).
[3]南帆.历史的警觉——读韩少功一九八五年之后作品[J].当代作家评论,1994,(6).
[4]汪政,晓华.神话 梦幻 楚文化[J].萌芽,1988,(2).
[5]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6]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78.
[7]李叔琳.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Z].北京:中华书局,2000:369.
[8]汉语大辞典[Z].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873.
[9]20世纪英美文学辞典[Z].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10]孔见.韩少功评传[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88.
[11]韩少功,夏云.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J].钟山,1987,(5).
[12]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2.
[13][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8.
[14]韩少功,李少君.词语与世界——关于《马桥词典》的谈话及其他[J].小说选刊,1996,(7).
——《革命后记》初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