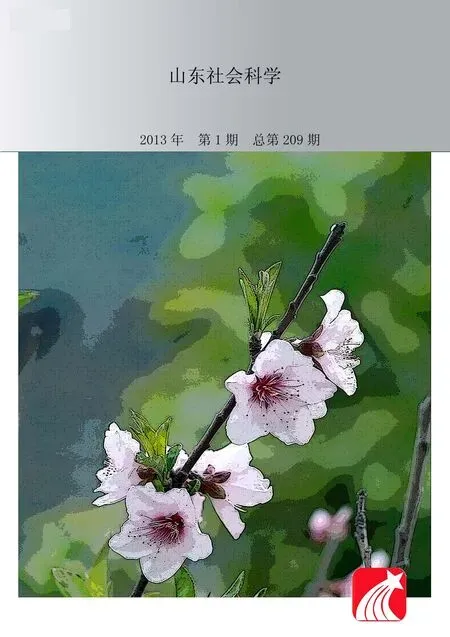启蒙、革命与女性
——以20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为例
李 静
(江苏省社科联,江苏 南京 210004)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人”的发现和拯救带动了对女性的发现和拯救,女性作为大写的“人”进入了启蒙作家的视野。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女性乡土小说自然延袭了启蒙的视角。女性作家以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为武器,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审视着充满愚昧、陋习的封闭的乡土中国。陈衡哲的《巫峡里的一个女子》,冰心的《冬儿姑娘》、《张嫂》,冯铿的《月下》、《一个可怜的女子》,苏雪林的《童养媳》,罗淑的《生人妻》,萧红的《王阿嫂》等小说均反映了生活在乡村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悲苦命运;而冯沅君的《贞妇》,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则主要通过乡村女性的不幸,刻画出了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注《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对乡土文化的历史惰性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一
20世纪女性作家创作的乡土作品中,真正能继承鲁迅所倡导的文学启蒙精神,并以女性眼光为描述视角的乡土创作首推萧红的小说。
“国民性改造”思想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从20年代乡土小说诞生起,想象乡村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就几乎承担了旧文明所有的黑暗面,农民身上积存了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从闭塞、落后的东北小镇“逃离”出来的萧红,犹如五四时代叛逃家庭的娜拉,很容易就接受了新文化带来的新思想,接受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精神。当她拿起笔,冷静地面对遥远的家乡时,启蒙视角就成为她小说创作的切入点和关注乡村的思想立场。
启蒙是萧红作品的思想底色,萧红作品的启蒙立场主要表现在对乡土愚昧、落后、野蛮现象的理性审视及其对乡土生活本质的洞察和揭示上。在这冷静审视和洞察的目光背后,隐藏的依然是知识分子“兼济天下”、拯救苍生的忧患意识,依然是寻找救国救民新生之路的家国想象。《生死场》中那一批贫穷、无知、受苦受难的女性形象,《呼兰河传》中那一群愚昧、落后、迷信、冷酷的女性群体,是作家站在启蒙立场对乡村历史、乡村文化,对国民灵魂的深刻拷问。
如果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仅仅是这些内容,那它们未必就能成为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凭借着作家对乡土世界的了解和对故乡人事的熟悉,作家以其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受,将启蒙叙事和女性叙事糅为一体,写出了中国乡土原始的、真实的生存状态,体现出一种女性切身的身体关怀和自我文化想象。萧红在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里就写到了乡村女性的生育和死亡,女性为了履行生育的天职而痛苦。她写那个死了丈夫的王阿嫂挺着大肚子去给地主干活,但因为地主的一脚而导致流产。王阿嫂倒在血泊之中,而小动物一样的小生命不久也死去。她的《生死场》,更是通过女性的生育、身体残缺、死亡、病痛,刻画了女性悲惨的命运。金枝对怀孕极度恐惧,女儿生下来一个月就被活活摔死,金枝在哈尔滨遭男人的性侵犯;五姑娘姐姐难产仍被丈夫虐待,孩子生下来就死掉,产妇横在血泊中;月英不幸瘫痪在床,做丈夫的不理不睬,最后活活腐烂而死。
当国家、民族的灾难降临在“生死场”之前,“生死场”里充斥着各种被生殖、疾病和男性虐待折磨得千孔百疮的女性的身体;而在灾难来临之后,在男女两性共同的家园认同和民族认同之中,仍然存在着无法掩盖的性别压迫和剥削。“女性的身体在萧红这篇小说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由于它的存在,‘生’和‘死’的意义因此被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之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生’,在女人的世界里指生育,它所引发的形象是肢体迸裂,血肉模糊的母体;‘死’也指向一个与之相关的血淋淋的现实,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肉体的变质和毁形,而绝无所谓灵魂的超拔。”[注]刘禾:《重返〈生死场〉:妇女与民族国家》,载《性别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1页。
由生育以及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揭示了乡村女性真实而苦难的生存悲境。女性的身体在萧红的作品中不仅是生和死的场所,而且还是小说获得其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
可以说,在萧红的乡土小说中,启蒙视角和女性视角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女性,萧红把自己所有的生命感受和生活经验毫无保留地、赤裸裸地写给大家看,在揭露乡土历史文化惰性的同时,提供了由女性书写的乡村历史,凸显了女性被遮蔽的性别表达、被忽略的性别牺牲。这样的叙事溢出了主流叙事的框架,对当时已经融入宏大叙事的乡土创作而言,是一种可贵的丰富和深化,也提供了文本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二
女性作家的启蒙意识是伴随着她们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责任不断强化的。由于乡土作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国民性”批判和“思想启蒙”成为她们共同认可的集体话语,因此当她们在启蒙的视野下倡导女性解放、个性解放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具有女性色彩的形式上的个人话语其实已经隐含着集体话语的指向,而且潜在内容上的群体性也使形式上的个人话语日益不可能。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救亡图存和社会革命的双重任务从本质上规定了乡土小说整体叙事方式的改变,现代个人叙事逐渐退隐,民族的、国家的集体话语全面登场。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下,女性写作消融在战争与革命的叙事主流之中,女性的性别意识、个体意识被遮蔽、被掩盖,但也并非完全消逝。
这期间,女作家丁玲的生活和创作选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丁玲现象’是女性意识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从个人到政治化的一个典型。”[注]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丁玲是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作家,在她20世纪20年代的创作中,充满了“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呐喊和以启蒙精神观照现实的理性力量,她的处女作《梦珂》以及其后发表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女性承受的各种压力,揭示了在以“现代文明”、“男女平等”等著称于世的大革命中,女性仍处于被观赏、被玩弄、被损害的不平等地位。她的乡土题材小说《阿毛姑娘》,通过对乡下姑娘阿毛悲惨命运的描述,既显示了乡村女性朦胧的、正在觉醒的性别意识和爱情意识,也揭示了这种主体意识的朦胧觉醒在那样封闭、落后的生存环境中带给阿毛的只能是悲惨的结局。乡村女性在文学作品中一般是个被动的存在,她在早已被规定好的位置上生存——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公婆的媳妇、生儿育女的工具,从未想到过也没有权力去表达内心的愿望。久而久之,她们便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任凭命运的激流将自己冲来冲去。但阿毛出现了,她在沉默与静寂的乡村女性群体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其“不正常”的行为显示了“合理”生活的不合理之处。阿毛姑娘的悲哀便在于她做了“铁屋子”当中最早清醒过来的乡村女性,她拥有冲出“铁屋子”的朦胧期待,却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式,最后只能在心力交瘁、悲伤绝望中走向死亡。
小说显示了丁玲走进乡村女性心灵深处的创作实绩,通过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描写了女性从“人”的觉醒到女人的觉醒,真正从启蒙视角入手,完成了“女性解放”的初步探索。
丁玲2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奠定了丁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可惜的是,1930年以后,丁玲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作品主要以社会革命题材为主了。不是说丁玲这以后的作品中再也没有女性形象、女性意识了,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意识在丁玲作品中消隐了,女性的自我审视和话语主体地位被置换了。重新解读丁玲的那些“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也许作家的本意是要让那些无路可走的“莎菲们”在黑暗中杀出一条生路,于是她让笔下的人物像美琳、丽嘉等有了“革命意识”、“社会意识”,美琳成了冲出“新家庭”的娜拉,走上了革命之途;丽嘉在韦护出走后也表示要走韦护所走的路,努力去“做点事情”。这些作品依然以女性形象为主,可是作家却在不自觉中放弃了其女性题材创作中最可贵的东西:放弃了对女性正常欲望、情感、意志的理性关注和思考,放弃了女性的独立身份意识和自我意识。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形看,丁玲和她笔下人物的选择并没有错,比起那些自甘堕落、迷失在肉欲社会中的女性,比起那些成为小市民、碌碌无为的“太太们”来,丁玲和她笔下人物的选择要有意义得多、高尚得多,但可惜的是,几代女性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换来的女性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丁玲的手中得到了延续、拓展后又在丁玲手中消失了。
毋庸置疑,丁玲放弃女性意识并不是有意的自觉行为,而且在她的主观愿望上正是为了拯救女性。因为女性的力量太弱小了,她们无力凭借自己的力量开拓一条新路,于是,丁玲让她们放弃了莎菲式的个人反抗,而投入了集体反抗的革命潮流。如果说,启蒙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共同之处在于作家对中国国体及国民“疾病”的“内在焦虑”,这种现代性的焦虑使他们渴望寻求一种宏大的集体话语,以一种普遍性的共同理念来向疾病沉重的国体施救;而不同之处在于,以鲁迅为首的启蒙文学重在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因而虽然存在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的可能,但这种精神诉求触及国民“沉睡”的灵魂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因此也内含着人性的复苏、个性的解放等思想要求,因此也兼容具有女性色彩的个性话语。而革命叙事话语则重在追求现代国家的激进的社会行为需求,重在追求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因而最终因为空洞的说教和宣传而丧失了其文学品质,与文学渐行渐远。
正因为丁玲并非主动放弃对女性人生的关注,因此在她4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再一次出现了她在2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中呈现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来自启蒙思想的理性批判力量。可以归为乡土小说一类的主要代表作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
从启蒙的角度看,贞贞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自由、敢于反叛封建家庭的年轻女性。她喜欢同村男青年夏大宝,家里人却非要她嫁给米铺小老板做填房,她愤而跑去天主教堂做“姑姑”,坚决反抗父母的包办婚姻。在20世纪40年代的敌占区,乡村女性想要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由仍然困难重重。不仅如此,乡村中仍然弥漫着封建的伦理贞操观和各种陈腐思想。由于贞贞的失贞和疾病,她在村民眼里成为淫荡和不祥的象征,许多人认为她“比破鞋还不如”,是没人要的“破铜烂铁”,“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在这里,作者的批判锋芒直指麻木、保守、愚昧的民众,继承了五四启蒙话语对国民性的探索和批判。贞贞没有屈服于日军的非人蹂躏,但却被封建小农意识汇集的无意识的“恶”压迫得无法生存。虽然这个坚强的乡村女子以洒脱、明朗、愉快的外部姿态回应村民们对她的不公和偏见,用不要人可怜的强硬姿态对抗悲惨的命运,但贞贞最后仍然选择了逃离,到延安去,开始新的生活。也许霞村的乡民们能够理解抗日的重要性、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但真的面对一个为抗战献身的女子他们仍然不能理解,而且给予责难和辱骂。作者安排贞贞去了延安,似乎贞贞从此以后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但从丁玲后来描写解放区的小说中可以想见,封建陈腐意识并非已在解放区销声匿迹,有时反而非常严重,贞贞的前景不容乐观。
从革命的角度看,贞贞是一个抗日英雄。她因逃婚落入鬼子之手,但又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抗日游击队传递情报。“我”对贞贞的高尚行为与牺牲精神深感敬佩,并以贞贞投奔延安完成了一个向理想人生迈进、不屈不挠的“革命”女战士形象的塑造。这是作者对其时革命叙事潮流的主动靠拢,希望能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探索女性的新的人生之路。但仔细阅读文本就可以发现这种革命叙事是不彻底的,因为作者也无法解释革命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小说肯定贞贞是源于一种宏大的政治神话,其思维逻辑较为简单,即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付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但实际上,丁玲无法圆满解释革命与贞节之间的悖论:一方面相对于崇高的革命利益,女性丧失贞节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她骨子里对女性心灵的惨痛创伤无法释怀,贞贞决定去延安学习以便“重新做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以往经历的忏悔和否定。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贞贞拥有自我尊严和社会价值,而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性别化的女人,贞贞是被人漠视和否定的,她的付出换回的只是偏见和冷漠。女性的个性价值与社会价值就这样产生了致命的悖离,而作者潜在的女性意识也就在这样的悖离中表现了出来。
贞贞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女性,她是因为追求爱情才落入鬼子之手,也就是说她走上“革命道路”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更多地,她是出于向日本人复仇的心态参加“革命”的。贞贞的遭遇让我们想起鲁迅《药》中的夏瑜。夏瑜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却反过来被民众施以冷眼、猜忌、误会和不理解,他的鲜血甚至成为治病的“药引”。贞贞还不是夏瑜那样成熟、理智的革命者,她对霞村人的行为同样不满、不理解。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民众不能理解革命者为此而付出的巨大牺牲,那么这场革命的意义究竟何在?既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它对民众的意义又何在,对女性的意义又何在?
《我在霞村的时候》涉及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题材,而事实上,像贞贞这类遭受身心创伤的乡村女性在当时的敌占区决不在少数,但出于种种禁忌,这些史实极少为人所知。丁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用小说的方式勇敢地表现了遭受战争凌辱的女性,并对落后陈腐的封建贞洁观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但从女性叙事的角度看,作者由最初关注女性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伤害而导入了符合革命话语要求的“走向新生”,实际上导致了女性话语的隐匿;而“革命”神圣的目标也使女性在“走向新生”时留下了明显的悬疑:如果不是为了“革命”,那么女性的失贞和被欺凌又将被如何看待呢?
作者在贞贞被日本人掳去后,加进了一个“后来是被自己人派去”的情节,被派去获取敌人的情报。这样贞贞就和千万个女性受辱者不一样了,也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组织的关心,奔赴延安。而在敌占区,单纯的女性受辱者占大多数,她们得不到任何同情与帮助,带着身心创伤艰难度日。“中国的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被侮辱的妇女不计其数,她们连同她们的苦难都湮没无闻,成为社会最为隐蔽的一个黑暗死角。”[注]王琳:《女性的隐遁与重现》,《当代文坛》2000年第1期。
三
1998年,年轻的女作家叶弥在《钟山》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在》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全金的乡村姑娘在抗战中的遭遇。全金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女,她16岁时因为抗日游击队队长的引诱,被动与他发生了关系。在一次与队长共度一宵回家的路上被鬼子捉住,受到强奸与折磨。她被放回来后,为了不让丑事外传,其父母和游击队队长一起替她编了一个谎言故事,全金由一个受害者被打扮成一个为游击队送弹药不幸被鬼子捉去,虽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的女英雄。村里人也都认可并荣耀她的英雄身份,甚至多年后有村庄要为她塑雕像。因为遭受过欺凌,全金的行为有时疯疯颠颠,甚至向人诉说被日本人强奸。他的父亲为保全全家,不让谎言戳穿,竟然暗示她应该消失。全金赌气出走,跳海自杀,却被人救起。从此全金消失,四处流浪,隐姓埋名几十年。有一天全金偶然从一张捡到的旧报纸上知道了韩国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的事,于是她重回故乡,想让村里给她开一张曾被鬼子强奸的“证明”。
作为一个女性,全金是在走投无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此下策,承认自己被强奸的往事,但她的遭遇比贞贞更惨:村里人一边对全金“被日本人奸得惨”的细节津津乐道,“把那个厚脸皮的将再次败坏村里人名声的女人,开一篇玩笑供大家饭后消食”;一边很害怕全金的出现,拒绝给她开证明。全村最老的全文标说出了谜底:“我们承认你就是全金,但是打证明是万万不行的。”因为全金是个“不洁的女人,会败坏了大家的名声”,所以人们一边津津乐道各种细节,但一边却拒绝接受事实而宁愿相信编造的谎言。没有人同情全金的遭遇,没有人去恨那些应该恨的人,也没有人想过她是一个受害者,反而怪罪全金,怪她不该出现。
全金的一生都是被动的,被迫进入种种角色,包括成为游击队长的恋人,包括被逼“消失”而投海,也包括没人肯证明真实的全金,她只能继续扮演“女英雄”全金而最终再一次遭受放逐,在年近70时继续过流浪、漂泊的辛酸日子。至此,受害人全金彻底消失,而英雄全金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记载的历史中。
这样的一种叙事可以说是对“革命”叙事的反讽和解构。“革命”有其正义性和合法性。革命叙事与启蒙叙事一起构成了主流叙事,但“革命”在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忽略了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启蒙命题,忽略了对人的命运、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也忽略了反对封建思想、改造国民灵魂的长久任务。
《现在》卸去或者说解构了丁玲笔下“贞贞”的英雄身份,将她还原成千百万因为战争受到伤害的乡村女性中的一员,让她的苦难赤裸、逼真地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时隔60年后仍然活着的“贞贞”以及她“现在”的遭遇。虽然过去了近60年,但像全金那样有着难堪过去的女人依然艰难地活在被规定、被安排的角色中。全金依然在为战争中遭的罪吃苦——她只能坐着睡觉。在她身上,战争并没有结束。全金的家乡之行实际上是一次企图化解痛苦的行为——身心的痛苦和精神的痛苦。她希望得到家乡人的同情,甚至能留在家乡度过余生。但人们害怕真实的全金,害怕她的出现,以村长为代表的权威话语否定了全金的合理要求,使她原有的痛苦没有化解反倒又遭受了另一重痛苦。
《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其文本复杂的语义场域提供了多角度阐释的意义空间,表面的政治话语、深层的启蒙立场、隐性的女性视角交织一起,构成了文本摩擦相冲的对抗张力,成为当时革命叙事主潮下可供多角度阐释、多层次读解的优秀文本。而近60年后出现的《现代》,则以全新的女性视角还原和发现了被“革命”叙事话语忽略的女性的真实生存状况,既显示了与丁玲不同的女性视角,更在深层次上提出了启蒙任务尚未完成的思想命题。
乡村女性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苦难群体,萧红以其女性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生育体验描写着生育、疾病、死亡导致的乡村女性的真实而苦难的生存境况,体现了一种来自性别觉醒的对女性身体的人文关怀。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叶弥的《现在》都选取了战争、女人、性作为叙事的基本元素和关注焦点,并以女性在民族战争中的处境为切入点,通过女性身体的遭遇揭示在表面平等的革命语境中对女性的不平等。无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时代,无论是革命的阵营还是反革命的阵营,女性都摆脱不了被利用、被不公正对待的命运,尤其是在民族战争的环境中,女性不仅受到异族侵略势力和剥削者的压迫和欺凌,而且还受到来自国家利益、来自男性同胞的利用和压迫。
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探求坎坷曲折。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在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党派、阶级的烙印,因此一边是启蒙现代性给女性带来的人性和欲望释放的可能,另一边是各种主流话语笼罩下的被忽略了的性别牺牲甚至是无法掩盖的性别压迫;同时,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性别身份的确认充满了深不可测的悬疑和摇摆不定的变数。困难来自于政治话语的功能性压抑,也来自女性自身精神“现代性”的困惑和艰难。现实中的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依然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依然承受着封建传统陈腐思想的精神束缚,依然承受着来自男性话语和男权政治的利用和不公正对待,甚至不可避免地遭遇着来自现代性的悲剧性体验。
一百年前,女性浮出了历史地表;一百年后,女性走到了哪里?现代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从一个角度诠释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