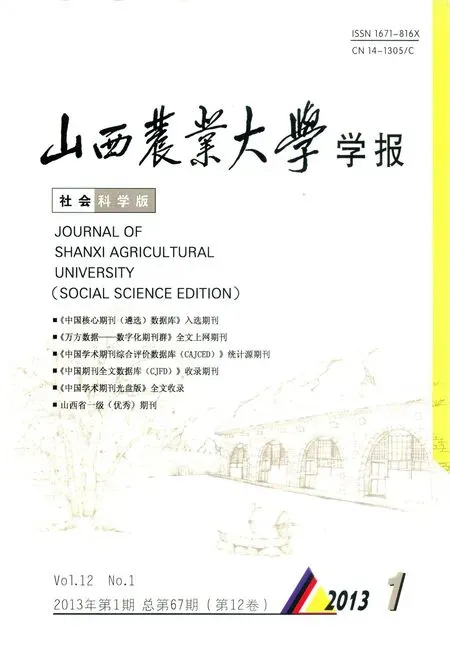阿拉伯帝国的政教关系及其对伊斯兰法的影响
李光
(惠州学院 化学工程系,广东 惠州516007)
法律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伊斯兰法是伊斯兰学说的缩影,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是伊斯兰教本身的精髓和核心”。[1]作为一个典型的宗教法,对伊斯兰法尊崇其实表现出来的是对宗教的虔诚。
由于哈里发一人身兼政治和宗教两职,人们一般认为阿拉伯社会是一元制的,即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但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在古阿拉伯帝国中,宗教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对立与斗争,这种斗争的此消彼长对于同期的司法理论与实践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伊斯兰法的特点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期伊斯兰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特点。因而考察古代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的政教关系对伊斯兰法的影响对我们认识伊斯兰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麦地那时期
(一)麦地那时期的政教关系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安拉的使者,也是伊斯兰教义上最后一位先知。这样的特殊身份使他拥有绝对的宗教权威,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宗教立法权、解释权。同时,他又是新的伊斯兰国家的缔造者,以真主的名义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各部落,是真正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所以先知的统治是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然而,在先知去世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伊斯兰教义,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是可以向人类传达主命的最后一位先知,那么他的去世也就意味着神启时代的结束。既然教义中规定了一切法律皆来自真主,是真主通过他的预言者穆罕默德向人们所做的启示,那么随着先知的去世,至少从严格的理论上来说即表示法律创造和修订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因为先知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也没有遗嘱规定如何产生 “继承人”,所以围绕着先知的继承人的问题的争吵,表明了不论是作为先知亲族的哈希姆家族,还是与先知曾经同甘共苦的古莱什族,他们都没有绝对的无可辩驳的神性去继承先知的权力。经过推选而产生的哈里发艾卜·伯克尔虽然也具有极高的威信,但他只能以 “真主使者继承人”的身份继承政权,而不能继承先知传达神启的神权。归根结底,由于教义中不能延续的神性限制了以后任何一位继承者拥有宗教意义上绝对的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
不过,在这一时期,哈里发们事实上在宗教方面仍然是具有完全的权威的。这是因为,第一,当时的宗教经典还没有完全成形,《古兰经》的正式编纂,要到先知去世若干年以后才开始着手进行,人们对于宗教的认识还不是完全的引经据典的。第二,作为阿拉伯社会的法制传统,人们一般都服从于习惯法 (即逊奈),“既然他们过去拥戴穆罕默德,而今服从他的继承人 (哈里发)也是合情合理的”。第三,先知的启示中也明确提到了 “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
(二)麦地那时期伊斯兰法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法还处于草创时期,但是《古兰经》中已经确立了神圣立法的原则。即现存的一切法律来自于真主,是真主在某一个历史时刻,通过他的预言者穆罕默德先人们所作的启示,因此,“穆斯林法学理论不能接受法学研究的历史观察法,即把法律看作取决于特定社会里变化的生活条件的一种事物来研究”。[2]
《古兰经》代表的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不是一部法典。在其中有关法律的内容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分散在各个章节之中,在其实体规范中,法律、宗教、道德三者之间的界限通常模糊不清。此外,《古兰经》虽然所涉法律内容甚广,但其法律规定却十分笼统,尤其是它的许多禁止性规定均无具体的处罚措施。我们只从 《古兰经》涉及法律方面的内容来看,同罗马的 “十二铜表法”相比,它也只是就某一个具体的案例进行裁决,而不是试图提出一个系统的普遍的法律原则。库尔森认为,《古兰经》里这些有关法律的章节的零星立法的性质表明了当时先知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立法需求时而采取的应急之举。比如说33章37节的经文中废除了伊斯兰教前的过继习俗,旨在解决因先知同他的义子宰德离异的妻子结婚而引起的争论。[3]
同时,《古兰经》所揭示出来的立法原则,并不是完全是先知的独创,而是基于麦加、麦地那的地方习惯法和流行于阿拉伯半岛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的教法精神,并由穆罕默德加以创造性地改进而形成的。先知对阿拉伯的习惯法的改进主要集中于婚姻问题和继承问题方面。比如将休妻权的法律效力推迟至待婚期 (妻子三次经期结束之后)的规定;又如对女性亲属继承权资格的确立。这些改进既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化,更反映了转型的阿拉伯社会的需要。在随后的四大阿里发时期,凭着个人的威望,他们也能像先知那样基于社会的世俗要求而对法律进行大胆的创制,而不只是拘泥于 《古兰经》的文本。例如,在灾荒之年,欧麦尔不判决偷盗者以断手之刑。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其一,在麦地纳时期的法律更多的不是基于 《古兰经》,而是基于传统的习惯法。其二,当时阿拉伯社会由原始的部落社会转型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国家的时候,仅凭原始的习惯法是不够的,也面临着严峻的立法要求。而 《古兰经》中涉及法律的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
正是因为 《古兰经》的法规修改了现行习惯法的某些细节,而不是完全代替了习惯法,而先知和哈里发们又能根据具体要求对法律进行创制,所以,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法的精神和实践基本上能符合当地的传统和新的需求。
然而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这种和谐,容易使人们将世俗的立法要求与宗教的立法精神混淆在一起,认为以宗教立法取代世俗立法是完全可能的,不能认识到其实先知与哈里发们具体的法律创制是基于社会的世俗的需要。这尤其表现在以后当他们的具体的判例而不是法律创制的精神被固化为沙里亚的 “逊奈”的时候。
二、倭马亚王朝前期
(一)倭马亚王朝前期的政教关系
倭马亚王朝建立伊始,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便处于困扰之中。穆阿维叶执政到680年,指定其子叶齐德作继承人,将哈里发由原来的选举制改变为世袭制,从而破坏了他死后交由穆斯林民众决定哈里发人选的承诺,激起了人们的不满,最终导致了伊斯兰教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
倭马亚王朝在政权巩固以后,便开始了对外大规模的征服。经过多年的军事扩张,帝国的疆域已经横跨亚、非、欧三大洲。许多具有高度文明的地区被征服了,这包括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地区,在这些新征服的地区有着诸多的不稳定的因素。而这时的哈里发是依靠武力获得的政权,在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方面均遭到了麦地那地区民众和什叶派的强烈质疑与反对,完全不能与麦地那时期的哈里发们相提并论。面临如此困难的哈里发作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不可能在宗教的虔诚与权力的稳定方面相兼顾,所以哈里发实际上更是一位世俗的君主而非一位宗教领袖。
(二)倭马亚王朝前期的伊斯兰法的特点
在麦地那时期,《古兰经》精神与麦加地区阿拉伯社会的惯例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又加之先知及哈里发们又能适时地进行法的创制,而较能满足当地的要求。但这一时期的法律创制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在麦地那时期,先知及其继任者们发展了 《古兰经》立法,所达到的实际程度则取决于穆斯林公社在麦地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4]而在新的征服地区,原来的成文法或习惯法已经比较发达,《古兰经》中的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再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地区的法律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里发自然要将维持帝国的统治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而顺应各地世俗的习惯法则更有利于其统治的稳固性,所以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司法实践转向了一个与日后伊斯兰法完全相反的方向即世俗法的方向。
出于统治的需要,倭马亚王朝保留了各行省原来的行政机构,因此,在其法律实践中,引入了许多外来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对非穆斯林属民的法律地位的确定,基本上照搬了拜占庭帝国非公民团体的法律地位。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社团 (迪米人)以交纳人头税为条件,获取政府安全保障之承诺,并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法庭行使的私人身分法之下,维护自己的权益。倭马亚还从拜占廷帝国继承了市场检察官 (阿格洛诺摩斯)制度,这个官职主要对于在集市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诸如使用度量衡标准和在那里发生的轻微违法行为具有有限的审判权。这样,外来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就慢慢地渗入了伊斯兰法的实践当中。
卡迪司法是倭马亚王朝早期的司法实践世俗化的一个体现。(早期卡迪是由行省总督任命的处理地方的法律纠纷的行政官员,而且大都属于兼职。直到倭马亚王朝末期和阿巴斯王朝初期,国家开始从通晓宗教法的法学家中选任卡迪,卡迪才转为专职法官,卡迪主持的沙利亚法院也逐步转为宗教法院。)卡迪作为下级官吏,必须服从总督的命令,总督有权随时任免卡迪。但实际上,统治者一般很少过问宗教法律事务,卡迪们具有广泛的司法权力。由于卡迪工作的特点是执行地方法律,而各地的法律传统差异很大,同时,法官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根据自己意见断案的权力,这就使得各个地区的司法实践尤其在私法领域中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5]卡迪司法制度的建立 “促进了智力的发展,提高了逻辑推理、思维判断的能,为后来意见、创制、类比、公议等法学思想和方法的提出创立了条件”,[4]当然毫无疑问也为后来四大法学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三、倭马亚王朝后期
(一)倭马亚王朝后期的政教关系
基督教有全世界宗教会议制定统一的教义,还有教令、教皇制以管理教务。而与之相比,伊斯兰教社会则是既无教会,也不存在为各地、各教派所普遍公认的最高教务管理机构。然而在一个宗教社会中,需要有这样一个宗教方面的绝对的权威,具有渊博的宗教知识和强烈的宗教热情,能对教义给予明确的界定;能以宗教的精神去审查和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状况。如果说麦地纳时期的先知和继任的哈里发们具备这样的权威和能力,而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却无这样的权威与能力。如我们在前面叙述的,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尽管哈里发身兼宗教与政治大权于一身,但是他既无精力更无高深的造诣使自己在繁忙的政务之外再去钻研和解释宗教信仰和教义。这使得倭马亚王朝在政治与司法方面更类似于一个世俗的国家。因而,研究和解释教义的职责就落到了后来逐渐形成的教法学者阶层的头上。这样,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合一体有了一种政教分离的趋势。
学者阶层的兴起,有着两个值得注意的背景。一是在倭马亚王朝后期,卡迪的逐渐专业化,使卡迪们开始深入钻研宗教法律问题。二是倭马亚王朝晚期,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形形色色的的教派运动、宗教思想运动极为活跃。在这种形势下,大约从公元720年开始,虔诚的宗教学者们以宗教道德为尺度对倭马亚王朝的政治和司法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政治上,清查过程导致对现行政府政策的仇视。倭马亚人被谴责为这样的统治者:他们因为追逐世俗权力而无视宗教的根本原则。虔诚的穆斯林们试图从复古的乐趣中寻求自己的归宿,要求恢复麦地那哈里发们的虔诚统治。[3]
而这一时期还兴起了旨在推翻倭马亚政权的阿巴斯派运动。阿巴斯派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的后裔在倭马亚时代建立的政治宗派。阿巴斯派运动兴起之初,主要采取一种叫达尔瓦 (即布道或传布真理神学宣传)的活动形式,阿巴斯派通过达尔瓦的形式,指责倭马亚人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原则,是伊斯兰世界罪恶的渊蔽和内战的根源。阿巴斯派声称,倭马亚王朝只是世俗统治而非神权政体,伊斯兰教已遭倭马亚人歪曲,必须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信仰,重建伊斯兰教的神权政体。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需要重新确立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权力。[6]
由以上我们可以知道,教法学家们的清算运动与政治学家们的阿巴斯派运动相互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指责倭马亚人违背了先知的教诲与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企图从宗教合法性上根本否定倭马亚人的统治。阿巴斯派运动的宣传需要教法学家们的理论作为基础,而教法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得益于达尔瓦而得到极大的提高。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则在于各自的侧重点上,教法学家们致力于确立纯正的伊斯兰教伦理和行为准则的至高地位,强调了自己对于宗教的唯一的解释权。而阿巴斯人则更多从先知家族的神圣地位入手,强调了自己对于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的继承性。这样的结果从事实上加强了倭马亚晚期就已经出现的政教分离的趋势。
(二)倭马亚王朝后期的伊斯兰法的特点
在虔诚的宗教学者们看来,倭马亚法庭的实践未能如实地体现 《古兰经》里所阐发的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于是,他们开始积极研究法律,并试图提出体现纯正伊斯兰宗教伦理的行为准则;为此,他们自发组成了松散的学术团体,并在倭马亚王朝最后30年里形成了伊斯兰教的早期诸法学派。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宗教界对现行世俗法律的完全否定,主张在法律上对传统麦地那时期的司法精神的回归。故而,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法并不是着眼于对现行法律实践的分析和深化,而是为制定一种与那种实践相对抗的法律制度而开始的。[3]
四、阿巴斯王朝时期
(一)阿巴斯王朝时期的政教关系
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斗争中,阿巴斯人得到了包括教法学家在内的大多数宗教学者积极的支持。然而,宗教学者们却在这一结盟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与地位,他们俨然已经成了先知教诲和真正伊斯兰精神的代表。这使得新王朝的哈里发在宗教与法律方面已经不能像他的前任那样拥有完全的权力了。阿巴斯统治者当政伊始就信守承诺宣布实行 “真主在大地上的统治”,公然声明实施当时正在由宗教学者指定的宗教法律制度的政策,宗教学者的地位获得官方的承认与支持,许多人被任命为政府要员。宗教学者尤其是教法学者地位的提高直接威胁了哈里发的权力,因为法律属于学者的领域,而在理论上法律对哈里发是有约束力的。将先知逊奈作为唯一的法源的观念事实上对哈里发权力构成了挑战。而早期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们仍然像倭马亚的哈里发一样,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的宗教权力,将自己塑造成为真主的代言人与委托人。于是,学者们与哈里发在宗教权力方面就有了潜在的冲突。然而,大多数的哈里发并没有在意这种威胁,他们接受了将学者们的主张作为法典的做法,并通过宣传和官方组织为他们提供便利。因为沙里亚法很少涉及税收、战争等公共事务,他们只是在婚姻、遗产继承、民事商业、宗教礼仪等私法领域中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不会在根本上对他们的统治构成威胁。大部分情况下,学者们也默认了这种权力的分离,他们甚至以沙里亚的名义对一些由哈里发所颁布的法令进行修饰。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对国王有利,而且也能维持学者们在所有法律事务上的权力。这样,在倭马亚时代就开始的政教分离的趋势在此刻已经明朗化了。“当沙里亚法官从统治者那里获得自己的权力的时候,他的法律却来自于先知逊奈的启示。”[7]
(二)阿巴斯王朝时期的伊斯兰法的特点
这一时期是伊斯兰法的全胜时期,在倭马亚王朝末期形成的早期诸法学派,到阿巴斯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批法学家被任命为卡迪,从法学家中间录用卡迪成为一项固定不变的司法制度。而且卡迪们不再是代表行省或地区总督的命令的法律的发言人,而是只忠诚于真主的法律。得到官方支持的法学家发起了法律的 “伊斯兰教化”运动,其具体的要求是系统阐发 《古兰经》提出的伊斯兰宗教伦理,弘扬伊斯兰精神。这种倾向到公元8世纪后期引发了一场规模可观的圣训运动,学者们普遍要求将先知视为法律学说的权威依据,并把这种权威表述为圣训的形式。在对倭马亚王朝的声势浩大的声讨中形成人们对麦地那时期司法理论和实践的神圣化。这一时期法学家们轰轰烈烈的学术活动的背后,突出的反映了这样的目的——力图以伊斯兰教的普遍伦理原则为标准,对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关系、遗产继承、民事商业关系、宗教礼仪制度等做一次大的彻底的清查和改造,从而形成伊斯兰教实体法的基础。
至此,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和繁荣之后,伊斯兰法学便关闭 “尹智提哈德之门”,进入了停滞期,后人也不再运用自己的推理创制和发展法律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代改革时期。[8]
五、结语
综上所述,阿拉伯帝国政教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伊斯兰法的理论与司法实践。麦地那时期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关系,阿拉伯半岛地区传统的习惯法和 《古兰经》法条则是这一时期的立法依据,而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法律精神和实践则被后来的教法学者奉为伊斯兰教法的立法渊源。倭马亚王朝的世俗化倾向使得法律开始突破传统伊斯兰教义的限制,走向世俗化。到了倭马亚王朝末期,随着专业教法学者的兴起,宗教的阐释权开始向宗教学者们转移,政教分离开始出现。而阿巴斯王朝是建立在阿巴斯派与宗教学者联盟的基础上的,宗教学者们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与地位,成为了先知精神的代表,出现了明显的政教分离。这一时期学者们掌握宗教法律的解释权,基于伊斯兰法精神对原来的法律进行了全面的审核与修订,成为了后来伊斯兰法的基础。
仔细考察伊斯兰法,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法的特点其实是以宗教法的理想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世俗法的现实主义精神,而这两种精神原本是在规范不同的领域。“政治立法从个人的行为对邻人或整个社会造成的后果的角度来考虑社会问题,而宗教法律则越过这些而注意行为者的行为对个人的良心和不朽的灵魂可能造成的后果。”[3]这表明伊斯兰法不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而立法,而是为了改造社会而立法,这也是伊斯兰法最终陷入停滞的原因。而阿拉伯社会的立法发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排斥世俗法的,从麦地那时期到倭马亚王朝时期,世俗法也经历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倭马亚时期的世俗法院与宗教法院的二元对立,更是预示了伊斯兰法走向完全形式主义的理性司法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伊斯兰社会的复杂微妙的政教斗争和对立,同时也由于 《古兰经》在立法权方面的绝对垄断,限制了伊斯兰法的发展,最终使得伊斯兰法完全走向了理想主义的宗教法。在韦伯看来,伊斯兰法的发展一度与罗马法相类似,但是:“伊斯兰教组织的某些关键特性,比如没有 [教会]教法会议,没有教义的永无谬误论,从而影响了神圣律法沿着稳固的‘法学家之法’的方向进一步发展。”[9]
[1]何勤华.外国法制史 [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61.
[2]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译.比较法总论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24.
[3]诺·库尔森著,吴云贵译.伊斯兰教法律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26,425.
[4]吴云贵.真主的法度——伊斯兰教法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3,17.
[5]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6]哈全安.阿巴斯派运动新探 [J].世界历史,1995(2):57-63.
[7]SAMI ZUBAIDA.Law and Power in the Islamic World,London [M].New York,NY:IB.Tauris,2003:78.
[8]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1.
[9]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 [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