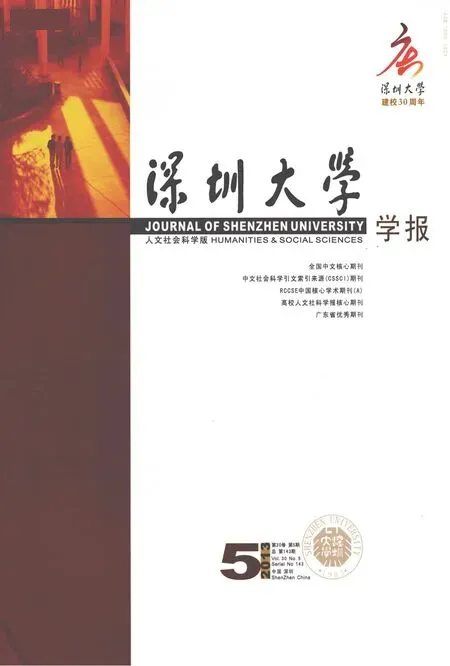洛克社会契约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倾向
高 旺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洛克作为社会契约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对政治社会与政府的范围和目的的思考与论证,历来受到高度的重视与赞誉。但其中所包含的虚无主义倾向,学界却甚少有人论及。本文通过分析其哲学前提,从而发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在将人类确立为独立自主的理性行为主体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虚无主义。而这一倾向发展至当今的现代社会,已然成为困扰人类的主要难题之一。
一、洛克社会契约理论要义
洛克将自然状态作为其契约学说的出发点。在自然状态中,所有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自然状态拥有某种自然法。它要求我们要自我保全,尊重财产权,保护无辜者,帮助他人。但由于在自然状态中生命以及财产的保全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人类通过缔结社会契约,从而结成共同体,而后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同时将自己在自然状态中的种种权利交给了社会,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并马上创建政府,以更好地互相保护自身的生命与财产。
根据这份原初的契约,人们向政治社会这一人类共同体转让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中的两种权力:(1)自由裁断的权力被限制——在自然状态中,为了能自我保全和保全他人,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其自认为适宜的一切行动;(2)完全放弃了处罚的权力——处罚所有对人类的自我保全和保全他人构成威胁的人。这两种权力是自然法赋予人类的,每个人都是自然法的裁决者和执行者,但由于人类的偏袒之心和普遍地对自然法缺乏研究,同时又不存在公认的权威以供申诉,所以自我保全的权力经常被过度使用,而对保全他人的义务持疏忽并冷漠的态度。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事实上是人人自危,并生活在日甚一日的恐惧之中的——对无法保全自己的生命与财产的恐惧。政治社会就是为了解除自然状态的上述危险与不确定性而被设计出来的。自然状态的反面就是政治社会,人们通过达成社会契约而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政治社会的特征源于人们同意这份协定的基本意图:建立一个公认的最高权威,通过它来制定众所周知的、经常有效的明文法律,以判决人们之间的纠纷与争执,同时建立一个常设的机关,以执行法律的判决,并惩罚罪犯,这一切,都是为了互相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这就是政府立法权与执法权的起源,政府掌握的这两项权力,是为了能达到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它的意图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无论任何形式的政府,其存在的目的除了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公众福利之外,就别无它义。总之,在洛克看来,政府的形式可以存而不论,无论它是民主制、君主制,或是寡头政制,只要它的存在是合乎其被建立其来的目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但绝对专制主义的政府体制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无论是出于人类自我保全的欲望,还是基于理性的教导,人们绝不会在走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后,居然还让一个人,一个最高统治者,居然还能保留自然状态中全部的权利,从而可以任意地毁灭他们的生命和剥夺他们的财产。洛克甚至有点戏谑地比喻道:“这就是认为人们竟如此愚蠢,他们注意不受狸猫或狐狸的可能骚扰,却甘愿被狮子吞食,并且还认为是安全的”[1](P57-58)。
既然人类现已处在一定形式的政府的统治之下,那么对他就有必须加以履行的义务。但洛克认为,尽管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有机会参与政治社会的缔结契约的活动,但是我们的政治义务仍然是以我们的同意为基础的。洛克同时区分了有关“同意“的两种类型:公开的和默认的。所谓公开的同意,指的是以明文的约定、正式的承诺和契约,或者是作出效忠的宣誓所给出的同意。公开的同意使人们放弃了自然的权利,而成为了一个社会中正式的成员,一个政府的公民,并永远地臣服于它,永远不能拥有自然状态中的那些自由。相反,他必须遵从它正式颁布的法律的治理,并从自己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缴纳税款;而一个人只要身处任何政府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不管他占有的是世代相传的土地,或只是一星期的居所,哪怕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就被视为默认的同意,他就必须服从这个政府的法律[1](P74-75)。纳税与守法,就是公民的基本政治义务。这实际上是一个限定性的学说,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合法性的说明,另一部分是关于个人之政治义务与责任的说明。通过公开的或默认的同意,人民有义务服从的是合法的政府,而非不正义的政府。因此,政府的合法性是人民履行政治义务的限定性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政治社会中,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政府存在的目的出现异化:或许是立法和执法机关蜕化变质,变得专断而蛮横,或许是它们已被个别人所劫持、所窃取——这个人此时就拥有了毫无限制的权力来贯彻自身的绝对意志,而变质了的权力机关或独裁者势必将人民的委托弃之不顾,反而残民以逞,人民就将陷入远比在自然状态下更大的恐惧之中。而这时,人民又当如何呢?
洛克在自己的学说中预设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观点,即当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变成了与当初人们将其建立起来的目的相反的事物时,它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再合法,政府事实上已经解体,人们重新又回到了自然状态。这时,人民没有义务再服从它所颁布的,已经毫无公信力的法律。人民有权反抗它、推翻它。因为社会契约最初是基于人们彼此之间的一致同意而达成的,而不是和任何形式的政府或主权者缔结的,是先于他们而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政府的权利是一种委托的权利。当人民意识到在政治社会中已经无法自我保全,并且政府的存在甚至是对自已和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毁灭性的威胁时,凭借着这最后的裁断权,人们有权利收回委托,并用强力去纠正强力,用战争去结束战争,用武力去反抗和推翻那一侵犯他们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统治者或政治权威,之后再次创建一个能保护自己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新政府。
二、洛克社会契约思想中的虚无主义
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源于他对人类本性的认知和论证之上的。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的上篇中,明白无误地宣示,自我保全的欲望是人类天性中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欲望,也是人类所有行动的原则。人类有权占有和支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一切物品[2]。洛克于此揭示了人类的自然权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绝对意义的权利,同时亦将其从对自然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人有权自由地占有和支配万物以达到自我保全。但洛克没有说明,究竟需要多大程度上的占有和支配,才能够充分满足人类这种强烈的欲望。事实上,这也无法证明。因为自我保全的欲望不是其有效要求的自证根源,它只有在对自身对立物的否定过程中方能验证。而对生存的欲望而言,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死亡。生命只有通过对死亡的否定,才能找到本身的确定性存在。这意味着,既然人类无法体会到欲望满足之后的幸福与愉悦,那么人类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只有通过对它的积极地否定,充满自觉地、永不终止地去创造和占有那些能产生幸福与愉悦,避免恐惧与痛苦的东西,人类才能认知到自身存在的真实不妄。这是人类欲望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起点。这也是洛克与古典哲学家大相径庭的地方。
古典政治哲学的宗旨是要解决共同体内部的政治论争,并建立与人的卓越品质如美德、奉献等相称的秩序,同时对这些品质进行道德的区分,分辨什么是勇敢与怯弱、善良与罪恶、文明与野蛮。洛克将这些统统置之不论,他只是肯定了人类自我保全的欲望和贪欲的释放,并将它们从《圣经》与传统中那些古老的训条中解放出来。人类不再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再不会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充当它的顺从的奴仆,而是作为独立自主的理性行为主体,充满希望地自强自立和创造财富。在洛克看来,人类既然生而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那么他们就有权利通过自身的一系列实践性活动——劳动、使用货币、缔结社会契约,进而组成共同体并建立政府,去维护和扩大这种自由。劳动赋予人类去占有能维系其生命存在的一切天然物品的自由,货币的发明与贪欲的释放使人类拥有更大的自由去积累财产,而将自己置身于政府与法律的保护之下,凭此人们又能自由地支配和创造更多的财富。而驱使人类不断寻求自由的,正是源于人类本性中最强大的一种力量,也是人类最初和最高的、不可分割同时也是不可放弃的权利——自我保全和保全他人的权利。这又是源自于人类本性中最原始和最强烈的、无法消失并且是无法摆脱的一种情感体验——渴望能自我保全的欲望和对无法充分满足这一欲望的恐惧。它们共生在人类的本性当中,是人类通往文明社会的最大原动力:在自然状态中,它们迫使人类从事劳动以免于死亡;进而又释放了贪欲,使人类免于匮乏;最后驱使人类结成共同体,创立政府,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与财产,从而使共同安全、和平、富足的生活成为可能。但这也是一种最大的破坏力:它可以令人类互相屠戮,使政府解体、社会失序和对生命与财产的毁灭。它只能被抑制、被引导,永不会消失或者被消灭,它是政治社会与政府的真正基础。政府的职责正在于去适应、去引导这一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望与恐惧的力量,并将之转化成为人类和平、富足与自由生活的根本,而不是试图以强力去改变那无法改变的东西——人类的本性。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论证了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真正起源,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的遗产。但与此同时,他也留下了巨大的问题:一个致力于满足欲望与规避恐惧的人类社会,将无法避免地滑入道德虚无的深渊。
纵观洛克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他始终没有证明如何才能充分满足人类自我保全的欲望,从而彻底地抚平对无法实现这一欲望的恐惧。事实上,这是他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人必将死亡这一基本自然规则令人类自我保全的欲望最终不能实现,而人类也无法预知那何日会到来,以及由谁来强加的死亡与毁灭。因此,人类终其一生都将处于对无法自我保全的恐惧之中。洛克是将生命的意义寄托于人类在现世的一系列对死亡与毁灭的否定性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类只有通过对死亡与毁灭的否定,从而获得在当前和未来之中能够自我保全的物品时,方能使恐惧得以缓解和抑制。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能体会到愉悦的生活,而是体现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人类能创造和拥有多少能实现愉悦生活的的东西之中。如果说生活就是对愉悦的毫无愉悦的追求[3](P213),那么愉悦就是充满恐惧地去慰藉恐惧,最大的幸福在于享有那些能产生最大快乐的事物[4](P257-258)。那么,如此追求物质财富,究竟是善之根、抑是恶之源呢?透视洛克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一概不是——无所谓善恶,只有巨大的虚无。
自格老秀斯以来,近代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所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古典哲人认为人们彼此友善地生活在一起是至上的善和最高的道德,但从中世纪开始所不断发生的事实告诉人们,追逐个人的利益妨碍了人们实现这种生活。那么,遵循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的指引,人类究竟能否达到至善的境界呢?格老秀斯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他只是根据日常经验承认了这样的事实——人们既渴望能彼此友善地生活,又的确在追逐着私利。但无论如何,必须尊重个人的选择:“人们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一些生活方式更糟,另外一些则更好,全在于个人的选择……因为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各不一致,而是应以人民的意志加以衡量。”[5]霍布斯则将其推向极端,他断言,人类无法和平友善地相处,更不可能达到那至善的彼岸,“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而短寿。”[6]因此,必需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来强迫人们遵守自然法和人间的法律,在他那里,社会契约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
洛克的解决方法是根本否认这一问题的存在:在自我保全的欲望驱使下追逐物质财富的行为是正当的,它是人类能和平、安全和富足生活的根本。人们缔结社会契约进而进入政治社会,并建立政府的意图是保护这种行为与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这也无关乎道德,所谓善、恶只不过是某种感官的体验。正如洛克自己所阐述的那样,“事物之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所谓恶,就是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4](P214)如此一来,人类除了不断地占有和积累更多的、更大的物质财富,除了追逐和沉溺于当下的、一时的满足与享受,就别无所求。既然生命无法永恒,那么就在今天及时行乐。
洛克既然先验地将自我保全的欲望视为人类的最根本的本性与行动原则,同时确立了每个人都是有权利、有能力去自由行动的理性行为主体,那么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而他们的选择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古典哲人枉费心机地探讨至善究竟是在于财富或者肉体的欢愉,还是在于德性或沉思,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欲望所要求和恐惧所支配下的活动才是生命存在的意义[4](P257-258)。这样洛克就否认了人类对至善的追求,也因此他就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真实存在着的种种高尚行为及其动机,也无法看到人类灵魂中最深层次的渴望——对高尚、荣誉、牺牲等美好品德的需求①。在洛克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中,我们能看到只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所连结成的政治社会是基于财产的利益关系,单个的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没有任何的权利与义务去提升彼此的道德感或者共同去追求那真正的善。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亦是如此,父母的使命是要将子女抚养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而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1](P38)。人世间无所谓对错,无所谓是非,也无所谓善恶,一切美德与卓越、一切善行和义举都是真空与虚无,再也没有能流传万世的永恒之人、永恒之事与永恒之业。洛克将人类从自然的和人为束缚中加以解脱,并赋予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的后果,就是令人类社会最终将演变成充斥着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与道德虚无的困境,人与人之间是原子式的、彼此孤立的大拼盘和大杂烩。即使洛克自己也无法掩盖自身理论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他认为人类正如蜜蜂或甲虫之类的昆虫一般,在享受了过后,便行消灭,不复存留[4](P257-258)。
三、余 论
几个世纪以来,洛克的政治哲学中那些最基本的立论原则屡受质疑和挑战:他的自然法学说与古典以及中世纪的自然法概念相比是那么的奇特;自然状态的假说被无神论者斥为虚幻而违背人性;诺齐克作为其思想的捍卫者,也对劳动究竟能否创立所有权表示怀疑;而有关社会契约的观点遭到休谟强烈的反驳,他认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社会契约的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还是相当肤浅的,与常识相互矛盾的;卢梭将道德原则重新注入了社会契约论中,试图设计出一种政治社会的理想状态,在这样的社会里,罪恶与不幸都不复存在;而列奥·施特劳斯更是指称,由洛克发端的自由主义哲学必须要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冷漠、极端的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负责,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即是虚无主义,它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而虚无主义正是由现代性运动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第二次是卢梭、康德和黑格尔、马克思;第三次是尼采与海德格尔)不断推动和加深的[3](P12、17)。洛克作为首先展开现代性逻辑的思想家,是难辞其咎的。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思想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思想史的研究者不能对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一无所知。在洛克生活的那个年代,旧有的道德训条依然有强大的规训力,毫无节制的追逐和占有物质财富被视为邪恶和愚蠢的。而自17世纪以来,不但英国,整个欧洲社会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古老的狩猎时代进入了商业和消费社会,商业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基本制度的延续性与经济的自我持续增长[7]。而只有建立个人对市场依赖,鼓励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才有可能使人变得更理性而文明——因为市场会奖励理性的行为,惩罚不理性的行为;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建立必须经由公民的同意,它的职责只是通过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来解决人们之间的纠纷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样方能使商业社会的实现和稳固成为可能。因此,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实际上是为了说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已经出现的一种现实状况,而不是执着于去探讨社会应该建立在何种形式的公平或正义观念之上。
至于现世中已经发生的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现象,洛克辩称,在现代文明的商业社会,即使最贫困的人,也要比原始的平等状态中最富有的人要富有的多,“在那里,一个拥有广大肥沃土地的统治者,在衣食住方面还不如英国的一个粗工。”[1](P27-28)因此他是实然世界的辩护者,而不是应然世界的建构者。在这个意义上,他被公认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言人。理论的历史就是对持续变化的问题提出持续变化的答案的历史,洛克在他所生活的年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今天面对这一虚无主义危机日渐加深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注:
①事实上,在自己的著作中,洛克很少使用或者根本没有使用诸如慈善、灵魂、荣誉、美德、高贵或爱等词语.
[1][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册)[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上册)[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4-76.
[3]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4][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荷]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M].何勤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0.
[6][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弗,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5
[7][英]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M].梅雪芹,石楠,张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