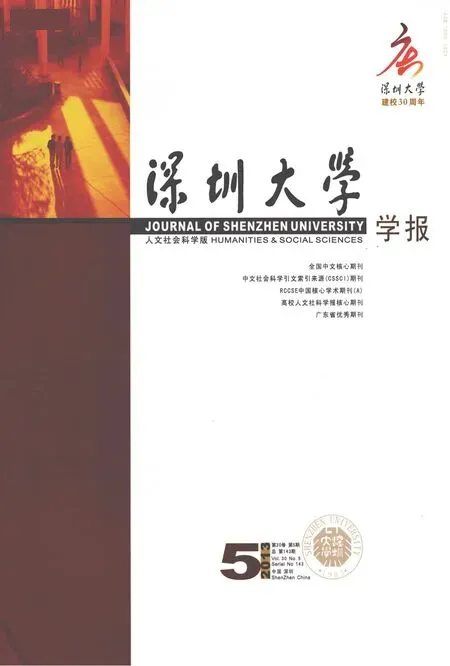论金堉的集杜诗
左 江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引 论
集句诗由来已久,早在西晋傅咸就有集句《七经诗》,因此他被视为集句诗的开创者。至宋代,在石曼卿、王安石等的推动下,集句的风气蔚为兴盛,集杜诗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如孔平仲有《寄孙元忠·俱集杜句》,共31首。至文天祥(1236—1283)《集杜诗》200首,将集杜之作大大推进了一步,如吴承学教授所言,其集杜“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对于杜诗的一种心理体验方式,其集句创作是一种与集句对象同化的过程”[1]。这一改变无论是对此后的集句诗还是集杜诗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集句诗在中国源远流长,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也很悠久①。如高丽时期(918—1392)的文人林惟正(1159—1214)有《百家衣诗集》,都为集句之作,共计289 首。到了朝鲜朝(1392—1910),金时习(1435—1493)有《山居集句》七言绝句百首。林、金二人的集句之作都属于杂集,相比而言,专集出现得比较迟,特别是集杜之作出现得更迟。考察《韩国文集丛刊》,直到16世纪中期才在文人文集中出现集杜之作,其中李民宬(1570—1629)尤为引人注目,不但有《忆舍弟集杜诗》五言十绝、《续集杜诗》五言十绝,还有《六公咏》一组,其中之一为集杜诗咏文天祥[2]。
金堉之前,无论集句诗还是集杜诗在东国都已比较成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金堉的集杜诗有五言绝句200首,七言绝句12首,五言律诗3首,五言古诗1首,共计216首952句,出自杜甫的515首诗作。据《杜甫全集》统计,杜甫写作的古体诗有413首,近体诗有1009首,总共1422首,金堉引用的杜诗已是三分之一强。金堉的集杜诗无论是数量之多,还是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颇值得研究。
二、集杜诗写作时间考述
金堉(1580-1658),字伯厚,号潜谷,是朝鲜王朝仁祖(1623-1649在位)与孝宗(1649-1659在位)时期的重要朝臣,是一代政治家,也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实学家。金堉不以文学著称,但在朝鲜汉文学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如正祖(1777—1800在位)云:“故相臣金堉用事业称,而不以文章著。今取其遗集见之,信是近世不易得之文字。”[3]其传世文字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集杜诗》。
金堉集杜诗的写作契机,是朝鲜仁祖十四年(明崇祯九年,1636)出使明朝逗留北京获读文天祥《集杜诗》200首,深受触发,遂创作了50首集杜五言绝句:“丙子岁,余奉使北京,卧病经冬,见文山集杜二百首,皆奇绝衬着,若子美为文山而作也,余亦试为之。不杂他诗,专集杜为绝句,谓之‘文山体’。”这是金堉集杜之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前后并二百余首,长篇短律,间或为之”,共留下了216首集杜之作②。金堉的集杜诗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其中写作于丙丁年间的50首五言绝句,有47首被收入文集,题作《丙子朝天录》。此外,另有153首。这153首又分两类,一类是写作时间确定,按时间排列如下:
仁祖十六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六月,金堉拜忠清道观察使,七月辞朝上任,至次年七月瓜满,八月还朝。此行有《巡湖录》,共15题15首。仁祖二十一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作为人质留在沈阳的昭显世子要回国省亲,清朝要求元孙入质,金堉作为辅养官陪同前往,十二月出发,甲申(1644)正月入沈阳,七月回国。在沈阳期间,金堉有《行矣堂录》1题8首。仁祖二十四年(清顺治三年,1646),金堉以谢恩副使的身份第二次出使北京,二月出发,四月到北京,六月回朝复命,此次有《感慨录》17题23首。仁祖二十五年(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金堉拜开城府留守,至己丑(1649)三月秩满,在任上有《居留录》,共24题49首。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1650),金堉以进香正使第三次出使北京,三月出发,五月到北京,六月复命,此行有《三涂录》8题16首。
另一类写作时间有争议,按时间顺序如下:
五言律诗《送俞子修出宰江陵》一首,俞子修即俞省曾(1576—1649),南润秀在《潜谷金堉的“集杜诗”考》一文中推测此诗的写作时间是1640年以后。实际上在仁祖十六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九月,俞省曾被任命为江原监司[4],金堉当是在此时写作这首集杜诗送别俞省曾。
五言律诗《次白洲兄弟韵,赠宋进士民古》一首,白洲兄弟指白洲李明汉(1595—1645)、玄洲李昭汉(1598—1645);宋民古(1592—?)为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人称文章、书法、绘画三绝。李明汉赠宋民古之作题为《次舍弟韵,题宋上舍民古扇面》[5],此次诗作次韵的首唱者是李昭汉,其诗题为《方伯郑君则世规为其表弟设庆席于临陂,要我同参,不获辞,赴会。宋上舍民古在韩山,闻余至,涉海而来。将还,求题便面为别,口占书赠》[6]。李昭汉的文集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这首诗收入卷三《侨寓录》,注云:“自晋州递归,寓居于全州。”据李殷相《先府君行状》所云,李昭汉于“己卯(1639)服阙,五月拜礼曹参议,力求外补,出为晋州牧使。……壬午(1642)秩满,入为承旨”[7]。(P561)又据《仁祖实录》的记载壬午十一月初二日,李昭汉被任命为同副承旨[4](P139)。李昭汉在晋州牧使任满后至十一月被任命为同副承旨期间,曾短暂寓居于全州,并见到宋民古,有赠诗之作。李昭汉返回京城后,与金堉同朝为官,金堉大概看到兄弟二人的次韵诗,亦以集杜次韵相和。集杜五言绝句中的《题宋生民古书画诗帖》一题三首,也应创作于这一时期。
五言古诗《北征,诗呈石室金尚书》一首,金尚书指金尚宪(1570—1652),号清阴、石室山人等,他因阻碍清鲜和议从1640年12月起被囚禁于清朝,至1645年2月方被放还回国。金堉在1644年正月以元孙辅养官进入沈阳,金尚宪也在沈阳,所以有这首集杜之作。南润秀认为这首诗是金尚宪1640年12月入清朝时,金堉的送别之作,是“金堉根据自己北京使行时的北上路程,并以金尚宪的立场写作的集杜诗”。虽然金尚宪入清与金堉入沈阳都是12月,在时间上吻合,诗中描写的景色也相符,但金堉丙子使行走的是海路,并没有经过诗中出现的大多数地点。诗中又云:“衰颜会远方,重与细论文。”可以证明这首诗写于二人相遇于沈阳时。
五言绝句《洪勉叔谪大静》一首,南润秀及金相洪都将其与《题宋生民古书画诗帖》三首归入《三涂录》中,实际上这二题四首诗跟《三涂录》中的作品并非完成于同一时期③。洪勉叔指洪茂绩(1577—1656),仁祖二十三年(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昭显世子由清回国后不久即去世,次年(1646)二月,仁祖要将昭显世子嫔姜氏赐死,洪茂绩时为大司宪,上疏云:“姜嫔可废,绝不可杀。殿下必欲杀姜嫔,先杀臣然后乃可为也。”[4](P259)仁祖大怒,将其流放至济州岛的大静,一直到己丑(1649)年七月,孝宗继位,才将其放归田里。所以这首诗当写于洪茂绩被流放大静的1646年。
七言绝句有《老人宴》五首,据《潜谷先生年谱》记载,戊子(1648)“十月,设养老宴”[8],同时五言绝句《居留录》24题中亦有《养老宴》六首,这两组诗应该写作于同一时期。
五言绝句《归田录》,共1题38首。关于《归田录》的写作时间,南润秀与金相洪都认为是1649年金堉由开城府留守卸任后,但二人的理由并不充分。据金堉文集中《归山居赋并序》一文所云:“辛卯(1591)夏,尝读《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心甚乐之,效之而作《六松处士传》、《归山居赋》,其传曰:杨州平丘里,有一山……。今六十年而余退居于此……”(卷一,页九)由序可知,他意欲归隐的地方是平丘,1591年以后的60年是1650年。再考察《年谱》,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1650),正月起金堉回平丘,屡次上疏乞致仕,归田的想法很强烈,但未能如愿,三月被任命为进香正使,只能返回京城。因此可推断《归田录》创作于1650年正月至三月之间。
五言律诗《发燕京》一首,南润秀《潜谷金堉的“集杜诗”考》认为这首诗“毫无疑问写于1637年4月”,但金堉《朝天录》并未收入这首诗,大概可以判断这首诗并非写于第一次朝天之行。从 “长吁翻北寇,从此更南征”来看,更接近清人入主中原以后的情形,所以这首诗当写于金堉第二次(1646)或第三次(1650)出使之时。
综上所述,金堉集杜诗列表如下:

?
可见金堉的集杜诗有很强的时间性,除6题7首不能判断写作时间外,其它作品可以说是他人生历程的反映。
三、集杜诗的诗史意识
金堉写作集杜诗是缘于文天祥集杜200首的触发。文天祥在诗中将自己忠君爱国的情怀、颠沛流离的艰难处境都已融入其中,如他自己所言:“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在集杜的过程中,文天祥已与杜甫融为一体,两人高度同化。金堉受文天祥影响,其集杜诗亦非单纯的游戏之作。在集杜的过程中,其性情、其人格与杜甫相合,诗歌的风格也与杜诗更为接近。文天祥又云:“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9]杜诗被称为诗史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以诗记载一代之历史;二是诗作如春秋笔法,抑扬褒贬都寄予其中。文天祥深得其中三昧,金堉对此也了然于胸,所以其集杜作品亦可视为 “诗史”,不但记事且有对人对事的评判。
丙子六月,金堉第一次出使中国,此次使行,他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有《朝京日录》,有诗歌,有上疏、奏札、书信,还有集杜诗。其中集杜诗的写作始于逗留玉河馆期间,诗中描写了他思乡盼归的心情,朝见、领赏、开市、验包等程序,对暹罗使臣的观感,以及回国的具体路程。无论是对重要事件的记载还是对归程的描述,都很详尽,充分体现了“诗史”特点。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几首是金堉对人物的褒贬、对中华民风的评判,这是在其他燕行诗作中没有的内容。《叹俗》云:“家家急竞锥,汉道盛于斯。识者一惆怅,慎哀渔夺私。”诗中毫不隐讳地直指中国民风的贪婪。《姜尚书逢元》二首云:“尚书践台半,于利竞锥恨。白日中原上,我何从汝曹。”“君子慎知足,捡身非茍求。物情尤可见,疾恶信如雠。”《何提督三省》二首云:“郎官幸备员,谬通金闺籍。刻剥及锥刀,衣冠兼盗贼。”“古人称逝矣,能诗何水曹。索钱多门户,后生血气豪。”姜逢元为礼部尚书,何三省为礼部主事,二人都是贪渎无耻之辈。金堉对何三省的讽刺尤为尖刻,说他是穿着官服的盗贼,虽然没有先人何逊能诗善文的才华,但在索取贿赂上却花样百出。这可以与金堉在《朝京日录》中的记载相印证:
礼部尚书姜逢元,渎货无厌。顷以咨文事,归罪小甲于文,累次杖之,仍为拘系冷堡,盖索贿也。于文每来恐吓云:尚书贪甚,不可不行赂,以免我罪。……以书册事呈文于主事(何三省)。主事曰:此皆题本已定之事,决难更改。盖皆欲贿也。近来搢绅之间,贪风益炽。行赂者以黄金作书镇挟于册中而进之。金价甚高云。(卷十四《朝京日录》,页 275-276)
姜逢元以责罚手下来要挟朝鲜使臣,何三省又以书册之事借故索贿,所以金堉说:“中朝之官贪婪成风,政以贿成,礼部尚书为尤甚,当奏之事亦不上请。”[10]对中国民情以及官员作风的评价,如文天祥所言“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从另一方面展现了集杜诗“诗史”的特征。
金堉作为朝鲜出使明朝的最后一任使臣,在丙子胡乱爆发后,明朝君臣给予他们从未有过的厚待与优礼,虽然在北京期间有诸多不愉快,但在他们回程时,明朝加倍赏赐礼物,派遣官兵随行护送,并且敕令沿途各司,不得为难朝鲜使行等[11]。这样的礼遇深刻影响了金堉对明清两朝的看法,明亡后,他在缅怀明朝的同时对清人的憎恶也就更为强烈。此后他两次出使北京一次进入沈阳,再无第一次出使时的激情,留下的文字只有少数诗歌及集杜诗。以清代明是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金堉的诗中也有表现时局变化的诗句,如“频年来往惜名山,沦陷腥膻在此间。恰似西施临老境,坐于涂炭整云鬟”(卷二《凤凰山》,页44),清人入主的中原已不再是礼乐文明之邦,而成腥膻野蛮之地。但总的说来,诗中的表述很委婉,更多的还是对物是人非的感慨。但在集杜诗中,金堉不再委婉也不再含蓄,将自己内心的悲愤以及对清人的鄙视都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如《感遇》八首其中三首云:“羌人豪猪靴,其俗喜驰突。万马肃骁骁,挟矢射汉月。”“胡虏何曾盛,中原鼓角悲。烟尘绕阊阖,拔剑拨年衰。”“降将饰卑词,隐忍用此物。破竹势临燕,杂种抵京室。”这八首一组诗写于以辅养官入沈阳时,在诗中直接将清人比作禽兽,斥为“胡虏”、“杂种”,并且对明朝重整旗鼓收复旧河山充满期待,诗云:“圣图天广大,树立甚宏达。旧物森犹在,皇纲未宜绝。”(《感遇》其八)
随着时间的流逝,清人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金堉发现“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所以对明朝的期待也慢慢消失了,集杜诗中如实地描写了硝烟四起的时代百姓的苦难生活,这也是不见于其它作品的内容。《感慨录》中有诗云:“四海一涂炭,千山空自多。居人茫牢落,丧乱饱经过。”(《千山村》二首之一)“中原戎马盛,突将且前驱。血战乾坤赤,抢急万人呼。”(《出军》)《三涂录》中《有感》云:“帝京氛祲满,关辅久昬昬。黄图遭污辱,无力正乾坤。”“公主歌黄鹄,都人惨别颜。中原戎马盛,恸哭望王官。”《感慨录》与《三涂录》分别写于金堉第二、三次出使之时,诗中描写了中华大地成一战场的悲凉情景,百姓饱受战争的摧残,整个中原似已成一片鬼域。对于清人在中华大地的肆掠,明朝根本无能为力,诗中弥漫着伤感却又无可奈何的氛围,对清人以胡乱华充满了愤慨之情。以诗记史,以诗抒怀的功能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集杜诗的忠君爱民情
杜诗被称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如实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程,还因为杜甫忠君爱国、一饭不忘君的精神为后人所颂扬。金堉在朝鲜历史上“操行经术为世模楷,文章是其馀事”(尹新之序,页3),作为一代政治家,他同样心怀国事,操劳不息。1650年正月至三月期间金堉短暂退居平丘,数次上疏君王请求致仕,并将这一时期的心绪寄托在《归山居赋》中,作为71岁高龄的古稀老人,金堉希望能远离朝政远离喧嚣,归隐田园遁居山林,过上闲适自在的生活。但“每一饭而不忘,独此心之难删”(卷一,页9),“一饭不忘君”的忠君爱国情怀丝毫不会改变。
对国家对民生的关注就成为金堉其它几组集杜诗《巡湖录》、《居留录》、《归田录》的主旋律。在任开城留守期间,金堉可谓诚惶诚恐,诗云:“居守付宗臣,小臣议论绝。新渥照乾坤,恐君有遗失。”(《居留录》之《拜开城留守》)既然身为朝臣,管理一方事务,当然要不负君恩,所以他在任期间也是兢兢业业为一方百姓造福。如轻敛薄赋,减轻百姓负担。《收籴》三首之一云:“租税从何出,薄敛近休明。愿闻锋镝铸,人藏红粟盈。”对于百姓的疾苦金堉感同身受,所以他希望朝廷能薄敛轻赋,希望世间不再有战争,兵器都改铸成农具,家家粮满仓足。又如设养老宴,推动敬老之风气,昭显君王之爱民。养老宴是金堉在开城府留守任上做的一件大事,不但有序记事,而且有集杜诗五言绝句六首、七言绝句五首记事。《养老宴》云:“接宴身兼杖,相逢皆老夫。真供一笑乐,击鼓吹笙竽。”《老人宴》云:“南极一星朝北斗,人生七十古来稀。细推物理须行乐,来岁如今归未归。”在一片喧嚣热闹中,是对百姓安康的祝福,国家富足的期待。
1650年,金堉已71岁,一边是为国为民的热情,一边是归隐田园的憧憬,二者在心中纠结,令他难以平静,《归田录》38首就是这种心境的反映。出与仕的矛盾令他左右为难,最终痛下决心:既然自己于国于事无补,又年老体衰,不如退隐吧,诗云:“恨无匡复姿,毫髪裨社稷。飘然去此都,出郊已清目。”《归田录》38首生动地描摹了金堉的心路历程,他虽然渴望闲适散淡的人生,但心系朝政,心系民生,终不能不问国事安然隐居,所以终其一生他都未能真正离开仕途,一直为国为民操劳不息。
五、余 论
金堉推崇杜甫,欣赏杜诗,还因为他的人生充满苦难,与杜甫颇多契合之处。在他11岁时,祖父金棐去世;13岁,壬辰倭乱(1592)爆发,为避乱四处辗转迁移;15岁,父亲金兴宇在海州去世;19岁,祖母金夫人去世;21岁,母亲赵夫人又于延安去世。丁忧结束后,金堉参加了科举考试,本该顺利步入仕途,但因光海君(1609—1622在位)当政,朝政一片混乱,所以直至癸亥(1623)三月仁祖反正,金堉才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此时的朝鲜危机四伏,整个东亚形势也动荡不安:1627年,后金第一次入侵朝鲜,朝鲜被迫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1636年,清人第二次入侵朝鲜,朝鲜被迫签订“丁丑约条”,成为清朝的藩属国;1644年,清人入主中原,建立了新的朝廷。金堉的一生,一次次面对亲人的离世,一次次遭遇家国的存亡,这使他对杜诗有一种特别的感悟,李纲曾说:
盖自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11]
相似的社会环境,相通的人生经验是金堉喜爱杜诗的基础,如吴承学教授所言:“优秀的集句诗往往是诗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之作……交织着集句诗人与古人的双重情意。”[1](P196)金堉的集杜诗与杜甫有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其忠君爱国、一饭不忘君俨如杜甫再现,而在诗中以诗记事,将那一时代朝鲜士人的心理特点呈现出来,也带有较明显的诗史特征。
关于集句诗的体制风格与创作特点,吴承学教授认为 “集句绝不是单纯熟练地把前人的句子凑合起来,切合声律就行了,其妙处在于思致,在于构成新的意蕴”[1](P196),金堉极为熟悉杜诗,可以娴熟地加以运用。如其《北征诗呈石室金尚书》,这首诗写于他作为元孙辅养官入沈阳时,诗中记载了他入清的过程,出发的时间是1643年12月,作者在诗中首言:“岁暮远为客岁暮,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非常巧妙地点出了时间,以及远行之惆怅与无奈。行至定州,遇上大雪纷飞的天气:“客行新安道新安吏,大雪夜纷纷舟中夜雪○定州。”金堉行程中的真实地点是定州,与诗中的新安道并不相符,但夜逢下雪却让人身临其境,这样的句子似乎还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一路的心情——那是类似于杜甫身处动荡时代写《新安吏》时的心情。行至龙骨山城,诗云:“山城仅百层登白帝城,石角皆北向剑门○龙骨山城。”至连山馆、高岭,诗云:“连山晚照红秋夜○连山馆,雪岭界天白锦水居○高岭。”作者在现实中行走的路径竟与引用的杜甫诗句达到了完美的一致。
这样的一致性在集杜五言绝句《巡湖录》中作者做到了极致。一种是诗题就直接出现在诗句中,如《连山》:“连山晚照红。”《怀德双清堂》:“宋公旧池馆,心迹喜双清。”《青山》:“青山自一川。”《石城》:“石城除系柝。”《忠州弹琴台》:“忠州三峡内,俛视大江奔。战哭多新鬼,琴台日暮云。”一种是将诗题藏在了诗句中,如《黄涧》:“白露黄粱熟,侵篱涧水悬。”《鸿山》:“鸿雁几时到,山深苦多风。”《报恩》:“报主身已老,恩荣错与权。”《清风寒碧楼》:“楼雨沾云幔,寒江动碧虚。清风为我起,临眺独蹰躇。”《文义忆重峰》:“文传天下口,义仗知者论。”这看起来像是文字游戏,却毫无生涩勉强之感。
作为东国诗人,金堉的集杜诗,无论是文字的使用,还是其中的诗史意识、精神内涵,都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精神和气质,但又不会觉得他是在模拟抄袭,这大概就是“言尽矣”与“吾以己言言之”的关系,虽然同样的文字被一再地重复,似乎难以再让人有新鲜感了,但“文学的定义既是必然的重复,同时又是自我消化:作者可以通过一种新排列或是未曾有过的表达成为其知题的‘所有者’。”[12]金堉正是在这样的“新排列”中延续了杜甫的精神,再现了杜诗的特色,让人感受到杜诗在域外的深沉回声与嗣响。
注:
①关于东国集句诗的历史及代表作家可参看:南润秀《潜谷金堉的集杜诗考》(载《中语中文学》第四辑,韩国中语中文学会,1982年,页1-35)、金相洪《韩国的集句诗研究》(载《汉文学论集》第五辑,檀国汉文学会,1987年,页3-74)、朴钐、金程宇《“笔端三昧,游戏自在”:浅谈韩国集句诗》(载《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3期,页123-128)。
②集杜诗收入《潜谷先生遗稿》卷三,《韩国文集丛刊》(86),页47-65。金堉文集有两种版本:一是由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社1975年刊印的《潜谷全集》,分为九个部分,分别是《潜谷先生遗稿》、《潜谷先生别稿》、《潜谷先生遗稿补遗》、《潜谷先生续稿》、《潜谷先生笔谭》、《种德新编》、《潜谷先生年谱》、《潜谷先生家状》、《潜谷先生世乘》。另一版本是由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的《潜谷先生遗稿》,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86册,这是前一版本的第一部分。本文所采用的材料出自《韩国文集丛刊》(86)者,只在文中标明卷数与页码,不再出注。另外,金堉的《朝京日录》与《朝天录》也收入林基中编的《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十六册中,文中亦有引用。
③据《潜谷先生遗稿·凡例》所言,《遗稿》由金堉之子金佐明根据家藏草稿初刊于1670年左右,1683年左右又由金锡胄增补使行日录后重刊,则遗稿编于金堉后人之手,他们不能确定《洪勉叔谪大静》、《题宋生民古书画诗帖》的写作时间,又不忍割爱,所以将其附在五言绝句之末,以致引起后人的误解,将这二题四首诗并入《三涂录》中。
[1]吴承学.集句[A].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十章[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188.
[2]左江.《杜诗批解》之产生背景[A].李植杜诗批解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2-114.
[3]正祖.日得录三[A].弘斋全书:卷一百六十三[M].韩国文集丛刊(267)[Z].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190.
[4]仁祖实录[M].朝鲜王朝实录(35)[Z].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35.
[5]李明汉.白洲集:卷六[M].韩国文集丛刊(97)[Z].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317.
[6]李昭汉.玄洲集:卷三[M].韩国文集丛刊(101)[Z].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233.
[7]李殷相.东里集:卷十四[M].韩国文集丛刊(122)[Z].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561.
[8]潜谷先生年谱[A].潜谷全集[M].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社,1975.478.
[9]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M].四部丛刊正编(六四)[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330.
[10]金堉.回泊石多山[A].朝天 录[M].燕行录 全集(16)[Z].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2.417.
[11]孙卫国.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A].域外汉籍研究集刊(6)[M].北京:中华书局,2010.230-236.
[12]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A].梁溪先生文集:卷一三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