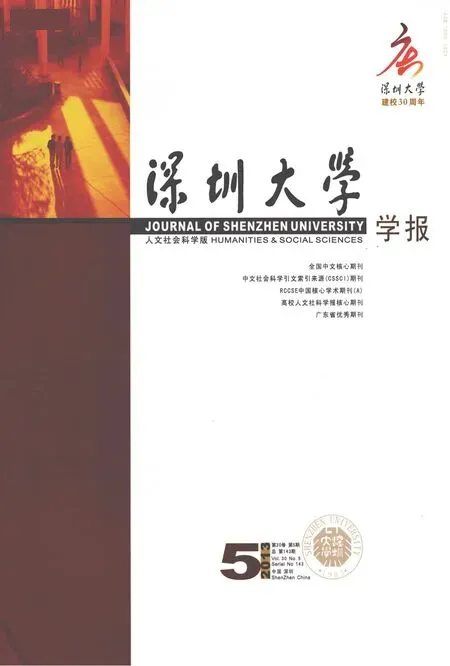设计的诗性
李 平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艺术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在当前技术化与商业化社会,设计的实用性、实证性与合理性被充分考量,设计的人文内涵——本然价值则往往被遮蔽或隐而不显。设计作为发展策略及工具手段大行其道,而其作为人类生存方式与文化方式的深层含义则被忽略而尚未深究。现实与问题是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需要创意设计的提纲挈领,创意经济、创意产业与创意产品的升级需要设计创意的价值涵养与意义范导,设计本身作为日益成熟独立的学科体系与文化形态则需要深层自我反思以自洽自足。全球视野中的本土设计现状落后决非技术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是设计文化自觉与自强问题,毕竟设计之器物价值最终乃是文化之精神的灌注与呈现。设计实践中种种表象化与工具化思维暴露着关于设计的普遍性认知盲区,设计诗性的探讨将当前设计中缺失遗忘而又至关重要的内涵价值与文化意义加以厘清与揭示,以溯源设计原点,彰显设计本体,涵蕴、提升乃至外溢设计—文化软实力。
一、设计的诗性意蕴
所谓设计的诗性,就是设计总有一些溢出具体有用的、当下现实的、科技逻辑的、系统合理的东西,这个溢出是体验的、多义的、模糊的、飘逸的、不可言说的,——设计的诗性是设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这“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道德经》)的朦胧诗性,是设计营造人为之事物乃至进入其创新—创意—创造境界的前行意欲、前摄意象与前瞻意义。例如将科技理性与艺术诗性完美融合的乔布斯认为,应该让新iMac电脑的每个元素都回复自然,电脑应该看起来像花园里的花,它应该像一朵向日葵!向日葵对太阳的积极响应隐喻了显示屏与主机的关系及其获取生命能源的方式与形式,如此iMac电脑流畅、飘逸和自由,显示屏悬浮在空中就像“会飞起来似的”。对“苹果”设计理念而言,产品的外表、材料、架构都应该产生一种效果,这种效果给人的感觉就像讲述一个故事,就像一首诗,由此其设计就于机械逻辑之外又洋溢着美的意境与诗的品质,“苹果”不仅是可用的产品,更可触动人心。乔布斯说他不喜欢一般点式的按键开关,因其让人联想到如生与死的截然切换,而如今苹果手机的滑块式开关方式带来的是一种从手到心操控自如、反应灵敏、耐人寻味而引人入胜的触觉—感觉,在开与关之间体验到的不再仅是单一功能的完成,而且有着更丰富更自由的意味氤氲,这意味着来自自然、生命、艺术也来自哲学,乔布斯将东方禅学融会贯通到“苹果”设计思维,在产品设计、生产、使用过程中伴随始终的是从悦耳悦目、悦心悦情,再到悦意悦神的模糊多义、自由飘逸的意味,就是设计之诗的生成,设计之诗性的呈现。从这个过程中,产品由一物理之物化身为人之生活的上手用具、心爱之物,成为将人带入世界的器具,物人合一展开其生存运动。如海德格尔的“物”就是一种“聚集”,桥是一物,一座桥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行,更在于实现了一种聚集。桥把河流、堤岸、树木、田野聚集起来而使之成为一道具有意义与主题的风景,桥把这道风景带上前来,带到人们面前,带到世界面前,带入当下生活,带入此在生存,一种聚集就实现了一个意义关联整体,一切原本沉寂无声的自然自在之物由此有机整体而获得新生并发出光芒。壶是一物,一把壶也是一种聚集。壶聚集了山泉的流淌、岩石的坚毅、天空的清澈、大地的供养,壶把这聚集带上前来,带给生活,带给饥渴的人们,也带出存在的意义。由此聚集之物为契机,产品—物—事物成为天地神人四方共舞的游戏,展开人与自然之间激荡回旋的饱满意蕴与丰沛诗性。
设计的诗性并非设计的诗意,即设计的诗性不仅是一种意味而更是一种本性,一种自始至终、彻头彻尾、由里而外的本然之气质、本体之特性。可以说,设计核心里与通体处都是诗的——技艺相通、情理相融;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终极所向,飘逸灵动。无论功能还是形式,技术还是艺术,制作还是创意,实用还是理念,设计的诗性渗透于设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蕴含在设计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诗是现实的抽象概括、高度凝练,设计则是问题的解构重构、符号表达。设计与诗有其本原的方法相关与形式相应,或可说无诗就无设计。没有一个设计不是一个符号、一个意象——一首诗,当然,如果它是一个“好设计”的话。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事实表明,只有用“诗”才能充分表达出优秀的设计。
二、存在,设计的诗性契机
设计的诗性首先指向设计之本源探寻,存在,则是设计者之本源,是设计之器、事、物这些世间存在者之本源。本源蕴涵着缘由,也蕴涵着神秘,即设计之为设计,设计之诗的神圣与隐密。
“在意蕴世界先行理解着存在而生存着”是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基本生存方式,即人的生活不仅是物质功能的生活,更是追问意义的生活,人的理想存在必须是充满意蕴的存在,是如同需要空气一样而需要意义的存在。海德格尔曾论及这个存在结构,“存在者总是就其存在而被言说。在所有对存在者的自然解释中都有一个特定的存在意义在引导着,它无须在范畴上是明确的。”[1]因为“‘在世界中存在’的缘在自身原初地就具有意义,存在问题在缘在不确定的前理解中才出现。”[1]因而生存自发性本身是构造的—创造的,同时是构想的—想象的,这个境域或恰恰可用“诗”来描述与命名,“无须在范畴上是明确的”与“不确定的前理解”都刻画出前理论的实际生活经验结构的原生性、混沌性与体验性等诗之特性,存在意义对存在者的引导无须在范畴上是明确地表明这种引导不是以理性明晰知识而是以诗意朦胧体验实现的。或者说在具有明确认知范畴的理论理性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前理论范畴与非理性认知的原经验—原体验境域,这个境域或更贴近存在,是与存在息息相通的生命本源与真理本真之所在。而作为对象化与课题化的派生之物,创造的密码与设计的奥妙只有在这生存之诗的本源境域中才得以领悟与探明,在生存自发性意义上设计也原始地获得了其诗性基因。
设计不同于科技之处正因其基于人的生存境域而非纯粹的物理规律来策划与言说,基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而非单一的理性逻辑去思考与创造,向着未来、可能、理想去行动,去生活,去创造,就呈现了此在的存在,同时也展开了设计的真理。法国设计师斯塔克的设计是面向未来、意在笔先的,他认为设计即是创意。意是事实背后的思维观照与文化想象,它将物理功能以文化的亦即人性的方式实现,人在对物的使用同时感受了启示的快乐与想象的愉悦,这正是作为文化动物之人的本源深沉而真实入微的生命方式,设计之诗如此将其激活并创造了一个“产品”,这正如他所设计的如昆虫又如外星探测器的榨汁机因此而具有了多重意蕴与多元功能。
当深入到设计与存在的关联底蕴,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探讨设计诗性本源的视角。在生活与生存的根基处,由存在论的境界,设计而彰显其本真价值与终极意义,设计的诗性就呈现出来。“只有在人并不执著于可对象化的‘有用性’而能领悟‘无用之用’时,也就是说‘在这种真正的在..之间里,人才栖居着’,人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才得以展开。”[2]设计之诗就是存在源头的泉涌,生存原点的光辉,彰显设计的诗性就是揭示设计的存在论意义,以及设计与生活、生存之内在丰富的根本关联,展现设计诗性在这种关联中的生成与生长。
三、语言,设计的诗性禅机
存在孕育设计的诗性契机,语言则呈露设计的诗性禅机,道说着设计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奥妙音律。设计的表达之所以关系于语言,在于设计活动的意向性与符号性。人将自己的物质需求委任于设计,同时将心理与精神的追求也融入其中。设计不仅要回答事物是什么,还要回答事物为什么;不仅制造科学的“实是”,还要创造美学的“应是”。正是理想的“应是”引导现代设计脱胎其传统工业制造的母体,进化为人类文明创造的新方式与新座标。设计的表达因而不止于指示事物的信号,更需有解释事物、表现事物的语言—符号。设计的意义指向不断拓展设计的内涵与外延,建构起设计的语言符号系统。产品材料、形态、色彩、结构等语汇构成有机整体的语言系统,不仅传达功能使用等技术与物理信息,更传递形式风格、心理感受、文化象征等精神意义信息。设计语言的特征在于其异质同构性,设计语汇是表达多重、多义乃至对立含义的多重译码,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技术与艺术等等设计词汇相互渗透、相互映射、隐喻象征而交织成环环相扣、层层勾连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网。当设计触及了形态的隐喻与象征,并由此建构人造事物的语言符号系统,就触发了诗的模糊多义,映射、隐喻与象征,闪耀着设计之诗的点点光辉、语言禅机,一种人物合一、物物相生、人物天交相辉映的互交结构即时显现。例如鸟巢以交织穿插的钢铁线性语言表现通透结构与动感空间,表达一种工业与生态隐喻;而水立方的朦胧膜性语言则将表皮与肌体、透明与封闭水乳交融,呈现一种技术与艺术隐喻。相互映射、相互隐喻消弭了异质之物时间的阻隔与空间的屏障,设计诗性语言宛然一种强大的公约语符与通约语法,化解了异类各自的独立与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至彼,由彼至此,在相互指涉、相互解释、相互同情的审美共生中重塑自身并重构彼此。异己各自的存在意义生存意向与设计价值在相互映射与相互隐喻的禅机瞬间得以激活并融会贯通、升华并全新呈现。
语言的隐喻召唤设计之诗忽隐忽现地出场,设计诗性若即若离地表现。设计也是一种筹划,其语言也必祈向存在的道说禅机。“筹划着的道说就是诗”,设计以其形象—形态—形式道说,它们是设计的意味、意象、意义语言,是设计的诗意家园。实用功能囿于物理时空的实体价值,因只能供少数人使用而具有偶然性与特殊性,但设计形式则携带超越时空的审美意义,可以让无数人共享而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当远古的彩陶、青铜器,远方的金字塔与圣母院对我们而言不是用经验的对象而是看体验的对象时,当人们不只消费设计之物的实用价值更是消费其文化价值时,设计“无用之用”的深层人文价值与精神审美意义或可得以更纯粹透彻与酣畅淋漓地表现。是沉淀并凝结于设计语言符号中的悦耳悦目之形态、悦心悦情之内涵、悦意悦神之意义,将设计带向其本然家园,带到其诗性境界,带入其终极存在。
语言,映射出设计的诗性禅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隐喻着设计造物之时不同的感悟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表达方式,呈现着设计由此而成的丰富多彩的风格类型。如语言的转喻利用不相类似但又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将不同类事物相互关联、相互指代,表现了一种求真的科学思维。其典型的表现如现代主义设计,遵循“功能第一,形式第二”及“形式服从功能”的合理性原则,并由此形成现代主义设计简洁划一的“方盒子”语言。转喻建筑中几何平(立)面、钢架结构、玻璃长窗、重复节奏中涵纳的科技理性,整体表达其对功能、技术、材料及大批量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及需求状况等的全面考量与合理应对,而当房屋终于成为“居住的机器”,“方盒子”发展为国际化机器美学风格,“喻”之诗性语言就游离而出。例如密斯“皮包骨”的西格拉姆大厦,那修长优雅的比例、晶莹剔透的表皮、嶙峋致密的紧张骨感,乃至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对上帝光辉的绵绵映射,就不断传递给人们超出其物理功能的机器美学的诗意信息,将现代主义的功能语言发挥到了机器美学的极致。
提喻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即认为人与世界相似相应、浑然一体而可达成生命主体间的对话与交流。生命提喻展现了无限的世界,即需以局部代整体,用现象界中的某个或某些局部的东西来指称形上本体,强调形上本体是大全,而现象界中体验到的事物只是大全的部分或代表,故提喻属于象征范畴,如安藤忠雄的“光教堂”就是提喻设计的典范。“光教堂”中清水混凝土的墙壁上镂空的十字架意味无穷,将人引向无限的时空穿越的诗性遐想。光由此透射进教堂内部形成巨大的光的十字架,风、空气、自然、宗教与光流转化凝聚出“光”之诗意符号,表达着宗教的神秘与信仰的神圣,“光”之空间内外充满了诗意的曼妙挥洒与弥漫震撼。提喻如同转喻,是对形上之道的正面观照与呈现,转喻求真,提喻由真而美,其设计语言显然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抒情诗意,设计的人文意象与审美意境更加明晰纯净、充沛饱满。
讽喻是悖谬性思维语言,如“圆的方”、“木的铁”之说,是人们用否定的语言,用负的和迂回的方式来表达对宇宙无限的追问。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设计实践更多地表现出讽喻思维与语言色彩,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以“非”、“反”、“讽”句式表达设计的哲理思考与前沿探索。索特萨斯产品设计解构中的多义结构、盖里近乎疯狂地破坏中的空间建设、哈迪德亦真亦幻的“圆润双砾”重构的城市景观,设计中的线性思维都由讽喻演化为非线性复杂思维、混沌意象与悖谬语言。“‘圆’的方”当然是一种广义与象征的说法,“圆”意指一切对“方”(本体)的游离与反拨而形成的充满多义、模糊与张力的意义形象。我们同时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种普遍性的设计方法,即在转喻与提喻的语言中,都或隐或现地闪现着“‘圆’的方”——讽喻的身影——对现成化的游离与突破。
四、时间,设计的诗性动机
诗性设计必与时间相融汇,由时间而永续。时间意味着日月流转、光影变化,这自然的脉搏与生命的韵律照亮了建筑与景观,舞动了空间与环境。时间意味着生生不息、推陈出新,这运动的千变万化与历史的丰富多彩塑造了事物与产品,创造了生活与时尚。开启设计的时间不是单维直线的流俗物理时间,而是往复回旋的本真存在时间,本真时间是人——此在面向未来创造历史的先行筹划。融入本真时间的设计诗性构成永不停息、永往直前、永远创新的设计意象。设计与时间互为意义,“时间”到达,就开启设计之诗。对设计而言,无论功能形式,还是材料技术,甚或时尚市场,都会时过境迁、风光不在,只有先行到未来的存在时间,作为设计的前摄引导,才能不断开启并促动设计创新的持续发生,涌现设计诗性生命的原始脉动。
现象学家胡塞尔将人之历史存在与生活世界的最终明见性归结为“进行最终构造的主体性的时间结构。这种主体性总在历史的当下将自身构造成时间性的东西,亦即赫拉克利特之流本身”[3]。赫拉克利特之流因其“不能以对象化的反思方式把握,也不会由被对象化的把握所穷尽”,而“将在总是超越自身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中持续向前伸展”[3]而生生不息,成为“贯穿一切变体的本质普遍的持存者……作为总是被蕴涵在流动的、活的视域中的本质。”[3]时间是主体创造的赫拉克利特之流,是设计诗性的内在生长机制;时间构成存在与生活创造的绝对前提与永恒动力,是世界万物变中之不变、不变中之变。如现代设计的经典产品——汽车的逾百年设计历史就是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历程,汽车作为伟大的产品,实现着人类千百年来对距离与速度的梦想,福特的流水线实现大批量生产与大众化市场,商业化设计将汽车变成了艺术品。而今,车—人—环境—生态友好成为汽车设计的基本原则,概念车、智能车、新能源车、多功能车、仿生车等让未来汽车设计更加富于理性又充满了无限诗意。生命、生存与时间水乳交融的一体化结构揭示了人的时间性是由存在意义所扩展了的生存时间,“从已经向尚未的扩展是其基本的结构,它出自在牵挂中被确定的先行而一同牵念着它的过去,并一同把自己带入现在,这种时间性使得缘在成为历史的。”[1]在人独特的内在时间中,过去、现在与未来渗透交织,现在既有对过去的保持,又是对未来的预持,人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映射不断涌现的时间流、意识流、生命流中。这是回旋往复的时间与空间,意识与存在。这个由内时间意识主宰的生活世界与实际生活经验是设计的背景与基础,在这个时间之流的大视野与大背景中,设计的诗性总会以源生的与原发的姿态来到我们面前。
时间性表达了终有一死者“人”之生命意蕴,终有一死突显出生命的历史性、个别性、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与自由创造性。在具体个别的生活中,人作为在世界中独一无二的自我而存在,践履具体、鲜活的生存经验。“实际生活经验自身就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它在其当下各是的境域中时机化自身,在畏和痛苦中决断自身。”[1]世界与存在通过个人之“畏和痛苦”成为可感知、可体验、可触摸的,个体也成为生活与生存创造时机的感应者、捕捉者、承诺者与担当者。时间的意义进一步在想象与创造的设计诗性视域敞开。想象带来一个源头上的开端与一个原点上的建立,制作和想象统一创造了全新的事物,同时使创造者的此在世界豁然敞开。创造开创了本真的生存时间,终有一死的特殊此在——人的存在由此时间才得以开始、得以结束、得以呈现、得以意义。对此苏格拉底感悟:“我与时间相遇,我与时间相蚀,我必不辱使命,得以相遇众生。”想象开启了时间,开启了存在,也开启了人生,开启了创造—设计。
相对于理性设计,诗性设计更凸显出个体的生命意义与创造价值。时间—生存—生命—个体—诗性,这其中的逻辑是,理性是可被一般认知与共同接受的,因而是普遍的、共性的;而诗性是心领神会同气相通同声相应的独特体验,因而是特殊的、个性的。又恰恰是诗性设计的独特性才能精准触发人类审美精神的共通性,并经由此否定之否定路径将理性设计诉诸认识层面的一般普遍性升华为诗性设计穿越生存层面的终极普遍性,从而实现诗性设计独特性与普遍性的水乳交融、融会贯通。因此,开启设计诗性动机的时间性必然融于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与创造之流动中而生成与涌现。设计师个体—个性价值将伴随着经验设计→理性设计→诗性设计的弘扬而凸显与张扬,可谓越是个性的就越是共性的,越是独创的就越是典范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总之,契机是一种因缘,即设计之诗由存在而生发。本真存在是天、地、神、人四元共舞的游戏,融入存在,就发生设计之诗,或诗性设计必然与存在相融通。而禅机是一种显现,即设计之诗由语言而表达。本真语言是存在揭蔽真理敞开的道说,语言之喻,就映射设计之诗,或诗性设计必须与语言相融合。动机是一种永远,即设计之诗由时间而永续。本真时间是面向未来创造历史的筹划,时间到达,就展开设计之诗,或诗性设计必将与时间相融汇。
当设计遗失诗性,就失去了与宇宙自然及人类生存本源的整一性。设计的诗性呼唤设计的本真之性,它召唤设计成其所是,设计成为存在者,成就世界的万事万物;它也召唤设计成其所不是,设计成为存在,融入永远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
[1]朱松峰.论海德格尔马堡时期的思想演变——以“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点”[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44-51.
[2]范玉刚.睿思与歧误——一种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审美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05.
[3]李云飞.“生活世界”问题的历史现象学向度[J].哲学研究,2012,(6):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