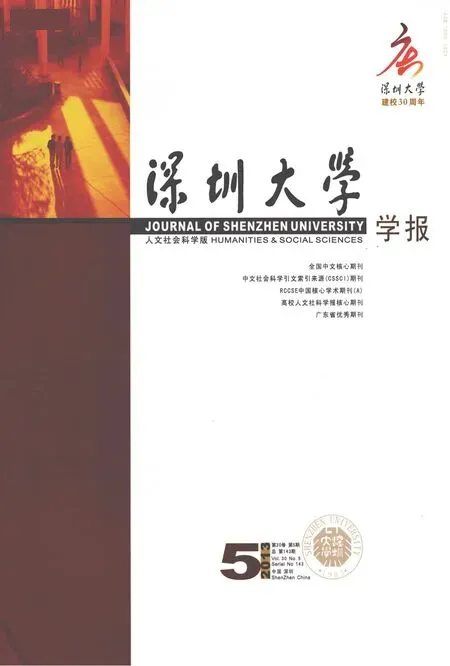做贤妻还是恶妻: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突围与困境
童晓薇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贤妻”与近代日本的“贤妻良母”教育
日本的女子教育是在明治维新后掀起的文明开化浪潮中发展起来的。明治以前的女子教育强调女性的“贤妻”身份,注重“女德”,强调顺从、贞洁、谨慎等所谓的妇道。尤其到了近世,战乱平息,社会逐渐趋于安定,为加强对天下的控制,德川幕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巩固封建“家”制度和封建统治,“女德”更是成为女子教育的核心内容。刊行于1716年的女德教育教材《女大学宝箱》,通篇强调的都是女性为人妻为人媳应遵从的道德规范,将女性置于社会与家庭的最底层,把她们当作繁衍后代的工具,要求她们绝对服从男性的支配。如第1条提出:女子皆要出嫁以事公婆,故需自幼受父母之训诲;第3条:女子须正男女之别;第6条:以夫为主君,敬慎侍奉,不可轻侮;第7条:尽孝养于公婆甚于亲身父母[1]。因此江户时期女子教育虽也教授女子习字读书,但花了更多力气在培养女子的女红技艺上,织布、缝衣、料理等成为近世女子教育中重要的教育科目。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将教育纳入国家建设的重要环节,大量介绍西方教育理念的书籍资料被引进到日本,并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促进了女子教育的新发展。创办于明治初期的日本最早的近代学术启蒙团体明六社中的成员便是日本女子教育的积极推动者。明六社会长、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等人通过对封建妇德的批判话语的建构,提出女子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和知识的母亲[1](P64)。即“贤妻良母”教育。中村正直特别指出,所谓的“贤妻”,不是对丈夫一味服从,而是具有“亲爱四分、女子意见二分、巧智一分、美丽一分”的“好性情”和“二分良善之教育才艺”,能“辅助丈夫”的伴侣[1](P69)。相比近世的女子教育,近代女子教育肯定一夫一妻、夫妇平等,且女性具有学习知识的权利。但女子教育的目的不是谋求女性自身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把她们培养成“贤妻”和“良母”,所以爱心最重要,一分姿色一分巧智增添女子的俏皮趣味,在遗传学上也自有道理,女子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不要太多,充分理解丈夫且能辅佐他的好性情和才能最可贵。正如1899年当时的文部大臣在《高等女子学校令》公布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育宗旨在于,使学生具备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所必需的素养。故而在涵养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的同时,要令其通晓中流以上生活所必需的学术技艺[1](P162)。试图通过“男工作,女家庭”的分工模式,使女子教育最终与国家近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近代以来,随着女子教育体制的逐步确定,“贤妻良母”思想在人们思想中扎下了根,甚至是一些思想开明、对女性境遇充满同情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大正三年,森鸥外发表了小说《安井夫人》。在经历了异国苦恋和婚姻不幸之后的大作家仍然没有获得安宁,他的妻子森茂子个性强烈,与他的母亲严重对立,使夹在其中的作家痛苦万分。在这篇以汉学家安井息轩和妻子佐代为原型的小说里,森鸥外以他的方式提交了自己理想中的妻子形象。佐代年轻貌美,看上了被姐姐拒绝的相亲对象。对象仲平虽满腹学识,却满脸麻子,独目,肤黑,个子矮小。尽管儿子面目不堪,仲平父亲对择媳却自有一套想法:“无论多年轻俊美之人,交往一段后,智慧不足之缺陷都会暴露,其俊美容貌终会被忘掉。……相反,有才识之人,即便容貌有瑕疵,交往一段,其丑陋会被淡忘。”。关键在女方能否慧眼识珠,这是为女人的智慧所在。“我要一个能‘识人’的女子做儿媳”[2]。佐代正是拥有这样的智慧的女人,不仅如此,婚后她一改往日内向的性格,乐观开朗,16岁出嫁到51岁因病离世,她不辞辛劳一心侍奉丈夫,抚育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终日身穿粗布,饮食简素,无欲无求,任劳任怨。她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婚姻,依照自己的意愿将一生奉献给了丈夫和家庭。作者通过这样一段画外音表达了自己对佐代的生存方式的认同。
“佐代一定有不寻常的愿望。在那个愿望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像尘芥般卑微。佐代期望什么呢?世间的贤达会说她期望丈夫的飞黄腾达吧。作为作者的我也不能否定。但是,就如商人投资是为牟利,佐代为夫坚忍劳苦,还未获取报酬即撒手人寰,从这方面说,我不才,不能同意上述说法。佐代一定对未来有所期许。她美丽双眸的视线一直投向远处,直至最后一刻。或许,她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死是种不幸。”[2](P189)在作者心目中,佐代是新时期的贤妻的典范诠释,有主见,又有无私的献身精神。
二、“恶妻”与“新女性”的等同关系
与“贤妻”相对,“恶妻”一般都不会将丈夫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她们性格好强任性,甚至善妒,过分强调自己的主张和意见,不服从丈夫的意愿,经常与丈夫口角相争,甚至离家出走。“恶妻”中的多数女性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新思想,对女性与男性的认识与传统伦理观大为不同。作家坂口安吾曾说:
“(人间)地狱的发现这是近代又一大发现,使地狱之火燃烧,在地狱中度过一生,需要的与其说是本能,不如说是对事物的判断力和思考力,即知性。所谓的贤妻,是无知性的存在,一旦有知性,女人必将变成恶妻。知性,即对人性的省察,经省察之处,体贴同情之心或许会加深加强,同时其冲突的深度亦在人性深处进行,进退两难。
对人性的省察,于夫妻关系上便如妖怪的眼,夫妇相互知晓其缺点、弱点,不如说在缺点之上加深关系和对立。这种对立会成为进退两难的东西,憎恨加深,没有安心感。联结夫妻的,苦痛大于和平。”[3]
坂口安吾指出了“恶妻”所以为“恶妻”的症结所在。她们有知识,有判断事物的能力和思考能力,对人性有省察,这使丈夫的存在和意志失去了绝对化。在近代,“恶妻”往往和一群活跃在都市中的女性联系起来,她们是所谓的“新女性”。
日本“新女性”(新しい女)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治末期。文艺界在介绍易卜生等西方现代戏剧时,注意到剧中的女主人公由过去的“贤妻良母”变成了追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但将这个词真正具象化的是创刊于1911年的女性杂志《青鞜》的一群女性。1911年,以平塚雷鸟为首,包括保持研子、与谢野晶子、物集和子、中野初子等女性以促进女性的觉醒、发挥各自天赋特质、培养未来女性人才为宗旨,组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性文艺社团“青鞜社”,创办了文学刊物《青鞜》,将当时一批有知识有主见的新女性长谷川时雨、与谢野晶子、岩野清子、田村俊子、野上弥生子等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女性问题,并宣称她们是一群“新女性”。平塚雷鸟在发刊词中写到:“女性本来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天,女性成了月亮。成了依赖他人生存,依靠反射发光的如病人的脸般苍白的月亮,终有一天(指女性自立),女性将重新成为太阳。成为真正的人。”[4]这堪称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的女性独立宣言。新女性们以《青鞜》为基地,以小说为武器,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恋爱、婚姻、家庭、性等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她们“首先向重视妇德的‘贤妻良母’思想提出挑战,批判‘贤妻良母’思想对女性个性和自由的扼杀,从而批判明治政府制定的女子教育制度,认为这种男权中心话语下的女子教育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男女平等,只能按男性欲望培养能够更好教子相夫的家庭附属品。”[5]因此,《青鞜》从出道伊始便遭致社会上传统教义派人士的责难和非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在实际生活中,这群新女性也经常做出些离经叛道的让人惊骇的行为。平塚雷鸟就是一个代表。1908年3月21日晚,平塚与作家、夏目漱石的门生森田草平相约从田端搭乘电车前往盐原殉情自杀,中途改变心意,殉情失败。曾造成当时社会一片哗然,又被称作“盐原事件”或“煤烟殉情事件”①。
尽管此事件发生时,平塚并未失去贞操,但社会依然对她婚前与男性离家外出、夜不归宿的行为大加指责,并恣意想象、讨论她的贞洁问题。《青鞜》创刊当年,她与比自己年少七岁的尾竹红吉玩同性恋游戏,并同登青楼与妓女畅饮欢谈,也曾引起社会保守人士的极大反感[4](P52)。
《青鞜》时期,众多的女性作家作为《青鞜》赞助员参与了对传统的贤妻良母意识形态的挑战。她们在作品中,也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了父权制的反叛者或逃逸者。其中不乏名人之妻。如长沼智惠子——著名诗人、雕刻家高村光太郎的妻子,与谢野晶子——著名诗人与谢铁干的妻子,冈本加乃子(岡本かの子)——著名漫画家冈本一平的夫人,田村俊子——幸田露伴的弟子田村松鱼的妻子,国木田治子——著名作家国木田独步的妻子,冈田八千代——著名画家冈田三郎助的妻子,森茂子——著名作家森鸥外的妻子,岩野清子——著名作家岩野泡鸣的妻子,野上弥生子——著名作家野上丰一郎的妻子,等等[4](P59),不一而足。这群身为人妻的女性中“恶妻”居多,她们与克己忍耐的传统贤妻良母大为不同,思想前卫,行为大胆,具有较强的自我主张和意愿,与丈夫的关系“苦痛大于和平”。
冈田八千代,著名戏剧家小山内熏的妹妹,青鞜杂志积极的撰稿人,1906年与三郎助结婚,因丈夫以自己为原型作画而不满,造成夫妻不和,1926年遂离家独自生活。冈本加乃子,1901年与一平结婚,婚后因丈夫的放荡不羁以及两人个性,时常发生冲突,生活非常苦闷。长女的夭折让加乃子对丈夫彻底绝望,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将自己的崇拜者堀切茂雄招至家中,开始一女二男的同居生活,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夫妻关系。岩野清子1904年因与有妇之夫的不伦之恋跳崖自杀未果,同年末结识同样心灰意冷的泡鸣,两人意气相投,更因为泡鸣承诺将她培养成一名作家,清子决定与他共同生活,但同时提出同居条件:拒绝发生肉体关系。森茂子,嫁给森鸥外时年轻貌美,是个热爱戏剧文学的时尚女性,但脾气不好,与婆婆关系极差,甚至坚决不与婆婆在同一饭桌上用餐,并坚称自己嫁到这个家是来做妻子的,不是来做婆婆的孩子的。森鸥外在小说《半日》中严厉指责以妻子为原型的女主人公,认为她没有丝毫克己之心,骄傲任性,不懂得尊重婆婆,完全是个“恶妻”,从而使茂子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有名的 “恶妻”代表。田村俊子与松鱼结婚后经济困窘,时常捉襟见肘,而俊子经常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丈夫少有体贴关怀,夫妻二人不时争吵甚至大打出手。俊子在应征写作入选后,二人的关系更是发生倒错,丈夫留守家中,妻子则出入社会,活跃在文艺界人士中间,最终导致两人离婚分手。
实际上,“恶妻”们是一群率先拥有自我意识的女人,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向传统的家族制和贤妻良母思想表示不满和抗议,希望自己决定女性的性别角色,并期望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诉求,体现自己身为女性存在的价值。正如平塚雷鸟在自传中回忆《青鞜》时期时说的那样,“当时女性的出路——除了贤妻良母主义之外,妇女的生活目标不被认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社会上既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自由的妇女们,借助思想、文学在内心世界谋求自由,希望在那里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自己的生命”[6]。作为一群坂口安吾定义的“知性”女人,她们必然与丈夫和传统家庭产生龃龉,男性冠以她们“恶妻”称号,无非是想将女性重新纳入贤妻良母机制中,使她们成为家庭的附属品。就像森茂子,她其实远没有森鸥外描绘的那么不堪,她家教良好,正直有个性,不善妥协。从森鸥外的《舞姬》和《半日》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森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式的人物,对媳妇多有苛刻之处。茂子与她敌对,实际上是在和整个传统的贤妻良母思想敌对,和压抑女性的家族制敌对。但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更由于女性自身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向往,女性作家往往很难彻底摆脱男性和家庭独自生活,她们在自我与家庭的夹缝中求生存,艰难寻找自己的道路。纵观日本近代女性创作史,女性作家们均面临着是成为一名作家作“恶妻”,还是放弃自我做“贤妻”的选择,这种艰难的选择造成了女性创作的困境、写作本身的困境以及写作主题的表达困境。田村俊子的短篇小说《女作者》便呈现出这个问题。
三、田村俊子的《女作者》与女性写作问题
田村俊子曾被称作“樋口一叶第二”。因为她是继樋口之后日本近代第一位真正的职业女作家,也是大正初期风靡一时的女作家。她曾师从幸田露伴,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和文学修养。1911年她在《青鞜》创刊号上发表小说《生血》,描写了初夜后的女人对 “夺去”自己贞操的男性既憎恨又难舍的复杂心情,从性的角度表现了新女性对两性关系中“侵犯”与“被侵犯”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的抗拒,从而声名鹊起。她创作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主题几乎只有一个:女人和男人,均从新女性角度,展现女性自我在家庭生活中与男性发生的冲突和纠缠。
1913年,田村俊子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女作者》。女作者的身份有两重:作家和妻子。前者代表了她试图从家庭这个私人空间突围到社会那个公共空间的自我的野心,后者则显示了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扮演。女性选择从事文学创作,是她走出私人空间,走向社会空间的第一步。写作可以在一个相对隐蔽的私人空间进行,“不容易引起社会批评的注意,女性向社会发展的力量可以比较少受干扰而生长。但对女性而言,社会批评的压力又在无形中存在,女性不仅担心自己不成熟的社会经验可能让她的写作招致批评,甚至女性本身从事这种不适合身份的写作活动,就可能是不名誉的,这些顾虑使早期的女作家不敢公开自己的写作活动,在女性早期的写作活动中,女性感到的压抑和女性渴望突破的愿望,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7]相比西方一些女作家为掩人耳目采用男性笔名,或甚至如乔治·桑着男装、吸烟斗,混迹于男性中间的行为,田村俊子的女作者则采用更日本化的方式。
“这个女作者经常脸涂白粉。尽管已是年近三十,依然画浓妆。无人时,化上舞台上那种浓妆暗自欣喜。”“必须写作而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个女作者会抹上白粉。而且,只要坐在梳妆台前用水溶解白粉时,定会想到一些有趣的话题,这已成惯式。白粉溶于水,冰凉触及指尖,这个女作者觉得仿佛如一次新的心灵触及。然后将白粉抹在脸上的过程中,想法逐渐成形。——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这个女作者的作品大抵都是从白粉中诞生出来的。”[8]
脸抹厚厚的水白粉,自然让人联想到诞生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日本艺伎。艺伎们表演时,会在脸上涂上厚厚的白粉,只在后颈处留下一块不抹,从侧面看上去仿佛带着一张假面具。其功能正如日本传统艺术歌舞伎中男扮女装(女形)者脸上抹上厚厚白粉一样,为的是遮住本来面目,转换角色。作为新女性的女作者在写作时将自己的脸涂抹成艺伎一般这个不同寻常的行为或许具有两层意义。一是掩饰自己的传统女性身份,通过面具,使自己从女性向女作家身分转换,摆脱女性身份对自我的束缚,同时构建一个非现实化的空间,以暂时摆脱家庭这个以男权主体的现实空间对女性的压制;二是水白粉作为一种化妆用品,其本身具有将女性妖媚化和满足男性窥探欲望的诱惑性,女作家用它遮盖新女性的素颜,示之传统女性的美,显示她内心的矛盾,既渴望逃逸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又希望用一种男性话语中的美或媚来维持家庭的平衡,从而获取某种安全感或刺激感。
在成为作家之前,女作家首先是妻子,与丈夫自由恋爱自由结合。小说中,田村俊子代替女作家作了如下的独白:与其说是初恋,或许不过是这个女作家奔放的情感虏获了一个年轻男人。但是那时因这个年轻男人而突然弹跳的心蕾的破片,现在依然楚楚可怜地在心的角落里守候着碎影。这个女作家对现在这个男子的温情正是从那影子里渗出的一滴露珠。这滴露珠必定会不断渗出直到这个女作者的生命结束[8](P303)。既然爱情仍然存在,按照传统的两性观念,最好的家庭模式就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应该承担相夫教子的责任,做一个贤妻。无奈的是,女作家是一个新女性,她无时无刻不在为“自我”的认识和定位感到焦虑,呼唤着“我的自我”“我的生活”。在随笔《微弱的权力》中,田村俊子坦白道,在我的生活里,某种微弱的权力一直跟随,那微弱的权力时常轻按我心灵的双翼,当我欲赶走那微弱的权力而焦躁时——然后相信自己已经赶走那个权利的瞬间,我才能稍许认可自我的影子和自己的力量[9]。
这个“微弱的权力”是什么呢?是一种压抑她的自我的力量。这个自我是田村俊子在多篇作品中反复提到的对艺术对写作的追求上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与现实中身为人妻的自我产生矛盾,导致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压抑着她,即做贤妻还是恶妻的问题。《女作家》的主人公显然希望兼顾,她涂上白粉掩饰自己不同于传统女性的真实面孔,当为写作苦恼时向丈夫哭诉期求他的帮助,有意通过男性(强有力)—女性(弱而小)的男权社会规定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缓解家庭暗藏的危机。但当她的写作遭到丈夫的蔑视,那张水白粉涂抹的面具立刻被她撕下,她用激烈的方式冲撞丈夫,用膝盖顶他的背,揪他的衣领,用力扯他的衣服想把他变成裸体,甚至将手伸进他的嘴里想撕裂他的嘴,所作所为与贤妻大相径庭,用其丈夫的话来说,俨然是个“泼妇”[8](P300)! 对女作家来说,身为人妻的自我和追求艺术的自我难以调和。其根底依旧在于:
其一,在家庭里,男性的自我如磐石般坚固不易动摇,它使女性的自我他者化、边缘化。女作家常常觉得与丈夫的“交流”流之于无聊。她说:“我要和你分手”,丈夫的回答一定是:“噢”;她说:“我还爱着你”,他则淡淡地答道:“是吗?”并未将她的想法当真或放在心上。因为“无论是眼前溜走的每件事,还是深入内心的每个人的感情,这个男人都无所谓,将一切从自我这个东西上滑走。”[8](P305)面对男性强大的自我,女作家觉得自己的自我无处安放。
其二,男性对女性写作的蔑视。这主要涉及到女性写作写什么的问题。近代女性作家的活跃曾引起男性的反感甚至是敌视。明治41年,《新潮》杂志上刊登了小栗风叶、柳川春叶、德田秋江、生田长江等当时知名的男性作家各抒己见的《女流作家论》一文。据台湾学者吴佩珍的研究调查可知,对女性作家的写作,男性知识分子们保持了几乎一致的口径:
“有女性特质,坚强,尖锐,激昂,讽刺,充满恶意的话为佳。但是近来的女流作家鲜有女性特质。姑且不论其作品优劣,由于我不满其缺乏女性特质,所以我不太读当今女作家的作品。”
“如果不断地以一般文学的取向来要求女作家的话,是太过苛求了。所以只要要求其到达一部分文学的标准便足够了。所谓的一部分指的是只要求她展现女性特质之处,此外无他。”
“日本的女流作家只要樋口一叶一人便足够了。女人有时间用来写小说的话,还不如花心思让丈夫吃点好吃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要装腔作势了。——我们不要从女性那儿听男子的假声,如果是女人便像个女人一样,发出你悲切痛苦的声音如何呢?”[10]
在男性看来,女性写作没有问题,关键是写作的内容应该表现男性无法表现的唯女性有的气质与特点,它不应该踏入男性的生活空间与精神领域评头论足,更不应该有颠覆现有秩序的企图。当然,她们什么也不搞,安心呆在整个社会机制为她们设定的归宿——贤妻良母的位置上,最妥贴了。《女作家》中,当女作家向丈夫哭诉自己不知道写什么时,丈夫说了下面一段话:“今年一年你就写了几百页,说什么没东西可写,说到底还是你不行。要让我来写,一天就可以写上四五十页!到处都是可写的,不是吗!周围到处都是题材。写写生活的一个角落不就行了!比如邻居家兄弟吵架,弟弟霸占了家,不让大哥进门,这些事拿来就可以写。女人不中用!……”[8](P299)这段话的解读直指男性对女性写作的态度,(一)在父权制社会形成的女性审视视野中,女性不具备艺术创作的智慧和能力,她们要么是打发闲暇时光,要么利用社会的猎奇心理用写作挣点钱财,实际上田村俊子本人的写作正是在丈夫的要求下以挣钱为目的开始的。(二)女性写作应该在父权制社会的框架下进行,例如批评一下长子继承制受到的威胁,维护父权制社会的核心体系,故事的主角永远是男性,不应该被女性所替代。
但是女作家所追求的艺术上的自我,恰好与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她渴望写自己想写的,即通过写作摆脱男权话语对自己的压制,让自己得以从现实空间暂时逃逸到文学空间,而不是充当她要竭力逃逸的对象的“帮凶”。正因为如此,女作家无法做到作家与贤妻的兼得,即便涂上厚厚的水白粉,戴上假面具,也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可以让内心释然的转换。其结果是,她在自己的困境中挣扎,艰难寻找为自己写作的道路,并必定将被冠以“恶妻”的名声。
四、困境的突围
做贤妻或恶妻,是近代日本诸多女性作家都经历的重大问题。作为新女性,她们往往具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意识,自由恋爱自由结婚,是新女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意味着她们必须经过对家父长制的反叛才能走到与丈夫的自由结合。对父母的抗拒,对家长意愿的违逆,是新女性确立自我的开始。而婚后当恶妻不做贤妻的选择,是她们确立自我后实现自我过程中与男权制的又一场抗争。日本最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家宫本百合子(1899-1951)在其自传体小说《伸子》中便刻画了一个典型的新女性的成长:从小立志把文学创作作为终身事业的主人公伸子不顾父母的反对与相爱的人结婚,婚后发现家庭成为压抑自我、抑制自我成长的地狱,与丈夫调和不成最终提出离婚。传统的家父长制给女性的写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困境,而她们的突围只能是决然而然地做个不孝女,做个“恶妻”。伸子无疑是个恶妻,婚后的她不做家务睡懒觉,抛下丈夫独自旅游,参加社会活动,甚至提出不生孩子,并主动要求离婚,种种行为都与传统的贤妻良母观背道而驰。新女性的困境突围也在给自己制造新的困境:终生不婚或离异,孤独求索。反映了女性写作的艰难和女性作家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她们的勇气和坚持,日本近代出现了女性写作的繁华期,将源于平安时期的女性创作的优良传统延续至今。
注:
①森田草平特写了一篇小说《煤烟》记叙与平塚雷鸟自杀事件的前后过程,故又称“煤烟殉情事件”。
[1]王慧荣.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1-42.
[2]森鸥外.森鸥外集(二)现代日本文学大系8[M].东京:筑摩书房,2010.185.
[3]坂口安吾.恶妻论http://www.aozora.gr.jp/cards/001095/files/42868_27482.html.
[4]中野久夫.大正的日本人[M].东京:鹈鹄出版社,昭和56.33.
[5]肖霞.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29-30.
[6]于华.〈青鞜〉的创办与日本近代女性问题[J].新闻大学,2006,(4):28.
[7]周乐诗.笔尖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83-84.
[8]田村俊子.女作者[A].田村俊子作品集第一卷[C].东京: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ー,1987.296-297.
[9]田村俊子.女作者[A].田村俊子作品集第三卷[C].东京: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ー,1987.333.
[10]吴佩珍.家国意识形态的逃亡者:由田村俊子初期作品看明治时期“女作家”及“女优”的定位[J].中外文学,2005,(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