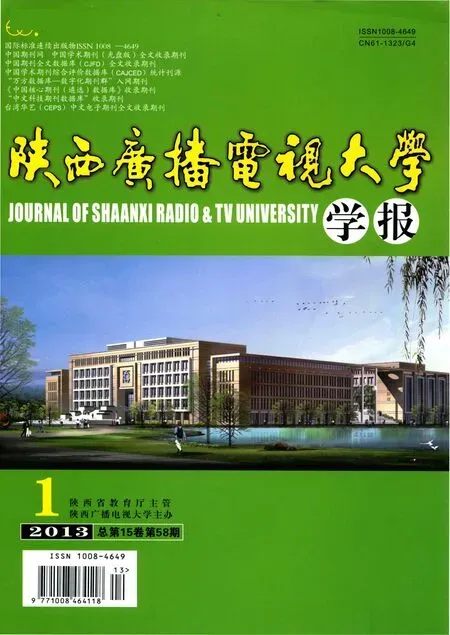国 学 要 略 (上)
李亚军
(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陕西 咸阳 712046)
“国学”诞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国人文化自省并努力维护、志在复兴的清末时期。一度兴盛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沉寂了长达数十年之久。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学重新受到国人的极大推崇。在再度兴盛的同时,又不断得到发展。这是党和国家理性反思并特别重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成效,也是经济发展、中外交流、民众寻根、媒体传播等等的成效。
一、国学的名义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中也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所谓“国学”,指的是天子或诸侯在都城设立的兼有教育管理职能的国家最高学府,教育的对象是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子弟,以及从庶民子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
“国学”作为教育机构的这一意义,后世名称并不一致:汉武帝后称为太学,晋朝改称国子学,北齐又改称国子寺,隋朝文帝时先是恢复国子学之名,不久又废而唯立太学,炀帝后再改为国子监,统领各官学。其后直到清末,除元朝和明初仍称国子学外,一直沿用从隋朝开始的国子监的名称及其制度。教学的内容,早期主要是以儒家的五经六艺等为主的修身进学、经世济民和安身立命的学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国家、社会的需要,渐次增加了律学、书学、算学、武学等科目。清朝光绪三十一年 (1905),由于种种原因,朝廷废除科举,始设学部,兴办新式教育。于是,以传统经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就此终止。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简言之,则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及其研究。所谓“国”,指本国,这里即指中国;所谓“学”,既包括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以此为对象的研究。
这一全新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在写给黄遵宪的信中讨论创办《国学报》时提出来的。他在随后所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还特别标举“国学”的概念,并与东渐日久、影响日巨的“外学”即一般所谓“西学”相对:“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 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显然,其意也是为了保护和振兴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学术并使之发扬光大。由于时世的需求和梁启超特殊的名人效应,自此,“国学”一词就不仅具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且很快被国人接受并风行天下。如1903年,《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的需要。邓实在1905年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公开标举“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其后在发表的《国学保存论》中,则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上的阐释,谓:“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至于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于1906年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
在梁启超提出具有全新意义的“国学”之前,“国学”曾被称作“中学”、“旧学”;之后,又曾称为“国故”、“国故学”等。
“中学”、“旧学”的称谓,出自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国故”的称谓,源于章太炎1904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和1910年在日本刊行的《国故论衡》一书。“国故学”的称谓,则始于毛子水。他在1919年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这一概念及其界定,很快便被胡适认可。胡适不仅随即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在1923年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此重新做了一番诠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至于“汉学”及“支那学”、“华学”、“中国学”等名词,除“汉学”在清代曾与国学基本同义之外,今之意义,均源于外国人,内容也基本与国学不同,主要是关于整个中国各种问题的学术及其研究。
二、国学的载体
国学的载体,除博雅多学、生生不息的“龙的传人”以外,主要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历史遗存、民间传说等。
传世文献,集中在始于《隋书·经籍志》而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古代图书分类之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之中。经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中的一个特有部类,不相当于今天图书分类的任何部类。经部所收的书籍,是封建统治阶级要求必读的书——儒经及两个附从部类—— “乐类”和“小学类”。史部所收,除过历史方面的书以外,还有天文历法、地理类和书目类的书。子部的书,为凡属学术、学派等而自成一家之言的著作。集部的书,全部是文学作品。
出土文物,包括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简帛古书等。
历史遗存,指历史遗迹和无文字的古物等。
民间传说,其事实从可信度上来说虽多不足征,但很多内容亦非空穴来风。即使纯属传说,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学的诸多精神内涵,研究的价值还是有的,甚至很大,所以理应视为国学的载体。
三、国学的范围
就范围而言,国学一般以传统的文、史、哲性质的学术为限。其中“文”的范围,包括传统的语言、文字、文献与艺术方面的学术,兼及“文”性很强的中医、数术之学等;“史”的范围,主要包括历史和天文历法、地理、书目方面的学术;“哲”的范围,包括哲学、思想与宗教方面的学术。从中可以容易地看出,其彼此之间显然是相互交叉的,甚至程度很深。这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文史哲不分家。
四、国学的类别与内容
国学的类别,因角度不同而划分不同。有完全遵从古代分类的,即上述经、史、子、集四大类;有从现代和性质角度分类的,即一般所谓文、史、哲三大类;还有从应用与特点的角度分类的,包括考据、义理、经世、辞章四大类。不一而足。
结合今人之用,参照前贤分类与说法,这里将原附于经部的“小学类”独立出来作为一类,其余经、史、子、集各部均予保留,再将“集”改为“文学”,外增“蒙学”一类,从而分为“蒙学”、“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六大类。
(一)蒙学
传统的蒙学,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之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泛指古代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则专指启蒙教材,即童蒙读本。这里广狭二义兼而用之,并及蒙学的研究与应用。
蒙学虽属基础教育之学,但因其在国学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实在重大,有关研究应用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故理应归属国学。蒙学教育注重背诵与练习,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能力,掌握最基本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
古代蒙学采用的教材,最主要的,是所谓“三百千千弟子规”,即《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此外,还有《名物蒙求》、《治家格言》、《家诫要言》、《增广贤文》、《心相编》、《小儿语》、《续小儿语》、《女儿经》、《女小儿语》、《弟子职》、《神童诗》、《续神童诗》、《幼学琼林》、《笠翁对韵》、《龙文鞭影》等。其中《幼学琼林》以其百科全书之特点,《增广贤文》以其人生常识之价值,亦极受欢迎。旧谓“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就是对此二者而言的。古人在学童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视情况而使之接触“四书”等经典书目,以便为日后的研习打下基础。
(二)小学
这里所谓“小学”,内容特指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小类。
1、文字学:文字学以研究文字的结构与演变为主,兼及音韵学与训诂学有关问题。历史名家为东汉许慎,唐颜元孙、唐玄度,南宋李从周,清戴震、段玉裁等,典籍有《说文解字》、《干禄字书》、《九经字样》、《字通》、《说文解字注》及近人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等。
2、音韵学:音韵学以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为主,兼及文字学与训诂学有关问题。著名人物为隋陆法言,唐僧守温,北宋陈彭年、丁度,南宋刘渊,元周德清,明乐韶凤,清顾炎武等,典籍有《切韵》、《守温三十六字母》、《广韵》、《平水韵》、《中原音韵》、《洪武正韵》、《音学五书》等。
3、训诂学:训诂学则以研究并解释古籍中的词义为主,兼及文字学与音韵学有关问题。历史上的名家数不胜数,其著名者,有西汉毛亨、扬雄,东汉郑玄、刘熙,三国魏张揖,西晋郭璞,唐颜师古、孔颖达、李善、陆德明,北宋邢昺,南宋朱熹,明杨慎、方以智,清江永、阮元、孙诒让、郝懿行、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典籍有《尔雅》、《毛诗诂训传》、《方言》、《三礼注》、《释名》、《广雅》、《文选注》、《五经正义》、《经典释文》、《四书章句集注》、《通雅》、《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等。
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三者,其实是一物三面而已:文字学重点在字词之“形”,音韵学重点在“音”,训诂学重点在“义”,历史名家及其典籍也深度交互。三者相合,“小学”之义庶乎尽矣。
(三)经学
经学除过“小学”,内容为“十三经”、“四书”及一个附从部类“乐类”。
1、十三经:指《诗经》、《尚书》、《易经》、《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十三部儒家经典。
2、四书: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长文和《论语》、《孟子》两部著述。四书的内容显然统属于“十三经”,本不必再立一类。但因为南宋大儒朱熹认为它们是为学之本、经典中的经典并为之作注之后,遂身价大增,所以在经部也成了一类。
3、乐类:指有关音乐的经籍。儒学十分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故儒经原为“六经”,有《乐经》一书。《乐经》后来佚失,故唯言“五经”,但《乐经》精华思想一般认为赖《史记·乐记》得以保留。
(四)史学
史学的内容,除过历史方面的书以外,还有地理类和书目类的书。其中历史方面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野史、稗史、职官、政书、史评等。
1、正史:这是史书的主干,民国以前所修的共有以下二十四史:
《史记》(西汉·司马迁)
《汉书》(东汉·班固)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西晋·陈寿)
《晋书》(唐·房玄龄等)
《宋书》(南朝梁·沈约)
《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
《梁书》(唐·姚思廉)
《陈书》(唐·姚思廉)
《魏书》(北齐·魏收)
《北齐书》(唐·李百药)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唐·魏征等)
《南史》(唐·李延寿)
《北史》(唐·李延寿)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
《宋史》(元·脱脱等)
《辽史》(元·脱脱等)
《金史》(元·脱脱等)
《元史》(明·宋濂等)
《明史》(清·张廷玉等)
这二十四史加上近代所修的《清史稿》,就是二十五史了。
2、编年体史书:是以时代为纲而编写的史书,如南朝梁沈约《竹书纪年》,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3、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以事物为纲、把时间和人物等都组织到事件的叙述中去、详录其始终的一种史书,如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明冯琦《宋史纪事本末》等。
4、别史:是编年体、纪传体以外,杂记历代或一代事实的史书。如西晋孔晁《逸周书》,南宋郑樵《通志》等。
5、杂史:杂史之目,始于《隋书》。其中《经籍志二》谓:“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如春秋鲁左丘明《国语》,战国无名氏《战国策》,唐吴兢《贞观政要》,清蒙古萨囊彻辰《钦定蒙古源流》等。
6、诏令奏议:顾名思义,即君主的诏令和大臣的奏议。如北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
7、传记:是按类划分的人或事的记述。如春秋齐国晏婴《晏子春秋》,西晋皇甫谧《高士传》,北宋胡仔《孔子编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明解缙《古今列女传》,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等。
8、史钞:为改编或删削众史的史书。如南宋沈枢《通鉴总类》,清沈名荪等《南史识小录》。
9、载记:是记载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的史书。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明无名氏《朝鲜史略》,清吴任臣《十国春秋》。
10、时令:指天文历法方面的书。如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清李光地等《御定月令辑要》。
11、野史与稗史:一般来说,二者虽颇多交互,但基本不同:“野史”与“正史”相对,是民间编写的有别于官撰正史的史书;“稗史”则通常指记载闾巷风俗、民间琐事及旧闻之类的史籍,如清潘永因的《宋稗类钞》,近人徐珂的《清稗类钞》。然而二者有时也完全混同为一,如清留云居士的《明季稗史汇编》。
12、职官:包括官制与官箴两类。如唐张九龄等《唐六典》,清永瑢、纪昀等《钦定历代职官表》,北宋吕本中《官箴》。
13、政书:是专述典章制度的变革的史书。有通论的,如唐杜佑《通典》,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也有分论的,如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义》、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清俞森《荒政丛书》。
14、史评:即评论史事并作为今鉴的书。如唐刘知几《史通》,北宋范祖禹《唐鉴》,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地理类的书属于史部,是因为历代山川形势、田地沃瘠等都与历史息息相关。其内容也颇为丰富,有总论的,也有分论的。总论的,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和珅《大清一统志》;分论的,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宋释法显《佛国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无名氏《三辅黄图》,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陈舜俞《庐山记》,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清谢旻等《江西通志》、毕沅《关中胜迹图志》。
书目类书亦属史部,与很早时候国家藏书就由史官管理并传之很久这一传统密切相关。其名家名著,有北宋王尧臣、王洙《崇文总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张寿荣《八史经籍志》、曹禾《医藏读书志》,近人丁福保、周云青《四部总录》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