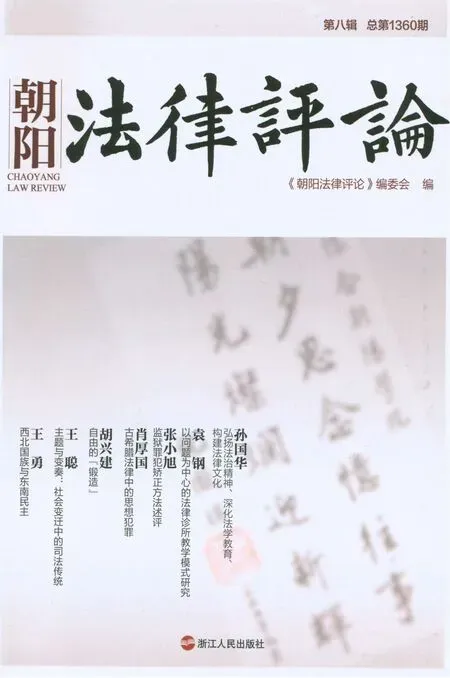论司法衡平传统及当代的价值
周明勇
论司法衡平传统及当代的价值
周明勇*
无论是西方的法律衡平还是中国古代的伦理衡平,其实质都是一种中庸之道,它既是一种不同利益的平衡方法,也是一种不同审判依据平衡的方法。通过探讨司法衡平传统及其公平、公正原则的理论渊源,笔者认为各种利益冲突的利益衡量与均衡博弈是司法衡平的根基;司法衡平是司法公正的方法和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衡平的目的和结果。因此,司法衡平传统在我国法治现代司法改革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衡平法 中国古代法司法衡平 利益衡量
公正的司法是解决社会冲突制度化的手段。公正即公平和正义,那么什么是公平、正义呢?正如罗尔斯所说,“公平、正义原则产生于利益的博弈”,纵观古今,这种利益博弈就是所谓的司法衡平。(司法等)制度是利益博弈的产物也是解决冲突的博弈的均衡解。以理性为前提,在一定规则下,在两个利益相反的利益竞争者之间,总存在一个对各方都是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因而,均衡是博弈的最佳战略或行动所达到的稳定状态,即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点,虽然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最现实的、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结果。所以,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法所确认和保护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还包括被统治阶级不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利益以及该社会的共同利益;法不仅体现统治阶级赞同的公平、正义,而且是与受生产力制约的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在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公平、正义,至少是该社会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公平、正义。
通过探讨中西司法衡平传统,笔者认为,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德主刑辅、以德去刑的儒家泛伦理的中庸思想,还是西方社会的衡平的司法制度,都是利用“衡平”原则和利益衡量理论通过司法衡平的博弈达到“定分止争”;司法衡平传统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衡平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的儒家和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都讲“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寻求平衡的方法,可以适用于各领域。其中,在司法层面它既是平衡不同利益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衡平(平衡)不同审判依据的方法。司法衡平是中西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其理念在中西司法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衡平的理念与中西哲学传统中的“中庸之道”有密切的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是一种中道的权衡。”立法和司法均应根据中庸之道去平衡不同的利益,如此才能有助于公平、公正。贝卡利亚说:“法官应该是一半与罪犯地位同等的人,一半是与受害者地位同等的人。”这是说法官应当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如此才能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实现司法公正。①崔永东:《司法平衡与“中庸之道”》,载《传承》2011年第13期。
“衡平”概念本意是指纠补可能被错误适用的法律,同时也是一种修正的法律正义,是超越法律本身而以法律之上“真正的真理”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原理。因此,衡平法是“公平”、“正义”之旨意,可以用自然法加以涵盖;狭义上讲,则是用来指称一种与“严格法”相对应的适用社会“公平原则”的司法现象,是自然法的具体化或“自然正义”原则和规则,或法律由自发演进进入自觉发展进程中人类有意识地以“自然正义”匡正、补充、影响或改进和完善“法律正义”的主要手段。①张彩凤:《现代英国法治的历史开端》,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一)西方国家衡平司法的历史发展
衡平法是在普通法(习惯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发祥地是英国;而英国普通法则是以令状诉讼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公元14世纪专门设立了衡平法院(或称大法官法院)。自此,在英国法中普通法与衡平法并存,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并存。总之,英国的衡平法或衡平法院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原因。随着中世纪后期英国商品货币的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和冲突层出不穷,形式主义及保守的普通法显然难以适应。由于令状种类和范围有限,许多争议往往由于无相应令状而无法在普通法院起诉寻求法律保护,即使有的诉讼普通法院受理了,又因普通法内容刻板和补救方式的有限而难以获得公正处理。于是人们根据传统的习惯直接向国王提起诉讼。面对日益增多的诉讼,国王便委托大法官处理。在最初几个世纪,衡平法并不要求严格遵循先例,只要求大法官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和自己的“良知”对这些案件进行独立的审理。这在赋予大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时,也带来了众多的争议和不满,人们批评早期的衡平法是“大法官的脚”,可大可小,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为了减少矛盾和纠纷,先例原则逐渐在衡平法院确立起来,衡平法院也像普通法院一样严格遵循先例,其判决也须附理由并采先例拘束理论。②陈锋:《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06年第8期。在此基础上,衡平法逐渐体系化,并成为一种独立于普通法和普通法院之外的衡平法体系和衡平法院系统。虽然英国1875年的司法改革废除了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不同的管辖,重组英国法院体系,使得两大法院系统合而为一,所有法院都可适用英国法的全部规则,同时,衡平法和普通法也日趋融合,很多衡平法规则被普通法或制定法所吸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衡平法已经消失,直至今天,衡平法仍是创造新原则和补救规则的重要手段。衡平法优先原则也在1981年《最高法院法》中得到重申,衡平法仍在英国法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14世纪以后形成的英国衡平法,是掌握着国王“良心”的大法官,为纠正和弥补普通法的不足而运用“衡平”手段创制的一种判例法体系。在西方尤其是英美法国家,特别强调法官应依据良心(conscience)和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进行审判。菲尔普斯(Charles Phelps)指出:“所谓司法衡平,是指有能力的法官,依据其受有训练的良心请求救济。”①Wassertrom.R.A ,The Judicial Decis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87.这种意义上的“衡平”,具有了超越英国衡平法乃至外国法的更为广泛的含义,正如沈宗灵教授就“衡平”概念所作的解释:在西方法中,衡平一词也是一个多义词。主要有以下三种相互联系的意义:第一,它的基本含义是公正、公平、公道、正义;第二,指严格遵守法律的一种例外,即在特定情况下,要求机械地遵守某一法律规定反而导致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因而就必须使用另一种合理的、公正的标准。一般来说,法律中往往规定了某些较广泛的原则、有伸缩性的标准或通过法律解释和授予适用法律的人以某种自由裁量权等手段,来消除个别法律规定和衡平之间的矛盾。第三,指英国自中世纪开始兴起的与普通法或普通法法院并列的衡平法或衡平法院。当然,衡平法或衡平法院这两个名称所讲的衡平也导源于以上第一种,特别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衡平。②参见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73页。
至于罗马法,在中世纪经德、法等国继受之后,受到自然法及人文主义的影响,衡平理念渗透入实体法,法律与衡平逐渐融为一体。许多规范具有衡平的性质,在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上容许就个案加以衡量,以实现正义。但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得法律与现实社会相脱节的矛盾日益凸显,仅凭制定法中具有衡平性质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能满足法律调节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德国以及其后的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在批判概念法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了利益法学、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论,要求法官进一步直接依据衡平理念处理案件。不过,这些国家仍然非常强调,法官要通过“法规的理论证成”等方式,一方面对照法律检验衡平结论的正确性和妥当性,另一方面也赋予衡平结论法律上的理由,以此增加裁判的说服力,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①参见陈锋:《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06年第8期。
从西方衡平司法传统来看,衡平理念发生于人类社会一个更为进步的法的自觉发展阶段,如罗马的“裁判官法”和英国的“衡平法”。其权威和效力来自于其特殊的具有伦理性的原则而非任何人或团体的特权,从而区别于拟制和立法。衡平的原则具有比普通的法律更高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衡平法重意图而轻形式。“求实质而舍躯壳,重实际而轻形式”是公平和正义的真谛。
(二)我国古代的衡平司法传统
在中世纪的思想中,关于良心的讨论焦点在个人的道德生活。理论家将良心分为两个部分:良知(synderesis)和心知(conscientia)。著名的经院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良知是人们对于自然法主要原则的先天知识;当个体将良知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时候,他将此称为心知。②参见冷霞:《“同途殊归”还是“殊途同归”?》,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2期。除阿奎那外,其他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家还将良心与神法、理性法联系起来。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良心是神法的“使者”:“良心事实上如同法律的命令”,“宣告一些行为应当被完成,或者本应被完成,或者被避免,或者本应被避免”。③Norman Doe,Fundam ental Authority in Late M edieval English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34.故从哲学视角而言,英国衡平法中“良心”原则是建立在中世纪的经院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原则。因此,由神职人员担任的大法官在大法官法院中作为判案基础的“良心”原则正是源自于基督教的信仰原则:不得背弃他人的信任,不得违背承诺,救助穷人和无助者;大法官在法庭上对于良心的探求和忏悔与神甫在拯救灵魂时对良心的探求非常相似,他们所关心的同样是“精神上的健康”、“灵魂之善”。与此相对应,英国中世纪与基督教神学有着密切关联的衡平法与理性法、神法相关联,对普通法进行道德评判。④参见冷霞:《“同途殊归”还是“殊途同归”?》,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2期。
综上,如果将中国古代衡平司法与英国中世纪衡平法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这方面非常类似。例如,中国古代的“春秋决狱”基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经义实现衡平,这与中世纪的大法官并非基于先例原则进行衡平司法,而是基于“良心”原则实现衡平不乏相似之处;同时,在法律活动的灵活性和能动性方面,中国传统的衡平司法也十分近似于英国的衡平法,司法官在衡平司法具体活动过程中以儒学作为总体指导,也比较倚重于个人的智识和经验。事实上,中国社会的文明源远流长,有一套独特、稳定而又和谐的规范性秩序,古代的司法官尽管缺乏系统的职业化的法律训练,但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了解传统社会的规则和习惯,洞悉本土的人情世故和社会风习,掌握着一套独特而又行之有效的解决社会纠纷和冲突的方法,从而形成了在形式和价值上根本不同于西方(也不尽同于其他东方社会)的法律观、秩序观以及法律运行模式。这个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的司法官群体,凭借读圣贤书所积淀下来的一套知识、态度、理念和信仰,形成并分享着群体内部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体系,力图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身体力行之,实践着自然和谐的社会理想,通过其大量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形成了关于“衡平”的司法传统。①参见顾元:《中国衡平司法传统论纲》,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总之,中国传统的衡平司法是以建立或者恢复一种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为根本的着眼点,来看待和解决现实的纠纷(特别是民事纠纷)的。在大量的具体纠纷案件中,司法官为了直接实现“公道”、“合理”,以达“平衡”和中庸和谐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牺牲法律的普遍性为代价,这有着文化上的深刻原由。而且,中国古代认知和处理纠纷的范畴体系,与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合为一体,纠纷的认知和处理也由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伦理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主体所主宰。所以,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导向的司法官,在必要时牺牲以法律规则来服务于现实之需,就不是很难理解的现象了。②参见顾元:《中国传统衡平司法与英国衡平法之比较——从“同途而殊归”到“殊归同途”》,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4期。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儒家全部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的真谛所在。孔子“仁学”体系的实质就是主张以调和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的哲学体系;因而,在儒家看来和解是解决现实纠纷和诉讼的基本办法。因此,古代中国审美意识中十分推崇和谐,强调对立面的均衡统一,而把均衡的打破以及对立面的相互矛盾和冲突视为应予竭力避免的缺陷乃至灾难。和谐的观念不仅涉及美的外在感性形式,而且更强调它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礼记·中庸》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这个“和”就是和谐,圣人之所以制礼作乐,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和谐。①参见顾元、李元:《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所讲求的自然和谐和中庸之道,不单纯是哲学思想和审美的评价,它更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统治者施政的一种理念,对于古代无讼法律意识的形成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②参见顾元、李元:《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总之,“中庸之道”作为一种“平衡术”,不仅指利益的平衡,还包括审判依据之间的平衡。中国古代儒家化的法官审理案件时注意寻求“情理”与法律之间的平衡。何谓“情理”?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说法,情理就是人们的公平正义观。情与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也有细微的区别,“理”更抽象一些,指道德原理、道德原则;“情”更具体一些,更感性一些,指道德规范、道德情感。中国古代法官以“情法允协”作为审判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指情法兼顾、情法平衡。《名公书判清明集》(汇集了古代法官平衡情法进行审判的案例)称法官审判就是“酌情用法,以平其事”,“酌情用法”就是平衡情理与法律,这样有助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平衡。③参见崔永东:《司法平衡与“中庸之道”》,载《传承》2011年第13期。
二、司法衡平传统对当代的价值
我国目前仍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法治国家转型的时期,虽然通过法律的大量引进和移植,我国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国际化程度得以切实提高,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国际化和法治化,却相对受到忽视。传统法律理念仍依着惯性持久地存在,并深刻影响乃至困扰着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在此情况下,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和理论,片面地强调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和法律的形式理性,全盘否定伦理衡平的司法传统,在实践中尚行不通。但是,伦理衡平将“人情”置于“国法”之上,这与强调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有着根本对立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断强化伦理衡平的后果,就是不断破坏正在形成之中的法治观念和正在建设之中的国家法治。因此,目前可行之计是在现代法治的视野下,对伦理衡平的司法传统加以改造,在尽量克服其弊端的同时,又能切实发挥其优点和作用,使其进一步服务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①参见陈锋:《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06年第8期。
(一)我国目前司法衡平实践的意义及不足
在现代法治的视野下,目前我国的衡平司法实践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衡平司法在裁判中能体现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中,伦理衡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减少或避免由于对形式正义的无限推崇而造成牺牲个案实质正义的现代法治代价。其次,衡平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法官能动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推进法律创新发展。疑难案件的存在对法律创新提出了要求,而伦理衡平则为法官如何通过个案衡平,对法律进行创造性解释和适用,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维视角和思维方法。②参 见陈 锋:《 从伦 理衡平 到法 律衡 平—— 我国 衡平司 法传 统的 意义、 困境 与出路》, 载《 法学》2006年 第8期。
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伦理衡平就总体而言,与现代法治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主要表现在: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损害了法律的普遍性,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增加了司法主观主义的危险性。
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就是法律至上、“规则之治”,它意味着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一旦制定,就应当严格得到遵守和执行。但法官在伦理衡平中往往过于倚重道德化的善恶判断,造成成文法的弃置,这无疑对法律的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其次,法律的普遍平等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伦理衡平却是要在个案中通观相关情况,有差别地适用法律,以实现个案正义。同时,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优点就在于法律的确定性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具体的预期,但法官在伦理衡平中绕开甚至违背法律作出的裁判,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甚至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预期。同时,由于伦理衡平以纠纷解决为导向,强调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而非个人正义与权利的张扬,再加上实际运作中,群体秩序往往掌握在强者手中,这使得强者容易假借群体和谐之名压制与其发生争执的弱者,进而损害弱者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最后,伦理衡平在漠视法律规则的同时,也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无限放大,再加上作为伦理衡平依据的道德化的善恶判断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标准,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法官裁判的限制。这种缺乏制约的自由裁量权,极易导致司法的主观和恣意。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社会中各朝各代难以根除的司法腐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①参见陈锋:《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06年第8期。
(二)衡平司法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在衡平司法传统的发展和传承中,尤其是西方英美法系国家仍然非常强调法官要通过“法规的理论证成”等方式,一方面对照法律检验衡平结论的正确性和妥当性,另一方面也赋予衡平结论法律上的理由,以此增加裁判的说服力,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司法公正是司法平衡的目的和结果,司法平衡是司法公正的方法和手段,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解法律的方法,其实质是利益衡量、利益均衡在司法领域的博弈,其具体目的是将纸面上的法律落实为个案的公正处理。因此,笔者认为衡平司法传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衡平司法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因解决法律与现实相脱节的矛盾而发展起来的救济途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只要存在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象,就存在衡平司法。目前世界各国都有着大量的衡平司法理论和实践,就连已经实现法治社会建设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因此,衡平司法在我国的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仍然有着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其次,西方国家的衡平司法传统是一种以法律、法意或法理作为衡平依据的法律衡平。西方国家崇尚规则之治,强调法律具有优于伦理道德等其他规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西方国家具有和我国伦理衡平不同的衡平理念和司法模式。一方面,西方国家法官适用衡平司法的情形是有严格限定的,只有在出现法律漏洞等法律适用上的疑难案件,甚至是法律明文规定授权法官可以衡平司法的情形下,法官才可以进行衡平司法。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法官在适用衡平司法时,其考量的因素基本上只是法律原则、法律精神或法律原理,即使是“公平正义”等类似于道德规范的抽象观念,也是将其纳入法律视角后,转化为法律精神进行阐释和考量。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伦理衡平就十分随意,这不仅表现在伦理衡平的适用情形极为广泛,①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法律适用的疑难案件外,还有其他大量的事实认定上的疑难案件,甚至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均无疑难,仅仅是裁判结果可能不利于解决纠纷、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其他大量案件,法官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伦理衡平,在考量裁判的社会可承受程度之后,才结合法律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更表现在法官在伦理衡量中考虑更多的还不是法律、法意或法理,而是“人情”、“大局意识”、“社会效果”等法律之外的因素。
再次,西方国家通过职业法官、尊重规则和裁判的论证说理,较好地克服了衡平司法的主观主义危险,并因此走上了和我国伦理衡平司法传统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一,西方各国的法官都是职业法官,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具有统一的法律知识结构和法律思维模式,这为其提高衡平司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西方国家或通过遵循先例制度确立衡平规则,或将衡平理念渗透入实体法直接依据实体法裁判等方式,有效地提高了衡平标准的客观性和统一性;其三,西方国家的法官普遍注重裁判的论证说理,能够以法律的论理解释或法规的理论证成等方式,公开衡平结论的推导过程,并详细阐明理由,从而进一步增进了裁判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这些因素使得西方国家的衡平司法传统至今仍保持着蓬勃的活力,特别是英国还发展出了一套活力不息、完整独特的衡平法法律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伦理衡平虽然与西方国家的衡平司法传统都是以“衡平”为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并且也是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联系的一种灵活裁判,但最终因司法的擅断和腐败而广受批评和诟病,这种中外衡平司法传统同途而殊归的情况,值得深思和反省。②陈锋:《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06年第8期。
总之,笔者认为,在完善以利益衡量为理念的我国衡平司法改革中关键还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加强对衡平司法的约束。衡平司法容易导致司法的主观主义危险,这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也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加强对衡平司法的约束,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一是借鉴瑞士等国家的经验,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法官衡平司法的情形。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关于衡平司法系“法官造法”的无谓争论,更有利于防止个别法官任意扩大衡平司法的适用范围,造成衡平司法中的恣意和专断。
二是借鉴英美法系的先例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现阶段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有意识、有针对性地选择公布典型案件,明确不同类型案件的衡平标准、方法和规则,以此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预防和减少法官在衡平司法中的主观恣意。
三是要强调法官在裁判中的论证说理义务,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衡平司法结论的推导过程,并充分论证说明其结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公众对法官衡平司法行为及其结果的信服和尊重。在进行价值衡平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道德感、公共政策、公共舆论、社会效果、传媒与司法等等这些标识着社会需求的因素都影响着法官的价值判断与衡量。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利益衡量的价值准则,是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应遵循的原则。因此,利益衡量主张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法官不能拘泥于某种严格的“法律条文”规定,使彼此冲突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并将其中的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不论是怎样的法律推断过程,都应在结论中予以公开详细的说明,对于其中的价值判断过程,也应有公开的表述。因为司法结论的正当性并不限于表面,而证明这一步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对做出结论的理由予以坦率的陈述,并以一种恰当而可证明的方式解释冲突,是证明结论正当的关键所在。也只有这样,司法人员的价值判断的过程才能得到充分的制约。”①修艳玲:《法律推理与利益衡量》,载《福建高等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其次,加强法官队伍建设。由于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不高,法律素质不强,在我国现阶段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的转变中,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切实增强法官衡平司法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一方面要严格法官队伍的准入条件,保证法官队伍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对已经在编在职的法官加强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特别是要加强法官在法律解释、法律适用和法律论证等方面的能力训练,进而切实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和司法技能,为法官更好地理解、把握法律精神和原理,更好地通过衡平司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②参见陈锋:《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载《法学》2006年第8期。
(初审编辑 林艺芳)
Discussion of Traditional Judicial Equity and Its Modern Value
Zhou Mingyong
In both Western legal equity and ancient Chinese ethical equity,the essence is a kind of doctrine of moderation,not only as a kind of balance of differing interests,and for different trial basi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judicial equity and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justice principles.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judicial equity means balancing various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its equilibrium.Judicial balance is the approach and means of judicial justice,while judicial justice is also the purpose and consequence of judicial balance.Therefore the tradition of judicial equity has been drawing significantly on Chinesemodern judici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Equity Chinese Ancient Judicial Equity Interest Balance
*周明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