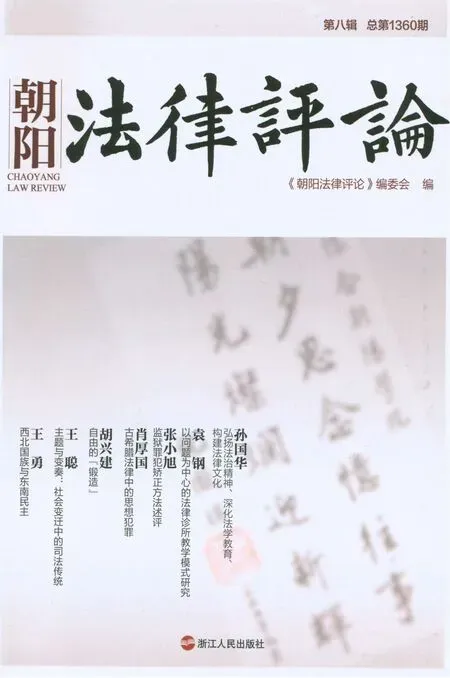主题与变奏:社会变迁中的司法传统*
——以人民司法传统的复苏为视角
王 聪
主题与变奏:社会变迁中的司法传统*
——以人民司法传统的复苏为视角
王 聪*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具有多重功能,其中经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功能即是为政治提供合法性资源。司法历来也是人民政权执政合法性再生产的场域。因此,人民政权自革命时期起就高度重视政法工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由此所催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及调解制度塑造了人民司法的新传统。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促使专业化的现代司法理念兴起,而人民司法传统则出现部分断裂。为纠正司法改革中所出现的偏差,国家通过一系列举措,又使得人民司法传统呈现复苏的趋势。将这一过程置于大历史和全球化的视野下,人民司法传统的复兴意味深长。
司法传统 合法性 马锡五审判方式
一、问题、意义与思路
司法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平衡器”、“减压阀”、“排气孔”,兼具多重功能。首先,其原始功能在于解决纠纷,息事宁人;其次,“法律是使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通过对法律规则的适用,司法也发挥着规则治理的功能,而且这一功能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因为只有在有规则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出一个大致确定的预期和安排;再次,司法作为维持政治及社会体系的一个基本支点,还发挥着合法性再生产的功能。①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合法性(legitimacy)②“legitimacy”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多译作“合法性”、“正当性”、“正统性”,这一概念也是本文的重要分析工具。法国学者夸克曾给“合法性”下了一个通俗的定义,即“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社会认同”与“社会满意度”。参见[法]让 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的第一要旨即在于证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心甘情愿的服从治理,①[法]让 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因为对于任何政权来说,如果没有使人们形成“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仅凭暴力和征服无法维持稳定和长久。现代社会中确立的合法性统治方式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统治”,即依靠法定程序的统治。②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社会生活中合法的统治方式大致分为三类:魅力型、传统型、法理型三类,并指出前两者是前理性时代的统治类型。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242页。而司法则通过正当程序吸收不满而成为政治合法性再生产的重要机器。人民政权自革命时期起就高度重视政法工作,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无疑也具有通过司法来证明其自身执政合法性的意图。本文将从这一容易被学界忽视的视角出发,把司法置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再生产的重要场域内,重新理解人民司法的运作逻辑。
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中强调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在一段时间内提出法院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强调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实践中诸如“能动司法”、“大调解”以及各项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举措都在各地法院如火如荼地展开。“人民司法”的话语与实践开始复苏并得到重视。然而,对于学术界来说,“司法改革是一场尚未达成共识的远征”③参见徐凯:《“司改”迷途》,载《财经》2011年第3期。。一些抱持“理想主义”态度的学者对于目前的司法改革路径与方法产生误解,其无论是对西方还是中国的司法实践都充满了过多的“浪漫想象”,过分专注于司法的独立性、专业性等经典理论,而未能将其立论建立在对本国司法传统④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曾尖锐地批评了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于传统的忽视和偏见(即反传统主义),继而指出传统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一个社会不可能破除其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事实上,我国学术界的很多“改革派”对于中国法律传统的无视也恰好印证希尔斯的这一批评。参见[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页。及实践的“同情之理解”基础上,这种用西方逻辑来解释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生硬的纠缠”(甘阳语),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未经审视即把“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误当作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①邓正来教授对这种思维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中国法学自1978年始至今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8页。笔者以为,关注中国司法所特有的规律,有助于审视上述思维方式存在的根本缺陷,以求探索一条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法社会学、政治哲学等理论,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通过梳理人民司法实践中的关键举措,透视人民司法的话语与实践,探讨其兴起背后的原因及实质、所欲实现的效果及其深层意涵,进而揭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逻辑与独特规律。
二、人民司法传统的历史谱系: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中心
学界一般认为,新中国的法律传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那一时期所产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成为人民政权法律制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这一传统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人民司法的实践。②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使人民政权寻找到了革命时期解决司法问题的有效方法和理想方式。③参见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总结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经验,并向整个边区司法系统加以推广,该社论把马锡五审判方式总结为三点:其一,深入调查;其二,在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为群众又依靠群众;其三,诉讼手续简单轻便,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④参见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1983版,第78—79页。其后,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成为人民司法的代名词,其在审判案件时,能较多地倾听群众的意见,使用调解技术将群众意见、党的政策、边区法律巧妙的结合统一起来,既显示了过硬的政治素质,又呈现出亲民的司法形象,因此受到了群众的拥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和肯定。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人民司法的创新制度实践,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纠纷方式,在当时还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涵:一方面,它是民主原则在司法场域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它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在司法中的具体体现。在纠纷妥当解决的追求与革命意识形态的裹挟之下,马锡五审判方式经过政治话语的不断阐释,“成为批判旧司法、确立新司法的象征,成为共产党的司法制度决裂于国民党的司法制度的标志”①参见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至此,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人民司法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实践推广中获得了主流的话语地位,人民司法的传统便是自那时开始形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里,马锡五审判方式仍然是司法实践中最主要的审判方法。在这一时期,从其运用最为集中与普遍的民事诉讼领域来看,人民司法理念在实践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形式主义的常识化司法模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不拘形式,一切以当事人便利为原则,法官定期下乡巡回审判、深入民间调查、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广泛运用调解及说服教育的方法等。第二,个别主义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解纷过程中,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仅满足于严格适用法律,而是与政策、道德、民俗习惯等“活法”相结合,重视调解,追求法律适用的实体正义,重视司法的社会效果。第三,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诉讼过程中,法官积极主动的收集调查证据,为当事人提供妥当的解决方案,法官是以一种人格化的、家长式的方式解决纠纷的。②参见范愉:《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人民司法的这些理念与技术不同于西方法律传统,并与后者法律形式主义、程序本位主义、当事人主义的司法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官完全消极被动的角色、只注重法律效果的做法是人民司法所摒弃的。
放宽历史的视界,人民司法的话语与实践之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马锡五个人的发明,而是历史社会环境塑造下的产物,“在一个本身就没有多少成文法可以依据,在整个社会法律意识普遍较差的社会里,在一个人们更多地把法律当作是政治斗争工具的年代里,在一个主要是以民众的满意与否来评价审判结果的环境下,马锡五的成功是必然的”③参见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216页。。它是将群众路线融入司法建设之中,把自身建构成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在司法中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性质,体现新中国司法的优越性和合法性。就这样,人民司法在为新政权运送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同时,其自身也在群众路线的历史叙事中获得了正当性。
三、人民司法传统的断裂:“织女星文明”与“秋菊的困惑”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愿意,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人民司法传统的嬗变亦成必然。正如希尔斯所言:“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如果某种职业的技术发生了变化,那么决定如何使用技术的诸种传统也要发生变化。”①[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使社会经济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及其交易链条的无限扩展,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部分“断裂”与“失衡”,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不断遭到瓦解,继而发生了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向。在传统社会中,“机械团结”是社会联结的纽带,它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随着市场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事务主宰人们的生活,集体意识削弱,整个社会呈现出异质、多元的状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失范”现象大量浮现,社会秩序呈现出混乱的状态。而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经济学家吴敬琏称其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②对市场经济与法治关系的具体阐释,可参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因此,市场经济的改革呼唤法治的普遍确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重新整合社会,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基本的思路是:建立法治社会,通过法律的治理,重塑社会的价值体系,力图使社会结构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③“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等概念的提出与论证,可参见[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93页。。为了回应市场经济分工对专业化的呼唤与市场主体意思自治的要求,同时也为了缓解呈“爆炸”趋势激增的纠纷涌向法院而带来的不堪重负的案件压力,一场以审判方式为突破口的司法改革在民事诉讼领域拉开了序幕。改革民事审判方式,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淡化和压缩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成为这一时期民事司法改革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司法职业化和专业化改革也不断深入推进,庞杂繁复的法律文本与复杂的经济纠纷,使法律人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运用经过长时间才能习得的专业知识与法律技艺为一般群众提供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凭借其“知识霸权”努力构筑法律职业共同体甚至是“法律帝国”。
正如尼采所言,对于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马上清晰地想象其相反的一面。尽管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情势的正确选择,但是,也必须意识到,这给人民司法的传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其中最为明显的即是人民司法传统中的“群众路线”日益萎缩,具体表现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由常规变成例外;巡回审理、就地办案边缘化,坐堂问案成为主流;人民陪审员制度名存实亡;调解在司法中的重要性下降等。①参见何永军:《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30页。人民司法传统的失落及专业化司法话语的兴起虽是客观环境使然,但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是程式化、格式化的司法风格使很多当事人感到很不适应甚至表现出了本能的抵触,这在经济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尤为如此,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法律意识相对较低,为其在利用现代司法程序的过程中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还遭遇到“秋菊式的困惑”②冯象教授通过生动的笔法揭示了作为一般当事人的“秋菊”在法治现代化之下所遭遇的困境与压迫及其所作的斗争与解放,而这“现代法治”就如同“织女星文明”(外星文明)与作为“法盲”的“秋菊们”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对立悖论。参见冯象:《木腿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129页。,结果,陷入“司法的专业性越强,社会的疏离感越强”的困境③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台湾司法改革的社经背景与法制基础》,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其次,法官机械司法所作出的背离常识、常理、常情的裁判,使当事人及一般群众产生疑惑与不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再次,当事人及一般公众在与法院窗口及法官接触过程中所遭遇的冷漠、生硬态度,信息沟通渠道不畅所带来的困难,都使其感到了司法所运送的正义难以接近,引起其怨气的郁积。④关于当事人及一般社会公众对司法服务质量不满的简单描述,可参见王亚新:《调解与司法服务质量的提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5日。此外,司法腐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使得一般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下降,司法公信力和司法自身的合法性也不断减损。人民司法传统断裂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造成了通过司法所生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四、人民司法传统的重新叙事:从关键词出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高法院对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与方法进行了反思性调整,而调整的重要思路就是重建已经部分断裂的人民司法传统。当然,重建并不意味着要回归到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标志的人民司法,因为其所依托的历史语境已经被置换;重建意味着对其进行符合当前社会经济条件的改造与重塑。正如吉登斯所言,“即便是在那些最传统的文化中,‘传统’都通过反思而被利用,且在某种意义上也‘通过话语而被理解’”①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页。,因此,正如历史不能重现,传统也不可能还原,而只能被重新塑造与理解。那么,最高法院是如何重塑人民司法新传统的呢?人民政权是如何运用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对新时期司法进行创新改造的呢?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近几年来司法改革中的部分“关键词”来作分析与透视,正是在这些“关键词”中,我们看到人民司法传统的核心精神和要素始终在围绕同一主题而进行变奏。
(一)关键词之一:“司法为民”
当事人是司法活动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人民司法的宗旨即是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因此,民众的满意应该成为司法制度设计与改革的出发点。2003年8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司法为民”是统领法院各项工作的要旨,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要求,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新发展。②参见刘嵘:《树立司法为民思想,践行公正与效率主题——记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9期。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颁行了《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也强调要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司法为民”的践行使一度被现代司法理念所怠慢的人民司法的一些传统理念和技术又焕发出新的活力,诸如巡回审理、就地办案、送法下乡、送法上门、诉讼指导咨询等司法便民措施在各地法院得到了积极响应。③对各地法院的司法便利化改革举措的实证分析,可参见姚志坚:《司法改革:诉讼便利化探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139页。倡导简易、快捷、低廉、易于民众理解、便于民众利用的程序运作,使司法显现出大众化、常识化的趋势,拉近了民众与司法的距离,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充分有效地“接近正义”,彰显了司法的人民性。
(二)关键词之二:“调解优先”与“大调解”
我国素来就有“和为贵”的儒家历史传统,重视调解历来也是人民司法的重要传统。人民司法认为,仅依靠“非黑即白”式的判决往往不能实现“案结事了”,相反,通过“说服——心服”式的调解,促使双方相互妥协,在达成合意的基础上妥善解决纠纷,既能“息事宁人”,又能修复社会关系。此外,从政治层面考量,人民政权把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对后者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并希望通过调解教育民众,培养其社会主义的情操和觉悟,塑造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因此,调解就成为最理想的首选司法方式。在这一语境下,“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就获得了正当性支持。而且,为了尽可能达到上述效果,必须充分动员和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因此,人民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必须重新加固与利用,《人民调解法》的颁行可以视为强化这一举措的一个信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大调解”,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形成整合、联动的格局,使“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纠纷解决体系覆盖社区、村和各级部门、各行各业,其目的是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因此,尽管曾一度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调解”却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重放光彩。
(三)关键词之三:“能动司法”
尽管学界至今为止仍未对“能动司法”的准确含义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显然不同于西方法律语境中以法官造法和司法审查为核心的“司法能动主义”。这一司法理念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法院的司法工作必须“服务大局”、“为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法官不应仅仅消极被动地坐堂办案,不顾后果地刻板适用法律;在尚处于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法官可以并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智慧,通过审判以及司法主导的各种替代纠纷解决方法,有效解决社会各种复杂地纠纷和案件,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①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简言之,“能动司法”就是强调法院要立足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司法。①参见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这些关键词所蕴含的司法理念,与西方法律传统中司法的消极保守形象和法律形式主义特征是大相径庭的,因而,也显示出了人民司法的独特规律。
(四)关键词之四:“模范法官”
司法人员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是司法得到公众信赖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共产党历来重视司法队伍建设,重视塑造司法人员的良好形象。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全国模范法官”、“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等项目的评选,表彰了大量的优秀法官,通过树立榜样塑造了人民法官的典型形象。从微观叙事层面观察,无论是之前的宋鱼水法官,还是金桂兰法官,以及最近受到学界热评的陈燕萍法官,都有一些共性:都很重视调解,不消极坐堂问案,积极能动司法,“辨法析理,胜败皆服”;都呈现出贴近群众的“亲民”形象,全心全意为群众着想,从群众利益出发,具有很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司法作风,都是“亲民法官、平民法官、为民法官”。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模范法官”的形象塑造具有边区政府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司法”中的某些似曾相识的印记。如此一来,一种“主动贴近群众”的司法模式又重新在人民群众的记忆中被唤醒,获得了具体丰满的鲜活形象,并显示出了其持久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这些模范法官也成人民群众所偏好认同的形象。在这里,人民政权再次发挥了它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所积累的善于抓典型、做好宣传的经验,使人民司法的新传统在部分断裂后又重获新生。
(五)关键词之五:“巡回审判”
近年来,巡回审判在全国法院系统受到广泛宣传与重视,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几乎都亲历了这一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还专门印发了《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的通知。然而,在很多学院派学者看来,巡回审判在当代司法实践中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徒增司法运作成本的“政治作秀”。这种纯粹的学院派思维不但忽视了巡回审判的理论意蕴,更是忽略了中国的司法国情,是一种典型的“用脑生产”而不是“用脚生产”的法律人,他们把法律或法学都只是想象成一种纯粹的思想产品。忽视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必然要回应社会生活的需求。如果巡回审判制度真如某些学者所批评的纯属一种徒具形式主义的“作秀”,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何这样一项制度会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从人民司法传统复苏的视角重新发现巡回审判当代法理价值是十分必要的①虽然学者们对前四个关键词都已经展开过大量详细的研究,然而,对于巡回审判及其价值则是不屑一顾、少有涉及;对于其是否应该存在,很大一部分“城市中心主义”法学研究者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因此,笔者在此处特意对其进行了较前四个关键词更为详细的解读,以指出巡回审判为何会具有持久生命力,并得到高层的重视。:
首先,从现实需求上来看,它主要是回应了中国基层司法的现实需求。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国的法治”必然有多层次的司法需求。对于幅员辽阔的基层社会而言,仍有大面积的贫困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国家的历次“普法”运动已经使其具备了不同程度的法律意识,而且他们也有解决纠纷的需求,但基于时间、经济等各种成本的考虑,他们大都放弃了选择司法救济的途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看到,所谓“炕上开庭”、“田间法庭”、“草原法庭”、“马背法庭”等各种巡回审判方式在基层不断涌现。这些举措在宏观意义上,是“司法为民”、司法“以当事人为本”的体现,但回归最本质的意义,仍在于落实司法便民、利民、亲民的理念,使“法律不入之地”也能够真正“接近正义”。
其次,从司法场景的视角来看,它显示出广场化司法模型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独特价值。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看,人类最早的司法活动多是广场化的,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后来才被剧场化司法所取代。但正如我国学者舒国滢教授所言,司法的剧场化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昂贵的司法活动方式,它是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而又以发达的经济、雄厚的财力作为其支撑的基础。一个贫穷的当事人,不适宜在司法的剧场化环境下生存。在剧场化的司法场景下,高高在上的法官、庄严凝重的法庭建筑、象征神圣权力来源的国徽、象征化的法袍、法官肃穆的表情、严格的法庭纪律、程式化的法律语言、有序的法庭论辩等司法仪式,向社会公众传达了司法的权力意识和权威形象,但另一方面,它又疏远了司法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使司法游离于一般民众。而巡回审判更换了司法的运作场景,改变了法庭的运作空间。它力图消除一般民众与法律之间的隔膜和距离,“使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即使对法律条文一无所知的人在受到权利侵害时,也同样能够感受到法律阳光的照耀,并在这种阳光的照耀下得到正义之手的救助”。①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
再次,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巡回审判是送法下乡的一种具体形式,其背后的意涵正如苏力所指出的,是国家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②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只有在这种语境下,你才能理解法官手举国徽走向田间地头,绝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向社会公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法官在巡回审判时,国家是“在场”的。
最后,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来看,巡回审判还具有普法宣传的功能。它去除了司法剧场化的隔膜,使得法官与一切诉讼参与人都处于公众目光的“敞视”之下,整个司法活动呈现出高度的透明性与公开性,司法过程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可自由参与的法律表演,浅显易懂的日常生活语言、充满感情色彩的地方方言,使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正义观念的实现,增加了法律的可触及性,这使得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都可以在平易近人的司法仪式中进行深度参与。在这一参与过程中,通过对话与交流、演出与观看,社会公众逐渐认识和接受法律文化,因此司法的过程同时也是普法宣传与法律文化传播的过程,它尊重“秋菊的困惑”,“认真对待法盲”,正如我国学者凌斌所言,它以种种方式号召和发动男女老少、方方面面来参与中国法治的建设,走的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追求的是“把法律交给亿万人民”,“让人民掌握法律”。③凌斌:《普法、法治与法盲》,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
从上述关键词,我们大致可以管窥人民司法的叙事策略,尽管这一策略包含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但更多是一种务实的考虑,是“时代的产儿”,它使得“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期“旧瓶装新酒”,在基本程序内得到继承和发展。人民司法以“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名义回归传统,其目的终归在于,通过司法大众化、民主化、常识化的程序运作,弥补司法专业化的缺陷,重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弥合仿如外星文明的现代司法(其实即法治论者作为参照系的西方司法)与作为其服务对象的社会大众的疏离,消除“秋菊的困惑”,重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感。
五、人民司法传统复苏的深层意涵
上文已经论述,人民司法话语与实践的复兴,部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增,而现有法律形式主义的消极司法已经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因此需要司法作出积极的回应。于是,最高法院审时度势,调整近年来司法改革路径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从而使人民司法的传统得以延续。
首先,从法政治学的视角来看,人民司法的“人民性”、“群众路线”、“亲民”形象又再次为国家输送了政治合法性再生产的资源。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宏观意义的国家治理策略的微观展开,是通过司法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以及行之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法”①刘星:《走向什么司法模型——“宋鱼水经验”的理论分析》,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5—96页。。更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强调人民司法传统,包含了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重建的大目标。②参见冯象:《诉讼服务好》,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6月16日。因为法律形式主义和秩序至上主义容易使法官丢失职业伦理,以程序技术掩盖腐败,而人民司法传统中的人民性和群众路线要求法官必须关注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最终福祉,切实尽到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伦理责任。
其次,人民司法传统的复兴是人民政权根据司法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努力。它表明简单的通过法律移植的道路并不能“包治百病”、解决中国司法中的所有问题,因为法律抑或司法在某种程度上注定具有地方性与民族性,必须警惕进而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迷信。换句话来说,中国司法制度的模式和道路设计必须从中国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出发。就此而言,人民司法传统的重获新生是一种反思性的制度创新,是一种“从群众中来”的极富经验色彩的司法模式。于此,也不妨将其称之为司法的“中国模式”。
再次,人民司法新传统的复兴及其对西方司法制度的改造,体现了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民族自觉性。近代以降,中国社会遭遇了“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用枪炮声敲开国门,国人开眼看世界,始发现中国之各种器物、各项制度均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至此,国人汲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师夷长技以自强”。在这一背景下,以清末修律为标志,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从其原动力来看,这是一个从“外源型”模式逐渐向“内发型”模式转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不断增强,中国人在对中国法治发展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寻求逐步摆脱西方法治发展模式的束缚,开始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思考和选择本民族自身的命运,而不是简单地继受西方的法律制度、司法理念、法律价值去安排本民族的法律事务”①杨建军:《中国能动司法理念的宪政逻辑》,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
结语:认真对待法律传统
尽管笔者力图为人民司法传统的话语与实践复苏的正当性提供合理解释,并与很多对西方司法理念充满想象的学者之立场不同,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司法改革路径转向人民司法传统的重塑抱持一种“同情之理解”,甚至是部分地肯定和支持。但为了不致误解,还需说明的是,对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理解也不能走向极端,尤其不能陷入对司法的虚无主义认识,不能忽视当司法被还原为作为解纷方式的本来面目时,其在中西之间都呈现出一些普适的固有规律,如中立性、被动性、终局性等特征。因此,必须对于司法理念进行辩证的分析。②江必新:《司法理念的辩证思考》,载《法学》2011年第1期。更为重要的是,法学界必须改变“在认识上的和精神上的分裂状态”③对于中国法律学人这种“分裂状态”的批评,参见[美]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夜郎自大;而应该具备一种学术自觉,认识到中国今天的法律明显具有三大传统,即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现代革命的人民司法传统以及西方移植的法律形式主义传统,三大传统实际融汇于当代中国的司法理念中,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现实,“三者一起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形成一个有机体,缺一便不可理解中国的现实”④[美]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又可见[美]黄宗智:《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5期。。因此,这三大传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中永远走不出的背景。而如何理解这三者融合的机理,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对立,并最终达到“通三统”①“通三统”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学者甘阳阐发,其认为当代中国有三种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共和国建立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以及历史悠久的古代儒家传统。参见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页。的理想状态,则成为中国法律学人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更言之,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律人都必须在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不断追问下,探索“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②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可参见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初审编辑 林艺芳)
Theme and Variation:Judicial Tradi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Wang Cong
Justice has multiple functions in a modern society,on which is often ignored is providing politics legitimacy.Justice is also a field where legitimacy is a reproduction of the rulings of the People's Regime.Therefore,the People's Regime places a great emphasis on politics and laws from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It strives to explore socialistic judicial systems which are adaptable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 China.Ma Xiwu's ways of trail and system of mediation shape new traditions of people's justice.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used by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ies,modern judicial philosophy has sprung up,while traditional people's justice is partly broken.To correct some devi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form,China takes many measures to recover the tradition of people's justi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and globalism,the renewal of the tradition of People's Justice is meaningful.
People's Justice Tradition of Justice Legitimacy Ma Xiwu's ways of trial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纠纷解决研究——基于西部十个社区的调查》(11XFX026)。感谢清华大学吴俊博士对本文提出的中肯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王聪,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司法制度专业硕士生,重庆市石柱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