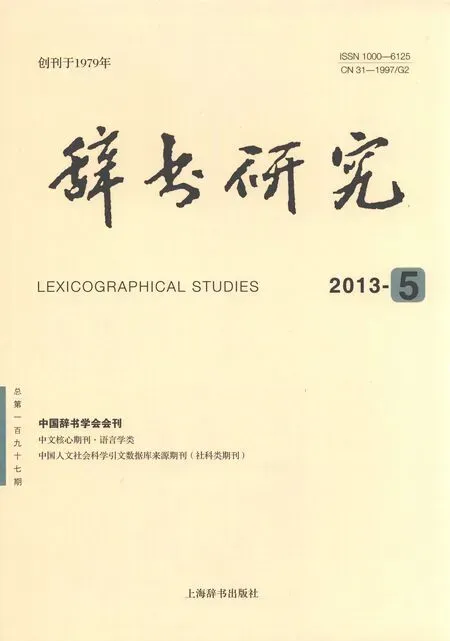先秦专书词典编纂概说
陈长书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济南 250014)
一、先秦专书词典编纂的现状
为重要的汉语古代文献编写专书词典,是我国词典编纂界的重要工作之一。前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王力和胡明扬都提倡编写专书词典,王力(1990:68)指出:“咱们应该有一部语源字典,和几部分期的字典(如先秦字典、汉代字典、现代字典等)。最好是有人先编专书字典或作家字典,作为基础。”胡明扬(1982:21)在谈及作家作品词典时,提到:“古代有影响的作品,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语言的作品,就有价值收录其中出现的全部语词。”其后,蒋绍愚、向熹、徐时仪、宛志文、陈海伦等又不断完善专书词典编纂理论,并各自发表专文对此予以论述。可以说,一般性的汉语专书词典编纂理论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是汉语史跨度长,分期多,不同时期的汉语又各有特点,断代的专书词典编纂也应该相应地反映这种语言的时代性,这就需要将这一理论与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特点相结合,总结出符合时代特点的专书词典编纂理论。这正如蒋绍愚(1989:61)所说的:“‘古代汉语’也不是一个时代平面,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的汉语都是‘古代汉语’,但是这些不同时期的汉语实际上也有很大不同,词义也有较大差异。编古汉语词典也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本文着眼于此,拟以我们正在编写的《国语词典》为主,结合目前已出版的其他先秦专书词典,谈谈先秦专书词典编纂的特点和规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专书词典仅指语言学意义上的词典,并不包括鉴赏性辞典和为方便查找文献词汇而编写的引得,如《诗经鉴赏辞典》、《孙子兵法词典》、解放前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写的《仪礼引得》等。
先秦文献共有20多种,其中已经编写并出版专书词典的有《今文尚书》《左传》《诗经》《论语》《孟子》《吕氏春秋》《老子》《庄子》《孝经》《仪礼》《周礼》《礼记》《尔雅》《战国策》《吕氏春秋》《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共计18部文献,这些词典包括8部单本词典和两套系列词典。其中单本词典按照出版时间排列如下:杨伯峻《孟子词典》(1962)和《论语词典》(1980)[1]、杨伯峻等《春秋左传词典》(1985)、向熹《诗经词典》(1986,1997)、杨合鸣《诗经词典》(2012)、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1987)、周民《尚书词典》(1993)和王延栋《战国策词典》(2001)。两套系列词典,一是“先秦要籍词典”,由王世舜、董治安主编,其中有万祥祯《诗经词典》(1989)、王世舜等《老庄词典》(1993)、袁梅《楚辞词典》(2000)、王世舜等《论语孟子词典》(2004)、郭太安《春秋公羊传词典》、苗若素等《商君书词典》和李廷安《列子词典》(后三部词典被合在一本书中于1997年出版),其中《楚辞》并不是专书文献,《商君书》和《列子》一般认为其成书在先秦以后,所以不能算作先秦专书词典。二是“十三经辞典”,由该书编纂组编纂,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至2011年底出版了11个分册,其中包括11种上古文献,它们分别是《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穀梁卷》《春秋公羊传》《仪礼》《周礼》《尚书》《尔雅》和《礼记》(其中《论语卷》和《孝经卷》被合在一册中,《礼记》分上下两册),最后的《周易》和《左传》分册也在2012年问世。
这些词典都是在各自先秦文献语言特点的基础上编纂的,可谓别具特色,各有所长。如果只从全面性和系统性来看,其中尤以向熹《诗经词典》、张双棣《吕氏春秋词典》和“十三经辞典”编纂最为严审和完备,它们的影响也要超过其他词典。
其余像《墨子》《韩非子》《国语》等重要先秦典籍目前都没有出版专书词典,而且近十年来先秦专书词典的编纂有放缓的趋势,仅有《左传》《战国策》和“十三经辞典”等几部词典出版,而且它们几乎都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编写的,到了21世纪才出版发行。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先秦专书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不够重视,这方面的成果较少,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以上提到的先秦专书词典都是全释型词典,都具有这类词典共有的特点,如追求收词、注释的穷尽性和细密性,收释范围是该文献中全部词汇和义项(也有极少数词组),统计了词频和义项频,例证丰富等。同时,每部词典又由于文献的特点和编纂目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如编排方式、繁简体字的使用、注音和释义的详略程度、词性的标注、例证的取舍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二、先秦专书词典的编纂程序和方法
传世的先秦文献篇幅都不长,少则两三万字,多的也就二十多万字,这样的规模最适合采用全释型专书词典的编纂方式,力求收录该文献中所有的词和义项。与一般词典相同,它的编纂过程也包括确定词目、注音、释义和编排四个阶段。过去整个过程都由人工完成(主要是制作卡片和手工编排),现在一般采用计算机处理和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方法编纂。通常的步骤是,先依照某一注本制作电子文本,然后在电子文本上进行手工分词;接着利用统计软件提取出含有每个词的所有例句,再由人工归纳出义项并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排列,同时标注读音;最后再依一定顺序进行编排。其中,依照目前的条件,仅有制作电子文本和提取例句两项工作可以由计算机完成,其余工作还要人工完成,这和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有很大不同,具体情况将在下文详述。
三、先秦专书词典字体的选择和词目的确定
(一)文献版本和繁简体字的选择
编纂专书词典,首先要从选取研究底本入手,尤其是先秦文献,每一部都有不同的版本,选择时要格外慎重,最好能够搜集所有版本进行认真比对,最终确定一个研究底本,并以此为底本来确定词目,这是版本选择时“择一而定”的原则,其中先秦的经部文献词典一般以《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如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诗经词典》以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2],“十三经辞典”则全部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为底本;而我们编写的《国语词典》,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国语》为通行本,所以以此本为底本。当然,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词典编者先编写注本,再以此为底本编写专书词典,如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词典》是以其注的《吕氏春秋译注》为底本,王延栋《战国策词典》是以他和张清常合注的《战国策笺注》为底本,杨伯峻的《论语词典》和《孟子词典》是以其所注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为底本。
确定好底本后,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制作电子文本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繁简体字的选择问题。无论是采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都符合国家现行的语言文字政策。目前已出版的先秦专书词典有的主要采用简体字,如周民《尚书词典》主要使用简体字,也酌情在一些单字条目后加圆括号附列通行的楷书繁体字和异体字,字条和例句都用简体字;有的主要采用繁体字,如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王延栋《战国策词典》和“十三经辞典”等从词目到释义、例证全部采用繁体字;还有的词目用繁体字,释义和例证用简体字,如向熹《诗经词典》、王世舜《论语孟子词典》等。考虑到先秦专书词典一方面用于古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满足现代人查阅的需要,我们认为词目使用繁体字,注释使用简体字是不错的选择。总之,从使用的便利和规范化的角度来看,先秦专书词典应该尽量使用统一的用字标准。
此外,先秦文献中有一些僻字,在一般人使用的计算机字库里是没有的,要想显示出这些字体,需要安装大型字库,或者用造字程序来创制,或者直接以图片的方式插入。这是一项慢工细活,需要编者格外仔细。
解决了字体的问题后,可以用手工输入或从网上下载电子文本,然后根据选择的底本认真比对,改正其中的错讹之处后备用。
(二)词的分离性判断
确定词目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文献中分词。这是一个逐字展开,再由字到词的过程,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文献中的字是否为词的问题,即词的分离性问题。
这需要词典编者对字词关系和词的辨识理论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我们认为,依照目前的分词理论和前人的注释,先秦文献中的大多数词都可以比较清楚地分离出来,但其中有两种情况较难判断:
一是词和词组交叉的现象。最常见的是“复语”[3],这是一种古代文献中常见的结构,其性质介于词和词组之间,结构上像词,但是出现频率低(大多数只有1次)、结构很松散。以《国语》为例,根据我们的统计,“复语”结构共有近150个(陈长书2011:151),如“安靖、纯固、淳笃、淳濯、艰急、讲贯、眩惑、训御、湮替、亿宁、幽昏、幼弱、宥赦、臧否、蚤晏、章明、政刑、阤崩、终没、衷正、资用、卒伍、罪戾”等。
还有同一形式的结构,既是词又是词组,如“朝夕”,有时指“早晨和晚上”,其意义是“朝”和“夕”意义的简单相加,应当为词组,如:“朝夕獉獉不相及,谁能俟五!”(《国语·晋语八》,以下《国语》引例只注国别名);有时形容“长时间”,是特定的意义,应当是词,如:“夫署,所以虔君命也。”(鲁语上)由于专书词典收词“从细不从宽”的原则,以上这些和词有较高相似度和密切联系的结构,也应该收录。
二是前人对句读以及释义存在争议的部分。这需要仔细甄别才能选择一种正确的说法来进行分词。至于其他看法,有必要的话可以列出来,如:
通过这样逐字逐句的判断,我们可以在电子文本每一个词上进行标记(如在词后加“/”),如“吾/闻/夫/犬戎/帅/旧/德/而/守/终/纯固/”,这样就能很容易地统计出一部文献的用词总量。这种分词情况一般并不直接反映在词典中,但目前许多先秦专书词典都在附录中附了原文,如向熹《诗经词典》、“十三经辞典”等。所以,原文上可以尝试标注分词的基本情况,例如可以在每个词后面插入一个空格或“/”,这主要是便于使用者将原文与词典内容对照,从而让使用者了解词典的立目标准,可以针对不同的需要获取更丰富的信息量。
还有一个与分离性相关的问题需要特别说明,即目前一些先秦专书词典没有区别单音词和复音词的构词词素,以《十三经辞典·毛诗卷》为例,该书第275页有“笾—笾豆,举—举趾,旧—旧业、旧姻”,这些单音词和复音词都用了同一个例证,例如都用《豳风·七月》中的“四之日举趾”来作为“举”和“举趾”的例证。据此可以推断,词典统计的单音词“举”出现的8次中应该包含了“举趾”出现的5次。一般的读者很难意识到这种问题的存在,从而容易混淆文献中字、单音词、复音词和词素,甚至会产生错误的理解。
(三)词的同一性判断
分离出全部文献中的词后,词目的数量还不能确定下来,因为先秦文献中的词存在大量同一性的问题,即在整部文献的范围内同一形式的字是表示一个词,还是多个词的问题。要想最终确定专书中所有的词目,必须解决“同一性”问题,其中语音和字形是最重要的两方面。
1.语音的同一性
编写先秦词典,首先要确定编写词典使用的上古音系统,进而才能确定语音的同一性。采用的语音系统不同,词目的确定也会有差异。目前大多数先秦词典多采用的是王力的上古音系统,如《诗经词典》《吕氏春秋词典》等。根据王力“入声又各分长短”说,同一个字在先秦时期不会出现“四声别义”的问题,所以像“王”,作为名词的“帝王”义和作为动词的“称王”义,语音相同,只能归并为一个词目,而不是两个词目。如果采用许多学者主张的“古有四声”说,则“王”语音不同,那就只能列成两个词目了。有的词典不考虑上古音的问题,按照现代音来判断先秦文献中的词,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2.文字的同一性
文字的假借、异形以及分化等问题对词目的确定也影响巨大。根据我们对《国语》字词关系的分析(陈长书2011:20—25),先秦文献中的字词关系大体有四种:字词“一一对应”、同形异词互相对应、异形同词互相对应以及同形异词和异形同词交叉对应。词目的确定也应该相应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不单独表示词的字是否需要列为词目
这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表示构成复音单纯词的字一般不另立词目,如《国语》中的“贲贲、嗛嗛、忸怩、匍匐、仿偟、侏儒、鸑鷟、蝄、屏营”等。
第二种情况是仅表示复合词词素而不独立成词的字,应该另立词目。这又有两种情形:一是这些字在专书中仅表示构词词素,在其他先秦文献中独立成词,例如“稇、垂、俪、瞑”等在《国语》中仅在“稇载、边垂、伉俪、瞑眩”中充当构词词素,但它们在其他先秦文献中独立成词;二是这些字不仅在专书中,而且在全部先秦文献中几乎都不独立成词,这说明这些字主要表示的是词素,而不是词,例如《国语》中的“、蕝、韎、骿”,它们在先秦典籍中几乎都不独立成词。因为就词汇史研究而言,词素的研究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两种情形都应该作为词目在《国语词典》中列出,注释时可以说明“不独立成词,只用来构成合成词‘××’”。
(2)同形异词互相对应如何分列词目
同形异词互相对应可能由文字假借造成,也可能由音变(上古主要是变声)或词义引申造成,但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应该分列词目,一般用上标的阿拉伯数字区分,如:
距1相距。如: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周语上)
距2通“拒”,据守。如:距险而邻于小。(郑语)
(3)獉异形同词互相对应应该如何分列词目
异形同词互相对应是由文字上的假借或异体造成的。专书词典的收录对象应该是词(极少量词组),但绝不应该是字。所以,这些不同的字形应该归并为一个词目,而不应该分列词目。其中,假借的情况其词目应该选用借字的字形,如果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则在词条中说明其本字的情况。如
当然,“渝”条下应做适当交代。
异形的情况,其词目选择其中一个字形,其后要用括号列出另一个字形,例证也需要列出分别出现两个字形的句子,如:
(4)同形异词和异形同词交叉对应如何分列词目
这种情况其实是第(2)和第(3)种情况的综合,即同形异词处理成不同词目,同时异形同词处理成同一词目,其中本有其字的假借发生交叉对应最复杂,如《国语》中的“飨—享”:“飨”,《国语》中共有4个义项:①饮。②款待,以酒食犒劳。③飨礼。④指宴会或祭祀所用的食品。其中,发生交叉对应的义项②应释为:
全部4个义项后面,还应当说明借字的情况(借字前用特殊符号标注,如“●”):
●又借作“享”,供祭品祭祀祖先。详见“享”词条。
●又借作“享”,享受,享有。详见“享”词条。
“享”,《国语》中共有4个义项:①供祭品祭祀祖先。②进献,贡献。③享受,受用。④受,承受。其中发生交叉对应关系的义项①和③应释为:
●又借作“飨”,用酒食款待。详见“飨”词条。
因为这时本字和借字其实表示的是同一个词,所以只需要在本字后说明借字并举例;同时这个借字在《国语》中又充当了其他词的本字,这时只需要在该词的词目下说明这个借字的情况以及意义,不需要单列义项和举例了。
通过同一性的判断,专书词典的词目最终全部确定下来。
四、先秦专书词典的注音
已出版的先秦专书词典中,给词目注音的情况也很不一致。其中,有的词典不注音,如杨伯峻《论语词典》《孟子词典》和《春秋左传词典》;有的只用汉语拼音标注单音词的现代音,如周民《尚书词典》、王世舜《论语孟子词典》和《老庄词典》;也有仅仅标注部分词的现代音的,如王延栋《战国策词典》只标注了多音词的现代音;而几部比较完备的词典则分别标注了单音词的现代音、中古音和上古音。但它们之间仍然有差异,其中向熹《诗经词典》注汉语拼音、《广韵》反切(《广韵》未收依《集韵》或其他韵书标注)、中古音(摄呼等调韵声)和上古音(韵部声母,不标声调);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也注了这四项,但是不同的是中古音只注声韵调,不注其他项,上古音只注韵部,不注声母;“十三经辞典”和《左传详解词典》基本相同,只是还用注音字母注了现代音;《吕氏春秋词典》则依上古音编排,先按韵部排列,韵部相同者按声母,声母相同按谐声偏旁,这样,每个词条下,不需要再注上古音,其余项同《诗经词典》。另外,这些词典里的复音词一律不注音。
我们认为,从研究和阅读的需要来说,注音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编纂的细密性要求注音应当力求完备,现代音、中古音(包括反切、摄呼等调韵声)和上古音(声韵)等基本形成定论的语音特征都应该标注。注现代音可以方便现在的读者查询和阅读,注上古音可以方便读者了解该词在先秦时期的语音形式,注中古音方便读者利用中古音上推上古音,便于语音史的梳理。
另外,复音词的读音也应该标注。同一部词典选用的古音体系应该保持一致,目前先秦专书词典中主要使用王力的古音体系,编纂词典时可参照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和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来标注读音。
五、先秦专书词典的释义
和注音一样,先秦专书词典的释义也得根据先秦文献语言的特点来进行。本文主要讨论义项的划分、词性的标注和例句的选择等问题。
(一)义项的划分
与中古和近代文献比,先秦文献成书较早,数量少,篇幅小,同一个词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因此,与一般的古汉语词典和其他时代的专书词典相比,先秦专书词典释义最大的不同就是收录了先秦文献中许多的生僻义、随文释义和歧解现象。
以《国语》为例,根据我们的统计,只出现1次的义项有2500个左右。其中,有的义项在其他先秦文献中普遍存在,并不是真正的生僻义;有的在其他先秦文献中也很少甚至根本不出现,这才是真正体现专书词典价值的专义。其中,有的专义可以补充大型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漏收的义项,如“辟1”(“辟2”是“譬”的古字),《国语》共有6个义项:1.法,法度(1次)。2.罪,罪过(3次)。3.开,打开(1次)。4.躲避(3次)。5.开拓,开辟(1次)。6.撤去(1次)。其中前5个义项虽然在《国语》中出现频率较低,但是在先秦文献中普遍存在,《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也予以收录;第6个义项“撤去”,就属于专义,其他文献很少出现,《大词典》也没有收录,如:优施出,里克奠,不飧而寝。(晋语二)韦昭注:“辟,去也。”
“明”,《国语》共有12个义项,其中有“水道”义(1次),如:“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以妨王宫,王而饰之,无乃不可乎!”(周语下)《大词典》未收录。
有的生僻义虽然为大型辞书所收录,但是缺乏战国时代的例证,《国语词典》可以弥补这种缺失,如“典”,《国语》共有4个义项,有3个义项为常见义,“掌管,主持”义(1次)为生僻义,如:“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之。”(楚语下)这一义项在《大词典》中的第一个例证是《尚书·多方》:“克堪用德,惟神天。”其后就是唐代的用例了。《国语》用例可以补这一义项在战国时期的用例缺漏。
当然还有许多《国语》中的生僻义,《大词典》已经把《国语》列为首见书,《国语词典》可以与之互证,如“待”的“假贷,宽宥”义(1次),《大词典》引证:“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之?”(晋语九)韦昭注:“待犹假也。”
“谍”的“侦察,刺探”义(1次),如:“自卫过曹,曹共公亦不礼焉,闻其骿胁,欲观其状,止其舍,其将浴,设微薄而观之。”(晋语四)韦昭注:“谍,候也。”
随文释义,是在文献中临时产生的意义,离开文献,这个意义就不单独存在。大型辞书一般不会收录随文释义,但专书词典与之不同,它应当收录有特点的随文释义,这已经是词典学界的共识。先秦专书词典在处理随文释义时,一般要为其专门设立义项,如《战国策》中“长城”出现了3次,分别代表三段不同的长城(齐长城、秦长城和燕长城),《战国策词典》分别为其设立了义项。
一些大型词典认为有的意义是随文释义,因此没有单独设立义项,而是和其他意义一起归入同一个义项,但是经过专书词典的验证,确认了它的静态语言义的性质,从而弥补了大型辞书的不足,如“宾”在《国语》中共出现25次,其中有3次是“他国派来的使者”的意义。例如:
这一意义《大词典》等都没有收录,它应当是作为随文释义归入到“宾客”义中了,它在《国语》以及《左传》等其他先秦文献中都有一定的使用频率,这说明它具有语言性质,因此,《国语词典》中的“宾”共有4个义项:1.服从,归顺。(8次)2.宾客。(4次)3.他国派来的使者。4.迎宾之礼。
最后谈谈对歧解的处理。少数先秦专书词典只在同一词条下取一种解释,这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众说纷纭者,则参校异同,斟酌得失,择善而从,也间或出以己意。”(王世舜,韩慕君,王文清2004:2);绝大多数先秦专书词典都会收录各家的歧解,但是详尽程度不同,如《吕氏春秋词典》就只收了很少的歧解,仅将一部分“词义不明者放在词条后[备考]下”(张双棣1987:1)。但是也有比较详尽的,比如向熹(2001:21)“(《诗经词典》)同一诗句有不同解释时,择要兼收,用‘一说’‘又一说’的方式标明”,后来向熹将这一原则概括为“首出己见,择要兼收”。我们同意向熹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主张收录所有各家的解释;另一方面,又主张收录一部分重要的歧解,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某一种解释放在义项开头。《国语词典》也是如此,如前面提到的“树惇”。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义项划分好后,还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一般是按照词义间的引申关系排列,有时专书词目具有引申自一个意义的几个义项,在排列时就要参考同时期其他文献,确定两个义项间的引申关系。例如:
阿 1.屋檐上翘的部分(1次)。如: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獉,公惧而走。
(晋语二)2.曲从,迎合(5次)。如: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其惑。(晋语一)这两个意义都引申自本义“(水或山的)弯曲处”,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可以,我们把表具体事物的意义放在前面,把表示抽象动作行为的意义放在后面。
此外,还有以词类为纲来排列义项的(如《吕氏春秋词典》),这一方法不足取,因为词类意义其实是在词汇意义基础上抽象概括而成的,依词类排列义项,实际是颠倒了二者衍生的前后关系;还有按照使用频率来排列义项的(如“十三经辞典”),这对确定常用义和非常用义有一定作用,但作为历史断代词典,这仅仅是次要的方面,按照引申关系排列义项无疑是最有价值的。
(二)词性和用法的标注以及例句的选择
除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和“十三经辞典”外,已出版的先秦专书词典一般都不标注词性。从语言研究角度来看,标注词性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由于各家对先秦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不一,先秦专书词典要想标注词性,必须先确定一个成系统的先秦词类体系。如《左传详解词典》就分14类进行标注,它们分别是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状态词、象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吕氏春秋词典》分12类进行标注,它们分别是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十三经辞典”共分12类,分别是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兼类词。这些词典的编者在标注词性的同时,也表明了对先秦汉语词类系统的见解。这是在先秦专书词典中进行词类标注的前提。
另外,对词类活用的处理,恐怕是最能体现先秦专书词典时代性的工作了。本着详尽性和细致性的原则,先秦专书词典必须反映专书中出现的词类活用现象,具体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词类活用处理成义项,另一个是将词类活用处理成某一义项下的特殊用例。
我们认为,先秦汉语中三种词类活用现象可以处理为义项,它们是:1.名词、形容词的使动和意动用法;2.名词、形容词用作一般动词;3.动词和形容词用作名词。因为这三类活用现象普遍存在于先秦文献中,而且意义都有所变化,并有一定的复呈性。这里举《国语》一例:“军”本义为“军队”,《国语》中又用作动词“驻扎”,这一意义共出现了4次,分别是,其他文献中这一用法也常见,所以应该单独立为义项,并且标注为动词。
另外一种活用现象“名词用作状语”可以处理为某一个义项下的特殊用法。这种情况下词的词汇意义并没有改变,只是临时增加做状语的用法,因此不单列为一个义项,可处理为该名词性义项下的特殊用法,随例证一并说明。例如:
夕 傍晚,日暮。《国语》共出现12次,如: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也。(楚语下)经常用作状语,《国语》共出现3次,如: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鲁语下)
下面再说说例句的处理。先秦专书词典主要采取全释的形式,理想的方案是给出每一个词和义项的所有例句,如王世舜主编的成系列的“先秦要籍词典”就是如此,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大部分先秦专书词典只给出了部分例句。在选择例句时,也要有一定的讲究,最好选择用法上有代表性的,普通的例句可以不必给出,比如上例中名词“夕”做状语的例子就比较特殊,不仅要给出,而且需要进行说明。当然,如果要让专书词典具备用法词典的功能,可以给出每一个义项充当不同句法成分的例句,如《吕氏春秋词典》就是这么处理的。以上主要谈的是纸质词典的情况,如果制作成电子词典的话,可以给出所有例句,两种词典配合,更有利于读者使用。
六、先秦专书词典的编排
目前先秦专书词典正文共有三种编排法,它们是:
1.音序编排法。其中最常见的是按照现代音(汉语拼音)的音序进行排列,如向熹《诗经词典》、周民《尚书词典》以及王世舜主编的“先秦要籍词典”等;也有按照上古音进行编排的,如张双棣《吕氏春秋词典》,先按韵部排列,韵部相同者按照声母,声母相同者按照谐声偏旁,这是一种极具先秦汉语特点的编排法。
2.笔画编排法。按照笔画的多少进行排列,如杨伯峻等编《春秋左传词典》、王延栋《战国策词典》、杨伯峻《论语词典》等。
3.部首编排法。按照部首排列,同部首的按笔画多少排列,如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
上面只是一些基本的编排法。有的词典采用了复合式的编排法,例如“十三经辞典”,单音词排列用的是部首编排法;单音词条下的多音词条目按音节数量排列(少的在前,多的在后),音节相同的按使用频率排(频数多的在前,频数少的在后),音节数量和使用频率都相同的,按照经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顺带说一下索引的情况。有的专书词典没有编制索引,如杨伯峻《论语词典》和《孟子词典》;或者只有一两种索引,如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只有笔画索引,周民《尚书词典》只有音序索引,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有笔画索引和四角号码索引;比较完备的是《战国策词典》《吕氏春秋词典》和“十三经辞典”,其中前两部有部首索引、音序索引和笔画索引,《吕氏春秋词典》还同时有上古音(王力上古音系统)和现代音(汉语拼音)两种音序索引,后一部还有四角号码索引。
先秦专书词典的编排法和索引要根据专书的规模和读者的需求来设计。从规模来讲,篇幅较小的文献编排可以简单些,篇幅较大的可以复杂些,但是应当采用断代词典和历史词典通常使用的编排方法,这既能方便读者掌握,也能更好地和这些词典配合使用,互相补充;索引可以只采取一种形式,也可设计多种索引,但是从现代读者的需求来看,不宜用上古音来进行编排。
七、结 语
前人在先秦专书词典的编纂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体现在繁简体字的选择、词目的确定、注音、释义、编排和索引等各个方面,学术界似乎应该总结一套通行的规范来统一先秦专书词典的基本体例,以利于这类词典更好地发挥作用。
附 注
[1]这两部词典分别附在杨伯峻所注《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后。
[2]《诗经词典》中没有明确说明其研究底本是哪一个,以上结论是根据书中所附“《诗经》原文”进行的推断。
[3]较早提出“复语”这一术语的是王念孙,他在《读书杂志》卷三中解释《史记·扁鹊列传》“疑殆”时提到:“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
1.陈长书.从《国语》看先秦汉语词素的发展.语言科学,2011(2).
2.陈长书.从《国语》字词关系看先秦文献中的分词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5).
3.陈海伦.论专书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河池师专学报,1994(1).
4.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5.郭太安,苗若素,李廷安.春秋公羊传、商君书、列子词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
6.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7.胡明扬,谢自立,梁式中等.词典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8.蒋绍愚.汉语词典的编纂和古汉语词汇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89(5).
9.刘叶秋.古汉语词典编纂简说.编辑之友,1983(3).
1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十三经辞典编纂委员会.十三经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2012.
12.宛志文.试论专书词典的编纂.辞书研究,1986(2).
13.万祥祯.诗经词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14.王力.理想的字典.∥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九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5.王世舜,韩慕君.老庄词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16.王世舜,韩慕君,王文清.论语孟子词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17.王延栋.战国策词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18.向熹.诗经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19.向熹.专书词典与训诂.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1).
20.徐时仪.专书词典编纂蠡测.∥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中国辞书论集(1999).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1.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2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24.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杨合鸣.诗经词典.武汉:崇文书局,2012.
26.张双棣,殷国光,陈涛.吕氏春秋词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27.周民.尚书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基于《广辞苑》从有无对应动词形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