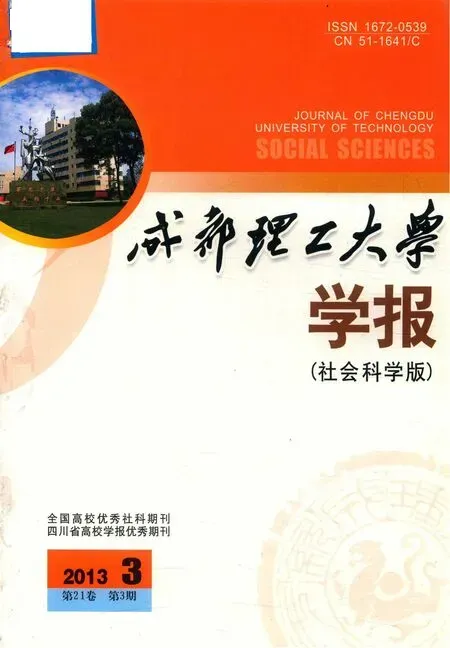“主体性失落”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元批判”与“去蔽”
钱美玲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9)
谁都不会否认,一个人刚出生时,不过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而这个自然存在要转化为社会存在物,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合格成员,就必须从小接受教化。不用说,教化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1]我们甚至可以说,个人接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学习语言的过程,而语言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单纯的形式和空洞的外壳,语言在其实际运用中(包括传授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也就是说,传授一种空洞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传授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授意识形态的过程。个体只有通过语言与意识形态认同,才会获得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也就是说,个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在其与社会交往关系中,逐步具备语言能力,也逐步融于和一体化于既定的社会系统意识形态中。
然而,于此同时,其主体性的失落也就越严重。在极端的形式下,他甚至成了一个装满意识形态语言的容器,陶醉于对子虚乌有的“主体性”的盲目满足。他常常会充满自信地使用下面包含这些语言的句型,如“我确信…”、“我认为…”、“我发现…”,实际上,这里的“我”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代名词。真正的我,即有独立见解的我已经淹没在意识形态的硫酸池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以来,“言”和“在”的关系便被颠倒过来了:“我不仅是说这种语言,我们从语言而来说。”换言之,“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被始终嵌入语言本质中了。”[2]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主体性谈得最多的地方,我们见到的却是一种“无我之我”,即“主体之死亡”。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涵括着各种情感和观点的意识形态时所说的:“通过语言和教化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的动机和出发点。”[3]611这段论述早已暗示我们:真正居于主体之上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个人通过教化的语言而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如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了“人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动物”的著名见解,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的阶级社会导致了主体无意识的死亡。
由此可见,个人主体性的实质变成了意识形态主体性。个人自以为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用双脚站立在大地母亲的躯体上。实际上,作为空虚的、单纯形式上的“主体性”,他只是像浮萍一样漂浮在意识形态的“以太”中。个人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幻觉中,即以为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地思考任何愿意思考的问题。其实无论是他所思考的问题,还是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或解决问题的方向,乃至他思考问题的语言和提出问题的句型,都是意识形态在冥冥之中提供给他的。
既然主体世界都是漂浮在装满语言的意识形态的容器中,都不过是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存在物,借用海德格尔类似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意识形态中的存在物”,那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祛除语言与意识形态的遮蔽物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寻找到真正的从事创造性的主体世界呢?因此,自觉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我们就获得了元批判的制高点。这种元批判的导向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向人类思想贡献出来的最卓越的成果,也就是说,为我们主体世界澄明了思想前提。说得严重一点,撇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就可能蜕化为一种实证知识,即成为一种完全丧失了批判维度和总体眼光的、学院化的知识。所以,只有恢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应有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质,才不会失去马克思赋予它的那种蓬勃的生命活力[4]16。在着手研究“主体性失落”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以澄明,而这一澄明的过程就是“元批判”的过程。
一、澄明“语言与意识形态”间的联系
(一)哲学主体消融在语言中,主体即语言
“语言本质”中的“本质”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所意指的是语言之为语言如何“成其本质”,对“语言本质”的澄明便成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澄明之镜。黑格尔在论述语言与主体异化的关系时候写道:“语言是纯粹的自我作为自我的定在;在语言中,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着的个别性才作为他的个别性而获得生存,这样,这种个体性才是为他的存在。我,作为这样纯粹的我,除了在语言中外,就不是存在那里的东西。”[5]这就告诉我们,主体非但不再构成“语言”的“源头”和基础,反而成了语言的结果和产物。正因为如此,福柯把“人之死”理解为“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语言本质和源头的主体之死。”[6]对于“语言本质”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地去探讨这个问题。真正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的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在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轮》中指出,哲学家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于理解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上的我不是人体或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的灵魂,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他这样写道:“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事实表明,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7]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上的主体是一个缩小至无广延的点,这个主体消融在语言中,因而实际上就是语言,所以,主体的语言的界限也就是主体世界的界限。正如18世纪末,是“表象范式”的危机时期和革命时期,是“表象范式”向“主体范式”的转换时期一样,当今时代便是“主体范式”向“语言范式”的转换时期。“大写的主体之死”不是别的,正是这种“范式”转换的产物和结果。
(二)克服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消除语言误用
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而语词的含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约定俗成或普通人的理解方式来加以确定的。假如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没有选择好合适的语词,而他们对它们的含义的理解又各不相同,就会妨碍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难达到相应的共识。尽管学者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澄清语词的含义,给它下定义、确定适用范围、做出确定的解释,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语言上的误解和误用状态,甚至在某些方面反而加剧了人们之间的无休止的争论。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但在许多场合下,语言也是阻碍思想交流的工具。要言之,有了语言,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相互亲近;但有了语言,人们也可能相互误解和相互疏远。培根的“市场假相”显示的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中必定会遭遇到的这种悖论。继培根之后洛克认为,人们在使用观念时,经常会产生混乱的情况,这种情况关涉到他们究竟如何运用语言。他告诉我们:“在一切语言中,人人都可以看到,有些文字在起源方面,在其习惯的用法方面,并不曾表示任何明白清晰的观念。这类文字大部分系各派哲学或各派宗教所发明。”[8]所以,洛克主张把经院哲学家以及后来的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称之为“编造这类名词的大家”。洛克还把人们在运用观念做判断时的先入之见或偏见归结为四种错误的尺度。我们发现洛克所批判的“四种错误尺度”与培根所批判的“四假相说”有不少相似之处。关于语词误用,意识形态这一重要观念的创制者拖拉西看来,宗教意识和来自其他权威的知识,如形而上学的知识之所以是谬误的、应当被决绝的,是因为这些观念无法还原为人们的直接感觉,而他所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唯一的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还原”。[9]
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应当如何克服种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系统的形成科学的观念?培根认为要真正地清除或避免语言误用所带来的假相,就必须面对新鲜的感觉经验,从逻辑方法上看,就必须诉诸经验的归纳。在洛克看来,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一定要使知识完全依据于经验,一定要谨慎地、准确地使用语言文字,一定要按照逻辑规则,严格地做出判断和推理。通过观念向感觉的还原,托拉西试图建立一种以数学的精确性为榜样的语言和语法。在这种语言和语法中,每个观念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语言记号,以此避免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的产生和蔓延[4]29。
综上所述,无论是培根、洛克还是拖拉西他们的澄清语词的学说唯一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人们从外部世界中获得的感觉和经验。然而,尚待追问的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获得的感觉经验一定是可靠的吗?以拖拉西为首的意识形态家们并没有沿着这个前提性的问题继续追问下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追问的中止表明,意识形态理论在创立之初已经蕴含着自己的局限性了。正如使徒彼得对安那尼亚说:“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10]
所以,真正的祛除语言的遮蔽物必须运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加以“去蔽”。
(三)“意识形态悖论”:统治阶级其根本利益必然被意识形态所隐藏
意识形态的悖论在于,它既要通过语言说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宣布这种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又要竭力遮蔽这种根本利益,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细节或其他问题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光要求人们记住什么,也要求人们忘记什么;不光为人们的思想提供可靠确定的领域,也为他们的思想划出不能擅入的禁区;不光使人们获得教养,也使他们失去自我;不光使人们在某些方面获得判断力,也使他们在另一些方面丧失判断力等等。总之,意识形态既要让人们知道它愿意让他们知道的东西,又要使人们不知道它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的东西。凭借这种语言上的技巧,意识形态在说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同时又竭力把它遮蔽起来。这样意识形态问题就转化为语言问题或“语言批判的问题”它要表达和描述世界的问题,从而归根到底是一个在可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的悖论问题[11],语言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真是意识形态悖论的真正的避难所。在《逻辑哲学论》最后的一段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强调说:“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12]到这里主体的言论自由已经在漂浮于语言下的意识形态世界里变得不自由,甚至丧失。
正是因为这种“二律背反”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通过批判,去意识形态之蔽,从而认识现实世界和主体世界的真相[15]136。
(四)马克思提出:语言决定于意识形态,如果无批判地使用某种意识形态的语言,主体只能成为该意识形态的囚徒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那里,马克思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的载体是语言。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者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形态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6]30在马克思看来,诸多意识形式虽然在意识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产生出来的,但他们同样是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和语言的关系还有另一方面,即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自己的。语言作为对意识形态存在意义的直接呈现,其实就是让意识形态本身说话,而不是让作为主体的人说话,正如海德格尔在“诗化本体论”中所阐述的:语言与人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倒转;语言不再是人的平等交流的工具,而成了意识形态存在的代言人,人反倒成了语言的工具[18]。马克思在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时,曾讽刺他使用了“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式的、意识形态的语言”。[17]34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蕴含着如下的意思:即一个人如果仍然无批判地使用某一意识形态所常用的基本术语,那么他的思想是不可能超越这一意识形态的。换言之,他在思想上仍然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囚徒。马克思之所以创制出一系列新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新世界观,目的正是为了彻底地(包括在语言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决裂。
二、批判是认识“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必要工具
如上所述,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以一定的语言为载体的。也就是说,即不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语言越来越成为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之间的媒介物,以至于说,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都漂浮在语言中。意识形态如同一种普照的光,笼罩着整个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问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对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的笼罩,同时又是对它们的变形,以至于主体性的丧失、退化与失落。既然主体不得不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语言)与其他主体沟通,并与其他主体一起面对客体世界,所以在对漂浮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获得深刻批判意识之前,对主体性的人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批判可分为:
(一)对主体性的历史性“蔽而不明”的批判
人们通常认为,认识论研究的是人的认识的起源和本质。这里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自然主义的思维态度。一旦导入马克思所倡导的元批判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先要的对认识主体加以澄明,而在通常的认识论研究中,尽管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认识主体,但对他们来说,认识主体的本质是蔽而不明。这里的“蔽而不明”并不是说人们不知认识主体为何物,而是指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历史性仍然是晦而不明。这里说的历史性不光是指人置身于其中的既定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和物质实践活动,不光是指人的一定社会地位和利益取向,也是指人置身于其中社会主导的精神状况,即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广义的教育学,这就是说,作为认识主体的某个人,可能是文字之盲,却不可能是文化之盲、意识形态之盲。意识形态是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人们参与社会生活,以维护自己生存的实用证书,是人们在社会中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所必备的“旅行护照”。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通过语言载体进入人们的头脑的,因而黑格尔把教化理解为语言的直接现实。由此可见,人是通过一套习得的语言,一套既定的概念来接受意识形态的。一般来说,人们不可能纯粹地学习语言,人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进入一种文化、进入一种意识形态的过程。所谓纯粹学习语言的说法,不过是我们无思考地接受的一种幻念罢了。正式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把语言理解为影藏着意识形态倾向的话语体系。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这些见解的话,那就是说,一个历史性已经被澄明的让你在开始现实的认识活动之前,已先行地接受了他置身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他的心灵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蜡块”或洛克式的“白板”,而是先行地写满了意识形态象形文字的“青梗峰下的顽石”。诚然,当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开始学习语言时,甚至在学习语言之前,已通过感官在接触、感受周围的世界,但我们得承认,一个人的主要的认识都是通过语言而习得的,而一般说来,儿童对语言和观念是缺乏批判能力的。当他进入青年时期,开始具有较成熟的反省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他骄傲地称之为“自我”或“自我意识”的东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自我和自我意识早已漂浮在意识形态的“以太”中。也就是说,他通常认为自己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时候,恰恰也是这种主体能力丧失殆尽的时候。
(二)对人的主体性异化直接现实的批判
在伦理世界中,语言表示规律和命令,在现实世界中则表现为建议。在这两种世界里,语言仅仅是它所要表达的本质的形式,而在教化中,语言却以自己这一形式为内容,并且作为语言本身而有效准。因为教化唯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教化世界乃是一个语言的王国。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语言是纯粹自我作为自我的定在;在语言中,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着的个别性才作为它的个别性而获得生存。”也就是说,普遍的自我,纯粹的自我只存在于语言之中,教化正是通过语言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而被感受到并发挥其实际作用的。这样一来,教化所期待达到的“高贵的意识”在语言上就成了“阿谀的英雄主义”,成了对国家权力的一片颂词,主体性高贵败给了意识形态的权威。于是语言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分裂和颠倒,而语言本身也发生了分裂,诚如黑格尔所描述的:“对其自己的感念有所意识了的精神,是现实和思想的绝对而又普遍的颠倒和异化;它就是纯粹的教化。人们在这一纯粹的教化的世界里所体验到的是,不管是权力和财富的现实本质,还是它们的规定概念善与恶,或者善的意识和恶的意识、高贵的意识和卑贱的意识,都没有真理性;相反,所有这些环节都相互颠倒,每一个环节都是它自己的对方。”黑格尔称这样的意识为“分裂的意识”;并认为,用来表示这种意识的语言是十分机智的。在他看来,狄德罗笔下的“拉摩的侄儿”的思想正是这种“主体性异化”的典型代表。
(三)对“颠倒的主体与意识形态”的批判
人出生之后,不仅呼吸物质的空气,也呼吸着精神的空气,这种精神的空气也就是通过习得语言而接受的意识形态当一个人成为成年人,即从外观上达到独立思考的年龄的时候,实际上也正是他的内心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头脑中国装满了通过语言媒介而接受的意识形态见解,中文“人”这个字的写法,即一撇一捺,就像一个真实的人分开双脚站在地面上一样,他的立场似乎十分坚定,实际上,通过语言,即吸允着意识形态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他,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他不是站在地上,而是漂浮在意识形态中,就像浮萍浮在水中。他私下认为,他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语言而获得的一切观念的主人,实际上,他完全颠倒了,意识形态才是他的真正的主人,而他不过是一个装满了意识形态液体的容器,不过是自己已然接受的种种观念的奴仆而已。其实,理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主体性”也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存在物,一个空的胡桃壳,而真正的主体乃是人们已然接受的并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创造人”的旧格言已经让位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或教化)创造人”的新格言。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动物,他的额头上总是印着意识形态的标记。在通常情况下,只要以诉诸言谈,作为“小我”的他就悄然隐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大我”——意识形态。
三、只有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获得自觉的批判意识,才能“去蔽”与“超越”
如上所述,真正的主体性根植于充斥着语言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样特尔斐神庙中著名箴言“认识你自己”也就转化为“认识意识形态”以及澄清纷繁复杂的哲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获得自觉的批判意识,个人才有可能找回已经失落的自我,并确立起真实的主体。实际上这也是人类寻找已经迷失自我的一个重要尝试。人是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方式找到自我的。无论是笛卡尔对“我思”的追随,还是胡塞尔对“先验自我”的探寻,都不可能找到已迷失的自我,唯有通过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进行深刻的反省,才有可能找到已迷失的自我。因为已迷失的自我漂浮在以一定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语言中,只有对这种语言获得批判性的识见,已迷失的自我才会隐退,真正的自我才会呈现出来。我们要想从语言和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主体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就从以下三方面祛除遮蔽物,实现主体认识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超越。
(一)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观察方式”
传统的意识形态所蕴含的方式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成有生命的主体。与此相反的观察方式:从现实的、从实际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对外部世界的意识。在马克思看来,超越一种意识形态,亦即从意识形态的世界下降到主体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说:“对哲学家们数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苦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存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3]525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代结构主义思潮席卷世界各地的时候,德里达就向人们宣告了结构主义的衰亡,德里达的根本努力就是用他自己的所谓的“书写语言”来取代“哲学语言”。这就告诉我们,走出既定的意识形态的世界,首先要跳出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灵魂的哲学语言的藩篱,要把这种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日常语言,从而认清这种语言乃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总之,一定要从思想世界和语言世界中摆脱出来,一定要真正的站在现实世界和生活的世界的基地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之谜的谜底正深藏在现实主体的生活中。从主体的真实的生活过程出发,深入地反省并批判意识形态和哲学或教化语言的虚假性和颠倒性,才有可能摆脱意识形态制造的种种神话和幻念,而人们关于意识的种种空话才有可能会让位于真正的知识,意识形态的主体才会让位于真实世界“人”的主体。
(二)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树立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
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的失落即“物化”和“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是,物主体化,意识形态主体化,人客体化,物和意识形态成为人的主宰,人成为意识形态的奴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将会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意识形态生存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得它们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6]79正是这样的共产主义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才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马克思把历史上颠倒的思想世界和主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又重新颠倒过来了。从此以降,主体和以语言为载体的意识形态之谜彻底的破解了。意识和意识形态终于回到了它们原先的地位上。事实上,也只有记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这一基本的学说,主体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理论头脑和独立思考的立场,识破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和语言假象,才能最终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意识形态的阶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实现主体个性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性最终转变为代表全部人类利益的“类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17]
(二)必须诉诸实践活动
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语言、意识或意识形态),都内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就是说,在人类认识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实践相对于认识、理论、语言、意识形态而言,总是优先的。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倡导了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归化法。“意识的一切形式的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他们消灭。”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的批判,它的基本宗旨在于使现实世界革命化,而不是仅仅诉诸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或语言词句的洛克式的感觉经验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