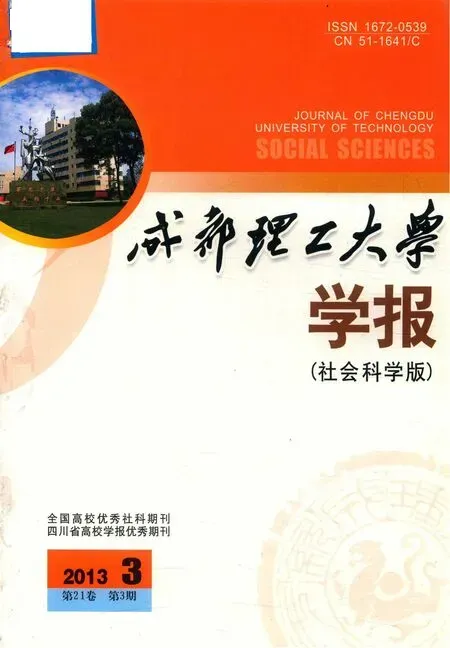论历史教育的生命关怀意蕴
杨金华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4)
一、传统历史教育观反思
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几千年连续不断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使中国人常引以为骄傲,史学工作者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国家的重视。说起历史教育的价值,大多数人可能马上联想到历史教育可以总结经验教训,提供治国智慧。作为我国史学开山之杰作,孔子写《春秋》的初衷就在于改变“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的乱世。《春秋》经世致用的普遍意义,为历史教育留下的优良传统,故有“史学之本于《春秋》”之说。司马迁著《史记》的目标之一就是“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并且明确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记·秦始皇本纪》),强调历史对后世的借鉴作用,即“明镜所以照形,观古所以知今”。前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后人可奉以为法;失败的,后人当引以为诫。后世史家承袭了这一基本思想,顾炎武、黄宗羲以及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无不以倡导以史经世为已任,强调通过历史对后代进行通古观今,鉴往知来的教育。所以,古往今来的政治人物与志士仁人也从不同视角追问过去,希冀从历史中探寻民族兴亡的历史轨迹、经邦济世的治国之道或者纵横捭阖的“君人南面之术”。
除了强调经世致用之外,用历史进行道德教育,历来也受到世人的重视。《周易·大畜》就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看得出古人非常看重历史教育对修身养性的积极价值。孔子在《春秋》里首创“贬褒义例”,在字里行间实现“寓褒贬,别善恶”。例如,同样是关于杀人的历史记载,就有“诛”、“杀”、“弑”三种区分。司马迁称其“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此以后,《春秋》笔法就成为我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史官们记载事实,往往把善恶功过、道德劝诫,当作题中应有之意。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就有“德行”、“忠义”、“节烈”、“奸佞”、“贰臣”等栏目。古代历史教育的载体以史籍经传为主,也有选辑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行,既重视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同时也潜移默化进行道德教育。所以,历史又是历代统治者进行人伦道德教育的一本活教材。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为后人树立起思想和道德上的楷模,要求后人仿照先圣先贤的言行以为行动的准则,以求用先人的事迹教育指导后人,从而达到辅助经典,规范百姓,教化民风的目的。
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就是一种立足于德育的政治教育,即以“人伦教化”来“化成天下”的政治工具主义。多少年来,政治工具主义思想占据历史教育界,正是基于人伦教化的教育理念,说到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或者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不假思索想到,学习历史无非可以实现“资治”,或者学习历史是道德“教化”的最佳形式。正是长期停留在历史的工具性层面,很少有人再进一步追问历史教育的本真目的或者历史教育的生存论基础。所以,在中国传统历史教育中,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占据了历史舞台的绝大多数位置,也是历史教育的主心骨和主旋律,很难寻到芸芸众生和普通老百姓的一席之地。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古代一部二十四史,全部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其实,对统治者及其所属集团的讴歌、赞颂和敬仰,在一定意义上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映射,也是农业文明和小农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客观印证。传统史学的教育内容为了突显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必然以政治变革和军事活动为重点编排对象,王朝兴亡、历史变迁甚至帝王发家史都是万人瞩目的历史闪光点,涵盖了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对学生灌输强化的主要思想。历史教育的政治功能决定了中外统治者对历史的格外亲睐,也决定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定年代,政治灌输成了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教育体系中体现尤为明显。
二、缺失生命关怀的现代历史教育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过度强调历史教育所承担的政治教育功能,历史教育的工具性一步步被强化。从历史学科的课程体系设置,到历史教材知识点的选择以及考试大纲的制定,无不打上政治教育的烙印。在历史教育内容安排上,大多把国家、民族、政权、阶级等政治话题作为教学重点,以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历史人物作为考核知识点,突出社会思潮、政治变革和朝代更迭中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性。在历史教育方法上,对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解释也是以政治原则作为判断标准,或者抛开具体历史情境对历史人物作空洞的政治概念分析。其结果,历史教育是实现统治者政治意识的必要工具,是意识形态内化的辅助手段,通过历史教育将施政纲领、价值取向和阶级意志顺利贯彻并得以全面实施。可见,历史教育被赋予了几重重任,至少包括论证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说明统治思想的至上性以及主流道德的完美性。历史教育依附于政治教育,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历史教育脱离其本来目标、失去其本真价值。这样,历史教育的工具性和政治性得以最大限度的张扬,功利性目标代替了素质教育目标,政治说教代替了人文关怀,而历史教育的人文内蕴却被严重削弱和深度遮蔽了。而文化认同、情感慰藉、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都不是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如果说还具有一定位置的话,也只是处于依附状态。
历史教育工具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纵横捭阖、血雨腥风的历史发展中,只有冰凉凉的历史事实而失去了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应当具备的是非观念、美丑意识、善恶标准以及基本的人性特征,都淹没在特定的政治活动中,甚至连对经济活动、政治观念、阶级意识和国务活动的历史分析,都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变成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的结构搭配或者是阶级意识的文化阐释和理论分析。“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1]515当历史教育完全被工具化所遮蔽,历史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所谓事先设定的因果关系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根据所谓的历史表象去深层次分析历史的内在本质,历史教育的本真价值被抹杀了,消退了。本来栩栩如生、鲜活明亮的历史人物被条条框框窒息,颇具人文色彩的历史教育变成曲高和寡的孤芳自赏,本来对历史知识很感兴趣的学生也对历史畏惧三分,采用逃课、开小差的形式消极对抗。由于历史教育内容的狭窄和固化,很难具有人的精神解放性质,又因其方法的武断化,至于什么是心灵抚慰、人文关怀、生命意识这类深层次价值都被遮蔽。我们简单地看待历史传统的过去性,把历史教育等同于学习历史教科书,甚至连民族认同、文化归属感、爱国主义等深层次的文化功能,也都建立在“背”“考”历史起因、历史过程和历史意义的基础上。在学生眼里,历史是已经过去的遥远传说与现实生活相距太远,更极端的看法是,历史教育无非是政治说教和思想控制的另一种翻版。与此同时,学生个体就成了盛装历史知识的容器,而不是活化历史的生命体,这就加深了历史与当下生命之间的鸿沟,造成历史成为个人思维记忆的材料,而不是生命的鲜活滋养。[2]
在教育知识化的理念指导下,历史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准确把握历史概念、构建完整的历史知识体系,同时兼顾学生思维的广度和理论的深度。在历史教育内容的选取上,琐碎的历史知识点独占鳌头,历史的生命世界隐而不显,历史教育成为抽象概念的演绎,变为空洞符号的记忆。当历史教育内容被抽去了活生生的精神情感,只剩下了干瘪瘪的条条框框,已经远离历史学科的人文属性、丧失了本真的生命价值。历史教育不仅没能让学生从历史中获得快乐,而且还在不断地强化着师生的死记硬背。学生对历史课认同度很低,态度也颇具悖论性,“我喜欢历史,但是不喜欢历史课,尤其是恐惧历史考试”。看来,学生对历史教育的淡漠并非我们常常说的是“世风日下”的产物,我们更应该从历史教育的根本性目的多做些反思。因为有血有肉的整体的历史,被现代教育体系格式化和简单化,失去了鲜活的生命价值,文化认同和生命关怀都淹没在枯燥的历史数据和空洞的历史事实之中。结果是,从历史教育获得的借鉴与判断能力,往往是比较简单的,甚或根本就是一种不被消化的概念而已。于是,社会各界表现出对历史学科的冷淡,史学研究同仁也多次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吁,历史教育在当代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失落感。其实,就历史教育而言,“价值序列最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3]141显然,这里就存在一个历史教育能否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的问题,或者说怎样挖掘历史教育的内在价值以更好地适应学生需求的问题。
三、历史教育与生命关怀的本真统一
从根本上看,历史传统是现代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我们的精神的家园和皈依之地,历史教育也是寻找心灵的归属之所。如马克思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4]128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历史教育不仅“点燃”了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文明之火,而且积淀了民族情感心心相连的精神血脉,并且生成了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兰克看来,只有历史文化保持连绵不断才能实现民族精神的源远流长,因为“历史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史学的研究使人们的精神有所皈依,使人们的活动有了动力和目标,得以享受历代的财富,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5]面对现代社会的五彩斑斓、光怪陆离,对现代人而言,遥远而深邃的历史不仅仅意味着祖宗先贤的生老病死、历史境遇的沧海桑田和历史人物的荣辱盛衰。逝者如斯夫的历史时间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薪尽火传、代代相因,同时包含现代人通过逝去岁月构建意义世界、追寻生命归宿和探求生命关怀。
历史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现象和庄严博大、惊心动魄的社会生活形象。在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里,既可以看到历史英雄的飒爽英姿、历史悲剧的荡气回肠、历史喜剧的激荡人心,还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跌宕起伏、历史结果的扣人心弦。人们在回味历史反思历史中,体验到人生的生命脆弱、时光短暂和情感破缺,感悟到生命的痛苦与欢乐、挫折和胜利,彰显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的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6]118从历史教育的本真价值来看,人对历史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经世致用的历史知识,精神追求和心灵抚慰也是后人对逝去历史的现代诉求。在历史教育中既不断地探求真,也以美、善等等为追求目标,并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着对生命的终极关切。历史教育就应该为生命的自由发展提供精神支撑,通过追问历史反思过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揭示生命的独特价值,并为超越生命凝聚巨大的情感力量和意志力量。
其实,历史教育的“鉴古知今”和“人伦教化”,仅仅看到历史教育的工具性并将其将放大到极致,工具意识甚嚣尘上的结果,就摒弃了历史教育的生存论基础,遮蔽了历史教育的更高境界:生命关怀和意义构建。与历史教育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功能相比,历史教育内在的生命意蕴并由此而生成的生命意识,则一直处于历史教育的视野之外,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历史教育所营造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世界,让为生计而奔波的现代人放下快速前进的脚步,形成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价值和世界的终极关怀。历史属每个人,生命也属于每个人,历史与生命在价值关怀问题上找到内在联系。因为“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7]84如果说历史的工具性给人类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那么历史的人文性则回答人类存在的价值、理由和可能。正如柯林伍德在回答“历史学是做什么用的”这一问题时所说,“我的答案是: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近我们人是什么。”[8]11柯林伍德的这一番话,简短、通俗而不失深刻。因为只有深入到历史与生命的深层对接的高度,才能深刻认识到历史对于现代人的敬畏感、神圣感和不可侵犯性,才能真正体会到历史意识与生命意识、历史境界与生命境界、历史高度与生命高度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一种与生俱来的联系。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借助历史教育,源源不断的历史记载才形成了人类在历史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民族感情上的亲和力。
在当前这样一个物欲横流、资本至上、一切向钱看的工业社会,现代人对已经逝去许久的历史不是希望快速收进记忆的匣子,而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有所了解。这种戏剧性的反差表明,就在历史教育被很多人认为没什么用的时候,在民众心中其实恰恰隐藏着对历史的巨大渴求。在尚新务实的工业时代,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大为频繁和复杂化,现代的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朝代更迭、王家兴衰的大事,也不仅仅是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这也说明,在大众文化加速更替的现代社会,许多人感受到困惑和不解,但是更愿意回望过去回味历史,希望在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现代心灵的皈依之所。因为“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9]46-47另外,从民众的普遍心态而言,人对历史都有着潜在的兴趣,人们在生活中往往有意无意地都有了解或反思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过去经历的欲望。于是,苍茫浩瀚的历史感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一代又一代人执着于经山史海、烛微探幽,引发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凭吊怀古、咏史叹史。回望历史不单意味着现代对过去经验的看重,更意味着代际之间希望保持生命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从根本意义上说,历史教育不仅培育了民族延续的生命之根,而且构建了文化血脉的精神家园。
四、构建历史教育的生命价值
在现代社会,历史教育的价值定位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习经世致用的历史知识和接受传统的道德情操教育,其本真的价值是从历史教育中获得文化认同、情感慰藉、精神寄托和生命的意义。历史教育的本真价值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品味,凝聚人的情感力量,强化人的意志力量,从而构建现代人的生命世界。就像布洛赫所言:“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10]23所以说,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让历史教育更加关心自己的命运问题,更关心自己的存在价值。“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11]5其实,历史教育关心自身命运和存在价值问题,恰恰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因为,历史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是“人要变得无限地关心自我生存和自我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承袭怎样的人类文化、发展怎就当前样的人类文化问题。就历史教育而言,我们应该在教育学生懂得历史“人事”的同时,更关心过去历史的“人心”;在关心“人向哪里去”的同时,更关心“人是从哪里来的”;在关心“现在的我是什么”的同时,更关心“过去的我是什么”。如果不是这样,历史教育就会萎缩自身的生命性,“构建现代人的生命关怀”就有可能变成一句空话。
历史教育的价值功能主要不在于存史、教化、资政作用——虽然这也是很重要功能,而更在于体现生命特有的自觉自由的本性和向度,体现生命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以及终极关怀。所以,当代中国的学校历史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学到历史知识、知道政治借鉴,更应该将历史教育的眼光从“天国”拉回“人间”,扩展到学生心灵深处,贴近学生的生命世界。历史教育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知识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的精神诉求。历史教育只有给现代人提供全面的生命关怀,更多地关心现代人的心灵需求,才能更好地获得大众的精神共鸣。正像马克思对历史价值的本质概括,“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12]650可以说,只有注重人文关怀的历史教育,才能使人们的精神有所皈依,使人们的活动具有动力。发挥历史教育的生命意蕴,不仅可以催肥壮大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树,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对生命本质、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的深层思考。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教育的本真价值就是提升人的境界,就是在灵魂深处激发对于信仰、德性、审美以及生命价值的挚爱和追求。通过历史教育强化生命体验和生命认知,观照历史与现实、探索人生和世界。经过长久累积的历史熏陶,逐渐凝结、升华为纵览古今的历史眼光、胸怀世界的精神气度和自我超越的生命意识。所以席勒多次强调,历史教育“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要“培养完美的人”,要使“人性自由地发展”。[13]54但是,当今历史教育的现状却是盛行‘能力主义’,拒斥对情感、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关注,从根本上忽视了历史教育的本真价值,忘却历史教育的本质属性。其实,通过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历史教育形式,陶冶学生情操,净化现代心灵,培养历史神圣感,既是现代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的需要,也是目前历史教育本身走出困境,获得正常发展的需要。因为历史学科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人文学科,历史教育的本质在于陶冶情操,抚慰心灵和生命关怀。所以,重视历史教育的生命内涵,加强历史教育与生命教育的内在沟通,发挥历史教育内在的生命意蕴,在纸醉金迷的物化社会重建全体公民的精神家园,其意义则远远超过政治资政和人伦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