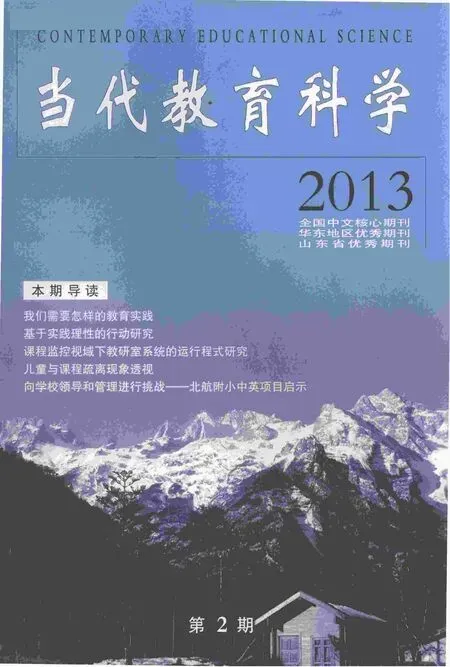儿童与课程疏离现象透视
●王一军
早在近百年前,杜威就明确地指出了儿童与课程的脱节问题,他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儿童的狭小的然而是关于个人的世界和非个人的然而是空间和时间无限扩大的世界相反;第二,儿童生活的统一性和全神贯注的专一性与课程的种种专门化和分门别类相反;第三,逻辑分类和排列的抽象原理和儿童生活的实际和情绪的结合相反。”[1]他认为,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感情和同情。学校里见到的课程所提供的材料,却是无限地回溯过去,同时从外部无限地伸向空间。儿童的生活是一个整体,一个总体。他敏捷地和欣然地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正如他从一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一样,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转变和割裂。儿童所关心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凡是在他心目中最突出的东西就暂时对他构成整个宇宙。”但儿童一到学校,多种多样的学科便把他的世界加以割裂和肢解。已经归了类的各门科目是许多年代的科学的产物,而不是儿童经验的产物。杜威指出的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课程开发活动中普遍存在儿童与课程疏离的现象。
一、课程目标没有关照儿童身心发展的一元性
在具体实践中,课程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作为课程结构体系建构的培养目标。我国2001年开始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培养目标表述为:“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2]第二层次是具体课程的教学要求,反映在各类课程的国家课程标准之中。“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应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和评价建议。”[3]第三层次是具体教学活动中的教学目标设计。“依据各门课程的特点,结合具体内容,加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加强思想品质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创新与实践。”[4]在这里,第三层次的教学目标和第一层次的培养目标具有一致性,第二层次的具体课程目标明确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上加以设计。不管是哪个层面的课程目标,都是我国“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无论是德、智、体、美、劳,还是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素养等,都是把儿童的整体发展等同于具体目标要素的相加,尽管目标很全面,但并不是和谐的整体,因为它脱离了儿童身心发展的一元性。
“人总是超过了他对自己所知或所能知的一切。”[5]在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上,几千年来,身体和感官一直被看作心灵和理性的对立面,而且被降到次要的位置。美国新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man)指出:“对身体的关注被哲学家典型地视为一个在根本上只是个人的、私人、甚至自私的玩意儿,它背离伦理和政治的更广泛的社会目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不仅身体受到社会目的的塑造,而且身体也促成社会目的。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是公众的。身体通常是我们心灵相遇的地方。差不多像通过你的语词一样,通过你的身体的表现,我明白你所感受和思考的东西。”[6]他认为通过身体美学的训练,能帮助我们重新构造自己的感受态度和习惯,从而使我们面对不同种类的感受和身体行为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容忍度。“身体美学的感觉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辩护我们的审美判断,然而却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审美能力甚至道德力量。”[7]梅洛-庞蒂对身体做出了这样的论述:“身体始终与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就是身体。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唤起向我们呈现世界的体验,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世界。”当我们在以这种方式重新与身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时,我们将重新发现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8]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与心理是不可分割的,“人的整体远在任何能设想的客观化的事物之外。”[9]人不等于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素质的相加,人的素质结构具有整体性,人的发展是身心一元的,比任何一种分解式的教育都要丰富与和谐。
身心的一元性在儿童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这是儿童的心理特点决定的。杜威认为,儿童经验的事物“不是分门别类地呈现出来的。感情上的生动的联系和活动的连结,把儿童亲身的各种经验综合在一起。”[10]夸美纽斯认为,感觉是儿童的第一位导师,他指出:“不能预先在感觉中存在的东西,无论何事都不能存在于理性之中。因此,努力地将感觉训练得能够正确把握事物间的区别,就奠定了所有智慧和所有知性的能辩程度,以及人生活动中思维能力的基础。”[11]儿童身心发展的一元性决定了现实中的儿童是具体的、整体性的、活生生的,其素质提高不可能被简单规定,更不可能被标准化和机械化。现实课程强调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实际上只能做到在德育、智育、优育、美育等方面片面的训练,难以达成儿童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的目的。
二、课程内容缺乏与儿童日常经验的联系
刘霞老师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观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她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为例,探讨涉及到儿童观的课文。在这些课文中,有写伟大人物童年的、有歌颂现实生活中的儿童的、有以童话或神话故事的形式出现的,从中折射出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观。课文中的“好儿童”主要有三类:刻苦学习的,乖巧听话的和天姿聪颖的。首肯的好儿童大量是勤奋认真、刻苦学习的。通过写名人、伟人小时候如何刻苦学习、勤奋认真,最终取得了成功,引导学生以此为榜样,努力学习。意在说明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一名好儿童,长大以后也才能有所成就。如《怀素写字》、《他得的红圈圈最多》(邓小平)、《说勤奋》(司马光和童第周)、《梅兰芳学艺》、《徐悲鸿励志学画》、《少年王冕》等。天姿聪颖、才华过人也是课文中着力宣扬赞美的好儿童。《司马光》、《少年王勃》、《晚上的 “太阳”》(爱迪生)、《歌唱二小放牛郎》、《孙中山破陋习》 等;尊敬长辈也是好儿童的标准,这种尊敬一般体现在“听话”方面,如《奶奶的白发》、《送给盲婆婆的蝈蝈》、《花瓣飘香》、《一株紫丁香》、《师恩难忘》等。儿童的乖巧大都是具有成人世界认可的许多高尚品质:向善,助人,坚强。如《七颗钻石》写了善良的姑娘,在每次善举之后总会得到奖励,肯定了善良的人总会得到好的报答。《蕃茄太阳》写了双目失明的残疾女孩明明开朗乐观、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了感激,她临走时对“我”说:“阿姨,妈妈说我的眼睛是好心人给我的。等我好了,等我长大了,我把我的腿给你,好不好?”《艾滋病小斗》讲述了恩科西是一个一出生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黑人小男孩,他的身体非常虚弱,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但是这位坚强的小男孩“不是悲观消沉,而是开始学习怎样坦然地面对生活,面对可怕的艾滋病。”刘霞老师认为,我们的教材更多地是以成人的视野看待儿童,用名人、伟人的标准来要求儿童,把儿童看作是“小大人”,反映出明显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甚至是名人本位的儿童观。[12]这种儿童观的分析表明了现在教材内容的成人文化取向,与儿童的日常生活体验是割裂的。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儿童是丰富多彩的,他们除了学习,更爱嬉戏、玩耍、幻想,还撒娇、任性、自私,他们喜新厌旧、缺乏耐心。这样的儿童在课堂上要学习的都是天才、伟人的童年,如此大的反差怎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引领学生的有效发展。
作为人文教育课程,语文在启迪心灵、发展思想、磨砺心志等方面有着明显的教育优势,但由于过于成人化,很难触及儿童的生活意义与价值追求,课程功能也随之消解。数学、科学等科目在课程结构体系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在当代基础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科技教育强调的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很难给人以完整的生活体验,与学生的日常经验距离更远。用杜威的话说,这些科学知识体系,“它意味着不偏不倚地和客观地观察事实的能力;那就是不问这些事实在儿童自己的经验中的地位和意义怎样。它意味着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它意味着高度成熟的智慧的习惯和科学研究的特定的技术和设备的运用。一句话,已经归了类的各门科目是许多年代的科学产物,而不是儿童经验的产物。”[13]因此,以科学教育为主体的现代课程不可避免地与儿童的日常经验分离,课程内容成为外在于儿童经验的东西。
现行的基础教育新课程强调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从学科概念出发,对教学内容进行生活化的改造,呈现出来的生活通常是概念化的生活而不是现实的生活。像小学数学教材中诸如“鸡兔同笼”、“相遇问题”等都脱离了现实生活,像“一个水池放满水要5 小时,放完水要6 小时。同时往里放和往外放,水池放满需要多长时间? ”这样虚假的应用题更是比比皆是。由于这种“生活化”本身脱离儿童当下生活,同样不能与儿童的日常经验建立联系。正是这种“联系”的缺失,教学内容难以纳入儿童的经验结构,儿童就难以实现内在的知识建构,导致在没有效率的学习中慢慢失去兴趣。
三、教学过程无视儿童的主体地位
由于知识本位的课程观占统治地位,教学过程被简单地理解为教教科书,学习过程就是学教科书,教学总是基于教科书,围绕知识的传授展开的。受科学主义的浸染,这样的教学本身走向技术化,教学过程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阅读教学总是按照“初读课文,学习生字词——再读课文,理清文章思路——精读课文,逐段理解——熟读课文,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数学教学总是按照“练习检查,复习旧知——联系实际,呈现新知——例题讲解,学习新知——尝试练习,深化理解——课堂作业,巩固练习”,其他学科学习也都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这种按固定套路展开的教学已经成了教师的一种行为习惯,成为一种封闭的教学行为体系,单向地支配着教学行为的展开,完全外在于儿童,儿童只是受众、只是看客,只是配合教师和教材的工具。
这种按“套路”展开的教学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目标控制的教学,教师是教学目标的代理人,教学过程具体表现为被教师控制。教师不仅控制教学的整体过程,也控制着具体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尽管有时教师给学生提供选择的机会、提供自主探究的时间、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但都是教师控制下的自由,学生没有真正的自由。随着儿童的回归,许多教师也试图在课堂上赋予学生学习主体的地位,或使学习过程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但往往是基于对儿童主体性的一种成人化解读,并无真正的儿童主体性可言。比如一位青年教师曾经上过这样一堂对联课,前20 分钟,教师带领二年级的孩子,或击掌,或叩桌,一组接一组,男生和女生,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地读:“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霞。黄鹂对翠鸟,甜菜对苦瓜。狗尾草,鸡冠花。白鹭对乌鸦。门前栽果树,塘里养鱼虾。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一位语文特级教师这样解读:“这是我听过的最为简单清浅的一课。然而,正是它的简单清浅,契合了儿童学习的内在节奏。”说这课“简单清浅”似有道理,说它“契合了儿童学习的内在节奏”却值得推敲。这个青年教师带领学生朗读的内容节奏简单明快,是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但这不等于儿童学习的“内在节奏”,从学习过程来说,儿童的学习节奏指向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力、兴趣能保持多久,二年级的学生不可能对外在于自身的事物保持20 分钟的注意力,也不可能在“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中始终保持主动的兴趣,尽管教师不断寻求形式的变化。教师对儿童的理解通常是从教材出发的,没有真正从儿童主体出发,因此这种教学从总体上说还是无儿童主体的教学。
在基础教育新课程结构中,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占有一定的空间。在新课程结构中思考校本课程,其功能主要是为儿童的个性发展服务,其课程形态主要是选修课。由于是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课程,教学过程从理论上说应服务于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学到什么程度都应由学生自主决定,教师的作用是适当引领和必要服务。但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并没有实现角色的转变或者说还坚守传统课程的理念,往往强调统一性,学习目标、内容等由教师决定,学生仍然是被动学习者。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中,教师的指导与服务往往存在缺位现象,学生主动了、自主了,但主体的认识、思维、情感等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活动有“热度”却没有“深度”,学生有活动却少感悟,儿童的主体性也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
四、教师很少尊重儿童的需要和权利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学生看作平等的人而是把他们看成远离良好的、有组织的和公正的社会的边缘人,为了把他们融入社会,就通过教育来灌输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和思想。在这样一种逻辑的支配下,学生只能处于教育的边缘,成为改造的对象。另一方面,教学长期经受行为主义学习观的统治,其着眼点在于发现教学带来的行为反应,并试图通过调整环境来改变个人行为,把教学看作是目标控制下的一套程序,学生接受的是一种动物性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也无形地被边缘化。正如对课堂进行政治学考察所揭示的那样,“课堂一方面是揭发、抨击权力与权威,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揭发与抨击持续形成特有的权力与权威的、充满矛盾的场所,即使特定的权力与权威被消除了,但不过是另一种权力与权威得以渗透与生成。[14]以赫尔巴特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教学,人们习惯地理解为教师中心主义,这种教师中心主义在新课程实施中并没有明显的改变。教师仍然借助“老师”的特殊身份,行使着制度化的权力。
一位中学生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是我最黑暗的一天。早上因为交通拥堵,公交车没有按时到站,迟到了5 分钟,被班主任抓个正着。他在问我原因时却说:‘为什么不早点起来?’真是好笑,我怎么会知道今天堵车。语文课上,我还为迟到而郁闷,老师竟然5 次喊我回答问题,真不明白,是谁给了老师随便提问学生的权利。更糟糕地是,像有传染病一样,今天所有学科老师都疯狂地布置家庭作业,也不考虑我有没有时间做、想不想做。……好朋友的生日晚会随之泡汤了。”这形象地描绘了老师行使权力的具体行为,他总是单方面地思考学生的需要,习惯于支配学生,无节制地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学生的实际需要和自主学习权利被教师无情地剥夺。
需要指出的是,教师个体并非都是专制主义者,都愿意充当压迫者的角色,他实际上仅仅是制度化教育的代理人,真正剥夺学生需要和权利的是教学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教师的权威来约束学生就范于学科课程,具体指向强制执行的内容体系及其理性逻辑系统,教师的权威因此只具有工具意义。他们对学生行使着权威却失掉了创造性的“自我”,“权威”也就沦为空虚的外壳。他们自身被压迫却又利用角色优势来压迫学生,实际上其自身的解放与学生的主体解放同样重要。“课堂,与其说是师生忠实于自己的本真而生存的场所,不如说是意识到需要迎合他人的价值观、要求、意志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场所。”[15]构筑具有师生自主生存意义的课程教学体系是教育变革的重要命题。
[1]杜威.儿童与课程[A].吕达等:杜威教育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11.
[2][3][4]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6.
[5][9]雅斯贝斯.雅斯贝斯哲学自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9.
[6][7][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文本前言.182.
[8]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265.
[10][13]杜威.儿童与课程[A].吕达等:杜威教育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11.
[11]夸美纽斯.图画中见到的世界[M].杨晓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致读者.
[12]刘霞.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观探析[J].上海教育科研2007,(9).
[14][15]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0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