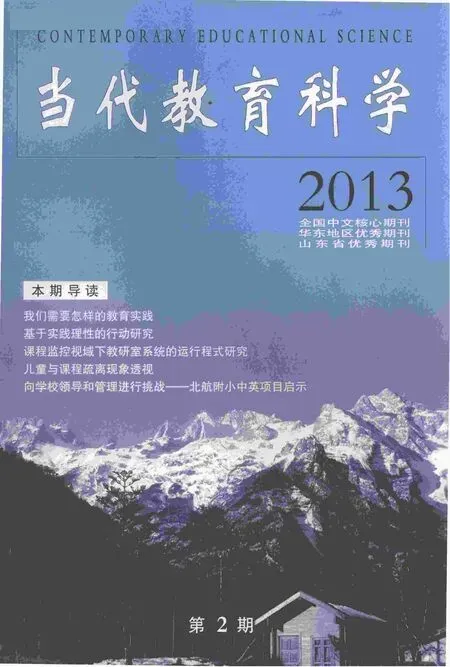基于实践理性的行动研究*
● 苏 鸿
长期以来,行动研究被定格在“科学研究”的范式之中,缺乏对其自身认识论基础的自觉反思与重建,致使行动研究对许多基础性的问题缺乏清晰的回应。例如行动研究是否应该和是否可能创生知识?行动研究的知识是否具有可推广性?行动研究是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等。晚近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对行动研究进行理论反思,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是行动研究的理性基础与理性重建。
一、超越科技理性的窠臼
由于受到传统科学范式的影响,行动研究一直热衷于在科技理性之中寻找自身合理性的根基,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将行动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例如我们常常就把教育研究与教育科学研究混合使用。然而在科技理性的宰制之下,教师在研究中不仅没有成为“研究者”,反而沦落为“帮助其他人收集资料的工具”。[1]
晚近以来,实践哲学开始在西方复兴和发展,并且为行动研究的认识论重建敞开了新的视域。[2]在实践哲学看来,行动研究的理性基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技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区分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这是当代行动研究认识论重建的重要方向。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实践理性的命题,并且对实践理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实践理性不同于理论理性(如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理性(如工匠的制作),实践理性指向的是事先无法预设的事物,体现的是我们行动中的机敏与判断。三种理性又分别对应着三种不同的知识领域,即实践知识、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
到了近代,思想家康德进一步区分了“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他认为前者指的是人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而后者是人的行为决策过程。康德指出,科学理性并不能决定实践理性,也就是说,对事物真相的了解并不等于指导如何行动,这是因为科学理性并不同于实践理性,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
行动研究的积极倡导者西雄则提出了 “技术理性”与“反思理性”的区别,借以说明行动研究的理性特征。他认为,“技术理性”的基本假设是实际的问题可以有通用的解决办法,而且这些解决办法是可以推广和移植的,因此技术理性倡导“研究——开发——传播”的模式。而“反思理性”正好与“技术理性”相反,反思理性的假设是:复杂的实际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发展出来;并且这些解决办法不能任意地使用到其他的情境之中。[3]
综上所述,在当代实践哲学看来,行动研究具有与自然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理性基础,行动研究只有植根在实践理性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源头活水。而深入地分析和阐释实践理性的特点,也就必然构成行动研究新的生长点。
二、实践理性及其特征
在实践哲学看来,实践理性具有与科技理性完全不同的特点,并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实践理性倡导差异逻辑
实践理性不同于科技理性,科技理性遵循“同一逻辑”,并试图借助于“抽象”模式和“简化”模式来获取普适性的知识。而实践理性则遵循“差异逻辑”,认为实践的情境是复杂多元的,研究的终极旨趣是建构多元化的实践知识。
亚里士多德最早对实践理性及其差异逻辑进行了诠释,他指出,实践理性总是与具体的事务相联系,因而一定是多种多样的。他对柏拉图所热衷的抽象的“善”进行了批判,认为实践之中根本不可能有抽象的“善”,所有的善一定是具体的、多样的、复杂的。[4]为此,亚里士多德具体而深入地分析了各种“善目”,例如勇敢、节制、公正、友爱,等等。同理,教育实践也是复杂、多样而多元的,教育领域的实践性知识一定也具有多元性、差异性。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可以把教学和教育的所有规律性都机械地运用到他身上的那种抽象的学生是不存在的。”[5]
实践理性及其差异逻辑要求我们首先在认识上超越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技术理性将教育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认为研究的目的就是建构某种抽象性的、普适性的知识。英国当代教育哲学家普林对此进行了尖锐批判,他“对企图创造一门教学科学的努力表示怀疑,这种科学试图给每位教师应该怎么教做一种确定的和能够证明的解释。”普林指出,教育实践具有复杂性,因此那些“断言能够创造一门教学科学的那些人,忽视了‘学科内容逻辑’的多样性和相关性、社会实在的可变性、相互作用因素的不可预测性以及教师带入课堂的价值、感知和教育目的的差别。”[6]
(二)实践理性强调情境关联
在实践理性看来,实践知识是与我们的生存处境紧密相连的,那些外在于情境的、可概括化的科学知识不一定能解决特定情境的问题。例如,很多老师在培训和学习过程中都接受了许许多多的理论,这些理论甚至可以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没有与我们自身特定的问题情境相关联,因此我们很难从这些理论中发现行动的力量。
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从诠释学的视角深入分析了实践理性的“处境”关联性。他区分了科学知识与实践知识,认为科学知识总是力图剥离语境追求“纯粹”的知识,而实践知识针对的则是我们的具体境况,“它们描述了具体的存在环境中的知识。”[7]也就是说,实践必然与具体的情境紧密相关,我们只能从自己特定的处境出发来进行理解和诠释,因此行动研究所创生的知识是一种情境化的、具体性的实践知识,而不是抽象的、普适性的理论知识。
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的领军人物劳斯则进一步破除了普适理论的幻象。他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地方性知识,都蕴含着特定的情境脉络。他把“理论”理解为“对特殊问题的范例性解答”,“理论理解的发展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转向另一个具体的案例,而不是从理论概括转向特殊的应用。”错误!未定义书签。实践知识的情境性意味着:行动研究创生的知识应该蕴含校本的经验、凸显校本的声音,只有彰显校本特色的教育经验才具有行动的力量。
(三)实践理性注重智慧生成
实践哲学认为,实践的场域具有复杂性、流变性、生成性,因此实践活动一定需要人们的实践智慧和艺术想象。可以说,实践理性是一种蕴含着智慧性、艺术性的理性形式,它与科技理性所强调的客观性、精确性、程序性具有巨大的差异。我们经常讲“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无定法”正体现出教育实践的艺术性与智慧性。
实践理性所具有的智慧性受到很多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实践理性理解为“适度”的艺术,认为“不及与过度都同样会毁灭德性”。[8]而对“度”的把握很明显不是科学方法所能够达到的,这其中需要的是我们的实践智慧。比如,我们经常讲“启发性原则”,然而如何启发?何时启发?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教学模式所能穷尽的,而是必须借助教师的教育智慧和艺术想象。
伽达默尔则将实践理性理解为解释学探询。在他看来,实践场域是一个充满着无尽解释的意义世界,只有开启实践的解释之维,实践之丰富性、意义性才会向我们敞亮。而科学方法却固守客观中立,反对主观诠释,结果忽视乃至压抑了研究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为此,伽达默尔强调指出:我们要切近充满生命意蕴的社会实践,就必须反对科学方法在实践领域的滥用。[9]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主张“放逐”科学方法,代之以解释学的探寻,在创造性的理解和诠释中去接近艺术的真理、历史的真理和语言的真谛。
(四)实践理性凸显对话协商
实践理性具有民主的维度、对话的维度,这是因为实践理性追求的是共识真理,而不是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真理。美国当代思想家邓津(Norman K.Denzin)指出,在社会研究中,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多种多样,“数据”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因此,社会领域不可能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事实”,而只有无尽的解释。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解释充满着冲突与争论,因此研究也就变成了一个对话、协商的政治行动。[10]
艾略特(John Elliott)从杜威和罗蒂的思想中挖掘实践理性所蕴含的对话特质。他指出,杜威所倡导的科学方法本身就已经包含着民主的诉求,因为杜威的科学观念蕴含着开放的心灵、宽容不同观点、思想的自由等民主品性。而罗蒂则指出,世界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科学研究并不存在终极真理或者权威话语。在不确定性的世界图景下,科学发展的方式不是靠压服而是靠说服,而衡量研究质量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对话与共识。罗蒂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之所以被视为是“最科学”的,并不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们遵循了某种科学方法,而是因为自然科学家最容易达成共识。
基于对杜威以来西方哲学理论中对话思想的揭示,艾略特主张把教育研究看做是发展民主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他区分了“教育的研究”和“关于教育的研究”。“关于教育的研究”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某种客观性知识,其背后蕴含的是过时的“旁观者知识观”;“教育的研究”则植根于民主理性,通过对话、协商创生共识真理。[11]
三、实践理性视野下的行动研究
与传统科技理性主宰下的行动研究相比,植根于实践理性的行动研究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旨趣、研究风格与方法路径。
(一)实践性知识
在实践理性看来,行动研究也有创生知识的旨趣,但是行动研究所创生的知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具有行动力的实践性知识。阿吉瑞斯(Argyris)用“Actionable knowledge”来表示行动研究中教师知识的生成。[12]实践理性认为,行动研究与科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就是科学研究生产理论知识,而行动研究生产实践知识。
实践知识不同于理论知识,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脉络和形成机制。理论知识依附于科技理性的脉络,强调研究者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数据,并由此构建客观性的、抽象化的知识体系。罗蒂指出,理论知识中的研究者是一个“旁观者”,因此理论知识代表的是一种旁观者知识观。实践知识则渊源于实践理性,在实践理性看来,研究过程不是从外面简单地移植概念框架,而是必须引发实践者的广泛参与与积极对话,并且在对话之中生成共享性的、情境化的、地方性的实践知识。由此可见,实践知识代表的是一种参与者知识观,强调的是参与者在对话协商之中生成的共识性理解。
行动研究要生成实践知识,就必须在研究实践中培育民主的研究文化。当前西方的行动研究正在走向参与式行动研究,参与式行动研究就是一种民主取向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认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因为人类的知识总是扎根在特定群体和特定情境之中,因而必然带有地方性、情境性的烙印。参与性行动研究把“承认、尊重、重视和优待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强调无论是外来研究者还是一线教师,在研究过程中都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利,研究过程不是从外面移植时髦的理论话语,而是必须关注特定学校情境中的经验与问题,并在民主的对话之中生成具有校本特色的情境性知识。[13]
(二)反思性实践
实践理性具有反思的向度,西雄就将实践理性理解为反思理性。行动研究的过程被看做是一个由计划、实施行动、观察和反思四个环节构成的循环往复的运作系统,其中,“反思”贯穿行动研究始终,是行动研究的精髓与命脉。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往往看到教师的反思流于形式、失之肤浅。个中重要的原因是反思没有真正抵达我们的内心深处,因而不能够有效地消融知识与行动的对立。行动科学的创始人阿吉瑞斯(Argyris)认为,我们大脑中的许多知识之所以没有产生行动的力量,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即信奉理论(espoused theory)与使用理论(theory-in-use)。信奉理论是当事人声称遵行的理论;而使用理论则是指人们实际运用的行动理论,这种行动理论只有通过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才能推断出来。阿吉瑞斯和舍恩发现,人们所持有的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人们一般很难意识到这种差距的存在。例如一位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反复强调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性,但是他的课堂实际却可能是灌输式的。
阿吉瑞斯的理论启发我们,行动研究只有深化反思的深度,聚焦和揭示教师隐性的“使用理论”,并且彰显信奉理论与使用理论的差距,才有可能创生出有行动力的知识。阿吉瑞斯用单路径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与双路径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来描述反思的两种不同的水平与深度。在“单路径学习”中,教师在采取一个行动后,如果发现行动的效果不尽人意,通常只调整行动本身;而在“双路径学习”中,教师不仅回环到行动策略,而且回环到自己行动背后的潜在信念,即“使用理论”。正是这种向更深层次的潜在信念的反思,才会使行动的改变更加彻底、深刻和持久。
(三)对话式民主
对行动研究之对话特质的揭示,是当代行动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Martin Maurer等人指出,行动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式行动研究、批判式行动研究和对话式行动研究。他们认为对话式行动研究不再像传统的行动研究那样聚焦于客观性知识的生产,而是聚焦于文化之内和文化之间的诠释性知识的培育,这种诠释性知识可以通过对话途径来达成。[14]
当代西方行动研究之所以重视“对话”,是因为只有借助对话,教师们才能真正成为知识的创造者。Cochran-Smith和Lytle对三种“教师知识”的观念进行了区分,并由此阐述了对话在教师实践知识创生中的重要意义。[15]他们认为,我们对“教师知识”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 “理论的知识”(knowledge for practice)。这种观点认为教师和指导他们实践的知识是分离的,教师是知识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第二种理解是“实践的知识”(knowledge in practice)。这种观点认为,有价值的教师知识是由少数优秀教师创造的,普通教师需要向优秀教师“学习”这些知识。第三种理解是 “建构的新知识”(knowledge of practice)。在“建构的新知识”看来,每个教师在知识生产中都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通过积极的对话、协商、合作,对别人的理论和研究进行批判性审视,并由此创造出独特性的教育知识。简言之,只有在“建构的新知识”的视野中,教师们才能由知识的消费者转变为知识的创造者。
(四)叙事性探询
实践理性认为,我们切近实践的方式不是科学方法,而是叙事探询。这是因为实践具有复杂性、脉络性、生成性,因而是“事件”的集合,而不是“要素”的集合。传统的科技理性将实践探究简化为“要素”及其关系,这只会使研究远离生动的实践。
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来理解实践,需要我们把抽样的“要素”降解和还原为生动的“事件”,通过对我们经历的教育事件展开叙事探究,从而敞亮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矛盾、冲突,变化,揭示研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开放性与生成性。
叙事探询重在建构我们自己的故事,故事的起点可以是我们的困惑,也可以是我们的经验。其中,尤其是我们成功的教育经验,更是开展叙事探究的良好起点。西方学者Chen Schechter等人分析比较了人类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种是从失败和问题中进行学习,另一种是从成功的经验中进行学习。他们认为,从成功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同样也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学习方式,而且可能还是更加有效的学习方式。[16]
传统的研究观将研究过程界定为问题解决过程,我们经常说“吃一堑长一智”,这里面就暗含着从失败教训中学习的思想。受这种传统研究观的影响,探询学校中的问题与教训容易被看成是行动研究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学校取得的成功经验却往往被人们忽视。
然而从失败和教训中展开探究却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例如组织成员之间会增加心理防御,削弱彼此真诚的对话与交流。阿吉瑞斯曾经指出,人们之所以对自己潜在的“信奉理论”缺乏反思,个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不愿意直接指出别人明显的错误或不足。与此相反,基于成功经验的叙事探究则是把我们的优点予以放大,在这种探究进程中,由于我们减少了利益的纠结和心理的防卫,对话将更加真诚,交流也会更加深入,研究过程也会更加愉快。
[l][6]普林.教育研究的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9.116.
[2]Carr,W.(2006)Philosophy,Methodology and Action Research,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40(4),421-435.
[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53.
[4][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3.38.
[5]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113.
[7]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98.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7.
[10]Denzin,N.K.(1989).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Newbury Park,CA:SAGE.
[11]John Elliott.(2006).Educational Research as a Form of Democratic Rationality,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40(2).
[12]Argyris,C.(2003).‘Actionable knowledge’in Tsoukas,T.and Knudsen,C.(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423-452.
[13]Bill Genat(2009).Building emergent situated knowledges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Action Research,7(1):101-115.
[14]Martin Maurer&Rod P.Githens(2012).Toward a reframing of action research for human resource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Moving beyond problem solvingand toward dialogue,Action Research,8(3):267-292.
[15]Cochran-Smith,M.,&Lytle,S.L.(1999).Relationships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Teacher learning in communities.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Education,24,249-305.
[16]Chen Schechter,Israel Sykes,Jona Rosenfeld.(2004).Learning From Success:A Leverage For Transforming Schools Into Learning Communities.Planning and Changing,35(3&4):15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