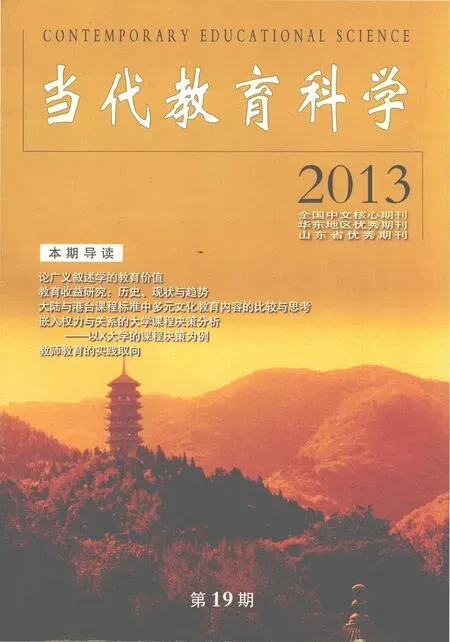论广义叙述学的教育价值
● 程 然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将所有的知识分为两类,即“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科学知识固然不可轻视,“但叙述性知识的模式涉及内部平衡和界面友好的观念,与此相比,当代科学知识则显得黯然失色”。[1]由此可见叙述(没有叙述就没有“叙事知识”)在人类生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与此相关的叙述学也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受到学界的重视。
一、何为“广义叙述学”
叙述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有了叙述学的萌芽,而作为一门学科则是在法国学者托多罗夫于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首次提出“叙述学”概念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叙述学逐渐成熟并广为人知,其影响力今天已经不可小觑。叙述学的提出在当时着眼于文学作品,托多罗夫说:“这部著作(《〈十日谈〉语法》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述作品的科学。”[2]后继者也正是在文学叙述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人们对叙述学的深入研究,发现叙述远远不局限于文学(特别是小说)中,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一门有别于狭义叙述学(文学叙述学)的广义叙述学应运而生。
研究发现,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有格雷马斯、库尔泰等人尝试建立所谓不同于文学叙述的一般叙述语法。而叙述学的真正转向则始于海登·怀特,后经闵克、格林布拉特、丹图等人的推动,叙述学最终越出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领域,也就在这时,叙述学从狭义走向了广义。1999年美国学者戴卫·赫尔曼在《新叙事学》一书中这样说:“叙事学家的注意力并不局限于伟大的叙事作品。原则上说,只要有故事的地方,就会有叙事学,可以在大街上,也可以在图书馆,可以在日常谈话中,也可以在著名的(或不太著名的)小说里。”[3]而中国学者则作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认为叙述几乎无所不在,除了小说,历史、照片、新闻、电影、游戏、广告、宣传、预言、诺言,甚至包括梦。换句话说,叙述包围着我们,叙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在无意识中人也会叙述。那么,什么是“广义叙述学”呢?
广义叙述学源自对叙述的重新定义,中国学者赵毅衡是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广义叙述学意义上的叙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有人参与的变化,形成情节,被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2.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4]由此,广义叙述学面向一切可以被纳入此定义的叙述,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叙述分为不同类型。按照事实性/虚构性,可以分为事实性叙述、虚构性叙述、拟事实性叙述和拟虚构性叙述;按照记录性/演示性,可以分为文字媒介的叙述、语言媒介的叙述、以身体为主的多媒介叙述、以心像为主的潜叙述和以图像为主的多媒介叙述;按照不同的时间向度,可以分为过去向度叙述、现在向度叙述和未来向度叙述。[5]一种叙述可以综合不同类型,而不同类别的叙述是不能随便越界的。比如,戏剧属于虚构性的、以身体为主的、现在向度的叙述,而日记则属于事实性的、以文字为媒介的、过去向度的叙述,二者不可以混淆,如果把日记变成虚构性叙述,则表明叙述者别有动机。
戴卫·赫尔曼认为,走出文学叙述的叙述学“它的主要焦点不是寻找关于基本概念的新的思维方式,也不是挖掘新的思想基础,而是显示后经典叙事学如何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同时也丰富其他研究领域”。[6]可见,广义叙述学不仅可以适用文学研究,而且可以用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关系中的人,研究人在叙述中成长和发展。因此,它自然可以成为学校教育可资借鉴和利用的资源。
二、叙述:重建人的生命意识
当布鲁纳提出“没有叙述就没有自我”[7]时,他其实是宣布了一个事实:叙述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当他人叙述时我只是一个听者,而不是一叙述者。所以,教育学意义上的叙述是学生的自我叙述。而自我叙述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因为叙述是一个生命的叙述,并且叙述的也是关于生命的故事(赵毅衡强调叙述中要有人或拟人),然而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教育出了偏差。
这些年,一些国内教育学者在大力倡导“生命化教育”,他们发现当代中国教育冷落生命,表现在“学校对生命的遗忘”,“教育对生命完整性的肢解”,“教育对生命活力的压抑”,“教育对生命个性的阉割”。[8]他们举出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例(包括杀人和自杀),大声呼吁我们要“反思教育,祈求生命的回归”。他们力主将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转变为以“生命为中心”的教育,即“以生命为基点,关注生命,创造生命适宜成长的条件,使教育真正成为生命的诗意存在地。‘让生命在教育中诗意地栖居’,是生命化教育的最高境界和追求”。[9]那么,如何进行“生命化教育”呢,他们提出了好多途径,其中有一条是“以经验为取向的生命化课程观”,他们说:“生命化教育主张经验的课程观,认为只有通过经验的东西,才能转化为生命。课程就是一种经验状态,这种通过经验获得的不只是片面的经验,还可能是系统的知识。”[10]这当然是个很好的建议,但是这里面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经验到达生命,语焉不详,二是生命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能成为获得知识的中介。所以,当代教育还是必须直面这样的问题,即如何把学生的经验转化成一种生命体认。
我们先来辨析一下 “经验”,经验既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名词指的是人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与“经历”同义);用作动词指的是体验、经历。叙述学意义上的经验,兼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意义,名词性的叙述指叙述的内容是叙述者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动词性的叙述指的是叙述的过程是人的一次体验和经历。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学意义上的叙述首先强调叙述的是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非常必要,因为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的第一份也是最基础的人生财富就是自己的经验,他的经验对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人生和事业,有着无比宝贵的价值。所以,所有老师在指导学生叙述时,他的最根本的落脚点应该是引导学生对自己经验的叙述。只有作为一种自我经验的叙述,它才是独特的、切身的、体验的、反省的。当然,教育学意义的叙述并不排除叙述他人的故事。
那么,叙述怎样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呢?它是通过叙述中的“时间”来实现的。波尔津霍恩说:“叙事是一种图式,人类通过这种图式赋予他们的时间经验和个人行动以意义。”[11]赵毅衡也说:“叙述性并不提取抽象原则,不可能把意义从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因为人与世界的特殊联系植根于个别故事的体验之中。”[12]可以说,所有的叙述都是通过时间对发生在时间中的事件进行叙述。这里有两个时间因素,即叙述时间和被叙述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既有区别又有叠合,它们的区别是,叙述时间是一个现在时,被叙述时间可以是现在时,也可以是过去时、将来时,而它们的叠合是,无论是叙述时间还是被叙述时间,都统一在时间的整体性、连续性、一维性之中。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利奥塔所说的 “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就会发现,“科学知识”是脱时间的,我们学习一个科学定理,不需要了解它产生的时代,它的发现者,它经过了怎样的变革和完善。总之,所有与时间相关的背景我们统统可以撇在一边,弃之不顾。而“叙事知识”则不同,赵毅衡强调叙述必须“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又说:“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一个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为获得了时间中的意义,叙述就起了一般讲述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叙述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13]可见,时间是叙述的核心要素。当学生在叙述中一点一点展示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他会感受到时间给他带来的人生变化,这种变化使他感受了生命的连接和绵延;而当学生运用“一年前”、“上个月”、“昨天”来叙述时,他就能意识到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这比用“时间就是生命”、“一寸光阴一寸金”来教育学生珍惜时间和生命要具体、贴近生活。因为叙述中的时间是他体验到的时间,他既能体验到已经流逝的过往时间,也能体验当下正在流逝的时间,这是他对生命的双重体验,是用什么说教都不能代替的他们对生命的真实感受。在叙述的时间中,你与世界合一,你与生命合一。
三、叙述:再铸人的伦理情怀
“科学知识”是中性的,无倾向性和伦理性,而“叙事知识”是人文的,有倾向性和伦理性。赵毅衡说:“叙述化不仅是情节构筑,更是藉叙述给予经验一个伦理目的:只有用叙述,才能在人类经验中贯穿必要的伦理冲动,情节表达意义,其中首先是道德意义。”“为什么讲故事能达到伦理目的?因为叙述不可能‘原样’呈现经验事实。在叙述化过程中,不得不对情节进行挑选和重组。经验的细节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述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述性’,就是在凌乱的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情节化’,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事件就有了一个时间/因果序列。‘情节将特定行动的诸要素连为一体,构成道德意义’。”[14]你选择叙述这个而不是那个,选择这样叙述而不是那样叙述,都带入了人的立场、态度,因此叙述不可能是中立的;且因为叙述使细节被唤醒,带上感情色彩,因此叙述不可能是冷冰冰的。总之,叙述绝对不是一种纯粹的技巧,而是通过叙述必能充分展示叙述者对真、善、美的判断、取舍的伦理情怀。
与上文所说相同的是,目前中国教育不仅淡漠了生命意识,而且也淡化了道德教育。举其大要,表现为考试作弊、论文剽窃、履历造假,而溯其源头则有人说,人生的第一次说谎始于写作文,这似乎在声讨是学校使人在叙述中精神堕落。其实,问题的症结可能是公共叙述对个人叙述不当压制和扭曲的结果。
从社会学的角度,笔者把叙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公共叙述(或叫集体叙述),一种是个人叙述。所谓公共叙述,是一个国家通过国家意志所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是反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其中正面的故事是一个国家为全民族塑造的道德楷模,比如,我们中国影响最大、最广的公共的叙述,是关于雷锋、焦裕禄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讲了几十年,还在继续讲,尤其在学校更是最常用、最好用的教育材料。为了宣传的需要,公共叙述中的正面人物往往被屏蔽了缺点,被塑造成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使人产生高山仰止的崇敬,这当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学校教育中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这样的叙述不能因此对学生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压力,仿佛如果自己的叙述达不到同样的高度,就会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事实上这种负面影响确实发生了,不少学生为了怕老师批评,在作文中从来不写自己的缺点,只写自己怎样做好人好事,即使没有也要编造出来,弄得作文中尽是扶老奶奶过马路的故事。另一种公共叙述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合谋”,他们把学习成绩好、高考分数高的学生塑造成“英雄”,一俊遮百丑,只要考分高,行为举止、思想道德都可以放在一边。于是我们看到有的学生在写作中胡编乱造,以谋取高分,尤其在中考、高考中,一些人毫无顾忌地在作文中捏造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死亡的情节,写得声泪俱下,希望以此打动评卷老师。总之,虚伪的叙述是不道德的叙述,不道德的叙述是人的情操变质、精神堕落的表现,这可以称之为叙述的异化。
叙述的异化不能仅仅归罪于学生,而是当代教育的悲哀,前者是由于教育树起的难以企及的道德标杆,使学生在叙述中失去了表达自己在伦理的道路上慢慢前行的勇气,因为无法一下子达到那样的高度,只能干脆用谎话来表现自己的完美;后者则是由于教育片面的追求分数,放松了对人的道德要求,使学生在叙述中放弃了对真诚的坚守。所以,教育叙述必须重铸人的伦理情怀。学校对于学生的道德要求要有梯度性和包容性,把真实的叙述作为叙述的基础和底线,使学生不怕在叙述中暴露自己道德上的不足和瑕疵,因为除了这个世界十恶不赦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道德上的完人,而叙述的目的恰好不是遮蔽它,是更好的让自己看清它、认识它、改变它,从而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
[1]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2.
[2]转引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2.
[3][6]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9,18-19.
[4][5][7][14]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27,330-335,322,324.
[8][9][10]冯建军等.生命化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2-30,12,122.
[11]转引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5.
[12][13]赵毅衡.“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J].江西社会科学,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