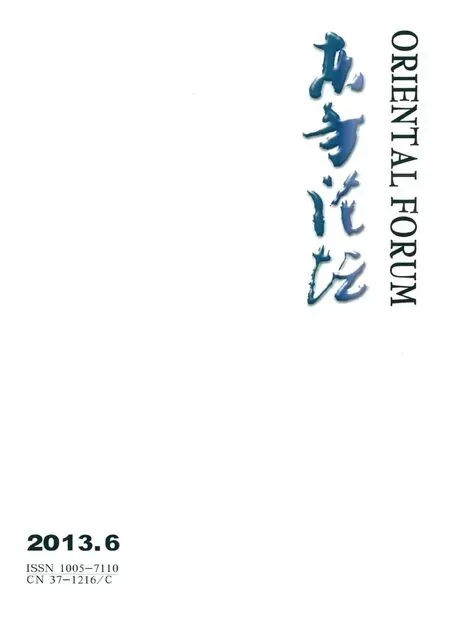论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转型表征
王 雪
论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转型表征
王 雪
(延边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
新时期以来散文文体叙述性增强,抒情性减弱,“情—景—理”的结构模式受到不同风格“个性化”叙事的解构,而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都更加丰厚。散文精神向度的雅俗分流,思维视角的“向内转”以及表达方式的叙事化成为文化转型期散文文体的重要表征,这同新时期的时代文化语境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散文文体表征的嬗变既可映现出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也呈现出话语创新的文体意义。
新时期;散文;文体;转型;表征
新时期以来作家的写作视域由社会时代之宏大叙事进一步向日常生活回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消费文化语境中逐渐消解,创作思想日趋多元化、创作风格更加个性化。散文写作模式基本告别了文革前“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方式,思维方式与艺术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既有王小波、余秋雨等融知性与智性为一体的文化散文,也有周涛、史铁生等融抒情叙事于一体的“美文”,还有张抗抗、周晓枫、格致等突出女性立场与体验的女性散文,在文体创新方面,还出现了钟鸣、张锐锋、于坚等实践散文文体探索的“新文体”散文。同建国后的散文创作相比较,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写作态势。
一、精神向度:雅俗分流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散文主要的文体特色是由“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转变,那么新时期散文创作的雅俗分流就是多元化、个性化社会语境在散文创作中的具象表征。正如林白在《死亡的遐想·序》中所说,“我的散文写作是一种个人化写作……个人化写作并不是一种风格,它只是一种立场,它以个体主体性来面对生命,这种写作所表现的世界也是个人的感官所感受到的世界。”[1]“个人化写作”概括了当下较为流行的写作趋向,是一种带有个人体验的写作。综观新时期散文,“个人叙事”一方面进一步向“日常生活”推进,另一方面则被植入文化的生命元素。以文化思考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散文和以反映人们日常生活为主的生活散文形成互补的散文格局,作家在雅和俗两个层面上关注着人生的整体存在状态。
文化散文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侧重理性精神和人文情怀。在余秋雨看来,散文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必须服务于文化的传播,文化绝不仅仅是部分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一种中国切实的传统,是一种能够用来塑造形象,教化众人,甚至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大文明的强力推进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文热”的文学思潮外部表征就是余秋雨、夏坚勇、季羡林、贾平凹等创作的承载着丰厚文化内涵的散文盛誉文化消费市场。尤其是余秋雨的散文成为“散文热”思潮中的翘楚。在对大学生“最喜欢的散文”和“最喜欢的作家”的调查中,余秋雨都是名列前茅[2](P233-234)。余秋雨倾注了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才情,在对历史文化的品读中充满感时忧国的情怀,对当代散文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等成为“文化散文”的典范,在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读者开拓了一片极具审美魅力的文化散文天地。同为文化散文倡导者的贾平凹,则侧重以民间视角在文化层面抒写自己的人生体验,并在地域文化的层面去感悟生命的意义。以《秦腔》为例,秦地贫瘠辽阔,民风粗犷质朴。同陕北纯朴的民性相契合,“秦腔”是最为“汹汹”的一个剧种,“这里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统”,“唱秦腔成了做人最体面的事”,从群众基础到秦腔演员,从舞台演出到台下看戏,秦腔皈依了秦地人的心灵,也成为他们衡量人才的价值标准。贾平凹的散文既有通俗的口语又有文雅精炼的文言,语言通俗又不失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也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语体风格。时至今日,文化散文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在向着更为关注个体生命体验的方向转变。文化不仅是被评述和关注的对象,而且拥有了价值理性,赋予了生命的温度,作家主体以生命个体为本位,以带有现代意识的学理视角来感悟生活中的现象,彰显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有一类直接关注普通人现实生活的散文,这类散文可称之为生活散文。比如风靡一时的“小女人”散文,是文化产品商品化的产物,它的主要作者都生活在上海和广州,这种散文形式是同都市文明与时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联的。散文文本可以说是呈现作者思想和生活的一面镜子。在“小女人散文”这面镜子中反射出来的是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时尚女性的“后现代生活”,它迎合了时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小女人”散文的认同更多是都市女性对她们所代表的现代时尚生活方式的认同。同时,一些时尚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女友》等不断加快发刊频率、增加版面,适应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这类杂志尤其钟情情感类和哲理类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具有散文的文本形式,取材于感人的情感故事,情节具有巧合性,具有浪漫的语体风格。比如初恋情人多年以后在异地相逢,重温旧梦的情节模式等,这些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情感故事呈现出情节模式化的特点,是消费文化模式化生产的文化商品。这类散文犹如快餐厅里炮制出来的花样繁多的各式“甜点”,成为都市人茶余饭后的“佐餐”。
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雅俗分流是多元化社会语境的必然产物,这两类文体契合着不同兴趣读者的阅读和审美需要。中国社会正处于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期,具有不同精神向度的散文类型丰富了散文的文化市场,各有其文化消费的人群,它们分别代表着精英文化意识和大众文化意识,二者在一定层面上也存在着合谋的趋向,雅俗分流的散文写作状况还将长期存在。
二、叙述视角:向内转
建国之初的散文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他们的创作讲究构思的巧妙,铺陈华美精彩。比如刘白羽尤其擅长描写恢宏壮观的场面,如《长江三日》、《日出》、《北京的春天》等。《日出》是先铺陈文人笔下“日出”的生动图景以及“我”几次与日出擦肩而过的遗憾,先抑后扬,之后烘托出这次邂逅是在飞机上出其不意发现的,日出景象宏阔壮观,结尾深情点题——“我深切感到这个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进而体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的含义。这些散文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常常通过生活中的普通事物来升华情感,引发哲理具有“先抑后扬,卒章显志”、“中间巧借自然之景抒时代之情”的创作共性。再比如刘白羽的《同志》,推进情节发展的是一个印着“八路”的小布片。在追赶大部队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老人和一个受伤的小兵,小兵对我的怀疑、抵触令我不安和痛恨,当“八路军”的臂章不经意间落到小兵的脚前时,这个小小布片代表的同志含义冰释了前嫌,使“我在这一瞬间一下获得了最需要的最崇高的热情”。文本情节跌宕起伏,从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写起,到小兵对自己敌意的升级,在敌意发展到极限——我忍无可忍,“预备离开他们的时候”出现转机,一个“八路”的小布片成为情感纽带,之前的仇恨烟消云散,“八路”的共同身份使我获得了崇高的革命友情,具有山穷水尽之后柳暗花明的艺术效果。结尾以老人的话升华了题旨:正是革命的大目标与共同追求使他们结成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同志亲情。全文结构如打了结的丝带,在对象征物——印着“八路”的小布片的轻轻一现中,实现了“诗意”的主题,但十七年散文缺乏对个体心灵的关注与自我情感的自然外现,由此也可窥见一斑。这也是建国初强调主流话语,漠视个体心灵的社会时代语境在散文文本中的镜像反映。
十七年“三大家”的散文作为中小学课本经典曾影响几代人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外向型的,常取材于紧扣时代脉搏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国家的大好形势、领导人阅兵、抗美援朝等,作家个体是“人民”的代言,借个人之笔抒时代之豪情,在更深层面上承载着自我和时代、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但自我除了是一种关系的主体,还是一种存在的主体。当关系主体在“自我”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创作主体的话语形式表现为以群体代替个体,文本主人公成为时代主旋律的领唱者,在关系主体范畴中,主体话语缺少自我的内在省察和个性化情感的抒发,因此创作呈现出共性化的情感特征。重视关系主体的群体属性,形成了十七年散文的共性特征,作者热情地歌颂政治主旋律淡化个体精神的同时,散文的思想情感和艺术魅力都受到影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个体意识的增强、思维观念的转变,十七年散文也由“文学经典”退变为“文学史经典”,淡出了人们的阅读视野。
伴随经济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个体的差异性和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时代语境反映在创作中,就是作家的叙述视角转向人物内心。散文和小说“向内转”的叙述方式,在伤痕文学的大幕中被徐徐拉开。这种思维方式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比较突出,比如叶梦、程黛眉、斯妤等。斯妤以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相交织,形成一种“心的形式”,展开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诗人也善于描绘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如西部散文家周涛,如《一个牧人的姿态和几种方式》中描述了一个草原牧人蹒跚地向“被苇丛遮掩着的河走过去”,草原人去卸除自身“多余的力量”,“他把刀子浸进冰凉的河水里,然后拿起来,用刀尖翘起的部位抵住额头,一划,上额至眉心处被划破”,“他凝视着自己的每一滴血,看着它们离开自己归还给河流和土地。他感到安慰、舒适”,草原人豪放粗犷的性格特征和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在景物与人物的相互映衬中,呈现出心灵的细密纹理和生命的厚重质感,人物形象真实生动。作家把草原人复杂独特的内心世界描画得鲜活深刻。
如果说周涛把“向内转”拓展到他者内心世界进行细致的描摹,那么“第三代”诗人于坚关注生命真实的程度则深可触及自身内心,他把自己的虚荣与痛苦进行了剖析和揭示,“敢于把自己生活最隐蔽的一面亮给人看”[3](P7)。于坚的思维方式是“世界的局外人,自身的局外人。观照世界,也观照自己。进入世界,也进入自己”。[3](P6)《火车记》中他以一个坐车人的视角讲述了所见所感,他冲破有限视角的限制,从他人的视角展开对包厢人的认识,进而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人与人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运动记》中讲述了“我”对于“动”具有根深蒂固的鄙视和厌恶,最终在医生的警告声中警醒,投入到动的环境。一个习惯于静的人进入“动”的情境是艰难的,“动本来是从肉体开始的,在我却是从思想的解放开始的”。由于曾经有被体育老师嘲笑过的运动经历,这使“我”在生活中也尽量不参加运动,以减少别人的轻视和嘲笑,长此以往心理与身体的惰性也引起了“我”对运动的偏见和歧视。从“伸伸四肢”起步到对“威尔森球拍上发出的那嘣的一声响上了瘾”,这其中经历了巨大的情感波澜。于坚真率坦诚地独白了自己的“私心杂念”。
内省式叙述同样苛求作家灵魂的细腻和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如张锐锋的散文就充满大量内省式话语。在《用黏土捏制——在自己的出生地记事》中,他写道:“我的胳膊被庄稼的叶片割得现出一些细细的红痕,感到了一种火灼一样的疼痛。可是,我对这充满了叶子的庄稼感到无限的兴趣,这是多么宽广的庄稼地啊,人的智力是很难数得清那些庄稼的数目的。”诗人苇岸则用她细腻的心灵真切感受着发生在《大地上的事情》,她由“日出比日落慢”的实地观察,发现了“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胜于崛起”的客观规律。
叙述视角的“向内转”表现在作家侧重自身的感受和体悟,不仅限于向他者和自身的心灵世界延伸,而且这种“向内转”在灵魂自由的层面上,也表现为对社会现象和现实的独特感悟及针砭时弊的批判。比如王小波秉持人本主义立场,在中西方哲学的关照中,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文化以牺牲个体幸福来稳固政权的“三纲五常”等愚民政策予以痛彻的反击。王小波的散文取材于日常生活现象,旁征博引,取譬生动,尊重个体生命与自由的现代意识点燃了泉源般的思想,比如“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而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仅仅是对名人感兴趣”(《苏东坡东坡肉》);“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如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人性的逆转》);“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科学的美好》)……,再比如于坚在《火车记》中对火车站特点和功能的评述,“一见如故,很可能是骗局的开始;志同道合,难说是有扒窃的嫌疑;促膝谈心,讲的全是弥天大谎;人由于互相不知底细,也就比平时更大胆,更自由。”承载着丰富人生体验的哲理性思索,既有洞察世事入木三分的深刻,也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诸如此类的个性化的真知灼见,呈现着当代散文思想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三、表达方式:叙事化
在表达方式层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激情淡出,叙事化倾向明显。“叙事化”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是非语式写作”,“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它完成了一种 ‘不在’的风格,于是写作被归结为一种否定的形式,在其中一种语言的社会性或神话性被消除了,而代之以一种中性的和惰性的形式状态”。[4](P68)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同小说创作的“零度叙述”相辉映,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一种冷静的叙述状态。比如贾平凹近期散文的创作,不再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的散文那样,惯于哲理性阐发,善于在篇末点明哲理内涵。而是把纷繁复杂的历史往事都包蕴在不动声色的叙述里,呈现出多重主题意蕴,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如对家乡《六棵树》命运的叙述,六棵树的命运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各个重要的历史潮流和社会事件,“树木”小命运与社会大命运休戚相关,树木与它的主人也“共振”着命运的和弦。秃子是皂角树的主人,以卖皂角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在续妻去世以后,秃子也吊死在皂角树上,秃子的死引起了人们对皂角树的恐惧,人们砍伐了它。药树的命运则紧密联系着社会历史事件。药树因树皮像“鳞甲”而被称为龙树,也是树庄“成龙成凤”的图腾象征。在文革期间,由于“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村人以各家捐献一百斤柴火保住了药树“尸首”,药树流出“暗红色的水”。故事充满神秘性,炸树人在村人的诅咒中遭到了报应。药树最后被做成桥板,架在丹江上,仍然造福村人。楸树牵连着两家的命运,一直是两家争议的焦点,最后做了李家儿子家具材料。楸树没了,刘家的堂屋倒了,李家也人去楼空。楸树不仅共振着“树与人共存亡”的自然规律,同时也给人类以“善待树,也是在善待人类本身”的生命启示。香椿的命运和一个人的成分有关,它的主人泥水匠被定了地主身份被抄了家,嫉妒者在对别人拥有美的不安中摧毁了美,最终美的香椿成为人类劣根性的牺牲品。三棵苦楝树中,一棵是由于戏楼倒塌而丧生,一棵作了村长儿子新屋的椽子,还有一棵由于高速公路占地被置换为三千元钱。如果说苦楝树的命运反映的是农村腐败和为经济建设占用林地的现实,那么痒痒树则带有讽刺意味地反映了农民对占地的态度。痒痒树的主人永娃由于反对占用耕地参加群众闹事怕被追究责任,落下了牛皮癣的后遗症。痒痒树被卖给了城里的小区,痒痒树没栽活,永娃也死去了。这六棵树的命运遭际呈现的是从文革到市场经济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树与人的摧残和破坏。每一棵树的生命都牵连着他主人的命运,树与人相互影响,相互映现,相互依赖。树的毁灭同其主人的死亡形成“共时性”因果关系。既有对各种社会现象、现实的揭示与批判,也有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体认。树和人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思想主题演绎得发人深省,多重思想意蕴渗透在六棵树命运的历时叙述之中,情节富有传奇性,人物形象真实鲜活,冷静的叙述中人性的复杂和思想的批判跃然纸上。汪曾祺就很推崇散文自然平淡的叙述风格,他在《蒲桥集·自序》中曾说:“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往往流于感伤主义。我觉得感伤主义是散文(一切文学)的大敌。……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同为“叙事化”的语体风格,作家们立足点又各有不同。余华散文的叙事化特征主要是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生活的本质、从生活细节之中品味事物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流行音乐》中他描述了自己安排儿子漏漏接受音乐熏陶的经历,虽然一心希望巴赫的《平均律》,巴尔托克的《小宇宙》能使儿子听到真正的宁静,但当漏漏听到儿歌《小燕子》时,近一年的巴赫“几分钟就瓦解了”,父亲望子成龙的教育愿望呈现出来,同时童真童趣又淋漓尽致。孩子是有其天性的,只有顺应其生长的阶段特点,才能使孩子得到健康的发展。《可乐和酒》中描述了漏漏区分“可乐”和“酒”的经过,作者把可乐叫做“酒”,使漏漏接受它,漏漏最初接受可乐的感觉描写得形象细致,比如漏漏第三次打嗝的时候,“他开始慌张起来,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嘴像是枪口一样,嗝从里面出来时,就像是子弹从那地方射出去。”之后漏漏把可乐当成了酒。当阳阳把真的酒给漏漏喝的时候,漏漏“痛苦不堪”,之后他拒绝喝“酒”,当爸爸再告诉他以前的“酒”就是“可乐”时,他终于知道他喜爱的饮料的名字了。这一叙述充满生命的智慧和语词命名的乐趣,描画得简洁生动。
综上所述,由新时期以来主要作家的散文创作可见,散文文体叙述性在增强,抒情性在减弱,“情—景—理”的结构模式受到不同风格“个性化”叙事的解构,而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都更加丰富。散文精神向度的雅俗分流,思维视角的“向内转”以及表达方式的叙事化特征成为新时期期散文文体的转型表征,这同时代文化语境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新时期散文文体的转型表征既可映现出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也呈现出话语创新的文体意义,而且这些文体表征在思想开掘的“深”与取材范围的“广”两个维度上还在不断拓展、延伸。
[1] 林白. 序[A]. 死亡的遐想[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2] 王先霈主编. 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
[3] 于坚. 棕皮笔记·1982—1989[A]. 拒绝隐喻[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4] 罗兰·巴特. 写作的零度[A]. 转引自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责任编辑:冯济平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se Styls since the New Era
WANG Xue
(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China)
Since the new era,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prose style have been enhanced while the lyrical features weakened. The "feeling-scenery-truth" structure has been de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styles of "personalized" narratives, while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ext are more abundant. The prose spirit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trends: elegant and vulgar;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has turned inward, and the narrative tendency has become typical of expression. All these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se style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embody both the gener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nd the stylistic signifcance of innovation in discourse.
new era; prose; style; transmutation; characteristic
I207
A
1005-7110(2013)06-0111-05
2013-05-18
2013年度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九十年代散文文体的话语转型研究”(201309)的阶段性成果。
王雪(1974-),女,吉林四平人,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