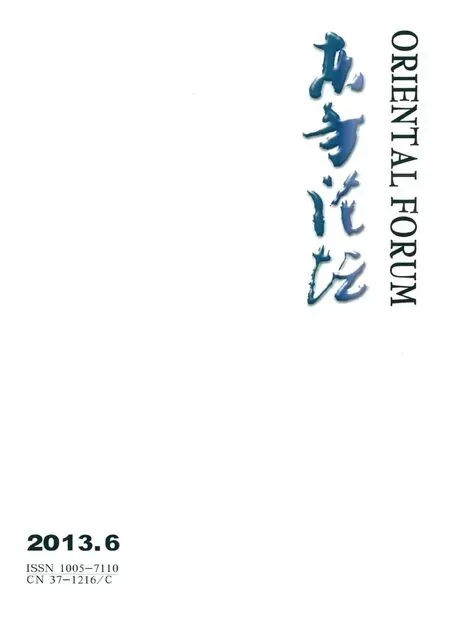《白鹿原》:乡土民族史诗的影像转换
周 仲 谋
《白鹿原》:乡土民族史诗的影像转换
周 仲 谋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小说《白鹿原》被改编成电影,是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一件大事。电影采取浓缩式的改编方法,对人物、情节进行最大限度的精减,运用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影像语言,对这部乡土民族史诗进行影像转换,尽可地将原著的复杂主题呈现出来。尽管大量的删剪造成不少遗憾,但影片深沉的历史文化感和注重艺术追求的品质仍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白鹿原》;电影;改编;浓缩;史诗;风格
在2012年的中国电影界,《白鹿原》的上映无疑是一件大事,这部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忠实同名小说的电影,从被西部电影集团买下改编版权到准备筹拍、再到摄竣后发行上映,经历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影片几个不同的版本和被推迟的上映日期,以及上映后的褒贬不一、众说纷纭,都使其成为2012年度一个颇受瞩目并引发争议的文化现象。那么,大陆公映版的《白鹿原》是否称得上一部成功之作,在艺术表现上有哪些成就和不足?本文试图从电影改编的角度对其做出一些评价。
一、改编方法的选择
当代文学界对小说《白鹿原》评价甚高,将其称作是“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1](P143)、“一部展现民族灵魂的大作品”。[1](P443)作品时间跨度自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以白、鹿家族及相关人物的命运变迁为主线,将人物的悲欢离合与二十世纪前半页关中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从乡土民间和宗法家族的角度展示出一幅魅力雄浑的近现代历史画卷,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想将这么一部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情节繁茂、思想复杂厚重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其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导演王全安知难而上,审时度势,反复权衡,以其敏锐的艺术眼光,为作品找到了合适的改编方法。
将一部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扩充。移植是指把与电影容量相近的文学作品直接挪移过来,对原作中的人物、情节、主题较少作明显的改动。节选是从长篇文学作品中选出人物、事件、场景较为集中完整的一段,予以改编。浓缩是指对长篇原作删繁就简,去枝砍蔓,仅保留主要人物和主干情节,以适应电影结构单纯、集中、简捷、明了的特点。取意指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启示,重新构思,但仍保留原作中的人物和情景。变通取意是指把外国作品改编成本国电影,使其本土化,而绝少忠实于原著的思想。复合是把两部文学作品合而为一,改编成一部电影。[2](P359-361)扩充则是指在改编短篇文学作品时增加人物和情节。[3]
就小说《白鹿原》而言,其五十万字的篇幅容量是不可能完全移植到一部电影里面的,如果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倒是可以采用移植的方法。由于小说《白鹿原》中主要的人物事件贯穿作品始终,不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著作那样某一章或某几章集中讲述一个故事,因而节选式的改编方法也不合适。运用取意的方法改编出来的则是和原著完全不同的电影,就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是脱离原著的自我创造。而对于《白鹿原》这种厚重的、影响巨大的小说,取意的方法不仅会造成对原著的不忠实,亦会丢弃掉原著的精髓,因而也不可取。变通取意一般在改编外国作品时才会用到,扩充则适用于改编短篇文学作品,这两种改编方法对小说《白鹿原》都不妥当。复合的方法在电影改编中不乏先例,如黑泽明的《罗生门》,就是将芥川龙之介的两部短篇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 糅合在一起。然而小说《白鹿原》本身就是一部自足的、内容丰厚的作品,不需要再从其他文学作品中取材,所以复合的改编方法也用不上。相比较而言,在上述几种改编方法中,浓缩的方法无疑是将小说《白鹿原》改编为电影的最佳选择。
王全安正是采取了浓缩的方法,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取其主干,去其枝叶。尽管大量的精简使电影不能呈现出小说的全貌,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但却抓住了原著的魂魄,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改编影片既充分尊重原著的精神,又不拘泥于原著的内容,做到了在取舍中有所变通,在忠实中有所创造,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人物事件的取舍
小说《白鹿原》中涉及到的人物达数百人,其中笔墨描写较多的有十几人,囿于电影长度和容量的限制,要把这么多人物逐一展现在银幕上是不现实的,必须有所取舍。电影将小说人物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删减,将表现对象集中在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等父辈人物和白孝文、鹿兆鹏、黑娃等子辈人物以及外来女人田小娥身上,通过他们的坎坷遭际、爱欲情仇揭示整个族群被压抑的人性欲望和新旧时代撞击下的命运之殇,折射出历史巨变给白鹿原这块土地打下的沧桑烙印。
小说中的白嘉轩是儒家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的人格化身,他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讲究忠孝礼仪,明荣辱,知进退,做事不疾不徐,做人不亢不卑,他有自己固守的原则,又懂得适当隐忍。作为白鹿原的族长,他自觉地捍卫伦理纲常、宗法文化的神圣,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饰演白嘉轩的张丰毅把握住了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将该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影片除了选取小说中最能体现白嘉轩性格特点的事件加以展示外,还创造性地增添了一个细节来强化其人格特征。在造塔镇压小娥骨灰时,负责收敛尸体的乡人告诉白嘉轩,小娥怀有白孝文的孩子,如果将她的骨灰压在塔下,有可能压断白家的血脉,并提出了变通的办法,尽管白嘉轩非常在意子嗣的延续,但还是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乡人的建议。这一细节极富张力地表现出白嘉轩对礼教伦常的坚决拥护,也突出了其性格中刚硬决绝的一面。
鹿三这一人物也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影片充分展示了他的刚烈直率、嫉恶如仇以及对白嘉轩的忠义,旧时代对他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在清帝退位多年后仍不肯剪掉辫子。和白嘉轩一样,鹿三也是儒家伦理纲常的坚决维护者,是一个极要脸面的人,当得知儿子黑娃领回的媳妇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时,鹿三悲痛欲绝,摔碎了院子里所有的东西,躺在地上失声痛哭,刘威在此处的表演是真实的、生动可感的。对鹿三杀死小娥的动机,影片中有充分的铺垫,这是与原著略有不同的地方:孝文为了小娥将自己卖了壮丁,鹿三想赎回孝文而遭到士兵们的殴打,导致鹿三对小娥的憎恶进一步加剧。愤怒到极点的鹿三在大雨中走进小娥的破窑洞,将她杀死。在杀死小娥前,鹿三给了饥饿的小娥一个窝头,这一颇具人性化的情节使鹿三的形象更显立体丰满。
黑娃和田小娥是电影中戏份较多的人物,尤其是田小娥,在影片后半部分成为带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核心人物。尽管在小说中田小娥也是主要人物之一,但并未像电影这样将其设计为如此重要的角色,影片的这种处理,一方面是为了从情欲的角度进行开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故事性和可观赏性。张雨绮的演出基本到位,使田小娥这一形象不至于太令人失望。段奕宏对黑娃的扮演比较出色,影片中成年黑娃第一次出场,那一跑鸡飞狗跳,冒冒失失、做事不顾后果的性情就流露了出来。在他身上蕴藏着原始和野蛮的激情,具有反抗的爆发力。这使得他后来的被情欲吸引、参加革命、成为土匪等一系列诡异跌宕的传奇性经历都有了性格上的内在依据。
一些喜爱原著的观众可能会认为,对朱先生和白灵的省略是影片改编中最大的遗憾,然而这种遗憾是难以避免的。在小说中,作家以白鹿作为崇高人格的象征,朱先生和白灵都是白鹿的化身,朱先生是关中学派的大儒,生就一副仙风傲骨,而白灵则代表着纯净与圣洁,他们身上那种飘逸的氤氲之气决非凡夫所有。作家对两个人物神乎其神的描写反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正如雷达先生所说,“朱先生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4]正是人间气息的缺乏,使两人游离于白鹿原上各种争斗之外。对于发生在朱先生以及白灵身上发生的故事,作家不得不以大量的插笔和补笔进行叙写,实际上是对主干情节的分散,以至于小说的叙述常常产生断裂和不连贯。王全安放弃这两个人物,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如果硬要把这两个人物放到影片中加以表现,或许会造成更大的遗憾。
整体上说,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影片通过对白以及人物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动作细节,弥补了影像语言在表达人物心理活动方面的不足,从而很好地展示了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完成了人物的意义,使其成为活生生的银幕形象,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在故事情节方面,电影不仅舍弃了所有与被删减人物相关的情节,还删掉了白嘉轩娶妻、换地等事件,并毫不可惜地去掉了小说中带有魔幻色彩和神秘主义的部分,如白鹿传说、法师捉鬼等。与小说相比,电影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尽可能的简化,将叙事节奏调整得更快,内容变得更密实,各种事件接踵而至,使白鹿原的一系列变迁如暴风骤雨般急促。影片由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鹿子霖负责押运的皇粮被劫拉开序幕,接着是白鹿镇第一保障所成立,鹿子霖当了乡约,县里向各村摊牌沉重赋税,引发了大规模的抗粮斗争。在白嘉轩让儿子白孝文认鹿三当干爸之后,时间迅速跳跃到1920年,白孝文和鹿兆鹏同日结婚,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兆鹏反对包办婚姻,在新婚之夜离家出走。鹿三之子黑娃出去揽活当麦客,邂逅了郭举人的小妾田小娥,二人偷情时被发现,遭到一番毒打,黑娃带小娥回到白鹿原,却不能得到父亲和族长白嘉轩的认可。1926年,在兆鹏的带领下,黑娃和小娥开始闹革命。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黑娃逃跑,田小娥被鹿子霖奸淫,成为他报复白嘉轩的工具,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之后,田小娥被杀。影片结束于1938年日军对白鹿原的轰炸。
纵观全片,故事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影片保留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摒弃掉旁逸斜出的枝节事件,没有让多余的设想随意迸发,而是紧紧围绕故事主线一路讲述下去。个别情节在时间顺序上做了调整,例如原著中黑娃打断白嘉轩腰杆是在田小娥被杀之前,影片将其调整到小娥被杀之后,使得戏剧冲突更加集中,更加富有冲击力。人物事件上也有一些变动,在小说中幼年时期给黑娃冰糖吃的是鹿兆鹏,电影将其置换为白孝文,这一改动是为了渲染孝文和黑娃的幼年情谊,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然而156分钟的公映版影片到1938年就戛然而止,这一伏笔并没有得到必要的照应,应有的力度也没能发挥出来。按照导演王全安的说法,220分钟的版本一直讲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这一版本中,白孝文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起义参加共产党,跟着打日本人,解放后他当了滋水县长,不顾白嘉轩的求情奉命处决当土匪的黑娃。临行刑前,白孝文带了一包冰糖到监狱里探视黑娃,黑娃看到冰糖,就知道该上路了。[5]通过冰糖这一细节的前后呼应,再对照少年时期孝文多次对黑娃说的“你如果坐了大牢,我卖房卖地也要救你”的话,昔日情谊蜕变所产生的那种悲凉意味便呼之欲出,更揭示了急剧动荡的时代变迁中个体不过是“历史的人质”。可惜的是,公映版仓促的结尾不仅使这一伏笔落空,成为闲笔,而且未能交代黑娃、孝文和兆鹏的结局,以至于使原著的长度、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艺术感染力也大打折扣。严重的删剪还造成影片情节的跳跃,例如挨打后被丢弃在荒野的黑娃如何找到小娥并将她领回白鹿原,火烧麦田后为何会有一个老人被枪毙,影片中都没有交代。这大概也是一些观众觉得电影《白鹿原》剧情不连贯、故事看不懂的原因吧。
三、复杂主题的影像呈现
西格尔指出,“每一部好电影,好小说,好戏剧都是有主题思想的。”[6]主题起着深化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作用,对电影成功与否意义重大。在电影改编中,一般都是先找出原著的主题,然后再考虑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语言对其进行转译。小说《白鹿原》以多视角透视的叙写方式构建了一个驳杂丰富的乡土世界,其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对传统宗法文化既有欣赏,又有批判,既在鞭挞,又在挽悼。小说所承载的主题也是极其复杂而沉重的:古老土地的历史变迁、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儒家文化的辉煌与没落、人性欲望的压抑与张扬……如此复杂的小说主题显然给电影改编带来了困难。导演王全安在抓住小说主干情节的基础上,通过对主要人物的群像式的描写,运用极富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影像语言,最大限度地将原著的复杂主题呈现在影片之中。
对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思索,是小说复杂意蕴的核心所在。电影抓住了这一点,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切入,进行主题开掘,影片中的不少矛盾冲突都跟土地、粮食有关,如农民抗粮、镇嵩军抢粮、白孝文卖地等,不仅如此,电影还以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意象,来深化这种主题。“麦田”意象是影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影片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风吹麦浪的推移镜头,这一大片金黄色的麦田,在德国摄影师卢茨的掌镜下,闪耀着纯净、热烈、浓艳的质感。随着影片故事的展开,麦田和麦浪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像一幅幅浓墨重彩的油画,使人想起梵高笔下燃烧着生命激情的麦地。一茬茬割了又长的麦子,就是生长在关中大地上的农民顽强生命力的形象写照,他们不管经历多少苦难和不幸,都牢牢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影片以金黄的麦田开头,又同样以金黄的麦地结尾,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剧烈的社会动荡,无言的土地始终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与金黄色的麦田相对应的是雪中白鹿原的意象,如果说前者给人的感觉是温暖,后者给人的感觉则是阴冷。黄色与白色的对比,既是热烈与冷寂的对比,又是张扬与内敛的对比。白色的雪景不仅是片中某些事件(如雪中抗粮的斗争)的背景,也不仅是纯粹的自然景观的呈现,而是具有象征的意义。麦田和雪景的空镜头画面在影片中交替出现,既标志着夏收冬藏的时间推移,也体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观念,与影片中翻来覆去的政治争斗、人物诡谲多舛的命运遭际是相契合的。
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意象是“祠堂”,该意象是儒家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的承载物。小说对儒家文化的思考主要通过朱先生和白嘉轩两个人物传达出来,并辅之以大量的描述性和评论性语言,由于电影出于情节凝练的需要而删去了朱先生这一人物,再加上抽象思维和心理活动是影像表达的弱点,所以要想在银幕上呈现这种思考是比较困难的。所幸的是,电影对其进行了巧妙的转化,以“祠堂”意象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通过视觉化的画面来弥补抽象思维的不足。在电影中,“祠堂”不仅是村人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以儒家道德观念和宗法制度规训人们的场所。白嘉轩带领村人在祠堂背诵“乡约”,可以看做是儒家关于“修身、齐家”的一场仪式化表演,白孝文幼年时因调皮捣蛋被父亲在祠堂中责罚,黑娃和小娥因所谓的伤风败俗而被拒绝进入祠堂,偷情者在祠堂中当众受到鞭挞,都是传统道德、宗法制度对出轨者的惩戒,体现出儒家文化及其道德观念在白鹿原的控制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控制力日渐削弱,革命浪潮中黑娃带人冲进祠堂砸毁石碑,是对儒家宗法文化的公然挑战,而片尾日本人的飞机炸毁祠堂,更象征着动荡社会局势下儒家传统观念和宗法制度的分崩离析。“小说《白鹿原》写的是一群人的悲剧,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悲剧,它唱了一曲为宗法封建制度及其人格化的代表们安魂送葬的挽歌。”[7](P23)而电影则以祠堂的土崩瓦解这一视觉性的具象画面,为儒家传统文化和宗法制度唱响了葬歌,尽管这曲葬歌带着一丝留恋的意味。
大量的性描写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欲问题一直是小说《白鹿原》颇受争议的焦点,也是电影改编绕不过去的一个沟坎。对于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情欲戏,王全安保留了原著的大部分情节,但考虑到审查的问题,电影对小说中较为直白的性描写,做了尽可能温和的处理。情欲在影片中被表现为一种原始的生命活力,一种自然本真的生命形态,与禁锢人性的传统宗法文化构成极其紧张的矛盾关系,同时与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田小娥是情欲漩涡中的主角,也是与宗法制度对抗的牺牲者。她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看似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郭举人养生延年的一个工具,对于强加于她的性剥夺,她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反抗。她对黑娃的挑逗和真心相爱,是黑暗禁锢中绽放的人性花朵,那喷薄的情欲像金黄色的麦浪一样热烈。尽管她和黑娃的爱情首先是为了性饥渴的满足,但这种带有生命本真色彩的原始冲动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冲破了功利主义婚恋观的藩篱,还原了性爱娱情娱性的本色,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儒家伦理道德和礼教文化的异己分子,不能进入祠堂拜宗认祖,也得不到白鹿原社会的接纳。田小娥是被礼教文化驱逐的边缘人,但她反过来又给礼教文化以极大的破坏,在她身上,一方面可以看到宗法制度和男权社会对她的压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她与伦理秩序和整个白鹿原社会的对抗。对白嘉轩所代表的伦理道德给她造成的伤害,她通过勾引白孝文的方式进行报复,无形中成了鹿子霖的帮凶。她与鹿子霖之间是一种性占有与反占有的关系,并勇敢地给他以最蔑视的惩罚。而对于白孝文,田小娥一开始是出于报复和玩弄,但当白孝文沦为家族的不肖子孙、从宗法文化营垒中游荡出来以后,她反而爱上了他,从最初的引诱发展为两情相悦。田小娥以情欲和身体表达了对儒家伦理道德和礼教文化的抗议,也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她最终被笃信礼教思想的鹿三所杀,死后还像白素贞一样被压在塔下。影片通过田小娥这一形象尖锐地批判了传统道德和宗法文化悖逆人性的一面,揭示出个体生命存在的历史性沉重。
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中,在白嘉轩和“祠堂”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道”与黑娃、田小娥、白孝文这一代人的“欲”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中,电影尽可能地实现了对原著复杂主题的影像转换,并对整个民族多灾多难、浸透血泪的近现代史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影片站在非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时代沧桑巨变中的个人,对片中人物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悲天悯人的情怀十分明显。电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生活在历史所规定的宿命中,这似乎是无法化解的悲剧,然而无论历史多么沉重,民族生命的蓬勃活力却不曾断绝,就像影片结尾时那金黄色的麦田,昭示着无尽的希望。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编. 《白鹿原》评论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 汪流. 电影编剧学[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3] 桑地. 电影改编与审美转换[J]. 电影艺术, 2006, (6).
[4] 雷达. 废墟上的精魂[J]. 文学评论, 1993, (6).
[5] 王全安. 《白鹿原》不得不说的事[EB/OL]. http: //ent. sina. com. cn/s/m/2012-02-18/ba3558306. shtml .
[6] L . 西格尔. 影视改编教程[J]. 苏汶译. 世界电影, 1996, (4).
[7] 何西来. 序[A]. 《白鹿原》评论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冯济平
White Deer Plain:Image Transformation of a Rural National Epic
ZHOU Zhong-mou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
It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China's literary circles and flmdom that the novel White Deer Plain has been made intoflm. The flm adopted the method of condensation by deleting characters and plots and used creative and expressive images to present the theme of the original work. The audiences were shocked by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and artistic quality in pite of the deletion of so many scenes by censors.
White Deer Plain; flm adaptation; condensation; epic; style
J95
A
1005-7110(2013)06-0116-05
2013-05-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消费文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学改编研究”(10YJC751137)和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09LZUJBWZY059)的阶段性成果。
周仲谋(1982-),男,河南南阳人,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影视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影视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