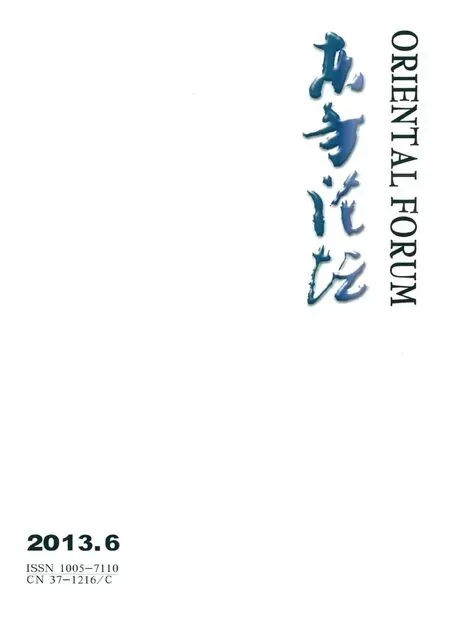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
吴原元
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
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费正清不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几经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迷恋与赞赏中共革命;新中国建立初期,拒绝与仇视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0年代中后期,对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持不确定与批判的态度;中美关系解冻后,则转变为承认并理解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的嬗变,启示我们必须正确、理性的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
费正清;中共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认识嬗变
众所周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不仅是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也是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1942年至1943年,费正清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士周恩来、龚澎和乔冠华夫妇、郭沫若等人有过接触;1946年6月,费正清夫妇在离华回国前夕,专程前往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1972年6月,费正清夫妇接受周恩来的邀请,作为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批尊贵客人访问中国;1979年,费正清作为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访华。不仅如此,费正清还撰著了《美国与中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观察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关于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与中国》,自1948年问世后,费正清便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在1958、1971、1979的再版过程中不断增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关于费正清,国内学者已从不同视角对其展开了研究:有的侧重于介绍费正清与中国的情缘及其学术人生①如陈祖怀的《费正清与中国》(《史林》,1991年第1期)、徐国琦的《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巫云仙的《费正清的学术生涯与中美关系》(《文史哲》,1994年第4期)等。;有的重在探讨费正清在创建美国中国学中的贡献及启示②如侯且岸的《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陶文钊的《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项锷的《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学术月刊》,2000年第1期)、钱金保的《中国史大师费正清》(《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等。;有的是对费正清的中国问题研究进行具体分析③如吴国安和高峻的《费正清的中国问题研究及其学术理论得失》(《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1期)、余英时的《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载傅伟勋、周阳生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93)、巫云仙的《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文史哲》,1995年第6期)、潘成鑫的《试论费正清关于近代中西关系的文化观》(《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李帆的《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陈宇的《费正清中国研究的文化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杨婉蓉的《费正清与〈中国新史〉》(《历史教学》,2002年第2期)等。、有的关注费正清的中国史观等①如陈同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与费正清的史学倾向》(《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王新谦的《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等。。在已有的研究中,鲜有学者探讨费正清视阈中的中共革命和建设及其认识嬗变②笔者仅见韦磊的《194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自信来自对自身的客观认识,而认识自身则无疑也需要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1]透过费正清关于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和评价,可加深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认识。再者,“一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费正清关于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拟探讨费正清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革命和建设?他对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哪些因素促使费正清的认识出现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益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焦点的今天,费正清的认识嬗变带给我们什么启示?限于学识和笔者的眼界,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见谅和指正。
一、新中国成立前:迷恋与赞赏
1940年代,费正清曾先后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美国新闻署驻华办事处主任身份活跃于战时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中共一些成员保持着无拘束的交往。1945年,在龚澎和乔木转赴香港前,他同他们进行简短的约见;1946年1月,当地中共代表团为美国新闻处在重庆的工作人员举行一次晚宴。费正清清楚地回忆起周恩来、叶剑英用筷子轻击桌玻璃杯打拍子,“两人就像卫理公会教徒那样唱着歌。”1946年6月,费正清和维尔玛访问了当时共产党人边区政府所在地张家口。作为边区政府的客人,他们用5天时间会见了可能的候选人,并与不同人员交流。[2](P112-113)
在这些交往中,共产党人的热忱,对未来的希望和忘我精神给费正清留下深刻的印象,“住在周恩来总部那条街上的共产党人进行着与美国人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的方针现在看来是尽可能的像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那样去行事。”[2](P104)费正清曾如是描绘重庆时代的周总理:“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态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的当机立断的才能,并以之为集体主义服务。”[3](P320)为期一个星期的张家口之行,则让费正清亲身感受到解放区“没有思想控制的气氛,人民解放的学说一如耶稣在早期新教徒传教会的教诲那样得到自由信奉”[2](P112-113);这次张家口之行,亦使费正清对共产党人的正直品行有了更深切地认识,“不论苏联的作风如何,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区内始终没有被歪曲过的,中共的干部永远是真挚地努力于他们同胞的福利与复兴的。”[4](P21)
费正清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充满着好感与敬意,而且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有着睿智的洞见。当时,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完全是莫斯科外来输入的结果,中共只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或者是傀儡;费正清则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绝不是像主流论调所想像的那样是完全受苏联操纵,这种论调忽略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国情。事实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土生土长的,由中国人自己根据历史环境和现实情势为解决其自身问题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并不是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4](P17-18)1946年7月,费正清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而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们只不过在主义和理论上同苏联有缘, 在实际和程序上却未必如此。他们同苏联保持密切关系的具体证据少得出奇, 倒是俄国人令人惊奇地保持了战时不援助延安却援助重庆的一贯记录。”[5](P317)他强调中共政权“是由清一色的中国人组成的, 他们20 年来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对付中国的环境, 历尽艰辛, 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计划。”[5](P316-317)1948 年11 月,费正清在“外交政策协会”的新闻简报上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帮助了俄国,但这不能看作是俄国对中国的征服。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 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名副其实共产主义, 而且也是名副其实中国式的。”[3](P389)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费正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坚定的判断,“我们必须把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看作是民族自决问题,而不是外来侵略问题。”[6](P11)基于此,费正清断言道,“中共目前并没有以苏联为他们的靠山,除非我们逼得他们不得不靠苏联来求生存,他们是不会走这条路的,我们相信在将来,和在以往一样,中共在内政的处理上是相当超脱苏联的干涉范围的。”[4](P19)
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前景,相当多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会成功。1947年4月17日的纽约时报》社论如此言道,“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会成功。中华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对任何激进的社会和经济理论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2000多年来,中国每一儿童被教导应行中庸之道。这种观点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很有影响力。不要指望4亿中国人会在几年内就转向共产主义这一奇迹会发生。”然而,费正清对此抱持乐观的态度,认为未来是属于共产党运动的。[2](P113)费正清之所以抱持乐观态度,是基于他所看到的事实,中共革命“有意识地消灭地主士绅阶级”,使“中国旧的阶级结构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5](P330-331)不仅如此,“凡国民党本来可以做到的那些事在中共统治区都一件件地做到了——识字运动、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动员、妇女解放等等”[3](P334)。费正清感叹道,“一场‘为了老百姓’而重建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5](P332),从中国老百姓的观点并用中国人的说法“中共政权按其迄今的业绩看来,可望成为近代中国最好的政府。”[5](P324)基于这些事实,费正清认为“共产主义虽然在美国是坏事,但它在中国看来却是好事”[3](P417),因为共产党不仅在理想上有一种精神的活力,在道德上有作为领导者的资格”[4](P17),而且“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根植于中国肥沃的土壤。传统秩序的破产和当代问题的迫切需要都呼唤激进的措施,马列主义恰好正符合这种需要”[6](P11-12)。总而言之,1940年代的费正清对于中共革命抱有前所未有的好感,甚至可以说进入一种“迷恋”的状态。如同他自己所说,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3](P315)
二、中美敌对时期:拒绝与仇视
进入1950年代,费正清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评价发生转变。他在给查尔斯·默茨(Charles. Mertz)的信中写道,“如同在广播监听报告中所看到的,这种宣传已变得如此公然并一味顺从于俄国的路线,以致我相信它将擦亮这个国家中许多人的眼睛。”[2](P135)几周后,即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前,他悲叹“中国加入俄国的体系……既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也威胁到中国人民的幸福”[2](P135-136);1950年,费正清在给国务院弗朗西丝·拉塞尔的信中再次写道,“它夺得政权主要是当地运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莫斯科影响夺得政权以后的共产党变得明显了……共产党的政权控制住局势,并成了俄国蹂躏中国的媒介物。”[2](P137)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国内纲领,在费正清看来亦不见得更好:中国的共产主义像其他地方共产主义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同样可怕的前景——包括为国家从事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压制、摧残、毁灭执拗的个性,以及孩子检举父母、邻里间互相暗中监视等所有可能出现的事情。[6](P482)换句话说,这种鼓舞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包含着一种引起种种弊病的因素,这些弊病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显示出来。对于那种把他在学术界中的许多好友的“执拗个性”统统磨灭掉的做法,他大为愤怒和震惊。他给当时流亡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改革委员会成员崔书琴博士写道,“现今在共产党政权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整部中国历史中所看到的最为狡诈的一种。”[2](P137)在1952年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麦卡伦委员会意见听证会上,他作证说,“蜜月时期早已结束,而且已被另一个时期所取代,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施加的压力开始使每个人受到控制,陷于孤立,并被共产党国家所利用。”[2](P137)
1950年以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所采取的倒向莫斯科、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等,对于无法理解新生人民政权所处处境的费正清而言,不仅让他感到震惊,而且在他看来似乎是向他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所发出的警告。正如谢伟思(John S.Service)所说,“在共产党统治的早期,难以看到许多想看到的事情”。[7](P4)另一方面,美国人的情绪也在发生变化。1947年后,有关中国以及对华政策问题的讨论,不再只是政府及大学专家的事情;尤其是到1949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国内关于“丢失中国”问题的争论渐趋白热化。作为亲历者的费正清回忆道:“随之而来的争论当然是通过传播媒介来进行的。它引起了公众异乎寻常的可以说是病态的关注,恰似25年后的水门事件那样。全国所有参加这场争论的人都充满了激情,似乎在做戏一样,然而这却是真的。”[3](P406)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掀起一股歇斯底里的反共狂潮——麦卡锡主义。当以极端“恐共”、“反共”为特征的麦卡锡主义弥漫于美国社会时,二战前及战时供职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John Davies)、柯乐博(O.Edmund Clubb)等驻华外交官,非官方机构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太平洋学会、美国学术理事会等曾积极推动现当代中国研究或对此感兴趣的机构组织相继被诬陷从事了“将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共产党”的阴谋而遭到不同程度的调查、打击和迫害。①参见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40-46页。在这种环境之下,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发生改变也就不难理解。正如埃文斯(Paul M.Evans),费正清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评价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完全可被视作在反共情绪日益增长的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2](P138)
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明显转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因素是公民的义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4个月后中国的介入,对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费正清很快接受了“由苏联、中国支持的北朝鲜人已挑起了战争”这样的观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资料》一书提供了一个生动有力的说明:“本书完成于1950年6月,”它最后写道,“从那以后,随着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北京政府生动地展示我们曾经描绘的极权主义的潜力方面,提供了许多东西……好像是共产党政权的性质所固有的。”[6](P484)当他在麦卡伦主持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听证会上被问到,他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1950年至目前这段时间内改变了他们的性质”时,他回答道,“我想说的是,他们改变了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他们成了更加公然武装的、在军事上具有侵略性的敌人……我想说,他们的目的几乎始终未变。”[2](P139)在他的国家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的那些年里,爱国主义的需要,似乎成了费正清思想中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对峙时期:不确定与批判
进入1950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阴霾逐渐散去,美国民众那种极端恐共、反共的情绪日渐消散;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中国不仅没有如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垮台,相反政权日益稳固,经济建设和国际影响力都取得巨大发展。1956年,美国《国家情报估计》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牢固的控制了中国大陆,正沿着苏联模式大规模重建经济、社会以及军事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军事力量已大大加强,并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经济产量已经超过以前的最高历史记录。它所取得的成就和不断增长的力量的后果是:共产主义中国在亚洲的声望已经有极大上升。[8](P231)然而与之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接连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令人匪夷所思的失误。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美国国内社会环境的变化,无疑对费正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产生影响。
首先,费正清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1900年以后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在之前的历届政权所办不到的一定形式的现代化。”[9](P6)比如,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了通货膨胀、恢复了国民经济,更重要的是“到1952年,国民经济达到了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大的统一。铁路线发展到一万五千英里,公路发展到七万五千英里。一个集中的银行体系和统一的单一币制现在通行全国。国家预算第一次能够真正地设法编制了。”[9](P284-285)又如,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方面,“共产党中国的工业成长是迅速的,动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比任何一个不发达的亚洲国家都快。”[9](P302)再如,在共产党控制以前,中国人普遍存在不守时间、缺乏公德心和公共卫生习惯、把家庭利益放在团体利益之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等行为和观念。[9](P291)然而,共产党上台执政后,“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9](P292)总之,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迟钝的群众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并且从政治上使他们活跃起来,农村经济业经改组,军队有了现代化的火力,民族意识也觉醒了。”[9](P8)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如此成就,费正清认为这是因为“重塑中国、改造民众,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是毛所关注的任务。”[10](P45)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费正清也强调了共产党统治具有极权主义的一面。他曾如是言道,“1950年,共产党建立了对大陆的统治之后,八年以来一直努力按照极权的苏维埃形象来改造中国。”[9](P1)在他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所创建的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有准立法的职能,但主要是作为回声板和传送带,维持民主程序的门面,和人民参加政治但没有最后权力的场所”;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等全国性群众组织,主要职能是“思想灌输——以奉命举行的会议、示威和抗议,在群众中间进行密切的活动”,这些群众组织“能够对于每一个人施用一种无所不包的压倒的公众压力”[9](P281-281);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发起的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旨在“消除大批反对现政权的敌人”[9](P290);通过“对于个人个性的鼓舞、强制和操纵”的思想改造,其结果是“资本家和富农笑着把他们的财产献给国家,教授们严厉斥责他们自己所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中学生忠心耿耿为党的工作而献出生命”[9] (P292)。简言之,费正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年统治之下,“中国蓬勃发展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庞然巨物。到了1958年,它的数以百万计的行政人员、党的工作者、群众组织和农业合作社的广大组织机构已经布满全国,深入到每个农村和每个家庭。报纸和无线电、旅行和交通,学习和技术、生产和消费现在都由中央以史无前例的效率控制着。[9](P8)
费正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上台的叙述中,强调了“它所具有的极权主义与人民民主共和国、依靠莫斯科与独立自主、恐怖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性质。”[2](P204)正是因为具有双重性质,他认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既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新的耶路撒冷。”[9](P291)这种对位性结论,说明了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性质的不确定性。费正清在中国共产党内,看到了“以救世主自居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看到了“对帝国时代官僚政治的某种怯懦的仿效”。[9](P294-303)基于此,费正清如是言道,“在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和外来的某种影响纠缠在一起。但是这个极权主义的产物将是个新的、有特色的东西。”[9](P278)然而,基于其价值观及当时的冷战环境,费正清这种评价上的细微对照,实质上是批判性的。如果与他在《美国与中国》初版中所作的评价进行比较,此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更像他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听证会上所作的证词。例如,当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高效率的集体化计划和工业化过程中令人难忘的进步时,他着重强调了这些成就在人际关系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对知识分子的蹂躏、成千上万个地主的被杀以及普遍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控制制度[9](P279-303);又如,当描述共产党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时,他特别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大众谋福利,而是谋取国家权力,“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群众的福利,那么就不应只以占重工业投资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投入轻工业,而花费在军队和战略性的铁路上的投资则可以减少。”[9](P303)再如,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改进公共卫生,费正清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早晚要爆炸的人口问题”[9](P13)。
四、中美解冻时期:承认与理解
越战之前,美国人长期自喻其国家是世界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世界方向的引领者。然而,越南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美国人开始怀疑长期以来所持有的这种不可动摇的信仰和支撑它的美国中心的价值体系。费正清曾言道,“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11](P459)越南战争不仅使费正清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产生怀疑,还影响到费正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他曾反思道,“在美国,由于快速的增长与变化,麻烦也已摆在我们面前。由于我们过去的错误,我们也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致怀疑我们的领导人,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尽管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我们应该对于中国的经历加以同情和理解。”[12](P355-356)对费正清思想认识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变动是中美关系的改善。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并逐渐走向正常化。费正清曾对尼克松访华这样评价道,“在20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11](P441)事实上,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解冻了这位冷战战士的思想,它亦使费正清逐渐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1979年,费正清在重新修订《美国与中国》时写道:“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11](P342)
在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改善等因素促动下,费正清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实际上可以分成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旨在把农民从二等公民的地位、无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来,它试图消灭由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官员、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剥削者组成的旧的统治阶级。……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旨在把现代技术应用于中国生活各个领域[13](P261-262);无论毛泽东的社会革命还是邓小平的技术革命,都是由两种梦想推动:“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像龙一样拼搏过的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目标;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家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为实际、灵活。”[13](P12)
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14](P329),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八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绩斐然的时代。”[15](P594)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出现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但费正清认为“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许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成就仍然是引人注目的。1977年,他在为《中国的阴影》所撰写的书评中特别提醒到,该书几乎只字未提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这有损于作者的立论,“实质上,人民共和国重建了中国,包括植树造林,修筑水坝、水渠、机井和良田,种庄稼和办工厂。它还通过让社会成员学文化、组织起来学习技术、讲卫生、介入政治、爱国、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组了社会。”[13](P243)他在1979年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凡是在1949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入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事实仍然说明,它们是值得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学习的活榜样。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有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11](P428)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费正清亦给予了高度肯定:乡镇企业家真正富起来了;工人发现铁饭碗裂缝了,雇用期的长短已更紧密地与工作表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现在能对各种政治制度说长论短;作家和艺术家正在进行试验。中国的文化界充满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几十年受压抑的创造才能现在正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才能也在国际上显示出来。[13](P278)对于改革开放的未来,费正清则充满了乐观,“邓小平改革的耐心和踏实作风使人想起旧时士大夫关心民生、解民忧患的治国传统,而现在的目标依旧是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和更为人道的社会。但这需要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此时在中国士地上成形的新型国家和社会今后还会使我们为它的革新而惊喜。”[15](P654)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费正清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辩护。1976年以后中国农村又回到家庭承包制度,因此有人怀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出现毛泽东主义时代是不是会同样快地走向现代化?也有人辩论说,中共干部和政府是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加在中国头上,只是他们更深入到公众中并对日常生活更严格地加以控制罢了。所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对此,费正清认为“所有这一切修改历史的企图所面临的困难,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局外人的假定基础之上。举例说,谁也不能证明在农村消灭地主阶级可以通过逐渐进化而不经过暴力来实现。同样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没有党的控制,大规模增加人民群众识字的人数和建立政治组织能够迅速地实现。我们还得回到那句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总归要按照中国的特色进行。中共沿着一条同过去相连接的路线完成了重大的变革。总之,它没有使中国变得更像苏联,或更像日本、或美国,中国只不过参与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变革进程罢了。”[14](P337)总而言之,费正清开始尽可能跳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客观公正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五、简短的结语
如前所述,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几经变化。费正清认识的嬗变,实际上是受认识主体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费正清自己就曾指出,“美国公众对毛和中国革命的看法的变化再好不过说明了美国人看待国外事物的价值观。作为一场解放中国人民的运动,中国革命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典型,中国革命就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洪水猛兽。赞美和恐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13](P88)不可否认,由于受价值观、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解读是我们所难以认同的;尽管如此,这种不同的理解仍是加深我们对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认识所需要的。因为长期浸淫于单一环境和语境之中,我们在认识时往往受限于惯性思维而难以提出新的识见。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缘于“身在此山中”。
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嬗变,则启示我们必须正确、理性的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我们切不可为西方学者某一时的夸赞而飘飘然,亦不可因他们的诋毁而妄自菲薄,应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因为西方学者在解读中国时,都有其所固有的价值观和预设的评价标准;而且,其评价标准会随着时空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这就导致他们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评价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埃文斯在评价费正清的中国观时就如是指出,“作为对中国的反应,他经历了迷恋、拒绝、不确定和承认等阶段,每个阶段都包含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过不同的希望和担忧。”[2](P400)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解读抱持的是现实主义原则,背后隐含着他们的利益诉求。余英时在评价费正清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言论时就指出,它背后“隐藏着两个绝对不变的一贯原则,第一是美国的利益,第二是现实主义”[16](P42)正因为如此,所以西方学者往往结合现实环境对中国作符合他们利益的解读,这就使他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曾自我解嘲道,“我是一个关于中国革命的乱出主意者。”[3](P341)总而言之,在面对中国受到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关注的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重视并加强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所作研究的反研究,以求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在重视加强反研究的同时,必须做到“以我为主”,以批判和借鉴的视角去看他们的解读和评价。
[1] (苏)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五卷[M]. 白春仁等译.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加)保罗·埃文斯. 费正清看中国[M]. 陈同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3] (美) 费正清.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 陆惠勒等译, 北京: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1.
[4] (美)费正清. 美人所见: 中国时局真相[M]. 李嘉译, 上海: 现实出版社编印, 1946.
[5] 陶文钊. 费正清集[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6]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7]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and Yesterday :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92nd Congress, 2nd sess. on China today and the course of Sino-U. S. relations over past few decades. [B]. U. S. Gov. Print. Office, 1972.
[8]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Washington, March19, 1957, communist china through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umIII
[9]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M]. Cambridg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 1958
[10] John K. Fairbank. 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 S. A[M].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1] (美)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2]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1.
[13] (美)费正清. 观察中国[M]. 傅光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4] (美)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M]. 刘尊棋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15] (美)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M]. 张沛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16] 傅伟勋、周阳生. 西方汉学家论中国[M]. 台北: 台北正中书局, 1993.
责任编辑:侯德彤
John K. Fairbank'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ts Evolution
WU Yuan-yuan
(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John K. Fairbank is not only a well-known American historian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 but also a witness and recorder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his understanding changed several tim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e liked and appreciated Chinese revol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 he refused and hated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late 1950s, he held an uncertain and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 the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fter the thawing of Sino-US relations, he began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change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teaches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John K. Fairbank; Chinese revolutio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evolution of understanding
K27
A
1005-7110(2013)06-0042-07
2013-09-08
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市教委“阳光计划”项目《美国学者视阈下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吴原元(1977- ),男,江西东乡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美国中国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