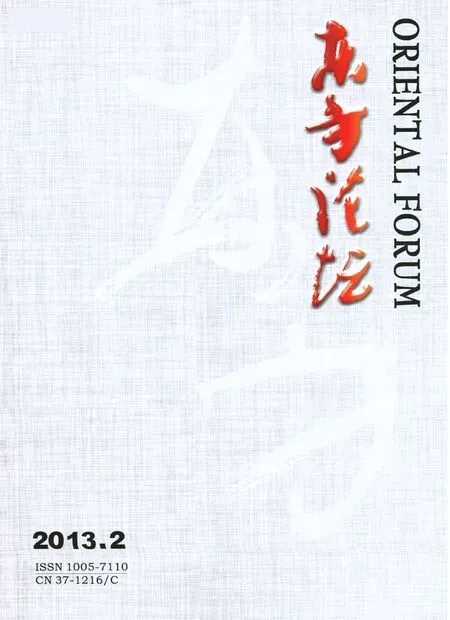六朝学风与骈文隶事
翟景运 牟艳红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闻一多先生曾经提出,初唐人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1](P3)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是指史学。作为杰出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在当时极受重视,研究者众多,以李善为代表的“《选》学”开山人物,对文学作品的注释着重追溯典故的来源,这也是当时《选》学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所谓“典故”,就是诗文作品中所引用古代的人和事,主要来自古代学术典籍,尤以经典史学著作为重,六朝和唐人习惯把引用典故称之为“隶事”。另一方面,初唐史学特重《汉书》,当时研究《汉书》的主流,乃是在其中寻找典故,以便在诗文创作中驱使和卖弄。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总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文学风气,但文学和学术毕竟是性质、宗旨都有本质不同的两件事,两者像唐代初年这样相互渗透如此之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初唐的学风和文风尽管有其时代特色,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六朝风气的延续和放大。本文拟围绕骈文隶事这一环节,考察六朝学风与它关系,进而明确骈文在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阶段上极为关键的一种变化。
一、六朝学风与诗文隶事的普及
六朝士族高门竞相以文化修养显示其身份的高贵,数典用事,正是他们显示高贵、渊博的方式之一。骈文和诗赋中重视使用典故,既是当时数典隶事社会风气的反映,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审美取向。
魏晋以来,“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即使经学名家,“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就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2](P153)《南史·王昙首传》载王僧虔诫子书云:“或有身经三公,蔑而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3](卷二二)学术的繁荣,知识的爆炸,激发了人们对博学的热情追求,助长了文人间炫博逞才风气。张绾“少与兄缵齐名,湘东王绎曾策之百事,绾对缺其六,号为‘百六公’”;[3](卷五六)梁武帝“曾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问(刘)峻,峻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呼,帝不觉失色”;[3](卷四九)孔休源“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略诵上口”;[3](卷六〇)吴平侯励“好《东观汉纪》,略皆诵忆……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3](卷五一)韦载“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4](卷十八)虞荔“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4](卷十九)……南朝史书中此类博闻强记的佳话可谓不胜枚举。史称沈约“博物洽闻,当世取则”,崔慰祖称刘孝标为“书淫”,都是南朝文人在书本知识方面渊综广博的反映。《南史·王摛传》云:“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3](卷四九)隶事多少,竟然在士人中间形成了相互博弈的风气,皇帝和臣子也会成为对手,甚至还会因此相互嫉恨。沈约作为萧衍的西邸旧友,因力劝萧衍代齐建梁而深得梁武帝的信任和器重,然而沈约自负高才,因为炫耀记诵之能而终于得罪了梁武帝:“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同时梁武帝又“自以为聪明博达,恶人胜己”,因此“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5](卷十三)
因为当时以博学记诵相高是普遍的风气,所以帮助记忆的学问也应时兴起,首先就是类书的大量出现。类书起始于魏文帝时撰辑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号曰《皇览》。”又同书《杨俊传》注引《魏略》:“王象字羲伯……建安中,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骑侍郎,迁为常侍,封列侯,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纂辑《皇览》的最初宗旨在于博览检阅的方便,但后来却成了属文时取材的宝库。《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序言说:“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南朝类书编撰之风大兴,就是受曹魏《皇览》的影响。《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有《皇览》一百二十卷,注云“繆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览》五十卷,徐爰合;《皇览目》四卷;又有《皇览抄》二十卷,梁特进萧琛抄,亡。”梁安成王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3](卷五二)“刘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梁武)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3](卷四九)编辑类书,目的是把各书所载同类的物事集中在一起以便记忆或作为撰文之辅佐。《隋书》卷三四《经籍三》杂家类总共有九十七部,合两千七百二十卷著述,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类书,其中《皇览》、《类苑》、《华林遍略》等等,本来就是文化史上著名的大部头类书;至如《杂事钞》、《杂书钞》等等,虽然较少为人提及,大抵也是当时风行的类书;另外还有沈约《袖中略集》、《珠丛》,庾肩吾《采璧》等等,则可能是篇幅较小的同类作品。这些类书为文士们的言谈和作文提供了便利。在相互竞争攀比的心理支配之下,类书的大量出现,无疑又会对隶事用典的风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是手抄经籍的风行。齐衡阳王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索,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3](卷四一)又《梁书·张率传》载:“直文德待诏省,敕使钞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使工书人琅邪王深、吴郡范怀约、褚洵等缮写,以给后宫。”手抄经籍的目的首先在于帮助记忆;再者此时手抄本多体积较小,称之为巾箱本,这是为了便于携带,以备随时浏览记诵。
博学之风影响到文学领域,其结果之一便是诗文广征博引、大量使事用典。南朝文学用典繁密而形成风气的特点在史籍中屡有反映。钟嵘《诗品序》说: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在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南齐书·文学传》也批评某些诗歌创作“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这正是当时一般文人共同的风气。《南史·王僧孺传》云:“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陈书·姚察传》云:“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钟嵘在《诗品》中评颜延之的诗歌说:“一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南史·任昉传》云:“晚节转好著诗,……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南朝有所谓“沈诗任笔”之说,任昉颇以文章著称于时,但诗歌成就不及沈约,任昉对此颇为耿耿。文章用事过多,已难免造成阅读障碍,若在诗歌中层层堆累典故,又如何能够自由抒情言志。因此《诗品》说:“任昉博物,动辄用事,是以诗不得奇。”《南史·徐君蒨传》:“君蒨辩于辞令,湘东王尝出军,有人将妇从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诛女子;将非孙武,遂欲驱战妇人。’君蒨应声曰:‘项籍壮士,犹有虞兮之爱;纪信成功,亦资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竟卒于官。”可见当时能随机用典、创作四六对句,乃是擅长辞令的表现。
二、骈文隶事的审美机制
典故既有其本来的意义,又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代言作家的当下心声,最能达到言能达意,又言不尽意的效果;大量用典,通过引申比喻说明意旨,能使道理形象、亲切;典故的妙用,可以通过极为精炼的语句隐括一系列的历史人文掌故,从而表达重叠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能够避免平板的叙述,使作品具有趣味性、象征性和书卷气,唤起读者起伏联翩的神游想象和隽永深邃的回味。让有限的形式要素包容更多的信息,促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参与作品的再创作,这样的作品无疑能够召唤出更大的艺术感应。正是由于上述特色,才使应用文性质的骈文具有了诗歌之美。那种运用典故、以古喻今的含蓄曲折的表情述意的独特方式,那种对举成文、相得益彰的工稳天成的叙事说理方法,那种抑扬顿挫的节奏、华美的文采,到任何时候、在任何特定场合下都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修辞方法。总起来说,用典作为骈文的基本表达要素,大致能够达到如下几个方面的艺术效果:
首先,通过古今类似的人、事类比,增强形象性、说服力和感染力。《文心雕龙·事类》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孤立地形容一件事不容易让人明了,再拿一件性质类似的事来作为参照,其功能接近于比喻。庾信在《小园赋》中形容其永别故国的情状说:“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庾信当年离开后梁而出使西魏,正像是荆轲别燕丹而赴秦庭,苏武别李陵而离匈奴,都是壮士一去,永不复返,悲壮情绪可谓古今同慨。如果读者对作者当下的情绪不易把握,可以借助历史上类似的情境增进体验。
其次,用典在表达手段上委婉曲折,并不直接点明意旨,然而实际的表达效果却比直来直去更加到位。隶事用典,与西方所谓“婉曲语”(periphrasis)相似,不把意思直接说破,使之耐人寻味。庾信《哀江南赋序》云:
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潘岳之文才,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
从这段最为人称道的以典故述心声的文字中,可以窥见骈文隶事用典委婉含蓄,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由此及彼,以古喻今;正反相形,相得益彰。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盖指事欲其曲以尽,述意欲其深以婉,泽以比兴,则词不迫切,资以故实,则言为典章也。”一连串典故既是流动阅读的阻碍,造成层峦叠嶂的感觉,又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读后不仅不疑惑淤塞,反而豁然开朗,而且在意义和情感层面上为读者留下了自由想象、发挥的空间。为了理解庾信当时的情绪,读者势必要全面理解他在文中所提及的各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各不相同的情绪。庾信的情绪,不单是用傅燮、袁安等人的情绪来作比,而是古今一系列人物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各种情绪的相互叠加。这样一来,读者所体验到的情感冲击显然就要强劲许多。
第三,大量典故经过灵活改造以后,以整齐的对偶形式镶嵌在文章里面,在增加了文化含量和意义层次的同时,又使语言变得典雅华美。一般生活语言和不对偶的书面文字在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它的思维逻辑往往是单线式的,然而骈文的语言逻辑往往是双线式的,它并不单纯体现在语言的对仗上,同时还伴随着意义的并列,即一层意义要用两种类同的方式来表达。刘峻《追答刘秣陵沼书》有句云:“若使墨翟之言无爽,宣室之谈有征,冀东平之树,望咸阳而西靡;盖山之泉,闻弦歌而赴节。”它所要表达的意思,用一般语言来说即:如果人死而真有灵魂,那就希望它能让树木和泉水都表现些灵异,以便让活着的人得到些情感安慰。为了表达“鬼神确实存在”这一层意思,刘峻用墨子主张有鬼论和贾谊在宣室向汉文帝解说鬼神两件事来形容,这两件事意旨类似,经过作者整合,句子字数相同、平仄协调,成为骈文表情达意的典型句式。如果只是为了把这层意思说清楚,本不需要连举两事,然而这种骈俪句式和对偶的表现方法正是骈文的特色,它并不仅仅追求实用,更追求超越实用价值的文字之美:骈俪句式的上下两联整齐对仗,具有建筑美;声韵协调,具有音乐美;一个意思用两件典故来形容,又使文章充满书卷气和典雅美。
当然,骈文中需要以典故形成层峦叠嶂之感,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和审美联想,但又不能使这种障碍不可逾越,而是要一旦登临,就能一览众山之小,审美视野豁然开阔。在追求语言结构形式美的同时,使典用事还应把握一种有张有弛的情感张力关系:既要包孕丰富,又要明晰易解;既非一览无遗,又不晦涩隐昧;才是成功的用典。用典使用不当,不仅不会给文章增色,还会带来语言表达的负担和障碍。有些骈文作者记诵虽夥但下笔生涩,由于用典技术不够高明,或断章取义,或杜撰生造,更是让读者大费周章,不知所云。如齐代王俭《褚渊碑文》有“具瞻之范既荐”一语,“具瞻”出自《诗·小雅·节南山》,原文是“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本身并非现成词汇,而是出自王俭本人的拼接改造。这种割裂原文、随意拼合的做法,目的在于追求语言文字的新奇以及勉强适应对偶句中字数的限制。晚清学者孙德谦(1869-1935)指出:
六朝文多生造之句,几有不能解者。……傅季友《为宋公修张良庙教》“照邻殆庶”,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功参微管”,皆是工于造句者也。《易·大传》:“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应以“庶几”、“管仲”连文,今不言“庶几”而言“殆庶”,已似讹谬;管仲为人名,截去仲字,反以微管缀用。如不知其句多生造,岂非等于歇后语乎?故六朝有生造句法,学者当善会之。(《六朝丽指》卷六一)
用典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常见,但在六朝崇尚记诵和博学学风的影响下,用典才成为诗文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尤其是骈文这种洋溢着唯美精神的文体在六朝逐渐发展成熟,成为典故的主要载体。用典的普及,一方面代表着骈文表现手段的进步,它增加了文字的历史文化含量,如同给读者提出了一道道难度大小不等的“考题”,通过读者对这些“考题”的逐一破解,文章意义得以贯通,既表现了作者的学养和智慧,又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思索和回味余地,展现出一种博雅深邃的文化魅力。不过另一方面,用典越多,情感意旨就越不容易明白显豁,实际上也就相应增加了骈文表达和阅读的障碍。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是后来骈文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骈文表达艺术水准的高低,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从骈文和古文消长盛衰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实用性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始终是在竞争中胜出的至为关键的因素。古文之所以最终能够在传统社会应用文体领域之外完全取代骈文,其优势就在于古文说理、议论、叙事的明白、晓畅,更能贴近实际生活的需要。再美的东西如果背离了现实需要,也难免为人所厌弃,古今中外,大抵不独骈文为然。
三、六朝骈文隶事演进的关键步骤
张仁青《六朝唯美文学》说:“用典隶事,起源甚古,屈(原)宋(玉)诸骚,已著先鞭,扬(雄)刘(歆)张(衡)蔡(邕),试用日繁,然多属意到笔随之作,非有成竹在胸也。爰逮建安,始刻意经营,渐趋美备,如应璩《杂诗》……太康以后,用典益繁,潘陆二子,导其先路。潘岳之《西征赋》,几于一字一典,……陆机之《豪士赋序》、《五等诸侯论》、《吊蔡邕文》、《吊魏武帝文》,以至短篇之连珠牍启,隶事之多,匪惟汉魏所无,抑亦晋文中有数之作。”[6](P56)文学作品用典,古已有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用典数量也逐渐增多。但建安以前的用典,多因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并未成为刻意的追求。建安以后,始有刻意用典者,但毕竟只是个别,并未成为普遍的文学潮流;而且用典的目的和功能主要属于引用和举例等等性质,同六朝骈文把典故作为组织语言和表情达意的主要载体完全不同。隶事的数量和功能,是考察骈文隶事演变的两个主要标准。
用典数量和性质变化比较明显的第一个阶段是西晋。受到文学上“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整体特点的影响,语言的华美绮丽、对偶的日益工整以及隶事用典的日益繁复成为该时期骈文的共同特征。李兆洛《骈体文钞》指出:“隶事之富,始于士衡。”[7](卷三)通观陆机骈文,用典句子的数量一般在全文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尽管用典比例较高的文章数量很少,对于前代骈文来说却有了很大的增进。据钟涛先生统计,曹魏文章用典比例普遍不超过三分之一,多数甚至不足五分之一;但《文选》中所选录的陆机文章,如《豪士赋序》、《五等诸侯论》等,用典比例都在三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陆机骈文的隶事首先在功能上发生转变:“陆机有些文章中,内容往往依靠典故来表达。典故隐喻和象征的内容,就是作者要阐发的内容。这样一来用典就不完全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成为了内容的直接表述方式。因此,也就成了文章的一种组织结构方式。”[8](P75)
刘宋开启了骈文大量用典的序幕,齐、梁而降,愈多愈繁。胡国瑞《诗词赋散论》之《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说:“到了刘宋时代,骈文进一步表现的特征,乃是使用典故的繁多。”[9](P89)《诗品序》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此虽论刘宋诗歌,但刘宋骈文也一样“殆同书钞”。例如鲍照的《河清颂》:“素狐玄玉,聿章符命;朴牛大螾,爰定祥历。鱼鸟动色,禾稚兴让。”区区24 个字当中包含了8 个典故,列举上古时期出现过的8 种符应,平均三字一典,以此引出对元嘉二十四年出现的“河济俱清”的称颂,用典之繁可见一斑。据钟涛先生统计,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用典102 处,《阳给事诔》60 处,《陶征士诔》 104 处,《宋文元皇后哀策文》 52 处,《祭屈原文》22 处。[8](P83)这几篇文章的总句数分别是138、149、176、104 句,用典比例最高达73%。可见,颜延之不仅写诗好用典故,其骈文也一般无二。刘宋骈文大量用典,已非某一个作家的专长,而是众人广泛追求并实践的风气。颜延之的骈文和其诗歌一样,好用典故,与鲍照同属刘宋骈文中用典较多的文士。可知,随着时代的前进,骈文用典也逐步增加。隶事之风愈演愈烈,齐梁而降,更加繁密。钟嵘《诗品》说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又论任昉说:“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诗歌如此,骈文又何尝不是如此。满篇经史,机械堆叠,博雅气息越发浓郁了,“自然英旨”也无从得见了。
南朝后期的不少骈文,其叙事、抒情、议论完全出之以典故,除了极个别的散句穿插其中之外,对于意旨再无额外的说明,几乎达到了一句一典的地步。这种变化,一方面代表着骈文表现手段的进步;另一方面,用典越多,情感意旨就越不容易明白显豁,实际上也就相应增加了骈文表达和阅读的障碍。由于处理这个矛盾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骈文的不同艺术风格的形成。后世的文论家对于前代作品这方面的艺术特征提出了若干比较恰切的总结和概括,比如徐陵、庾信某些作品中的用典,可以称之为“使事无迹”。“使事无迹”本是形容庾信诗歌中的用典手法,如清代沈德潜《古诗源》卷一四云:“子山固是一时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又过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三云:“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方比抽薪。”又云:“事必远征令切,景必刻写成奇。”李调元《雨村诗话》云:“其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又过之。”这些评论虽然针对诗歌而发,实可移来形容庾信等人的骈文。骈文隶事,至徐、庾几乎到了无一字无来处的程度。但徐、庾的绝大多数篇章很少给人“殆同书钞”之感,多数情况下明白自然,如出胸臆,用事灵活,擅长融化。如庾信《谢滕王赉马启》有句云:“柳谷未开,翻逢紫燕。临源犹远,忽见桃花。”紫燕、桃花,都是古典中骏马之名,用以答谢赉马,自然格外恰切。在这层典故的隐喻义之外,紫燕、桃花的字面义又同柳谷、水源构成一片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字面之义和隐喻之义两个层面相辅相成,自然贴切,圆融无碍;典故的字面之义又能在脱离隐喻之义的情况之下单独构成完整的意义,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艺术美。这就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对于读者知识面的要求,扩大了受众群体。陈寅恪论庾信《哀江南赋》云:“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0](P234)援古证今,“用人若己”(《文心雕龙·事类》),才能自由驱驾典故而不为典故所累,这可以说是六朝骈文用典艺术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如果说从两晋到宋齐之用典日益繁多,是对先秦汉魏用典较少的一种否定,那么梁陈时代徐陵、庾信骈文使事繁多而又如出胸臆这种艺术效果的出现,又是对机械堆叠典故的否定。经过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骈文隶事用典的艺术表现手法才真正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度。尤其是庾信骈文,把骈文的用典隶事技巧推进到圆融无碍、游刃有余的地步,使典故最有效地服务于叙事、议论和抒情,遂成为骈文艺术臻于巅峰的重要标志。
[1]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 [M].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 颜之推.颜氏家训 [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李延寿.南史 [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4] 姚思廉.陈书 [M].北京: 中华书局,1972.
[5] 姚思廉.梁书 [M].北京: 中华书局,1973.
[6] 张仁青.六朝唯美文学 [M].台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7] 李兆洛.骈体文钞 [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 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 [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7.
[9] 胡国瑞.诗词赋散论 [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M].北京: 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