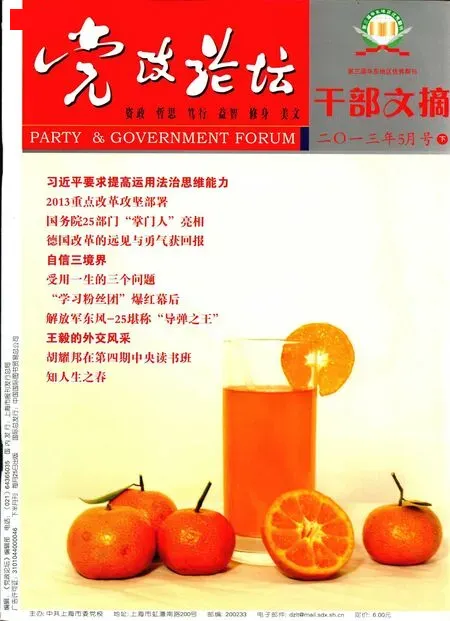官德建设的可行路径探析
○马用浩
官德是指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官德具有政治性、强制性、示范性和导向性等特点。近年来,执政党和政府对于官德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2011年11月,中组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2011年11月,国家公务员局制定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拟在“十二五”期间对在职公务员进行道德轮训。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度重视官德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笔者认为,加强官德建设应坚持如下路径:
一、官德建设法制化
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实际上,每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他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的而又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我们可以把官德视为官员阶层的道德,同任何阶层的道德一样,这种道德也有被破坏的可能。鉴于官德对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作用非同于一般意义的道德,法律和制度的作用就是对那些逾越官德界限的行为进行约束、惩罚,这种约束和惩罚将起到教化、自律、舆论影响不能起到的作用。
从经验层面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法制化途径或手段进行公务人员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律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证明法制化对于官德建设具有普适性意义。公务人员职业道德法制化,就是以立法的形式将其道德规范确定下来,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它的有效实施,国外关于公务员职业道德立法的内容,大体包括:公务员必须忠于职守,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公务员必须廉洁奉公,不能以权谋私;履行职责、服从命令;公务员必须严守国家机密;树立公务员在公务内外的良好形象;对公务员违反职业道德的惩处等内容。各国公务员职业道德立法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专门行政道德法典”,“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以及“职业守则及法律实施细则”三种。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公务员道德法规的形式趋向于专门道德法典,特别是呈现出公务员道德法规分层分类的特点。国外公务员职业道德立法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对违反职业道德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比较具体明确,易于操作。惩处一般分行政机关的惩处和司法机关的惩处,包括警告、记过、减薪、停薪、降职(级)、免职、经济罚款等。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公务员和雇员道德法》除规定了各种罚款外,仅扣除薪金一项就有扣除数额和时间的详细规定。二是有专门的道德监督机构,如美国的道德办公室、英国的公共生活准则委员会和加拿大的政府道德咨询办公室。三是有严密的惩处程序。由道德监督机构对公务员的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在对公务员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调查后,向其上级机关或司法机关提出处罚建议。
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些关于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准则,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未从立法层面上规范官德。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探索制定公务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深化改革,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公务人员从政道德方面的法律法规。
二、官德考核标准科学化
要科学有效地考核官德,构建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官德考核标准和考核体系是前提。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把近代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归因于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该论断或许带有某种绝对性,但是“数目字管理”不足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缺陷。这一特点在当下的官德建设方面亦有所体现,即官德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足。比如,《公务员法》中有关官德评价标准的文字,有第十一条“公务员应具备的条件”之(四)“具有良好的品行”,第十二条“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这些文字表述显然比较笼统、模糊,难以作为官德考核的具体标准。
就总体而言,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有效考核一直是一个模糊化的问题,有抽象标准却无具体细则,可以大言其道但无法操作,有质化标准而无量化评定”。近年来,有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推出“领导干部道德评价体系”,其目的在于“将抽象的德具体化、生动化、显性化,让测评者好理解、可把握、易评价,让德的考评结果精准化、数据化、可比较,有效提高评价信息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信性”。在对于这些探索给予应有肯定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我国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相对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主要问题有:“试图建立一种对所有官员都适用的官德评判指标体系”;指标设计粗糙且均为质化指标;标准参照系设计不尽合理;评价方法鉴别度较低。
在官德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方面,需要注意对于不同门类、不同层级的人员应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广义上的官包涵了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可细分为党政机关、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三种门类,制定官德标准应该考虑不同门类的区别;此外,官员还有层级和岗位的区别,在官德要求方面应有不同要求。“对干部德的考核,要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根据干部不同层级和岗位,分级分类提出德的考核重点。对中高级干部要突出考核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的情况,对高级干部还要按照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对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乡领导干部,要突出考核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办事公道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对党政正职,要按照关键岗位重点管理的要求,突出考核党性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原则、履行廉政职责等方面的情况。要注意根据不同地区、部门和行业干部队伍的实际,确定和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德的考核项目,突出重点和针对性。”在具体指标设计方面,需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细化考核指标,增强考核指标的适用性和针对性,减少模糊性和随意性,努力构建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官德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三、官德监督社会化
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将握有权力的官员置于广泛的监督之下是保障良好官德的重要保障,没有监督,就没有官德。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内的对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这些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在肯定已有监督体系作用和成效的同时,还应该看到不足和问题。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在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规范官员行为、防止权力滥用方面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同体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过去30多年,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同级纪委监督出来的;在舆论监督方面,媒体监督有时受到干扰,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有人将目前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良好官德形成要求进一步完善对官员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强化各级人大的监督,加强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和权威,创新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司法监督的力度,完善监督运行方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和参与热情,充分发挥公民舆论监督的作用。
四、官德教育实效化
康德曾经说:“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出的东西外,他什么也不是。”詹姆斯·布鲁斯在关于南美的著作中写道:“教育如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能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好公民。”威尔·杜兰特则指出,“美德是种艺术,非经训练或习惯不能掌握。”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毫无疑问,官德教育是官德建设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首先应充分认识官德教育的重要性,改变“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状况;其次,官德教育要讲究科学性、时代性,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我们以为大致可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官德修养和官德建设的精华内容,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服务人民的宗旨理念以及有关规定和制度,国外在官德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第三,官德教育重在长效机制,避免运动式的、应景式的学习和培训活动。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