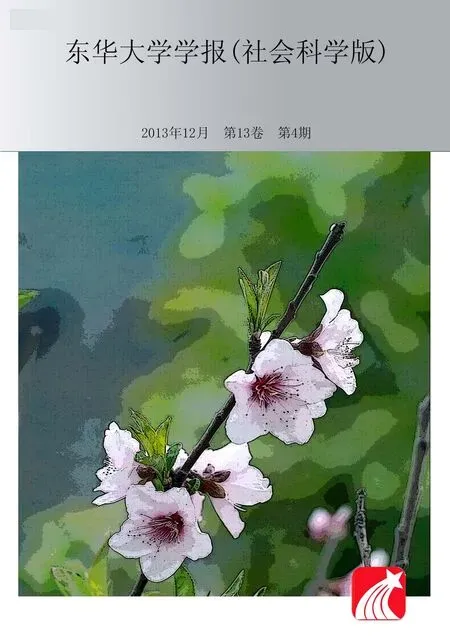论梅曾亮的思想特色
陆益军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梅曾亮(1786—1856)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弟子,主要生活在嘉庆(1796—1820在位)与道光(1821—1850在位)时代。他推崇桐城派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体的文学主张,讲求义法和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同时强调时代气息和真我个性。他关怀现实,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呼吁改革礼、法,澄清吏治,以稳定社会秩序。他崇尚义理,对学术主流汉学追逐考据、标榜师法、诋毁宋学,深表不满,主张汉宋兼采,重塑学风。他的这些思想观点,生动展现了嘉道时期学界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色。
一、强调时代气息和真实个性的诗文论
梅曾亮,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少时工骈文,转学到钟山书院后,受到桐城派大师姚鼐(1732—1815)的赞赏。经管同(1780—1831)引导,遂皈依门下,“义法一本桐城,稍参以归震川”[1],名声渐起,与同门管同、方东树(1772—1851)、姚莹(1785—1853)并驾齐驱,成为桐城派的重要传人。道光后期,他的文坛声望达到高峰,其诗文“皆为同人推服”[2],“同时方闻钜德之彦,趋之如水赴壑”[3]。曾国藩(1811—1872)从其学,受益匪浅。
嘉道时代是桐城派形成和扩大的重要时期。“许多集合在桐城旗帜下的作家,还是颇具自家面目的”[4]。
梅氏尊崇文章之学,主张文章之道与治经之道相通,文以载道。他认为班固的《汉书》只有《儒林》没有《文苑》,表明文学与经学并重,并列于儒林。范晔在《后汉书》中,将二者区别对待,于是文学与儒林分离。这是历史性的错误,造成文苑巨大的困惑。两者其实密不可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5]。他希望文章之学重返儒林之列。
其文论提倡简洁明快。他批评宋朝文章“明健酣适”而“失之冗”,战国文章雄奇而“抑扬太甚,有矜气”,欣赏汉朝文章的“简而明”,期望将汉人的简明和宋人的义理相结合,使文章臻于完美[6]。
讲究精气相贯、首尾不断。他认为作文之道与穿衣服一样,“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如果衣上加衣,裳下有裳,则杂乱无章,首尾相断。六朝人的文章反复重叠,正犯了这个毛病。精气是文章的灵魂,必须“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俱全,具有情感、学识和思想的力度。做到这点,非熟读周秦汉及唐宋人之佳文、“多闻见并蓄理富”、“博学心知其意”不可[7]。
强调时代气息。“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虽“其事之微,物之甚小”,也能反映“朝野之风俗好尚”。独特的时代气息,是文章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人们在读唐朝贞元、元和时期或者宋朝嘉佑、元佑时期的文章时,读不出丝毫时代气息,那就是无价值的文章,就是韩愈所谓的陈词滥调。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固然大体相同,但“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过于强调古今生活的共同之处而忽视时代的差异性,尽管遣词造句不同,也属于陈词滥调[8]。
追求表现真我。人的性格有缓急刚柔之分,文章有阴阳动静之殊,犹如楂梨橘柚,味道不同形状也不同,仿佛裘葛冰炭,所长所短鲜明突出。试图兼采众长、掩饰所短,结果必然是味道怪异、湮没特长,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失真是作者的悲哀。“见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真者也。见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真者也。”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只有表现作者真实性情的文章,才能流传百世[9]。
其诗论主张同中求异,展现个性。人的境遇、性情、心思、才力,充满差异。没有独特个性的诗歌,“是天下人之诗,非吾诗也”。诗歌创作要避免雷同:境遇相同则“舍境而从心”,表现性情之不同;心思相同则“隐心而呈才”,表现才力之不同[10]。诗人要将自己独一无二的性情才力,“呈露于文字声律之间”,写出自己的境遇而“非人之境”,自己的情而“非人之情”。这样的诗歌,才能“悬万世而不竭”[11]。
物我交融、情真意切。诗歌是物我交融、激动而成的产物,所以“无我不足以见诗,无物亦不足以见诗”。对于廊庙、山水、斋居、觞咏,如果极尽古人之长技状而咏之,“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如果昧于物态万千和声色差异,竭力表现自己的庄严和悲壮,“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有物无我,古人后人则没有区别;有我无物,则道形不肖,机心不应,千篇一律。诗歌应当“肖乎吾之性情”、“当乎物之情状”,物我交融,情真意切,这才是“诗之真”[12]。
如果说文以载道、简洁明快、精气相贯,主要表现的是桐城派的文学主张,那么强调时代气息、表现真我个性,则是梅氏的个人特色。将所处时代和个人真情实感相结合,赋予诗文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反对陈词滥调,既为桐城古文注入活力和生机,“从活泼的时代取得活泼的真理”[13],也与龚自珍等“尊情”主张相呼应,展现了嘉道时期关注、反映并干预现实的文学精神。
二、主张改革礼法、提倡“民佣”思想的政论
嘉道时期,社会危机四伏,经世思潮涌起。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梅氏自少留意“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办”,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主张士大夫在世不可苟且,应上佐天子,宰制万物,或象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那样,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14]。他期望建功立业于世,或垂文章于将来。
时人最推重梅氏的两篇政论文是《民论》和《刑论》。《民论》撰于嘉庆十八年(1814年)天理教林清事件中,一介书生的他上书汪尚书,指出“邪教”是基层教化传统崩坏的产物。古代圣人制作饮射之典、傩蜡之礼、月吉读法之令,目的是宣传法令、教育百姓、沟通消息、化解矛盾。汉朝强盛时,郡太守和县令都亲自参与这些活动。东汉后期,其法渐衰,“此黄巾米贼之祸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当今应该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加强基层教化,导民于乐,重建地方秩序[15]。《刑论》撰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在离他辞去户部郎中之职前一年。他感慨“天下之法,未有久而无弊者也”,主张变法,以免积弊难返,“得罪于天下后世”。他批判司法者“救生不救死”的观念,扰乱了法律意识和社会秩序。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人们“易知难犯”的朴素法律观念。现在法律“严密而难知”,滥生枉死,动摇人们朴素的法律观念,也弱化了法律的威慑力,结果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他呼吁加强刑罚的客观主义标准,重视司法的社会效果[16]。这两篇政论文,体现了梅氏对嘉道时期社会秩序的关注,希望从礼法两条路径重建社会秩序。
此外,他还关注吏治问题。梅氏认为事势盘根错节、法令松弛、财政不足,固然是当今的严重问题,但最严重的是“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除主体不纯、升迁困难外,赏罚不明是其主要原因。高位者往往委过于下,所受惩罚不过是降级、罚俸,而“位卑者则一蹶不可复振”,因此身不能安、职不能尽。要改变现状,必须做到职责明确、赏罚分明,加大对权贵责重者的惩罚力度,使其“不敢有以位为乐之心”,才能使下者“乐其职”、“安其心”[17]。
州县无权,是地方官吏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天下事取办于督抚,督抚取办于州县。”州县直接面对民间的利病兴废,即使竭尽聪明才力,也未必诸事尽举。地位如此重要,权力却受到制度设计的制约,以致倡议之事,“逆阻于文书、阶级之烦扰”,“此合彼牾,往返旷日”,“功不收而罪集”。他指出,“今为州县者,皆苦无权”,其结果是“荡荡然若无所事”。权力制约的目的是钳制不法官吏,使其不得率意妄为,困苦百姓,结果却限制了州县积极作为,致使州县的聪明勤苦,用于应对“上官宾客之过境”,唯恐供张不办、馈遗不供、礼数不密,而非百姓福祉[18]。要改变这种状况,除加强上下沟通外,重在制度改革。他呼吁借鉴汉唐时期的管理经验,赋予州县自主的权力。如汉代的太守那样,刑政自专,曹掾自辟,逐捕主动,基层组织完整,成为朝廷依赖的地方支柱。如果州县拥有自主权,则“其权专,其势便”,“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19],定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梅氏欣赏“民佣”思想,也希望以此改善吏治。“民佣”思想源自州县级官吏石家绍的自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梅氏对石氏关爱百姓、尽心尽责的事迹非常敬佩,对其自记则赞赏道:“父母之保抱其子者,盖日为佣而不自知也”[20]。他指出,政府官员不但要做百姓的父母,对百姓关怀备至,而且要做百姓的公仆,事事服务于百姓。“民佣”思想所透露的仁爱思想和服务精神,是留给后世的一笔遗产。
梅氏的上述改革主张,成为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内容之一。尽管亮点纷呈,终究属于体制内的改革者。而且,像同时代士大夫一样,在没有外部资源资鉴的条件下,只能运用本土资源应对时代危机,不免具有“药方只贩古时丹”[21]的局限。其视政治为士大夫的专属权力,反对“农工商贾皆汲汲然有为士之心”的参政议政愿望[22],也是其局限性所在。
三、批判汉学、主张汉宋兼采的学论
宋学汉学是清朝学术的两大壁垒。宋学以程朱理学为典范,提倡心性之学,强调“尊德性”。汉学以东汉许慎郑玄为典范,提倡考据之学,强调“道问学”。乾嘉时期,汉学达到高潮,形成乾嘉学派,占据学术主流。
梅氏曾试图跻身学术主流,走汉学之路,终觉得与自己志趣不符,于是放弃。他在给亦师亦友的王惠川书信中写道,“间以暇日游心章句,但两载所得,似语无成”,对古人的“秘思曲致,未有得也”。他发现博闻强识并非自己所长,遂引韩愈的话自喻,“但求义理,不暇及名物经制”[23],以扬长避短。此时他对于汉学,是充满崇敬之情的。他称赞清朝近二百年间,汉学兴盛,名儒大师层出不穷。汉学家“说一字之误,陈书至数十种。穷搜而远采以上及杳冥不可知之年,下至骫骳慢戏,假托名字,间脱分裂,古人之所不称,往往立之。而书出于刺取收捃之中,盖几于尽矣”[24]。汉学既非所长,他便将精力转向文章之学。
皈依姚门后,姚鼐的汉宋学术观影响了他。他曾回忆自己侍坐先生旁边的时光,当谈到清初颜元、李塨对宋儒的批判时,先生说颜元是个“谿刻自处”的人,可以理解,现在的汉学家们,德性堪虞,却一味以训诂文字讪笑宋儒,与颜元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汉学宋学,先生的观点是:“吾固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25],主张汉宋兼采,义理与考据并重。这种学术观改变了梅氏。
梅氏像同门陈用光(1767—1835)、方东树一样,对如日中天的汉学诋毁宋学的做法,颇为不满。道光元年,他成为进士,在与陈用光的信中,就批评汉学“好诋毁儒先”,“骇动后学,不顾所安”[26]。辞去知县之职后,他奔走于上元、宣城、安庆、六合之间,讲学客幕,交往中不乏汉学家或倾向汉学的学者。他在不少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汉学的不满。如在宣城时,他为程菡宗的著作《春秋溯志》作序,称“百年以来,名儒老师相逐于训诂、名物、象数之学,凡宋儒说经空虚道术之谈,变之唯恐不尽”。《春秋》一书,褒贬善恶,贵取其义,汉学家觉得“无可肆其捃摭”,就“杂出于谶纬之诬,科例之烦苦”,结果“迂怪破碎”,人心难安。究其用意,“好与宋儒为异而已”。他评论说,康熙时期,公卿之间“多崇尚理学”,以致时好成俗,“儒先语录之书遍天下”,士子高谈义理,空疏谫陋,“视经传如异物”。在这种风气下,有志之士倡导考证,慨然变之,学术于是分化为义理、考证两派。当今的考证之学,已经发展到“昔之言义理者矣”的地步,风会所向,“不因时尚者,固亦有之,而不可数数觏”。这种学风也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了。“昔时而能言考证者,真考证也;当今之世而能言义理者,真义理也。”[27]他呼吁重塑学风。
道光十二年,梅氏出任户部郎中,重返京城。他发现:十年之前京城“多好古博洽之士”,十年之后其人或死、或归、或远宦、或始同终异,“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28],真可谓“云卷波徙”[29]。他在重读姚鼐《九经说》时,回顾宋汉学术的转化,感慨不已。他说,清初的理学名臣李光地、桐城派祖师方苞,都以宋元诸儒议论糅合汉儒,疏通经旨。由于“惟取义合,不名专师”,不免无“望文生义、揣合形似”之说,存在空疏之处。尽管如此,他们的经典阐释,虽“不必尽合于经”,却“不失圣人六经治世之意”,对于扶树道教,弘扬程朱之学,端正人心治术,颇有裨益。对此,应“略小疵而尊大体,弃短取长”。然而汉学兴起后,倡导“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应经义不倍师法为宗”,批判理学的空疏,汉宋之争愈演愈烈,形成“辩汉宋、分南北”的学术格局。至于汉学“末流”,变本加厉,矫枉过正。“言《易》者首虞翻而黜王弼,言《春秋》者屏左氏而遵何休”,对于“前贤义理之学,涉之唯恐其污,矫之唯恐其不过”,甚至“周内其言语文字之疵,以诡责名义骇误后学”,极尽嘲讽之能事。汉学“末流”之“党同妬真”,“寻逐于小言辟说”,于经义“不要其统”,对学术人心的祸患,“逾于空疏不学者也”,最终走上“自蔽”之路。他认为,经典是“群言之君”,经典研究有助于“继往开来”、“扶微起废”,不可拘泥一家一派之说,“治一经而惟一师之言是从”,否则就不能谓之“正学”。对于将来的学术走向,他称赞姚鼐不悖宋学、不薄汉学的学术思想,主张“兼其长而无其短”[30],汉宋兼采,重塑新时期的学风。
梅氏擅长诗文,自然不忘批评汉学家创作的诗歌。他评价汉学家阎若璩、惠栋、何焯在学术上各有所长,诗歌则非所长。顾炎武、朱彝尊的考证、诗歌都出色,但顾炎武并不以诗人著称,朱彝尊的诗歌追求工整,作品丰富而“自得者少”,这是因为受到考证学的影响。他认为“诗人不可以无学”,但是作诗必须“置其心于空远浩荡”,不受繁重丛琐之名物象数的束缚。后者可以作为诗意更充分表现的工具,但是绝不能受之牵累[31]。
梅氏的学论,揭示了汉学宋学在清朝的历史变迁,以及自己从汉学的崇敬者到批判者的转变。其中不乏偏见,但汉宋兼采的学术主张,确能代表嘉道时期学风转化的趋势。
梅氏的文论、政论、学论,颇能代表其思想的特色。综上所述,其思想特色不仅是个人境遇、性情、才气的体现,也不仅是桐城派学术观和文学主张的体现,还折射出嘉道时期的时代气息。人的思想观念,无论曲直隐显,终究是其时代精神的折射,于此可见一斑。
[1] 清史列传:卷73[M].北京:中华书局,1987:6026.
[2]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M].长沙:岳麓书院,1991:1136.
[3] 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M].北京:中华书局,1990:174.
[4]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78.
[5] 梅曾亮.十经斋文集叙.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7-138.
[6] 梅曾亮.与姚柏山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2.
[7] 梅曾亮.与孙芝房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3.
[8] 梅曾亮.答朱丹木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8.
[9] 梅曾亮.太乙舟山房文集叙.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1.
[10] 梅曾亮.黄香铁诗序.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5-116.
[11] 梅曾亮.吴芴蓭诗集序.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31-132.
[12] 梅曾亮.李芝龄先生诗集后跋.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2-123.
[13]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64.
[14] 梅曾亮.上汪尚书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4.
[15] 梅曾亮.民论.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4.
[16] 梅曾亮.刑论.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13.
[17] 梅曾亮.臣事论.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16.
[18] 梅曾亮.上汪尚书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4-26.
[19] 梅曾亮.送张梧岗叙.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9.
[20] 梅曾亮.石瑶臣传书后.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62-163.
[21] 龚自珍.《乙亥杂诗》第44首.龚自珍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5: 513.
[22] 梅曾亮.臣事论.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
[23] 梅曾亮.寄王惠川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92-393.
[24] 梅曾亮.王惠川墓志铭.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61.
[25] 梅曾亮.九经说书后.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9.
[26] 梅曾亮.复陈石士先生札.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3.
[27] 梅曾亮.春秋溯志序.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4-95.
[28] 赵尔巽.清史稿:卷486[M]:中华书局, 1998: 3437.
[29] 梅曾亮.赠余小坡叙.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2-63.
[30] 梅曾亮.九经说书后.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9-120.
[31] 梅曾亮.复刘楚桢书.柏枧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