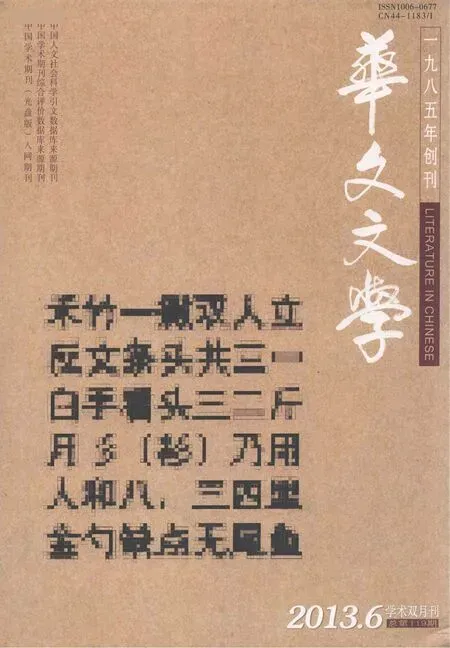“独步”台湾现代诗坛的一匹“狼”——纪弦在台湾现代诗“史”中的意义与地位①
[马来西亚]李树枝
一、狼的足迹
2013年7月22日离世的百岁现代主义诗人纪弦(1913~2013),堪称台湾现代诗的开山鼻祖。纪弦对台湾现代诗书写内容与形式、现代诗运动产生重大之影响。纪弦,原名路逾,字少丹,又字越公,生于河北。纪弦于十五岁初试散文,隔年开始对新诗产生兴趣,并写下第一首诗《初恋》。他20岁时深受现代诗派之“诗坛领袖”戴望舒《望舒草》影响,并曾积极模仿戴之诗风。纪弦曾用笔名路易士等,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据资料显示,纪弦于1933年12月出版了《易士诗集》;1935年与杜衡合办《今代文艺》;1936年和徐迟及戴望舒共同创办《新诗》月刊;1939年在上海出版了《爱云的奇人》等三部集子。一般认为,1930年代的李金发与戴望舒等人深受法国象征主义之影响,可以说纪弦亦是同在法国象征主义谱系里锻炼诗艺。
纪弦于1938年11月渡海到台湾,先在《平言日报》任副刊编辑,后任教于台北成功中学至1974年退休,之后于1976年赴美定居。纪弦出版多部诗集与评论集,他持续创作,于1996年出版《第十诗集》。1969年,纪弦出席菲律宾“第一届诗人大会”,并获得菲总统大授金牌奖,次年赴韩国出席国际笔会。1974年,纪弦获得第一届中国现代诗奖特别奖。1981年,纪弦出席旧金山的第五届“世界诗人大会”,更获得了世界文化艺术学院赠与荣誉文学博士。因此,纪弦堪称具国际性名望的台湾诗人。
在台湾,身为台湾现代诗坛三元老(另二老为钟鼎文与覃子豪)之一的纪弦,于1953年独资创办台湾现代派诗人的共同杂志《现代诗》季刊。继而于1956年1月,在台北“风云雷动”地集结方思、郑愁予、商禽、林亨泰等人,成立“现代派”,形成百人以上的庞大的现代派诗人群团体。后于1956年2月,在《现代诗》第十三期,推行“领导新诗再革命,新诗现代化”的文艺纲领,并提出了对台湾现代诗坛(运动)影响深远的“现代派六大信条”,为(中国)新诗再革命。概言之,纪弦“先锋”地拉开了195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学的帷幕,明确竖立了“现代诗”名词旗帜,于台湾现代诗书写历程史及文学史具有“特殊”的地位。
笔者需特别指出的是,本文题目之动词“独步”、名词“狼”及“史”蕴意了纪弦“独特”的书写风格于台湾现代诗“书写史”及其现代诗“文学”(活动)史的意义与地位。基此,笔者拟于下文探讨纪弦的现代诗“书写史”以及其在台湾文学活动史/现代诗史/文学史之“史”意义与地位。
二、槟榔树下,爪握烟斗与手杖④,“俳谐幽默”的一匹狼
首先,就纪弦在台湾现代诗“书写史”方面来看,纪弦主要是以其“独特”的“俳谐幽默”的书写手法独步台湾现代诗书写史。必须先说明的是,笔者使用“独特”词汇意涵,并非指“独有”,而是指诗人奠基并继承前辈诗人如戴望舒等人书写技艺的基础上,锻炼出为读者或诗评家可轻易明辨出其书写风格成熟的“特殊”技艺特征。审视纪弦的漫长的书写历程,我们可粗略地划分其中国大陆时期的书写史止于1938年,渡海去台的书写止于1973年,以及1976年12月离台赴美止于2013年为其美西书写时期。台湾诗评家张默清楚指出纪弦的书写特征为“手法独特”与“有个性”。诚如纪弦的诗句,“当我的与众不同,/成为一种时髦,/而众人都和我差不多了时,/我便不再唱这支歌了。”中所揭示,纪弦贯彻“手法独特”与“有个性”的主张及艺术探索。我们暂且不论其情绪愤慨的“战斗诗”之书写风格,尝试聚焦纪弦对于生活的感悟,融入情绪张扬,突出自我,随性地建构可谐趣嘲讽之诗风。台湾诗评家罗青精确地指出其“俳谐幽默”的谐趣书写,不仅丰富五四以来的新诗书写内容,也开拓了台湾现代诗“俳谐幽默”书写范式,供新一代年轻的台湾诗人继续参照、探索及追寻“诗与谐隐”诗思程式。综上张罗二家的观点,具体而言,纪弦以其独特、主观且个人化的自嘲/他嘲/“自他嘲”诗文本里的飞跃的意象以及谐趣戏剧之语法,“独步”台湾现代诗坛。
笔者认同张芬龄的观点:纪弦的“俳谐幽默”诗文本具有“机智”与“讽刺”的诗意质地。笔者以为,还可以增多两个质地“风趣”与“调侃”。诸多诗评家已剖析其名诗《6与7》之“俳谐幽默”之艺术特征;故笔者拟择取其从1934年至1999年约跨65年的书写文本,以其于1934年创作的《脱袜吟》、1994年发表的《动词的相对论》及1999年发表的《在异邦》三首现代诗为例,进一步说明其一以贯之,并兼具“机智”、“讽刺”、“风趣”及“调侃”的诗意质地说明其“独特”的“俳谐幽默”书写风格。易言之,“俳谐幽默”书写除了是“喜剧的谐趣”外,也进一步深入地挖掘自我/他人/众人的生命的悲剧。
兹列《脱袜吟》诗句如下:“何其臭的袜子,/何其臭的脚,/这是流浪人的袜子,/流浪人的脚。∥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家呀,亲人呀,/何其生疏的东西呀。”纪弦深受杜衡的“人生的写实主义”主张影响,排斥“事实架空情感虚伪”书写。纪弦以“流浪人”的“臭袜子”与“臭脚”,并将“流浪人”与“亲人”进行对比,机智地刻画了“流浪人”生活境遇的悲凉及沧桑,全诗充满了谐隐、悲天悯人之诗意外,更多的是“讽刺”彼时社会流离失所的惨况。
纪弦的“机智”地“俳谐幽默”亦将讽刺从前文的广大社会提升至对深沉人性的挖掘、揭露、挖苦及批判。纪弦顽童式地表明了“用世界上最辛辣的字眼讽刺我自己,嘲笑我自己,直搔到我自己的痒处,同时发见我自己的伟大”。兹引《动词的相对论》诗句如下:“为了取悦于我的女人,/让我看来性感一点,/我常用手拦拦我的两撇短髭,/使之向上微翘。//这和一只爱干净的大头苍蝇,/停歇在我的书桌上,/不时用脚刷刷它的一双翅翼,/究竟有何不同呢?/我拦拦;它刷刷。/我用手;它用脚。/我是上帝的;而它也是。/多么的悲哀哟!”纪弦“俳谐幽默”地透过“人”与“苍蝇”意象之比对思索,赫然惊觉/警觉“人”之性等同“苍蝇”之习性。“这和一只爱干净的大头苍蝇”是“俳谐幽默”式的反讽诗句,人性没有多高,人和苍蝇乃是上帝“共同”创造之物!全诗充满了自嘲与他嘲的嘲弄意味。
《在异邦》的诗句写道:“在异邦的大街上走着,/边走边骂人,用国语,/而谁也听不懂,多好玩!//还有更好玩的哩——/那就是:/被遗弃了似的,/被放逐了似的,/被开除了似的,/被丢入了纸篓似的,/被倒进焚化炉似的,/和黑板上一个粉笔字被擦掉了似的//一种感觉。”移居美国加州,仍不脱“俳谐幽默”外,更多的是以风趣斜睨命运,对人生充满了悲剧的调侃。
综上三首诗的分析;概言之,罗青认为纪弦的“俳谐幽默”可分为早期的“向命运开玩笑的雅量”、“滑稽玩世的遁逃”及晚期“不遁逃”/“不征服”“与命运和平相处,以风趣的态度欣赏之(命运)”的论点,当是公允且正确的。
三、狼的长啸:“现代诗”之口号、宣言及信条
承上有关纪弦于台湾现代诗书写史地位之概述,笔者继续尝试在本节简介纪弦于台湾现代诗(活动)史及台湾文学史两个方面的意义与地位。粗略而言,台湾现代诗历经20世纪50年代的“播种奠基”期、60年代的“吸收开放”期、70年代的“反省蜕变”期,而后达致80年代至今21世纪前二十年的“多样与多元”期。整体而言,台湾现代诗此四个分期堪称一个异常丰富的文学成果累积。就现代主义或曰现代派之“现代诗”文类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是台湾现代主义诗运动的活跃期;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面对现实主义诗潮兴起,并进行应对、审思及调整;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虽不独霸一方,它仍与浪漫、写实、后现代等各种艺术思潮倾向并立呈多元之姿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空“包裹”的诗人诸如纪弦,继承五四又汲取欧美各种诗风与诗潮,对于台湾现代诗运动,贡献出重要的力量,为台湾“现代诗燃起一把火炬”。
相较于1948年和1949年的诗集出版惨况,1951年自立晚报副刊《新诗周刊》供新诗作者发表的园地,诗集出版的数量依然不多,1952年由纪弦主编的《诗志》只出了一期即宣告停刊,1953年纪弦创办的《现代诗》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口号,是台湾现代诗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拐点,开启了之后台湾现代诗,至少影响并促进了1980年代的“银山拍浪之气象”。
诚如上文第一节所言,纪弦身兼发行人、社长、编辑人、经理于台湾创办的《现代诗》、乃延续戴望舒《现代》之精神。因此,中国大陆“现代派诗”之名源至《现代》杂志的意义;犹如台湾“现代诗”之名因《现代诗》而定名之意义。“现代诗”继而成为了“在台湾发展的中国新诗”,也在一定意义上,连接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现代主义思潮。李欧梵精辟定位了纪弦与戴望舒的连接,“诗比小说抢先一步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主流,原因很明显。纪弦为戴望舒所主持下的气数不佳的《新诗》杂志的同仁之一,在1953年创办《现代诗》杂志,显然又使1930年代那点微末的遗绪复活起来。”三年后的二月一日,《现代诗》第十三期里的“现代派诗人群共同杂志”字样、83位现代派加盟者名单、纪弦撰写的《现代派信条释义》、《战斗的第四年,新诗的再革命》补充信条等内容,对中国新诗发展奠下重大意义。
就《现代诗》与“现代派”动员结社活动力量而言,“现代派”诗人群几乎涵盖了台湾彼时大部分的优秀的诗人诸如方思、李莎、郑愁予、蓉字、杨唤、辛郁、罗门、痖弦、林冷、周梦蝶、罗马(商禽)、林亨泰、洛夫、羊令野、梅新、楚戈等,不可不谓如诗评家感慨道:“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纪弦领导的“现代派”运动,刺激了彼时年轻诗人的创作与多部诗集出版。
基于现代派信条之第六条太具“政治性”,与文学美学无涉,因此简列现代派的其他五大信条以说明纪弦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意义与地位,该五大信条为:第一、“新诗乃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的精神和要素”;第二、主张“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第三、强调“新”,探险诗的新大陆,开拓诗的处女地。“新的表现之内容,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现,新的手法之发明”;第四、强调知性,“反浪漫主义的。重知性,而排斥情绪之告白”;第五、追求诗的纯粹性,“排斥一切‘非诗的’杂质”。“现代派”汲取自波特莱尔以降的象征主义等新兴诗派精神与要素,激烈地矫正与刺激新的形式的“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追求诗的纯粹性。
此五条信条延续了“新诗”目标。就“正面”意义而言,此五信条不仅冲破了彼时文艺界思想精神如“战斗文艺”的困囿,也开创并丰富了台湾现代诗诗艺内涵:象征、暗示、影响建构与营造等方面“新”的形式实验及探索。第五条有关“纯粹诗性”的追求,亦遥接了早期象征诗派“纯诗—贵族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在彼时文艺政策高压政治下,台湾现代主义现代诗书写得以迂回开展。有关第一与第二条的主张,我们知晓,纪弦事实上不能/也不可能摒弃传统,他要除去的乃是五四以来新诗滥情的浪漫主义之“新”传统。纪弦“矫枉过正”的“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与“主知”之主张,更多为了突出现代诗“新”的形式与内容。但过激的“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使得他无可避免地成了争论中心,纪弦或现代诗受到“保守”势力诸多批判;然而,正是其“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奠下了信条“公告天下”后,台湾现代诗彼时十余年至二十年的基本发展趋势。
受到纪弦“现代派”结社“刺激”,台湾诗坛三元老之一的钟鼎文(不久即退社)有感于“纪弦初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刺激”下,于1954年3月,和覃子豪以及后起的余光中、邓禹平及夏菁成立了蓝星诗社。蓝星诗社不认同纪弦要“横的移植”西洋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之主张,又以“抒情”主张来制衡纪弦的“主知”创作主张。实事求是而言,纪弦的巨大影响与刺激,使得覃子豪创作出《瓶之存在》,余光中亦于1950年代末大幅调整诗风。另,1954年10月,洛夫、张默及痖弦发起成立创世纪诗社也受到纪弦之影响波及,诗社强调“新民族诗型”“追求中国风的东方风味”抗衡“现代派”“知性的强调”及“非纵的继承”主张;过后创世纪诗社扩大继而提倡“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及“纯粹性”,并过度地“横的移植”超现实主义精神与手法,加速了台湾现代主义现代诗现代化进程,使得19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文本“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当然,也遭致了学院内外的批评。
姑不论纪弦如何在1950年代末后,见到比自己更“顽童”式的极端超现实“现代诗”之“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晦淫,乃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等总总偏差”,并称营造如此极端超现实世界的“现代诗”为“伪现代诗”;不论直率且顽童性格的纪弦,如何于1965年5月发表《中国新诗之正名》,又于1966年4月尝扬言取消造成诗坛种种偏差的“现代诗”名号;不论纪弦与现代派影响力于1966年后如何逐渐稀释,无可否认的是,纪弦对台湾现代诗“史”的影响,从1950年代持续至今。换言之,1960年代中期后《笠》现实主义诗潮兴起;1970年代以后,龙族诗社、大地诗社及草根诗社等与诗刊纷立,乃至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台湾现代诗/新诗,或多或少,与纪弦的主张与宣言“正面”或“负面”之影响,有着千丝万缕“史”的内在影响关系。
四、结语:世纪之弦[40]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创始者”或现代主义的“宣扬者”与“见证者”/诗坛的常青树/老顽童(皆张默语)、“中国现代诗史上第一个响亮的名字”以及人瑞作家(痖弦语)的纪弦,其“独特”的现代主义现代诗“俳谐幽默”书写,着实开拓并丰富了五四以来新诗的题材内容。其在现代诗(自由诗)语言形式之尝试,刺激了余光中、郑愁予及痖弦的诗语言的锤炼,让台湾后起诗人进一步去探索“新”诗形式。而其积极推动台湾现代诗的文学口号、信条及活动,西化的主张,不仅加速了台湾现代主义现代诗书写,更进而影响了台湾现代主义达致扩张与深化的文学史进程。不仅1950年代是纪弦的年代,1950年代以后至今,纪弦更是以“新诗再革命”以及“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古典化”等主张,在台湾现代诗坛留下了不可淹没的狼踪。概言之,纪弦这匹爪握烟斗与手杖,又“俳谐幽默”的狼,在台湾现代主义现代诗旷野上,嚎出了世纪之(弦)声。
①本文题目启发自纪弦的名诗《狼之独步》,见张默、张汉良、辛郁、菩提及管管编:《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台北: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7年版,第36页。
②罗青:《纪弦的〈足部运动〉》,见罗青:《诗的照明弹》,台北:尔雅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③⑥[12]《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第10-14页;第15页;第17页。
④纪弦在台的作品,于1974年按5年重编,分别以《槟榔树》甲、乙、丙、丁、戊5集出版;手杖及烟斗为其名诗《6与7》重要意象;狼为《狼之独步》的主体意象。故诗评家认为,“槟榔树”、“手杖”、“烟斗”及“狼”为纪弦诗文本的重要代号或象征意象。
⑤罗青:《俳谐幽默论纪弦》,罗青:《诗的风向球》,台北:尔雅出版社1994年版,第79-116页。
⑦《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第9页。此观点乃身为《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编辑群之一张默的论点,见张汉良为《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写序文之说明,第5页。亦见张默:《老顽童后劲十足:评纪弦〈第十诗集〉》,收录于张默:《台湾现代诗概观》,台北:尔雅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⑧罗青:《俳谐幽默论纪弦》,第114页。“诗与谐隐”的观点见朱光潜:《诗论》,台北: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24-27页。
⑨张芬龄:《现代诗启示录》,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19-121页。
⑩“喜剧的谐趣”为张默观点,见《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第9页。
[1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13]纪弦:《饮者诗钞》,台北:现代诗社1963年版,第127-128页。
[14][15]余光中总编辑,白灵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89-2003:诗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第25页。
[16]《诗的风向球》,第114页。诗评家如洪子诚与刘登翰等亦认同罗青的观点。见《中国当代新诗史》,第317页。
[17][19]《台湾现代诗概观》,第10页。
[18][24]《中国当代新诗史》,第301页;第305页。
[20]《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之《纪弦小传》,第10页。
[21]“银山拍浪之气象”为罗青对战后1946年至1980年的台湾现代诗的概括语,有关纪弦现代诗集出版、发表刊物等内容参考自《诗的风向球》,第147-148页。

[23]叶珊(杨靖献,另一笔名为杨牧,台湾著名诗人兼中国古典诗与比较文学学者)认为纪弦主编《现代诗》并成立“现代派”后,“现代诗”已被“确定为新诗的通称”。见叶珊:《写在〈回顾〉专号的前面》,台北:《现代文学》第46期之《诗专号》,1972年3月,第5页。
[25]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收录于《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2·文学现象卷》,台北:正中书局2000年版,第139-140页。原文由吴新发译,刊载于台北:《现代文学》复刊第14期,1981年6月。
[26]杨牧:《关于纪弦的诗社与现代派》,收录于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台北:故乡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384页。
[27][32]余光中:《第十七个诞辰》,收录于《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第394-395页。
[28]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台北:《现代诗》十三期,1956年2月。
[29]钱理群、温儒敏、吴福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30]陈芳明的观点,见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上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31]罗青与陈芳明似乎持类似观点。见《台湾新文学史》上册,第329页。
[33]罗青:《诗的风向球》,第151页。
[34][35]张默:《创世纪的发展路线及其检讨》,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第418页;第418-426页。
[36]余光中:《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37]纪弦:《从自由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古典化》,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第23-29页。
[38]龙族诗社的宣言既是对纪弦“横的移植”主张“隐约”之反拨,倡导回归“龙”中国传统。见陈芳明:《诗和现实》,台北:洪范书店1977年版,第20页。
[39]草根诗社采取制约修正的主张:“我们拥抱传统,但不排斥西方”,也是修正方式批判“横的移植”或过度西化的偏颇。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史料篇》,第458页。
[40]取自台湾诗人兼诗评家萧萧(原名萧顺水)对纪弦的赞语。
[41]张默的论点,见《台湾现代诗概观》,第299-301页。
[42]萧萧:《纪弦与现代诗运动》,收录于其《灯下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65页。
[43]罗青尝称20世纪50年代为“纪弦时代”,见《诗的风向球》,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