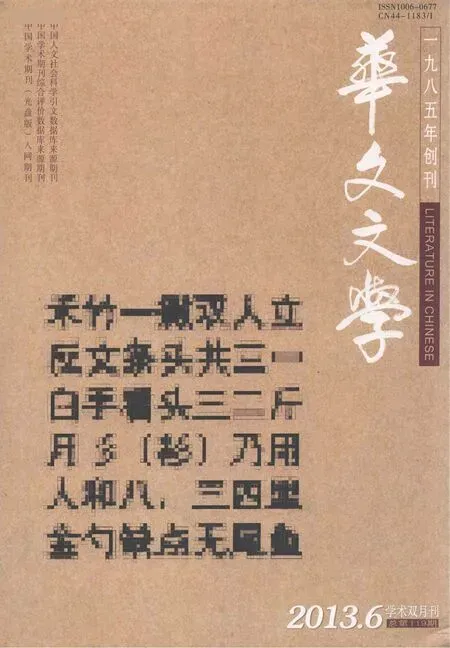台湾现代图像诗文体新探
赵敬鹏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台湾新诗的发轫,可以上溯到“一九二三年五月追风(谢春木)以日文创作《诗的模仿》四首短制”。近百年来,台湾新诗中的现代派诗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尤为耀眼,以现代诗、蓝星和创世纪三类现代派诗歌为例,三者“是大同小异的孪生兄弟,他们相异的只是西化程度的差别”。“台湾现代图像诗”便是其中一股重要的现代诗歌潮流,风靡一时。具体来讲,这是一种“利用汉字的图象基因与建筑特性,将文字加以排列,以达到图形写貌的具象作用,或藉此进行暗示、象征的诗学活动的诗”。
然而,这种文体却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文字游戏,遭到了种种非议。例如颜元叔在谈到台湾现代图像诗的代表作《流浪者》时,不无讽刺地说,“有人(近来亦颇流行)在诗行的排列上下尽功夫,如写‘地平线’三字,写成一线”,“假使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倒不知如何排列”,其中所表现的鄙夷之情非常明显。不能说这些批评完全没有道理,但文学艺术贵在不断寻求新的可能,“拒绝承认由惯例所确定的边界,常常是将艺术对象谴责为不道德的根源”。图像诗遭到如此讥讽与偏见,大概也受到了主流诗论和既有审美经验的影响。但是在“图像时代”的今天,我们不妨从这一立场重新审视其中所隐含的深层学理。
图像诗之“图像”
如果按照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以摹仿媒介来区分艺术类型,那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就认定语言是文学的唯一媒介。换言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语言并非文学的全部”,语言和图像皆为图像诗的媒介,这就使它明显有别于纯粹以语言表意的文体。



以《流浪者》为例,诗歌的前四行文字被布置成了一棵树的立体剖面图,以示站立着的丝杉,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同一棵丝杉树的四种姿态;中间几行将“在地平线上”五个字排成水平一线,唯独那“一株丝杉”树的图像似乎伫立在旷野之中。从诗歌的第一行到第十五行,诗人将文字排列成文本图像绝非轻佻之笔,而是有意而为之,尤其是第五行到第十五行这一处文本图像,展示着“一株丝杉”站在广袤的地平线上,形象地意指了这株丝杉树的孤独。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图像诗是难以定义的,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认为原因在于“图像诗(Pattern Poetry)不单是一个事物,它至少既是视觉的、又是文学艺术视觉化的诗歌”,尽管如此,图像诗仍可以被看成一种“通过单词或者字母的布置,而建构成视觉图像的诗歌”。可见,就文本图像而言,中外图像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台湾现代图像诗使用的书面语言是汉字,希金斯所讨论的西方图像诗多使用英文、法文等,然而,汉字的图像性却是包括英文在内的表音文字所不可比拟的。
研究表明,“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表现前者,而语言、文字、图像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则需要通过梳理文字史才能更加显豁。“原始岩画和早期象形文字的关系是文字源于图像的最确凿的证据”,“文字出现之后尽管仍然是一种‘图像’的存在,但是已经被赋予了‘一串声音’,成了‘音响形象’的标记,越来越远离了图像的相似性原则”。质言之,与一般意义上的图像相对而言,文字就像乐谱那样是可以发音的图像。
在《说文解字》9353个汉字当中,指事字的比例仅占1.25%,象形字占3.71%,会意字占8.75%,形声字占86.29%,除去相对抽象的指事造字法,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加起来要占到当时汉字的98.75%,而会意字、形声字莫不与“象”和“形”有关。例如会意字,就十分“依赖字符形体的形象特征及其组合关系”;至于形声字,“中国文字,十之八九,都由于这种方法造成的”,其“形声结构的发生,首先孕育于别的构形方式(象形)之中,进而才脱胎而出”。所以,有学者说象形是汉字的基本原则,“因为会意和形声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概言之,尽管象形字在汉字中占有很小的比重,但我们不难看出汉字高度的象形性(图像性),进而将文字书写视作图像也就成为可能。
在台湾现代图像诗里,文字是另一种图像类型,我们不妨称之为“文字图像”。这种诗作也有很多,如詹冰的《我的桃花源》、王润华的《象外象》、林亨泰的《车祸》、陈黎的《战争交响曲》等。在此类图像诗中,汉字的部件可以拆分并单独表意,甚至表达与原意无关的意义;而汉字字号的大小、字体的反转等都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以《战争交响曲》(图三)为例,与其说它是一首可以朗读的诗歌,毋宁说它适合于“观看”;不过,观看仍需遵循“用书写符号的线条空间代替时间上的前后相继”的线条性原则:“兵”字一开始完好无损,随后逐渐开始残缺,要么是丢掉了一撇,要么是丢掉了一捺,成为“乒”字和“乓”字,再后来连那一撇一捺也不见了,都成了“丘”字。从“兵”到“乒”、“乓”再到“丘”,文字图像所发生的变化即为战争的过程及其后果。《说文解字》释“兵”为“械也,从廾持斤”,“械者,器之总名。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籀文体为“ ”,小篆体为“ ”。这就是说,“兵”既可做兵器讲,也可以理解为士兵。“兵”虽为会意字,但它保存了汉字中的象形因素,兵字下方一横两点(“廾”的变体),原意应为两只手,兵字上方部件所呈现的图像(“斤”的变体)实为兵器。而《战争交响曲》将“兵”字拆为“丘”、“乒”、“乓”,可谓是对汉字图像的重新分解与言说——战争由士兵参与,故前几行诗中全部是“兵”;随着战争的持续、激化,开始出现伤亡,士兵损失了胳膊或者腿脚,兵器也许因为搏斗而变得残缺,于是“兵”字之后出现了“乒”和“乓”,同时也暗示着士兵之间、兵器之间的“乒乓作响”,应和了这首战争“交响曲”的诗作主题;直到战争结束,大量士兵双手或者双腿丧失,只剩下满地的兵器,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很多士兵因此丧命,或被埋葬,一个个坟墓呈现出“土丘”的图像。

由此不难发现,之所以这种文体名曰“图像诗”,盖因图像作为语言之外的媒介出现在诗歌中,但无论是将诗歌语言排列成图像,还是文字本身的图像,图像诗的语言与图像都重叠于同一个文本。然而这种图像并非严格以线条、笔墨、色彩绘制的,从本质上讲,图像是对诗歌语象的摹仿。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展开分析。
语象的图像化
“语象”(verbal icon)首见于维姆萨特(W.K.Wimsatt)的著作,意为“一个与其所表示的物体相像的语言符号”,或者说语象就是头脑中“清晰的图画”(bright picture)。这就可以说明“语象”概念触及了语言和图像的关系,而这一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则有着更为确切的论述:“现在有一幅图像与句子相联。它是否在我们心里并不重要。设想诺曼告诉我说到鲍斯玛先生家该如何走。接着我按照他的描述绘制了路线。于是我有了一幅图像。不过很显然,我可以摒除这幅图像。我走路时只要简单记住他说的话就行。词语充当了图像。我画的图像是不必要的。”之所以“画的图像”不再必需,是因为通过语言描述,我们可以在头脑中形成一幅图像,这幅图像就是语象,亦即维姆萨特所言头脑中“清晰的图画”。这不过是将索绪尔的“音响形象”换了一个说法罢了。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其中的“观念”可以理解为概念、意义等,即语言的所指,但在语言符号的能指方面却存在比较含糊的阐述。索氏首先肯定语言的“音响形象”与“发音”并不是一回事。在此基础上,他一方面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由此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而音响形象“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也就是说,语言的能指是属于心象的“音响形象”;另一方面,索绪尔还将语言比作一张纸,即“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这意味着语言的能指是声音。如此一来,声音能指的物理性质就与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两面的心理实体”互相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语言的声音作为音响形象的物质载体,二者互相依存,语音中本来就含有形象;简言之,语言的能指是含有音响形象的声音,而不含音响形象的声音就不是语音,当然也就不是语言了,如动物的吼叫、鸟鸣等。从这一角度讲,语言作为声音的存在,与一般声音的区别之处在于它含有音响形象。这里的音响形象,正是维姆萨特的“语象”、维特根斯坦的“词语充当了图像”。
我们知道,文学艺术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通过概念(逻辑思维),而是形象(形象思维、象思维)。由此而言,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语象的艺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研究,也应当建基于语象分析。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具备图像这种语言之外的表意媒介,就像我们阅读图像诗时会有一种别样的审美体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诗歌的图像造型,而它同时也是诗歌语象。换言之,图像和语象的同构是图像诗的基本存在方式。
既然语象是头脑中的图画,那么作为文艺理论的传统命题,所谓“诗中有画”,指的便不是诗歌里存有的真正的、实在的画,而是如画般的语象,亦即诗歌语言呈现在头脑中的图像。图像诗在这一方面,与传统的纯粹以语言表意的诗歌并无二致。如果单纯阅读《流浪者》中的诗句“在地平线上/一株丝杉”,而不顾及其文本造型,那么我们头脑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丝杉树”的语象。然而图像诗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将语象转变成了可视的文本图像,使我们在阅读诗歌的同时也能观看到诗歌中的若干语象。
比如《水牛图》(图四)第四行至第十九行的文本图像,就是将水牛躯干与四肢的语象摹仿了出来,“按水牛的外在形体为标准,四足与尾巴的地方,诗行的字数较多较长,身体肚子的地方则行数较短而且字数均匀”,一个水牛模样的文本造型赫然纸上。而《流浪者》、《楼梯》、《十八摸》中的丝杉树、楼梯、台湾地图等图像也都是对相应语象的摹仿,概莫能外。

由于“文字表现语言”,“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换言之,语言符号之所以可以捉摸,要归功于“文字把它们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即文字的视觉形象——引者注)里”,于是,“我们将可以看到,每个音响形象也不过是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音位的总和,我们还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文字作为图像,实质上同语象之间存在相似关系,如此方能说明文字这种“视觉形象”何以能够“固定”语言的“音响形象”(语象)。
这就是说,图像诗中的文字图像对语象的摹仿有着充足的合法性。仍以《水牛图》为例,诗歌中水牛的躯干和四肢属于文本图像,但第一行到第三行的“水牛头”则主要由文字图像构成,诚如罗青分析的那样:“一开始,诗人便利用中文的特色,把水牛的头部,以三个方块字‘画’了出来。‘角’这个字,十分象形,与有横纹的水牛角在外貌上十分相似。‘黑’这个字,则像极了水牛的头部,上方两个框框及逗点,正好像水牛的眼眶及眯着的眼睛;下面‘四点’(火字部首),则好像水牛下巴上的鬃毛。况且,水牛的颜色为黝黑,因此‘黑’不但描摹了水牛的头部形状,同时也写出了其颜色的特质。”诗人詹冰为了以图像摹仿水牛的语象,在遣词造句上用心良苦。再如《战争交响曲》以“兵”字摹仿完好无缺的士兵,以“乒”、“乓”摹仿受伤的士兵,以“丘”摹仿死亡士兵的归宿;《车祸》则通过字号由小变大的“车”字,摹仿了汽车由远及近的运动过程等。
简言之,图像诗中的“图像”本质上是语象的图像化:无论《流浪者》中所呈现丝杉树状的文本图像,还是《战争交响曲》中的文字图像,皆为对相应语象的摹仿和再现。图像诗的图像,只不过是把语象这种内视图像、语音的“心理印迹”予以外化和图像化。而语象的图像化,实则是一次朴素的陌生化尝试,即将表意活动中原本通过语音唤起语象(“语音含象”),转变成了“图像含象”。图像诗人“同语言作斗争”,借助图像延长了“使石头成为石头”的过程和时间,使语言符号能指得以延宕。然而就其之于图像诗文体的新变化而言,图像诗的图像和语言共享同一个文本,二者构成互文关系。
语言和图像的互文
承上文所述,图像诗的图像并非严格以笔墨、线条等绘制而成,仅仅是依靠对文字的布置,或者文字本身的图像,这就有可能使诗歌的图像趋向于简单化。因为图像诗之图像的“质料”只是文字,其“画法”不过就是文字图像的构造、对文字的布置和排列,如《流浪者》中的丝杉树图像,它只能由文字排列成树的模样,绝不可能用墨线勾勒树木的主干,更不可能借墨的干湿去表现丝杉树的远近虚实。所以,这种图像也就深深受制于仅有的“材料”与“工艺”,不可能像文人画那样精密、繁复,尚简趋势是不得已、也是必然而为之。事实上,我们不应以文人画的笔墨画法去要求图像诗之图像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制作工艺”,就图像制作这一角度而言,文字及其布置等同于文人画中的笔墨点线。由此观之,“图像诗多与笔墨无关,与笔墨点线的物理层面合体也相去甚远”的观点似乎失之偏颇,既然图像诗之图像与语言重叠于同一个文本,即便图像并非笔墨的“造化”,图像诗中的语言与图像也在物理层面做到了“合体”。
如果不满足于仅仅认识到图像诗之语言和图像在物理层面上的合体,借助互文性理论,我们还可以在更深的意义建构层面取得新的发现。克里斯蒂娃继承并发扬了巴赫金的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译(改编)”,图像诗的图像摹仿语象,同样也是一次转译,只不过由于图像本身是一种虚指符号,“相似性”的生成机制注定了它意指的“多义、含混和浑整”。
尽管图像诗的图像并不复杂,但这并不能消弭图像符号的虚指本性。一旦忽略对组成图像的文字的理解,便不能准确达到图像的意指。如果我们只观看《流浪者》的文本图像,它不过就是几条竖线,与随性的涂鸦别无二致,这幅图像既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线条,也可以看做几个人的缩影,诸如此类,只要与这几根竖立的线条相似即可,未必一定使人将图像与“丝杉树”联系起来;如果请一位文盲去观看《战争交响曲》,他肯定能辨认出从“兵”到“乒”、再到“乓”过程中的字体外观变化,然而只是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也必定不能讲出其中的意义以及所蕴藉的意味。这就说明,虽然图像诗的图像将语象予以摹仿,但它本身仍不具有表意的独立性,因为不阅读文字或者不理解语言文本的意义,这些图像的意指便不明确,而图像在诗歌中的作用也就会被“架空”。反过来讲,只有理解了语言文本(“前文本”)的意义,我们才会把《流浪者》的图像(“互文本”)视为丝杉树;也只有理解了《战争交响曲》的语言意义,我们才会把“兵”字看成一个人的图像,才会把拟声词“乒”、“乓”的文字图像看成受伤的士兵。只有这样,我们方可进而一眼便知诗歌的意义——看到《流浪者》的文本图像,我们就知道它是丝杉树,隐喻着类似“流浪者”的漂泊情怀;而看到《战争交响曲》中成排成列的“兵”字变成了“丘”字,我们也就领略了战争的残酷。

总之,图像诗的语言和图像呈现为“合体”态势,二者构成互文关系,图像虽然由摹仿语象而成,二者之间存在相似关系,但也只有依靠语言才能明确表意;而语言的表意效果却未受到任何不良影响,反而有了自己新的“代言体”。如果说文学是对世界的摹仿,那么图像诗的图像便是对摹仿的再摹仿,“恰如古之‘文以载道’,今则‘图以载文’”,这种图像只不过是诗歌的“自我放逐”而已。
①林淇漾:《长廊与地图——台湾新诗风潮的溯源与鸟瞰》,林明德主编:《台湾现代诗经纬》,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郭枫:《四十年来台湾文学的环境与生态》,《钟山》1990年第5期。
③丁旭辉:《台湾现代诗图像技巧研究》,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④张汉良:《论台湾的具体诗》,孟樊主编:《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新诗批评卷》,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88页。
⑤[美]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9页。
⑥赵宪章:《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⑦“图像诗”概念的内涵宽泛、外延模糊,给相关研究带来了不便。图像诗又称图形诗、图象诗、图案诗、拟形诗、具象诗、具体诗等,相对应的英文术语为Pattern Poetry或者Concrete Poetry。《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Pattern Poetry定义为“诗行的排列或排印成的形态本身可以表达或延伸诗的情感内容的诗体”,将Concrete Poetry定义为“一种视觉艺术,以某种方式使用印刷字体和其他印刷成分,使所选择的单位——文字片段、标点符号、字素(字母)、词素(任何有意义的语言单位)、音节或词(通常用于视觉意义而不是所指意义——和印刷间隔构成一幅激起人们想象的图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能使诗的意义独立于排印形式而存在,即前者的诗句可以朗诵而不失其意义”,后者则“朗诵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它的精髓在于它在页面上的形,而不在于构成其形的词语或印刷成分”。详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卷,第79页、第4卷,第394-395页)。易言之,Pattern Poetry虽是可视的图像,但更是可读的诗歌;Concrete Poetry则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一首可读的诗歌,倒不如说它是一幅可视的图像。不过,图像诗的实际创作中并没有像Pattern Poetry与Concrete Poetry之间这样明晰的界线,图像诗内部的复杂性可能尚未被充分认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⑧Dick Higgins,Pattern Poetry: Guide to an Unknown Literatur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p.3.
⑨Dick Higgins,“Pattern Poetry as Paradigm,”Poetics Today,Vol.10,No.2,1989,p.401.
⑩[16][20][21][22][24][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7页;第106页;第37页;第101页;第158页;第37页。
[11][30]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2]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3][瑞典]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8页。
[14]黄德宽:《形声起源之探索》,《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15]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3页。
[17]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18]W.K.Wimsatt,The Verbal Icon: Studies in the Meaning of Poetry,Lexington: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1954,p.x.
[19][美]鲍斯玛:《维特根斯坦谈话录:1949-1951》,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页。
[23][25]罗青:《从徐志摩到余光中》,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年版,第268页。
[26]“像”与“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侧重意指通过摹仿的方法制成的形象。相对而言,“像”是一种再加工活动的产物。请参见《“象”与“像”在名词义上的用法有新界定——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科学术语研究》2001年第4期),或倪梁康《图像意识的现象学》(《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7]周宪:《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28]李彦锋:《中国绘画史中的语图关系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13页。
[29]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in Toril Moi,eds.,The Kristeva Rea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37.
[31]李森:《“失明”的文学——从空间到空间理性》,《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33][法]米歇尔·福柯:《这不是一只烟斗》,邢克超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34]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