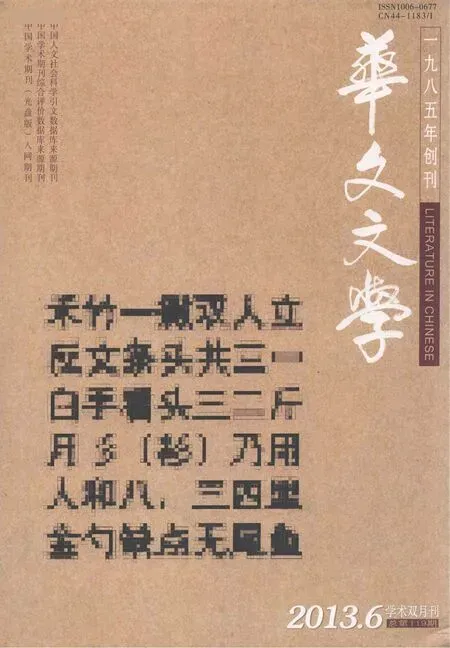讨论问题的方法与态度——回应付祥喜博士的商榷
陈国恩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查资料,偶然发现付祥喜博士在《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与我商榷的,题目为《文学的身份认同:民族的还是国家的?——与陈国恩教授商榷》。我觉得他提出的问题涉及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和治学方法等问题,值得探讨,所以写此短文作为回应。
付祥喜博士不同意我提出的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点,他的理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都体现了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而不是国家身份认同”。他特别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是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而非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海外华文文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那么,至少海外华文文学里面的现当代部分,应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其实,海外华文文学能不能划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原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是可以讨论的,我难以赞同的只是两点,一是付祥喜博士讨论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先别出心裁地对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做一番自己的界定,然后在他所界定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从而有别于他人基于这一概念的一般意义所做的研究。付文的关键问题,他自己也清楚,就是界定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的“中国”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而非国别的身份。事实真的如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中国文学部分,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当代文学史”)。这个国家标准,同时规定“世界文学”项下分为“俄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很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中国”是国家身份,它与“俄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国别文学对应,而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我搬出国家标准,并非找顶大帽子来压人,主要还是为了说明一个常识。按常识,现在高校中文专业所开设的基础课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国别意义上的文学史,它是与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国家的文学史相对应的。当然,“中国”的内涵在历史上有所不同,主要是它的版图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在不同的年代,由于版图不同,“中国”所包含的地域有很大的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学”就是指不同年代中国版图内的文学,“中国作家”是指不同年代中国版图内的作家。至于台湾文学,肯定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说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大陆方面说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样取得共识,有待于时间来解决。不过,两边说的“中国”显然都不是指民族身份上的,而是国别身份。如果一个作家加入了外国国籍,那就是华裔作家,作为华裔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我认为写入国别文学史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不妥。
当然,要写一部民族身份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文学史,也未尝不可;现在还有人试图写新汉语文学史——把所有用汉语写的文学作品都收进来。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大家取得共识的国别文学史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硬生生地要来说一番这个文学史是族别意义上的,这就难以对话,没有讨论的可能性。
我难以赞同付祥喜博士文章的第二点,就是治学态度问题。我认为他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学态度是不够严谨的。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意向,没仔细看别人的文章,先入为主地想当然了,比如他在文章的第二节开头写道:“陈国恩教授之所以担心,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主要因为他以国家身份认同作为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依据。”我什么时候“以国家身份认同作为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依据”了?我是用国家身份认同来界定中国文学,而且正因为以国家身份认同的标准无法凸显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海外华文文学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因而才认为要超越国别身份认同的观点,提出一个“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来加以指称。所谓“海外华文文学”,其实就是放弃了国别标准,只看重其“华文”的形式(形式中也包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因素),凡是用华文写的(一般是华人所写),就可进入“海外华文文学”。付祥喜博士费了很大力气,意在提出不同见解,绕回来却其实是要强调“以华文作为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依据也是必要的”——这不正是我的意思吗?而且其实也是学术界的一般意见。我的意见是,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要强化其独特性。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除外的所有用华文书写的文学的总称,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而不应把它当作中国现代文学来研究。不过,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一些悖论,比如说是“华文文学”,却不包含华文文学的主体——中国大陆的文学,用了一个“海外”来限定,所以一些学者后来提出了“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意谓凡是用汉语写的新文学,不管中国国内或者国外,均包括在内。“汉语新文学”的概念避免了“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悖论,所指非常明确,并且也是有效的,但它在目前显然没有成为大学中文专业的基础课,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付祥喜博士的文章可以讨论的地方还在于,如果像他说的,“大部分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写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那么“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就基本失去存在的必要了。这一概念,本来就是为了超越国别文学史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好处理“中国”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困难而提出的,现在既然海外华文文学的大部分都可以写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能写入的仅仅是非华人用华文写作的作品,那还要这个概念做什么?
至于说海外华文文学的根仍在“中国”,这毫无问题,原是常识,华文本身已经决定了华文文学与“中国”的深刻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不会妨碍一些国家的华文文学早已开始了它的独立发展的历程。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的联系仅仅是文化上的,而且即使是文化上的,也不能排除我在一些文章中曾经强调过的,一部分海外华文作家不是想叶落归根,而是有一种由民族身份认同的困境所诱导的“斩草除根”的情结。
有意思的是,付祥喜博士在文章中还写了下面一段话:

说实话,我对这样很不严肃的强加于人的逻辑感到十分讶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作家的创作“不属于台港文学”了?这些作家是台湾作家和香港作家,当然也是中国作家,他们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他们如果加入了外国籍,按我的理解,就不便归入中国文学史了——但应该写到他们加入外国籍为止。当然,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我的意见也只是个人观点。
不能不说,付祥喜博士的这篇文章,立论是比较武断的,一些推论也相当主观化。名为商榷,实为自我言说,难以构成真正的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处于调整时期,一些学者表现出了无节制扩张学科边界的冲动,而且有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倾向,试图把越来越多的内容整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来,以为这样才显得这个学科重要,我认为这至少缺一点对海外华裔作家的主体地位的尊重。这意思我在《从“传播”到交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模式的选择》等文章中说过。当然,这还是属于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那些加入了外国籍而主要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而且在中国大陆发生影响的作家,像严歌苓,怎么处理,能不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确需要斟酌。照我现在的看法,一部文学史不能持双重标准——既然是国别文学史,外国籍的作家就不应进入,哪怕她或他是华人,她或他的作品是在中国发表,而且影响很大,就像高行健,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都写到他加入法国籍为止,而没有把他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灵山》算做是中国文学——这样处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坚持国际准则。而中国作家在国外用英语、日语、法语等写作的作品则可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比如林语堂的许多作品,包括他的《苏东坡传》,后来被译成中文,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部力作来研究。鲁迅、郁达夫等人也用日语写了一些作品,它们都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当然,严歌苓等作家特殊一些,或许美国学者有兴趣把她(他)们的小说作为其非本国母语写作的美国文学作品来研究?而且这样的作家多了,美国的学者或者更有理由把它作为一种国别文学史意义上的文学传播现象来考察?我们换位思考,就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他们这样做,他们做的仅仅是在美国文学史的框架中对美国公民的华语书写进行研究罢了。如果美国的学者没有这样的兴趣,也不要紧,严歌苓的作品绝对是会写进文学史的,一个现成的办法,就是写进海外华文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正好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仍然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有待以后深入的探讨。范伯群先生曾说,写文学史就是建祠堂,谁能够进“祠堂”是有讲究的。我想补充一句,进这“祠堂”的标准虽有定规,也有例外,怎么处理,并非易事,所以存在分歧是很正常的。我想,只要不是曲解别人的意思,而且保持对话时所用概念的同一性,任何方式的讨论都有益,我随时准备接受合理的意见。
①陈国恩:《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②陈国恩:《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J3 2009年第6期转载。
③陈国恩:《从“传播”到交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模式的选择》,《华文文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