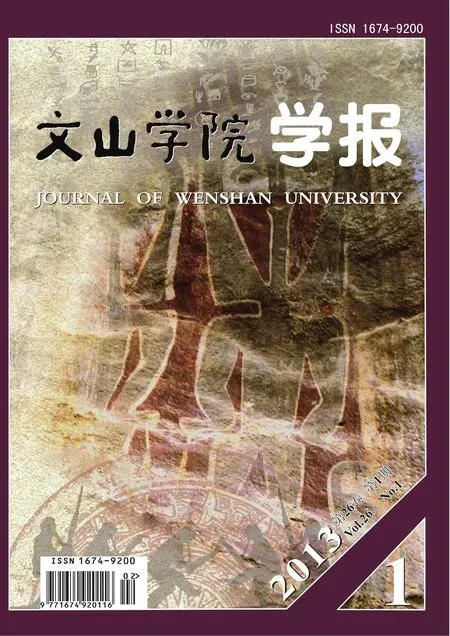“亲近自然”与“崇拜自然”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之比较
许辉
(文山学院 中文系,云南 文山 663000)
“亲近自然”与“崇拜自然”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观之比较
许辉
(文山学院 中文系,云南 文山 663000)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一个代表中国晋宋之际田园诗的顶峰,一个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丰碑,两位诗人都崇尚自然,返回到了自然之中。由于他们的生活背景和中西文化的不同以及所受的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使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两人诗中的自然有着较大的差异。陶渊明诗中的“自然”具有一种亲和力,而华兹华斯诗中的自然却因具有神性而让人崇拜。
陶渊明;华兹华斯;自然观;玄学;泛神论
陶渊明和华兹华斯,一个代表中国晋宋之际田园诗的顶峰,一个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丰碑,两位诗人都崇尚自然,他们都以自然作为主要的诗歌素材,在其中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可以说,自然是两位诗人共同的主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背景和中西文化的不同以及所受的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使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中的自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这源于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对自然的不同理解。
一、陶渊明:亲近自然
在魏晋以前,《诗经》中已出现描写自然景物的句子,但大多是作为比和兴的表现手法出现。这种情况在屈原的作品中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屈原通过对所见各种景色的描写,抒发了内心的复杂情感,增加了诗歌的浓度和情志色彩;到了汉赋中,自然山水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并未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表现。直到陶渊明所生活的汉末魏晋六朝,虽“是中国政治上最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P208),自然才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写进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才出现了最具民族特色的山水田园诗。可以说,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人们对外发现了自然,对内发现了自己,正如宗白华所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1](P208)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庄哲学被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崇尚自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陶渊明就是其中的典范。
陶渊明的诗文中共有4处使用了“自然”一词:(1)“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2)“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3)“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4)“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2](P563)
《形影神序》的主旨在于反对违反自然的宗教迷信。序言中所言的“自然”即指当时老庄玄学的自然观。《归园田居》中的“自然”除了有顺应天然的含义外,更有跳出“樊笼”后获得自由的意味。《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所赋,其中的“自然”主要指淳朴本然,无欲无为的人格。《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渐近自然”说明朴素本真的“自然”状态是美的极致。
从以上可以看出,陶诗文中的“自然”概念源自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指的是一种生活状态,非外人和外力所为,本来如此,自然而然,以达到自由的人生境界。但陶诗文中的“自然”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众所周知,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而体现“人的觉醒”的新哲学就是玄学。玄学以崇尚“三玄”:《老子》、《庄子》、《周易》而得名,以何晏、王弼、嵇康、向秀、郭象等为代表人物。“玄学”又称新道家。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提出“名教即自然”,三人对名教或褒或贬,各有不同,而其共同点就在于对“自然”的充分肯定,即基于自然观念的超尘脱俗。陶渊明生活在玄学流行的时代,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陶渊明融合玄学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独特的自然观念。陈寅格谓之“新自然说”,以区别旧自然说;又谓“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顺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分,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3](P563)。然而,陶渊明“自然”观念,除包含委运顺化人生态度之外,又具有重视性情或精神之特质,即“自然”观念更多从自身性情出发,认为人之本性应得到舒展散发,而不应加以羁靡束缚。此可称之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3](P563-564)即陶渊明将本然的心性融入自然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状态,他虽有“猛志固长存”这一兼济天下之大志,但在看到官场的阴暗后,毅然辞官归隐田园,走向了“独善其身”之路。虽然田园生活充满着更多的艰辛,但寻求灵魂的自由已超越于所谓的功名之上,一点点身体的疲惫又算得了什么,即使饿到在街上行乞也仍坚持自己的操守,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韧性。在种种的矛盾与困惑中,陶渊明仍执著自己的理想,真正闻到了泥土的芳香,达到了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完美融合,完成了老庄思想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陶渊明既继承了嵇康等人的伦理观和审美观,又去掉了他们的放诞色彩。他以躬耕农野、从事劳作的生活实践,来开掘、品嚼自然朴素的人生乐趣,熔铸自己的人格理想”[4](P342)。因此,比起魏晋任何一个名士,陶渊明都更朴实、更从容、更彻底地实践了他崇尚自然的主张。他的整个人生和创作都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由于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本性,在面对自然时,就有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超然。正是这样一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使他做到“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5](P131),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6](P205)。
在陶渊明的诗作中,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自然及乡居生活怀有始终如一的爱,自然是如此的具有亲和力。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隐隐约约的村庄,那依恋缠绵的袅袅炊烟及从深巷中桑树间传来的鸡鸣狗吠,都洋溢着素朴与和谐,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又如“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等等都是如此的亲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透露出的不仅是田园的诗意,更传达出陶渊明对待自然就像朋友一样,从不将其视为一种超然、冷漠的对象,而是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因此,自然在他心中是如此的亲切。
二、华兹华斯:崇拜自然
西方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最早可追溯到《伊里亚特》《奥德赛》中,但山水等自然景物在古代西方一直被视为异己力量。到了黑暗的中世纪,自然成了上帝精神的体现,沉溺于山水会影响人的灵魂的拯救。可以说,在17世纪以前,大自然的神秘、丑陋和暴戾在西方文化中被认可的倾向是比较大的。[7](P47)直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卢梭提出了“返回自然”的思想及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自然才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创作的视野。华兹华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富有激情地歌颂自然,正是对自然的描写,奠定了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华兹华斯之所以走向自然,不仅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当时的现状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受到了卢梭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因此,是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华兹华斯曾亲自到法国对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但是法国大革命的进程,特别是雅各宾党的专政,把他推向失望、痛苦的深渊,1795年10月他怀着一种恐惧和失望的心情回到了英国。而英国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迅猛发展并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时代。科学和理性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却未给人们的心灵留下栖居之地。华兹华斯对于资本主义异化文明深恶痛绝,因此,出于对政治的不满、对人性失落的厌倦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华兹华斯把目光转向和谐的大自然,选择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定居,潜心进行创作。他针对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提出了诗不仅要写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而且特别是要以田园生活作为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心中主要的热情找到了更好的土壤……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8](P335)。华兹华斯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幻想通过表现田园生活来唤起人类自然而纯真的情感,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慰藉。
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中,华兹华斯这样写道:
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你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是你让千形万象有了生命,/是你让他们生生不息地运转
朱光潜先生曾说“西方诗,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没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就没有歌德、华兹华斯和雪莱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和泛神主义……”[10](P112)泛神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文学与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泛神论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的流溢说,认为神的灵魂按由高到低的等级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泛神论更是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出现了斯宾诺莎这样的大哲学家。他认为,上帝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上帝之中,他是一切存在物的泉源。他还明确地否认上帝有人格和意识:上帝没有理智和感情,也没有意志。他不按照目的而行动,一切都遵循规律,必然地来自他的本性。[11](P343)因此,“神即自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直接影响到19世纪初期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从上面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华兹华斯深受泛神论的影响。
华兹华斯认为宇宙精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受宇宙精神的制约,又都是宇宙精神的体现,而“宇宙精神”就是上帝,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真、善、美,代表着崇高和庄严。相应的,自然界也是真、善、美、崇高和庄严的体现。因此,华兹华斯在《自然景物的影响》一诗中,直接把自然称作“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华兹华斯将上帝引入到所有存在物,将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世俗世界中来,使世俗世界充满了神性的光采,具有一种神圣、崇高的意味,从而表达了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崇拜之情。
泛神论还认为,上帝和世界是同一的。他在没有意识过着一种宇宙磁性生活的植物中显示他自己。他在动物中显示他自己;动物则在感性的梦幻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感到一种模糊的存在。但最出色地是他在人类中显示他自己。[12](P72)因此,上帝在植物、动物及人类之中显示自己的神性,这与泛神论在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表现不谋而合。
首先是神性在植物中的显现。如《岩石上的樱草》第1、2节:
有块岩石,它平凡的模样/不引过路人的注意;/可萤火虫却在那里挂起灯——/象星星有高也有低;/岩石上还有羞怯的樱草,/在邀来的春风里摇曳。/
打过多少次丑恶的战争,/多少个王国给推翻——/自从我当初发现那樱草丛,/并视之为我的财产;/它是自然之链的永恒环节,/是从九天之外下凡
诗人在第1节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平凡的岩石上长着极不起眼的樱草,在春风中独自摇曳,陪伴樱草的只有时隐时现的萤火虫,一切都显得如此凄清和灰暗,或许樱草花在岩石上寂寞地自开自落,又有谁注意过它的存在?接着第2节,却让我们感到,就是这样极普通的小草,诗人却将它视作自己的珍宝,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世事如何污浊,这种心中的爱仍没有改变,竟成为诗人心底的永恒。
在第4节写道:
天然的岩石则紧偎大地——/那样子虽象要倒下;/地球又守着它那片空间;/上帝把这一切筹划:/寂寞的草就这样开着花,/一年葬一次也不怕。[13](P334)
在这,樱草被诗人赋予了神性而不再是客观的自然,自然之物就在神光的普照中而拥有神性。樱草也因上帝的在场而有了这样的坚定:一年葬一次又何妨,即使寂寞也心甘情愿。
其次是神性在动物中的显现,如《鹿跳泉》:
白发苍苍的牧人,你说得有理;/你的信念跟我的差不了多少;/公鹿的横死,造化不会不在意,/她以神圣的悲悯表示了伤悼。
上帝寓居于周遭的天光云影,/寓居于处处树林的青枝绿叶;/他对他所爱护的无害的生灵/总是怀着深沉恳挚的关切。[9](P122-123)
在欧洲人的观念中,造化(即自然)为阴性,故用“她”;上帝为阳性,故用“他”。华兹华斯认为,上帝就在周遭的天光云影中,就在树林的青枝绿叶里,上帝与自然几乎合二为一。即使不受人类重视的公鹿的离去,上帝也万分悲痛。在这,华兹华斯将公鹿提升到了神灵境界,让人感受到神性的氛围。正如丹麦著名文学家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说:“基督教要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泛神论却要人们爱最卑微的动物。《鹿跳泉》无疑是华兹华斯所特有的对自然由衷虔敬的崇高证明”[9](P115)。
第三,神性在自然中的人身上显现。如《坎伯兰的老乞丐》:
上帝创造的万物,不管多低贱,/形象多卑下、野蛮,即使最讨厌、/最蠢的,都不会完全与善无缘——/任何形式的存在,都会同一种/善的精神的意向,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尽可放心,生来就有仰望/上苍之眼和不凡脸容的人们,/只要保得清白,再落魄也不会/沉沦到遭受鄙视的地步;只要/不冒犯上帝,就不会永遭驱逐;/不会象种子已经撒落的花枝/空剩下枯梗或穿破了的衣裳/一钱不值。[13](P12)
在这即使最低贱的乞丐都具有一种神性,也应获得一份人们对他的敬重,因为泛神论要人们爱最卑微的人物。这位老乞丐的受尊重,不是来自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来自于与上帝的联系。
三、结语
通过比较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我们发现他们虽然都崇尚自然,但对待自然的态度却不相同,这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及其所受哲学思想的影响相异所致。陶渊明受老庄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融合玄学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独特的自然观念,谓之新自然观,即将本然的心性融入自然之中,因此其自然观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华兹华斯望尘莫及的。在陶渊明的自然诗中,人与自然保持了和谐、亲密的关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因为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那样的亲和关系。[14](P165-166)置身于这一文化系统中的陶渊明,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所感受到的是人对自然的天然的亲近感。而华兹华兹由于受西方“天人相分”及泛神论“神即自然”思想的影响,将大自然视为无处不在的神,视为宇宙精神和智慧而加以歌颂,自然散发着神性的光采,对大自然充满着敬畏之情。正如马斯在《世界文学史话》中所说:“华兹华斯写过不可胜数的诗,其中许多是全然愚拙而不可卒读的,其中最优者则触着神性。他崇拜神和自然,且感到星和雏菊之间有巨大的统一存在。因而神或自然或星或雏菊有时控制了他那没有间断的笔,而将本身放进他的诗里,以作高贵的回报”[15](P363)。因此,与其说华兹华斯感受到了自然的亲切,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崇拜。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5]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陶渊明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苏文菁.华兹华斯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西方文艺理论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杨德豫.译.华兹华斯诗歌精选[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10]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1]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M].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3]黄杲炘.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5]马斯.世界文学史[M].香港:中流出版有限公司,1975.
Closing to Nature and Worshiping Nature: A Comparison of Tao Yuanming’s Outlook of Nature and Wordsworth’s Outlook of Nature
XU Hui
(Chinese Department,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Tao Yuanming and Wordsworth, one represents the pinnacle of idyllic poems and the other represents a monument of the 19th century English Romanticism. Both of them respect nature and return to nature.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living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philosophical outlooks, their outlooks of nature expressed in poems vary greatly. Tao Yuanming’s poems express a kind of affinity while Wordsworth’s poems worship divinity.
Tao Yuanming; Wordsworth; outlook of nature; metaphysics; pantheism
I207.227
: A
:1674-9200(2013)01-0072-04
(责任编辑 田景春)
2012 - 06 - 20
许 辉(1975 -),女,云南文山人,文山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