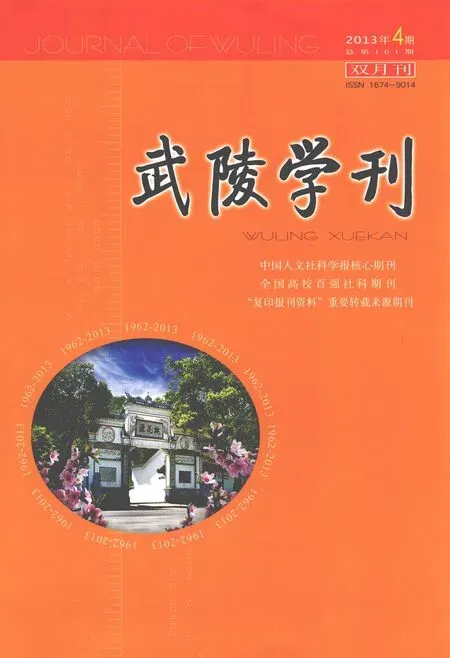明清山东新城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
沈 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明清新城王氏家族为山东地区的望族,二百年来“科甲蝉联不绝”[1]2,不仅在政治事功上卓有建树,对由明入清时期的诗学与文化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氏由元末默默无名的大户佣作起家,第六代族人在嘉靖年间达到家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人云“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2]。明亡清兴的激荡风云之后,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第八代族人创作成就斐然,在清初形成了“本朝文学,山左为盛”的鼎盛局面。
“家族本位”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心理基因。同中古以来多数的文化家族一样,新城王氏亦具备世代簪缨、家学相承、一门风雅的特点。王氏族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包含两重发展趋势:一是官宦世家向文学世家的过渡,逐渐建立起家族的文学传统,从而使族人成为兼具官员与文人特质的士大夫;二是文学影响力越出门户的范围,从一家扩散至一国。本文试图从王氏族人的生命历程与创作脉络中探寻家族文学构建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世系流变中传承与变革的过程,从而探寻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
一 王氏家族文学的准备期
文学能量的累积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中占据了漫长的时光。王氏始祖王贵于元末为避战乱从山东诸城迁至新城,一世祖贫无立锥之地,二世祖王伍始有积蓄,常常资助乡人,而三世祖王麟执教乡里,“始肇文脉”。嘉靖至万历年间,四世祖王重光创立家训。这一时期的王氏家族仍未展现出文学创作天赋,但物质、精神基础的储备尤其是家训的创立,对子孙的人格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家族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回忆了王重光家训的具体内容以及传播形式:“公(王重光)教子最严,家训云:所存者必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此条家训为子孙代代相传,直至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仍“刻石忠勤祠中,先祖方伯公督不肖兄弟,恒举此训,厅事屏壁间,亦皆书之”[3]108-113。
“读书”和“道义”二字,正是世代业儒的家族所秉持的核心要义,而仕宦是家族文学得以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凭借读书取仕,王重光一脉的后人陆续科举中第,甚至官居高位,从而为王氏家族的发展壮大疏通了道路;而持守道义在这一时期则更多地表现为在政治风波中步步为营。王士禛的祖父、第六世族人王象晋将“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记挂在心;各方正厅悬挂“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3]113;屏风之上则书“余家自高曾祖父已来,各方正厅皆置两素屏,一书心相三十六善,一书阳宅三十六祥,所以垂家训示子孙也”[4]170。这种小心谨慎的圆融之道使得王氏族人于明中叶门户纷纭之时,无一涉足党争,从而保证了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并未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攻讦。可见,在家族初步发展的阶段,王氏家族这一新入仕的族群在当时政坛的影响力仍很有限,而家族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还在积累期,前六代族人为家族的壮大兴盛努力争取时间和资源。族人的兴趣主要放在读经求仕上,在文学创作上投注的精力并不多,诗文创作多为自娱,且并不丰盛亦不突出,影响力并未超出一家的范围。
二 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初步建立
据《新城县志》的统计,王氏家族第六代族人创造了累世功名的顶点,共出了9位进士、3位举人、1位贡生,其中王象乾还做到兵部尚书、太子太师。王士禛《池北偶谈》论“门户”,王象晋拒绝成为亓诗教、韩浚的同党而被中伤罢官,而王象乾遭人忌恨,有小人作《东林同志录》,收录其族人籍贯。而“至从叔祖吏部象春,为东林闻人,而才浮于名,家法始一变矣”[3]140。为官的王象乾、王象晋有诗集传世,其他族人如王象艮、王象明也有诗名,钱谦益编纂的《列朝诗集小传》中,对王象春的刻画更是多为人们所引用,相比于前辈族人谨慎的处世态度,王象春跌宕使气的人格特征在初入官场之时就可以略窥一二。《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象春)万历庚戌,举进士第二人,与苕上韩求仲名相次也。季木(王象春字)每叹曰‘:奈何复有人压我!’其语颇为时所传。而求仲科场议大起,遂以季木为讦己,党人用壬子北试,移师攻季木,牵连谪外。稍迁南吏部考功郎。”[5]653
王象春在党人中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辟门庭的诗风。王象春与文天瑞齐名,并与冯琦、公鼐三人推尊古风,成为东林党山东籍十三士人中的代表人物[6]。另外,第六代族人中,王象艮、王象明与王象春的诗作被王士禛合著为《三公诗选》。《山左诗钞》中所评王象艮诗作“思止舂容淹雅,白真韦澹,自然神合”[7]2379,正如王士禛在《居易录》中所言的“诗名出考功(象春)下,然谨守唐人矩镬,不失尺寸”。王象明“才不逮考功,而与驰骤从之”[8]3946。王象春一辈族人宗唐的美学风尚为王氏家族所推崇,并延伸到后辈族人最初的创作倾向之中,无形间使家族文学的影响和熏陶愈发地强烈而深远。
从王象春而始,前辈远离党争、小心守成的传统被打破。“家法始变”是王氏文学传统中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在家族发展史上有着多重意义。从嘉靖至万历“门户纷纭之时,无一人濡足”的“家法之恭谨”,到“家法始一变”,意味着族人的态度偏离之前既定的保守轨道,开始陷入明后期政治斗争的漩涡。但“家法”之变不仅仅是政治态度的变化。从后辈的回忆录中可见,王士禛等对叔祖王象春影响下的“家法始变”并无怨怼,甚至常标榜王象春的“雅负性气,刚肠疾恶,扼腕抵掌,抗论士大夫邪正,党论一同,虽在郎署,咸指目之,以为能人党魁也”[5]653。这体现了族人对“名士”之风的认同与推崇,也寄望于以人格魅力进一步拓展家族的影响力。自此而始,家族路径转向带来的能量激发了族人的创作灵感和生命的多元可能,文学开始凸显其在维系家族特色中的显著地位。文学传统不仅体现为实体层面的诗文结集、活动场所、书库、家塾,更体现为创作的理念与审美取向,王氏族人构建起初步的家族文学传统。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第八代子孙为何屡屡忆及叔祖在家族文化中的贡献,又在其基础上构建自己的诗学理念和创作风格。因而,王氏族人的“家法”,不仅包括家族的从政观、道德观,也包括了文学观,而族人的诗歌创作开始成为一种稳定的日常活动、维系家族记忆与情感的文化空间,进而通过文学影响力巩固家族的社会地位。
王氏第七代族人在明清之际的杀戮与动乱中损失惨重。《静志居诗话》中记载:“新城王氏科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7]2899王与允自经殉主,遗手书一则,末世危音悲戚不忍卒听,钱谦益赞之为“遗音孤苦,孤桐玉律,吟龙戛石,梵猨噭月。浩歌悲啸,雷风交加。虫豸不蛰,象华其牙”[8]4760。而以遗老自居的王士禛祖父王象晋隐读林下,《年谱》云其“盛暑整衣冠危坐,读书不辍”,“诫子孙无矜门第,务力学为善”。临终遗自祭文一卷,云“:不敢丧心,不求满意,能甘淡泊,能忍闲气。九十年来于心无愧,可偕众而同游,可含笑而长逝。”[1]10二十余年教导子孙,使这一支脉成为王氏族人保存文脉、维持家法的重要力量。
三 王氏家族文学发展的鼎盛期
王氏家族在清初时局初定之后大放异彩,尤为显著的是王士禛在文坛上的建树,使文学在家族的再度振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王士禛为代表的兄弟三人取得了空前的创作成就,将家族文学推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清朝初年文化政策较为宽松,王士禛等诗人广交文友,悠游唱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灵感。王士禛的笔记中对顺治年间的交游有大量的记载:“未中进士,与海内闻人缟纻论交,交道始广”;与王象春的外孙、当时著名的遗民隐士徐夜亦过从甚密:“徐东痴高士隐居系水之东,蓬门昼掩,惟余兄弟时过之”[4]102。王氏族人少年成名,王士禛的“秋柳诗社”与王士禄的“晓社”汇集了当时一批优秀的文人,并与朱彝尊、汪琬等文坛大家往来频繁。“予少游京师,日与汪琬、刘体仁唱和,晨夕过从无间”[4]147。家族文学从保持与时代发展的大致同一,到引领文坛的风气,在山东、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可谓举世无双。
追寻王渔洋得志于诗坛的过程则可以看到,他在转益多师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第六代前辈族人文学创作的烙印。具有杰出文学才能的人对后辈族人的文学创作,往往提供了强大的示范作用;后辈对前人的追思与倾慕,对其美学倾向、诗学理想的继承与改进,成为家族文学传统构建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王氏家族文学传统于此成形。
(一)王象春对王士禛辈创作的影响
王士禛的《香祖笔记》、《渔洋诗话》、《分甘余话》等笔记著作,多次提及第六代族人,尤其是叔祖王象春。王象春一辈族人凭借独特的诗风和人格魅力,为子孙进入诗坛铺平了道路。众所周知,王士禛在诗坛一举成名,得益于钱谦益的奖挹提携,并许其接过诗坛盟主的大旗“,钱王代兴”使王士禛成为康熙一朝的文坛巨擘。钱谦益在给后辈王士禛的书信中,曾云“:倾闻门下雄骏绝出,整翮云霄,鸿裁艳词,衣被海内。才笔之士靡不捧盘执匜,愿拜下风。私心庆幸,以为大槐以后复产异人。”“新城门第,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禽息之精阴,庆在季木可知也。”[9]
“庆在季木可知”几字,便已道出钱谦益与王象春不凡的交情。钱谦益与王象春是同年同科进士,王象春免官后在济南大明湖畔南侧百花洲上购楼筑亭,“时钱谦益、钟惺等诗人均与之交往”[10],诗酒唱和,交游甚广。二人平生论诗文相契,季木更是被牧斋引为知己。但需要注意的是,二人诗歌中呈现出的美学风貌其实差异甚大。钱谦益如是评价其诗风:“(季木)尤以诗才自负,才气奔逸,时有齐气,抑扬坠抗,未中声律……季木如西域婆罗门教邪诗外道,自有门庭,终难皈依正法。”[5]653-654
何谓钱谦益所首肯的“正法”?钱谦益在顺治十四年写给王士禛的诗序中说道:“贻上(王士禛字)之诗,文繁理富,衔华佩实,感时之作,恻怆于杜陵;缘情之什,缠绵于义山。其谈艺四言曰典曰远曰谐曰则。”[11]544在褒奖王士禛创作合乎“典、远、谐、则”的同时,其实也是将杜甫、义山标榜为正面楷模。在诗序之后,他又在赠予王士禛的五古中声讨明“前七子”与竟陵派“:献吉才雄骜,学杜餔醴糟。仲默俊逸人,放言訾谢陶。考辞竟嘈讃,怀想归浮漂。”还抨击了严羽的“妙悟掠影响,指注阙厘毫”[11]765。王应奎对此段的解读是:
阮亭(王士禛号)为季木从孙。而季木之诗,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离此一派。林古度所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也。顾王、李两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堕入两家云雾,故以少陵、义山勖之。序末所谓用古学相劝勉者,此也。若认文繁理富、衔华佩实等语以为称赞阮亭,则失作者之微旨也。[12]
王应奎认为,钱谦益此言并非单纯褒奖,而是暗劝王士禛莫要步叔祖后尘,指陈其宗法王世贞与李攀龙之弊。关于这段话的解读仍存争议,孙之梅等学者首肯此说,蒋寅先生则认为其解读求之过深[13]7。王士禛早年宗唐,中岁宗宋的诗学理念之变化,与钱牧斋的影响不无关系,但由此我们亦可以看出,王士禛循着叔祖之径而学唐诗,并在交游与生命体验不断丰富之时对其进行改造。
王象春曾于明末拟古之风盛行之时,提出“禅诗”之论,其《公浮来小东园》诗序称诗中世界分为四等,“曰禅,曰儒,而益之曰侠。禅神道趣,儒痴而侠厉,禅为上,侠次之,道又次之,儒反居最下”。好友吕维祺更如是描摹其诗风与人格:“其人眉宇步骤欠伸笑焉,任取一景,任拈一题,任出一语,无在非诗无诗,不惊人死即自以为不适意,而人鲜有及者,则诗抑又奇矣。”[14]其所著《问山亭前后集》,诗作不下数千首,述说儒家传统济世情怀的怀古诗篇透露着“箕踞悲歌王季木,时敲石几激清音”的任侠使气,更有一股反常规思维的“邪气”纵横其中。如《题项王庙壁》一篇,可谓是“邪魔外道”的集中体现,风格想象之奇令人咂舌:
三章即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汉王真龙项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语,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矣鼠。
沈德潜评此诗“奇僻可俪谢皋”,而朱彝尊亦以为,“《题项王庙壁》一篇,比于谢参军《鸿门》作,更觉遒炼。亡友颖川刘考功公勈亟赏之,几于唾壶击缺,此非邪师外道之传也”[15]。
相比于这类咏史诗的奇崛,王象春所作竹枝词在众多济南竹枝词中影响更大。《问山亭前后集》(亦称《济南百咏》),收录了105首竹枝词,石城的朗月、雨后的山家、慈宁宫飘飞的不落夹、北庙的赛神会,在王象春的笔下以白描的手法一一呈现,历来被认为是济南竹枝词的上乘之作。如《打枣竿》一首:“打枣竿,光莹莹,岸上小儿赤身擎。去而复来无时停,终日剥啄不盈升。低枝已尽高枝熟,我竿根无三尺六。”明快脱俗的竹枝词、乐府诗与慷慨使气的怀古咏怀诗,呈现出王象春“重开诗世界,一洗俗肝肠”的通脱任放与鲜明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王士禛曾多次征引王象春的竹枝词,并认为竹枝词是“泛咏风土”之作,每到一地辄创作一首竹枝词,曾作《江阳竹枝词》、《西陵竹枝词》、《广州竹枝词》、《东粤竹枝词》等共50首。如:
青青桑叶映回塘,三月红蚕欲暖房。
相约明朝南陌去,背人先祭马头娘。[16]
与王象春相似的是,王士禛善于捕捉眼前之景入诗,“任取一景,任拈一题,任出一语”,以寥寥数笔勾画意境,颇得禅诗之趣。《香祖笔记》卷三云:“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如杨廉夫《西湖竹枝》之类。前人亦有一二专咏竹者,殊无意致。”[4]57可见其善于观察,精于选材,有意从民间风土中汲取诗歌创作的灵感。
相比于王象春《打枣竿》等诗作,王士禛的诗歌脱去了几分源于民歌原汁原味的俚俗,多了几许词藻修饰和清丽典雅。清初宋诗诗风流布,弊端渐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言清初“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而王士禛从叔祖的“禅、侠、道、儒”四境中,拈出“禅”一境加以发扬,又补之以钱牧斋的“典、远、谐、则”,滤去了“侠”风之奇异,于是“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二)一门酬唱的相互砥砺
王士禛一辈族人在少时接受了严格的家教与诗文训练。《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多次提及幼时长辈的爱护与督促:
山人兄弟每自家塾归,孙夫人从牕闻履声,辄呼而问之:‘儿辈今日读何书?为文章当祖父意否?’命列坐于侧,予之酒食。或读书墅中,夜分不归,则遣小婢赐卮酒饼饵,慰劳之,率为常。兄弟四人每会食,辄谈艺以娱母,夫人为之解颜。[1]9
王士禛与其长兄王士禄科举中第获得祖父珍藏的文物一事,亦广泛地见诸王士禛的传记、墓志铭等材料。“方伯公旧藏刑太仆侗《兰亭序》、《白鹦鹉赋》二卷,深所宝惜。尝谓诸孙:‘有登贤书者,当以为赐。’戊子长兄报捷,得兰亭卷。至是,山人得白鹦鹉卷。”[1]10可见,祖父象晋的悠游林下、父亲与赦的以教导子孙为业、母亲的关爱呵护为王氏兄弟幼年才学的积累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也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文学培养形式。“千古是非归啸傲,一门酬唱盛交游。”亲族之间的唱和寓教化于日常,在一种稳定的熏陶与激励机制中建立起了诗文创作的共同场域。
同辈人之间的相互勉励与竞争则为提高诗文创作质量提供了重要的辅助力量。王士禄、王士祜、王士禛三兄弟时称“三王”。王士禄“其文去雕饰,诗尤闲澹幽肆”;王士祜“其诗长于情韵,在吴兴与宋琬等游白雀寺,赋五言诗颇清绝,人比之孟浩然‘微云河汉’”[17]。只因王士禄仕途坎坷,并且早逝,王士祜早卒,未能如其弟王士禛一般,在政坛、诗坛上有长时间的耕耘与积累,故声名不显。而王士禛与王士禄友爱最甚,二人少时促膝读书,士禄见士祯诗“甚喜,取刘顷阳先生所编《唐诗宿》中王、孟、常建、王昌龄、刘眘虚、韦应物、柳宗元数家诗,使手钞之。十五岁有诗一卷,曰《落笺堂初稿》,兄序而刻之”[8]3760。
在古典诗歌美学漫长的“意境”发展过程中,王士禛总结了前人创作的得失,历经宗唐、宗宋又复宗唐之“三变”,终而发展出“神韵说”,成为“意境”一线的集大成者,和初学诗时伯兄意趣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王士禛兄弟成年之后携手同游,诗酒唱和之作甚多,相互砥砺,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篇。王士禛多次动情地回忆道,“四十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文章经术,兄道兼师”。即便在王士禄下世之后,王士禛忆及当年情形,常常不胜悲慨,恍若隔世,多有怀念之作,并编有《王考功年谱》,以遂先兄生前所愿。
王士禛兄弟生前嗜书、买书,大量藏书,则予以家族文学传统雄厚的物质支持。《年谱》中记载“:王氏至太仆、司徒二公发祥,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山人兄弟宦游南北,次第收辑。康熙乙巳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箧。及官都下三十年,俸钱所入,悉以购书。”[1]54终而建成《池北书库》,藏书颇丰。
王士禛还整理了多部先人遗稿,避免了家族文献的遗失,为家族文学传统的延续作出了极大贡献。王士禛为伯兄士禄编纂《王考功年谱》、《考功集》四卷;辑考功诗因撰平生师友诗为《感旧集》;与西樵先生选士祜诗为《涛音集》,《古钵山人遗集》;并将叔祖象春、象艮、象明诗选编为《三公诗选》。在《分甘余话》中,他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先人的奏议、著述、诗文集,略记其目,以示后人,甚至曾经试图将先人的所有著录“录其简要,合为一编,藏之家塾。”遗憾的是,渔洋一生“奔走四方,卒卒未暇。今老矣,未必能终践此志,聊志其目,存之家乘”[8]4997。终而未能完成这一心愿。
四 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衰落
遗憾的是,清初“三王”耀眼的光芒之后,王氏家族的文学传统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家族文学传统被突如其来的时代风潮所压制,不复有往日的光彩。王氏族人文脉的衰微可以从几个迹象中得到证明。
王氏子孙在科场上大多不如意。王士禛长子启涑为荏平县教谕候补知县;启浑早卒;启汸官至唐山知县,候补知州;启汧岁贡生,候选教谕。而第八代族人的其他子嗣,除王启沃与王启潭各获得文武进士的科名,其余大多为同知、候选知县。第十代族人之后,王氏后世仍科甲蝉联,官缨不绝,并有许多未仕举人和贡生,虽然族人中博取功名和为官的并不在少数,但相比于前辈显赫的政治地位,在事功上并没有突出的代表性人物出现。科场上的成就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家族发展的整体态势,但在与科举制度紧密捆绑的专制社会中,仕宦上的逐渐没落毕竟是一个仕宦起家的大家族衰落的表征之一。王氏后人不乏有诗文传世者,要取得与王士禛相匹的文学成就固然是极难的,但的确没有出现能够接续前人传统、有自己独特风格,并在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家族文学接班人。
家势的衰微还表现在池北书库的遭遇上。王士禛所建的池北书库藏书在长子启涑死后迅速地散失殆尽。“渔洋门人黄叔琳驰书询问渔洋遗著及藏书情况,启汸、启汧答道:‘先君平日藏书,自弃世后不思后析。因先长兄一病五年,不幸于丁未下世,后始查点,三分收藏。孰知半饱鼠蠹,半坏积霖,而乘间攫去者亦复不少。及经查检,已多残缺,致使先人手泽尽付东流,可胜浩叹!’”[13]164-165由此可见,启涑是王士禛所遗留的精神财产的唯一守护人,而其诸子不能读父书。时人因之惋惜渔洋毕生心力付之流水。
在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与衰落过程中,家族成员的入仕是家族文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相对稳定的家族文学传统的建立,尤其是诗文创作理念的传承与嬗变,则成为家学中的核心部分,带动起一代甚至几代族人经久不衰的创作热忱。同时,家族作为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结构单位,其生命形态、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为时代风潮所左右。王启涑之后,王氏族人的史迹渐隐,但同时期、同地区的世家大族如曲阜孔氏、栖霞牟氏能够提供旁证。乾嘉以来,山东地区是反清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捻军起义、天理教起义及义和团运动中,齐鲁家族尽数历劫,甚至遭到灭顶之灾。
新城王氏家族文学只是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世家大族中的个案,但因其跨越明清两朝,拥有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可以由此看到家族文学发展中的起承转合与文学史之间的对接。家族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正对应着明清文学史从理学控制下的台阁文学转向心学影响下的诗文创新,至清初诗坛的再度繁盛,最终步入乾嘉万马齐喑的流变过程。
[1]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黄景进.王渔洋诗论之研究[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4.
[3]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王士禛.香祖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张永刚.大雅久不作,古风起三齐[J].德州学院学报,2009(2):9-12.
[7]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王士禛.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9]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75-84.
[10]李伯齐.山东文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3:289.
[11]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王应奎.柳南续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8-179.
[13]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转引自黄金元.明清之际济南府望族与诗歌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113-114.
[15]朱彝尊.明诗综[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81.
[16]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7.
[17]赵尔巽.清史稿·卷 484[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