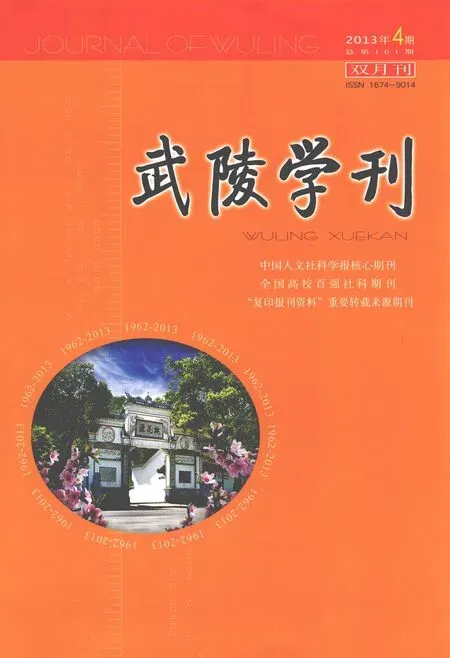审美人类学视野中侗族“哆耶舞”的文化解读
熊晓辉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审美人类学视野中侗族“哆耶舞”的文化解读
熊晓辉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哆耶舞”是侗族人最喜爱的一种自娱性的集体式舞蹈,具有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特征,显示了侗族文化的神秘性与娱乐性。侗族“哆耶舞”在形态、结构、音乐、表演及生态生成等方面的原始性与不成熟性,为侗族民间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哆耶舞”中所表现出的祭祀性、封闭性、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等文化特征,体现了丰富的侗族人文精神,蕴含着侗族人朴素的审美追求。生态与民俗的结合、审美与环境的结合、文化与自然的结合,构成了侗族“哆耶舞”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侗族;“哆耶舞”;文化;文化生态;审美人类学
“哆耶舞”流行于湘黔交界的侗族地区,是一种群众自娱性的舞蹈。“哆”是侗语,译成汉语是“唱”、“舞”的意思;“耶”也是侗语,指的是边唱边舞的合唱歌曲。每逢春节期间,侗族人都有“月耶”的习俗,他们走家串户,表示团聚友好。在表演“哆耶舞”的过程中,人们举行祭祀祖母的仪式,这一古老的祭祀仪式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至今仍鲜活地存在于侗族民间。笔者从审美人类学视角出发,将湘黔桂边邻侗族人生活地区作为调查区域,对“哆耶舞”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同时对“哆耶舞”的文化生态变迁、审美特征、历史反思及当代发展进行了探讨。
一侗族“哆耶舞”的文化解读
侗族有人口290多万,主要分布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边邻地区,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的文化、经济较为落后。侗族人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把各种超自然现象视为不可冒犯的神灵,认为祖先之魂及鬼、怪、精灵对人的生命与成长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侗族的舞蹈再现了侗族先民生活与生产过程,表达了侗族先民们的原始艺术思维。侗族的“哆耶舞”是侗族原生态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侗族文化生态的原始胎记。侗族人一直过着封闭的族群原始生活,称自己为“宁更”,也就是遮掩、隐匿的“峒人”[1]。到了明朝末年,汉族与侗族开始了文化、经济交流,明朝统治者也向侗族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征蛮”和“平蛮”战争,大量汉族军屯户、民屯户、商人、流民迁移而来,使得侗族文化受到了很大影响。此后,侗族人尊儒崇教,汉化严重。但是,侗族的民间艺术仍保留了原样,它们承接了本民族的古老原始文化。“哆耶舞”作为表达侗族原生民俗的艺术形式,是侗族人民生活、宗教祭祀、农耕文化及民族特性的历史沉淀,它生动地反映了侗族历史文化的变迁。
(一)侗族“哆耶舞”的表现形式
侗族“哆耶舞”是一种集体舞蹈形式,舞步简单,不受场地条件限制,无论屋内或场外,都可以跳。春节来临,人们相互作客,为了表示友好,青年人聚在一起,手拉着手,围成圆圈,边唱边跳;再者,是谁家有喜事,为了祝贺也跳“哆耶舞”,但跳舞的男女双方不能同姓,可同班辈;侗族人举办酒宴,在酒席上老年人为了助兴,也跳“哆耶舞”。老人跳的“哆耶舞”带有说教性,人们称其为“正耶”;跳“哆耶舞”也是人们祭祀的一种形式,如果在祭祀祖先(尤其是祖母)时跳“哆耶舞”,人们称其为“耶哺”。有时演唱的内容是男女爱情,侗族人称其为“爱情耶”,每当跳唱到深情之处,舞者步伐会变得缓慢、柔情。如这首流传于湖南侗族地区的《爱情耶》(歌词大意):“唱起进堂唱,进堂唱,他们不来我们来啊,他们不来我们跳。同家二兄发我我们了。不怕羞不怕丑,进堂唱,男女唱歌结姻缘。唱起来,保后代,保后代呀才唱完。”从这首《爱情耶》中可以看出,侗族人希望通过歌唱结社来获得爱情,他们希望神灵保佑族群平安、五谷丰登。
蹲跺步是“哆耶舞”的主要舞步,表演者上身挺直,身体随着脚跺地,左右摇摆。有进三步停一步、进三步退两步、一进一退步三种步法。跳“哆耶舞”时,人们以呼号伴唱为节,以增加动作的节奏感,起到渲染气氛和抒发、交流感情的作用。呼号伴唱速度越快,动作越激烈,情绪越热火。跺脚也随着节奏起伏,带有“打板”、“叠拍”的风格。
(二)侗族“哆耶舞”的社会功能
在表演“哆耶舞”时,人们载歌载舞,主要是歌颂美好生活和赞美大自然,具有自娱自乐和宗教信仰的功能。“哆耶舞”内容,有关于天文地理、神话历史的,如《祖源歌》、《忆祖歌》、《迁徙歌》等;有关于山水草木、鸟兽鱼虫、日常生活、生产知识的,也有即兴填词的。
1.“哆耶舞”的宗教信仰功能。同其他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一样,侗族人对自然力和自然物感到惊奇与畏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认为天地间的一切都有鬼神主宰,有着多神信仰的习俗。侗族人把神分为保护神和邪神两大类,把祖先、土地神、山神、水神、寨神、郎家神、外家神等看作是保护神,把瘟神、豆娘、火殃、邪神、鬼、怪、妖等看作邪神[2]。在“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在固定的日子里人们举行敬祭仪式。“哆耶舞”是人们祭祀活动的产物,最初主要是为了愉悦祖灵和祖先,后来,它逐渐成了人们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侗族原始宗教极为兴盛,宗教职业者“鬼师”既掌握神权又掌握基础政权,主持着善神恶鬼的祭祀,他们利用宗教祭祀把本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下来,同时也成了侗族舞蹈的传承人。“哆耶舞”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虽然已向娱乐或娱人发展,但其根源都是以祭祀为目的的。侗族地区流行的是原始宗教的多种信仰,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汉族封建文化对其的影响较大,不少地方信奉“萨虽”、“飞天大王”等本民族神祗的同时,也信奉五昌、南岳、文昌、关圣等神。宗教活动的盛行决定了以祭祀为背景的舞蹈的盛行,舞蹈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为宗教服务。“哆耶舞”在宗教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其才得以流传并发展至今。
侗族的“哆耶舞”与宗教祭祀有关的有《进堂歌》、《转堂歌》、《散堂歌》及《敬祖歌》、《忆祖歌》、《迁徙歌》等。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汉族的许多神祇信仰被侗族吸收,如灶神、土地神、五谷神等,也成为侗族人普遍信仰的对象。
2.“哆耶舞”的娱乐功能。一般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中,人们抒发自己情感、表达心中感受、娱乐自己所跳的舞蹈,称为自娱性的舞蹈。“哆耶舞”及侗族青年聚会所跳的舞就有自娱的性质。据《靖州志》(清光绪版)记载,明朝末年,一位住在靖州青云山庵中的禅师侯大错曾有诗云:“投足歌呼效葛天,三时耕鑿古黄年,社鼓鸣豚迎寨老,家家余得杖头钱。”[3]由此可见,侗族人对节日欢庆的期盼及其歌之舞之的喜悦情绪。在侗族聚居区,一般重大活动都在鼓楼里进行。每当夜幕降临,歌班纷纷进入鼓楼,在专设的长凳上面对面坐着,等对唱开始时,由主队唱迎客的歌。当客人近入寨门时,主人以锣鼓迎接,年轻人头插金鸡尾,身穿鸡毛衣,吹起芦笙,跳起“哆耶舞”。“哆耶舞”不仅仅为抒发自己情感而跳,也希望让旁人产生共鸣,让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得到他人认可。“哆耶舞”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在娱人的同时传递着民族文化。
(三)侗族“哆耶舞”的文化生态环境
“哆耶舞”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传承着侗族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形成了某些特有的形式与文化认同。侗族人世代居住在湘黔交界的山区峡谷中,宋代史籍对他们就留有“洞蛮”的称呼,由于他们习惯于生活在山洞中,狩猎成为其主要的食物来源。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是产生“哆耶舞”的生活基础。“哆耶舞”产生并在当地扎根,而且成为了侗族人文化和心理的一部分,它与侗族人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文化生态是“哆耶舞”得以发展的环境与土壤,而“哆耶舞”本身则成为了民族文化生态的构成因子与表现形式。
1.行为文化。“哆耶舞”作为侗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载体,在一定的民俗环境中既是独特的又是开放的,它离不开人们的参与,在其传承过程中逐渐得到侗族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成的条件和背景,它包括人类活动与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影响下人类行为的表现方式。作为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哆耶舞”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它反映了侗族的宗教信仰和风土人情。在社交场合,“哆耶舞”成了一种交际工具。在表演过程中,因活动内容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活动形式和特点。载歌载舞是“哆耶舞”的重要特点,跳时由舞首者领唱,舞步与情绪随唱词而变化,唱到欣喜事儿,舞步干净利落,豪迈自得;唱到忧伤的事情,脚步变得缓慢、凝滞。“哆耶舞”是集体劳动的产物,是侗族人联合起来与自然抗争所产生的歌舞,又是用来组织劳动、鼓励劳动的手段之一[4]。“哆耶舞”的表演在动态中进行传承,特定的环境、气氛(也包括非节日的欢聚场面)激发着在场者都投入舞蹈的活动,热烈地演唱,使歌声与舞步融合在一起,男士身穿青色无领对襟上衣,下穿百褶裙,佩戴项链、耳环、手圈,脚穿绣花勾鞋,他们手拉手围成圆圈,合着音乐节拍,边跳边唱。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场面的氛围和表演者的舞蹈形象立刻深深地印入人们的脑海,这些心象会鼓动人们去模拟与再创造。
2.物质文化。侗族聚居于崇山峻岭之中,以及平坝、河溪旁边,主要经营农业生产,兼营林业。其居住地雨量充沛、气候温暖,侗族人民因此形成了与环境相适应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居住方式。侗族人狩猎,狩猎也是人们的食物来源,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与生产方式,是产生“哆耶舞”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汉文化的传播,侗族社区的物质文化日趋丰富,它为侗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受到感性欲望的驱使,人们的物质文化总是渗透着审美的因子,同时,再加上受社会礼仪及伦理性的规范、限制,取得感情欲望与理性规范的和谐统一,就成了物质生活审美层面的需求。侗族的音乐舞蹈文化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侗族就有本民族特色的歌舞形式,“哆耶舞”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歌舞。“哆耶舞”在从江、黎平、通道、三江等地比较流行,表演时,人数有时达百人之多。侗族人的物质生活以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哆耶舞”,充分表现了侗族人的文化素养和丰富多彩的审美特征。
3.制度文化。侗族人崇尚“万物有灵”,有着多神信仰的习俗,在其宗教信仰上仍然保留着原始文化遗风。由于长期与汉、苗、瑶等民族的交往,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其宗教信仰又融合了其它宗教成分,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制度文化。侗族人崇拜祖先,信仰鬼神,特别尊重“先母”,许多村寨都设有“先母坛”,“祖母神坛”、“先母祠”等。比如“哆耶舞”中的“踩堂对歌”就是追叙祖先功绩的歌舞。侗族的春节,除了祭神、祭祖、拜年、玩龙竹、耍狮子等项目外,最隆重的就算跳“哆耶”了,跳“哆耶舞”成为春耕大忙前的一次群众性的盛大集会。
在羁縻州时期,中央王朝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推行特殊的笼络统治方式。中央王朝在溪峒蛮地创建佛寺,兴办学校。据《黎平府志》记载,明洪武年间“拔军下屯,拔军下寨”,由江西调来三万军民进入侗族地区“下屯”、“下寨”,他们到那里后,受侗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当地人通婚,融入为当今侗族的一部分。对于边远地区的侗族人来说,文治教化及移民政策积极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在侗族社会中,很长一段时期,“哆耶舞”一直在社区传播,被看成是侗族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精神食粮,直到今天,许多侗族人都坚持认为是汉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的积极倡导促成了“哆耶舞”在侗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4.精神文化。“哆耶舞”这种艺术形式是侗族人集体创作的结晶,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并通过非物质的形式直接反映生活,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体现服务生活、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哆耶舞”涉及人们的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及民族性格等方方面面,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民间审美文化。侗族的文化艺术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侗族人酷爱歌舞,许多聚居区都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用侗族的俗语说:“饭菜养人体,歌舞养人心。”歌舞在侗族人民的生活中确实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劳动生产、社交活动中,还是在追求爱情、祭祀祖先的过程中,都善于通过本民族艺术形式来表达情感。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述了辰州、靖州侗族地区“农闲时,至一二百人为曹,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可见,芦笙舞在千年前就流行于侗族地区了。“哆耶舞”是侗族人边唱边跳的歌舞形式,虽然无乐器伴奏,但人们用歌唱曲调来统一步伐,以及变换队形。千百年来,侗族歌舞成为侗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侗族人精神文化的再现,其舞蹈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宗教观念和思维方式,它的总体精神体现了侗族民俗文化特征。
(四)侗族“哆耶舞”的文化特征
“哆耶舞”具有宗教、民俗与农耕文化特征,其舞蹈形式都是通过祭祀与民俗活动而得以表现,它的主题始终表现为祭祖、生产劳动及其农耕文明。在侗族社会组织中,其分工不太明显,几乎全体成员都是生产劳动的直接参与者,没有脱产的职业舞蹈家。“哆耶舞”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有着积极、乐观、向上的特点。
1.封闭性。侗族社会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主要生活在湘、黔、桂三省毗邻的山谷地带。侗族的村寨大都依山傍水,以种水稻、杂粮为主,山区多种糯稻,以“侗禾糯”为主食。山地的生活环境使得侗族舞蹈具有浓郁地农耕文化舞蹈特征。农耕民族热爱土地,期盼丰收,形成向往人与自然、人际之间和平相处的心态。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由于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利于本地艺术的保留。因此,侗族“哆耶舞”舒展大方、刚柔相济,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哆耶舞”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美的艺术魅力。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侗族山寨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侗族人一直过着原始简朴的耕作生活,保留着落后、封闭的意识形态,落后与封闭无形中保存了侗族文化发展的相对稳定,使侗族文化的因子较少变异。“哆耶舞”在解放前是侗族山寨与山寨之间人们交往的一种作客习俗,每逢节日与庆典时,山寨之间相互交往,人们聚在一起,手拉着手,跳起欢快的集体舞蹈。随着时间的推移,“哆耶舞”成了侗族人最喜爱的歌舞形式,因为它既朴素平实,又很粗糙原始,简单的动作、紧凑的节奏,歌舞相溶的表演,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美的艺术享受。“哆耶舞”是地道的民间艺术,是劳动人民审美精神的体现。从审美角度观察,“哆耶舞”这种边歌边舞的演唱形式和活动方式,应该是侗族艺术最古老的艺术源头。由于“哆耶舞”流行地区相对闭塞,这种民间艺术被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可见,侗族文化传承是有着自己的运行方式的,最主要还是看能不能满足侗族人日常生活的文化需求。像“哆耶舞”这样的民族文化载体,无论经历怎样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它始终保持着侗族传统文化的专属性,吸纳其它文化的因子,不断传承与更新发展。
2.群众性。“哆耶舞”作为侗族的一种民间艺术,它是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又在群众中直接传授和传播。“哆耶舞”在侗族社区最为普及,它不受条件限制,无论屋内屋外,场坪山地,人多人少,都能合节起舞。“哆耶舞”这一古老的歌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少内容往往与本民族文化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观赏性。后来,经人们整理加工,成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艺术,其独特的舞蹈韵味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因此,群众乐于参加,显示了它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特征。“哆耶舞”在娱人的同时传递着民族文化,又因为步伐简单,动作易学,表演时便于和谐一致,所以广泛流传。“哆耶舞”在侗族地区的普及率是相当高的,整个传播区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跳“哆耶舞”。如今,在湖南靖州县的许多侗族山寨,还建有鼓楼,一般每逢重大节日活动,人们便成群结队地来到鼓楼,姑娘全身银装,手拿侗帕,小伙子吹起芦笙,跳起“哆耶舞”,参与跳“哆耶舞”的人数可达数百人之多,气氛十分热烈。
3.传承性。“哆耶舞”作为侗族传统的民间舞蹈形式,有其独特的表演程式,其变化也是相当缓慢的,它保存了许多侗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形象特征,积淀了侗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因素。“哆耶舞”作为侗族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载体,它和人们传统观念、民俗活动是紧密结合的,世代相传,不断发展。“哆耶舞”流行于民间,是群众根据自己的集体生活创作的,反映了群众的生活习俗与审美情趣,所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这种自娱自乐性的舞蹈从古流传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的民族传统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侗族人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和感情的来源,与侗族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历史传说和宗教信仰及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哆耶舞”有其顽强的传承性,即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它产生于生产劳动和祭神活动中,舞蹈以粗犷、豪放为美。“哆耶舞”由于与侗族某些特点的习俗及人们日常生活有联系,故而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4.变异性。“哆耶舞”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会融入一些新形式或内容而发生一定的变化,由于传承载体的个性化,变异就成了一种自然和必然的事,也成为自身得以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今,在民族舞蹈的发展方向上,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影响和渗透。由于现代社会的科技文化日新月异,以及其他种类的文化影响的渗入,传统的民间舞蹈文化朝着多层面、高知识、广交流的方向发展,从而游离于传统民间舞蹈特征以外,更多地表现出“变异”的特点[5]。在侗族社会,“哆耶舞”只是作为一种习俗、一种仪式形式而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哆耶舞”经过不断提炼与美化之后,不再是原始的单纯模拟,而是注入了人的感情,这也体现了舞蹈的美之所在。
在民间舞蹈的发展过程中,侗族“哆耶舞”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含义在不断变化,因为文化是一种变体,它随着社会的变革,扩充着新的内容。侗族人手拉着手踏歌而跳的“哆耶舞”流传了千百年之久,受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其功能不同、作用不同、载体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在侗族节日中,以“哆耶”形式纵情欢歌,宣泄情感,体现集体意志,今天,人们从中还能摸触到侗族融合变迁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民间舞蹈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民间舞蹈逐渐转换成为新的形式,有些民间舞蹈虽然因民族的融合或受另一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消亡,但它的内在精神却在新的民族或另一种民间舞蹈中保留了下来。
二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哆耶舞”
“哆耶舞”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具有宗教文化神圣性、原始舞蹈神秘性和现代舞蹈娱乐审美性等特征,称得上是一种文化的、神性的和审美的舞蹈。舞蹈审美人类学提供了不同于舞蹈审美研究的另一种研究视野,这种研究,能更好地从生态与民俗、审美与环境、文化与自然的联系中考察“哆耶舞”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
(一)生态与民俗
文化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相互交织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整合,构成了人类各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学者们认为,生态环境是形成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重要条件,是构成一个区域或一个民族美学思想观念特性的基础[6]。当我们在考察“哆耶舞”的发展历程与传承谱系时,发现文化生态是其得以保存的首要条件。“哆耶舞”的原始形态是侗族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祭祀、狩猎的群舞一样,是先民们在进行原始宗教活动和狩猎之前的操练或活动之后的表演性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为下一次活动作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哆耶舞”的原始形态首先是作为文化的舞蹈,随后才是娱人的舞蹈。可见,“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的发生,远远早于其作为人类审美的对象”[7]。自然生态当然是文化生态的基础,生态及生态美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可以视为审美文化生态的一个基础层面,我们看重的就是人与自然在互动中生成的文化活动。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与生态和民俗是分不开的。民俗是文化系统中组织层面的非强制性组成部分,它通过文化的自然延续去节制社会成员的生产、消费和协调人际关系。比方说,就拿“哆耶舞”的衣着来说,一般男人上身穿青色无领的对襟衣服,下身穿大腿裤,脚穿草鞋或钉鞋,头上包着侗帕;女人上身穿紫色或蓝色的圆领衣,下身穿百褶裙,头戴白色且绣有花边的帕子,系花色绑腿,佩戴耳环、手镯、项圈,脚穿绣花勾鞋。从民俗的角度观察,“哆耶舞”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是什么、人们在聚集时穿什么衣服、有没有特殊的民族特征等等。这些特征都可以从具体的表演中被观察到,而这些物质形式或非物质形式又是看得到、听得到、摸得着的,并可长期保存下来的,显然,这就是我们所考察的民俗。民俗对于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来说,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哆耶舞”的活动方式与活动内容往往是侗族一组组相互联系的民俗因子。侗族先民依附自然,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之后,人们认识到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并广泛利用环境,将之融入其文化之中,“哆耶舞”就是对侗族先民与艰苦环境抗争,以及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来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生动描述。
侗族民俗为“哆耶舞”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也为其增添了民族文化色彩。在“哆耶舞”中,侗族代表性的《赞鼓楼》、《赞团寨》、《赞朋友》、《萨岁耶歌》等都集中体现了侗族民俗文化精髓,也是侗族民俗思想的体现。侗族居住在山区,行走和生产活动大多在山坡上完成,必须具备勇敢沉着的心理素质,他们艰苦劳作、猎耕互济,世代保持着这种民俗文化美德。
(二)审美与环境
环境是形成人们审美心理结构的重要条件,也是构成一个区域或一个民族美学思想观念特性的基础。民俗学家认为,当我们将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论述时,必须论及其得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论及其植根的地理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政策及族际结构等[8]。“哆耶舞”流行地区的地理环境、血缘宗法社会与农耕文明的结合,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侗族人的审美思想,强化了当地人们的重生命亲自然、重现实人生与实践体验的意识,也导致了侗族先民“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这一切又构成了孕育侗族民间艺术审美思维的哲学土壤。从生态环境上观察,侗族后裔生活在湘、黔交界的侗族地区,他们以耕种、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在田野山间生产劳动,他们以舞助兴,以歌记录各种耕种时令、捕猎程序。因为在野外劳作,自由性强,歌舞由此变成了侗族人宣泄情感的主要方式。由于侗族先民的自然宗教崇拜、神灵崇拜,他们发明了“哆耶舞”这种极富象征意味的艺术形态,使各种想象力物化,正是这种浓烈的象征意味使民间艺术具有了审美的张力。“哆耶舞”与侗族宗教文化和农耕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哆耶舞”具有鲜明的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特征,同时为我们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研究侗族先民审美意识提供了原生材料。
环境对人们审美意识能产生很大影响。侗族聚居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自然农业和生活方式催生了这里的人们与自然之间的亲近之情,这种亲近感、同情感就是观念上的“自然的人化”的体现,也就是审美意识的体现。“哆耶舞”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一直传播着侗族文化,传承着侗族的精神观念、道德意识及价值观和审美观。由于侗族聚居区位于偏僻地带,这里的文化流动与运动主要是在民族和区域内作纵向的传承。可以这样理解,一种文化一旦在当地扎根,就会与本土文化涵化共生,成为当地人文化和心理的一部分,不太容易发生改变。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艰苦的社会条件养成了人们奋发图强的生活情调,而“哆耶舞”正符合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节奏。长期以来,侗族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追求平静、自然,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因此产生了以和谐、蛮勇为美的审美意识。
(三)文化与自然
文化与自然、民族、民俗等具有直接对应关系,一个民族是靠文化来维系人们聚合的。早期,人们只知道人类纯自然的生存空间,把自然与人类文化隔离开来。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外部环境并非纯自然的,而是人类加工改造的结果。我们在研究侗族文化艺术时,就必须考虑到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Alfred Loues Kroeber)曾指出,文化虽然与自然有着关系,但前者决定后者,文化的发展不可能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最终是由于文化本身的作用[9]。由于环境是根植于民族的文化之中,与该民族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协同运作的。在侗族“哆耶舞”中,它所产生的自然环境必然是针对特定的文化而言的,没有文化归属,“哆耶舞”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自然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来说尤为突出,就侗族而言,其聚居区与汉族交杂,在相互交错杂居的极为相似的地域空间内,若不就文化的归属性而言,似乎它们的环境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仔细分辨侗族与汉族因文化造成的生存空间的差异后,必然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
民族民间艺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把最精炼、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东西当作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当今人们从“现代化”社会理想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普遍审美心理。“哆耶舞”不论从内容、形式、题材,还是从表现对象上而言,都极具生活性、民族性与民俗性,能表现侗族人审美观及族群人性、人情的方方面面,“哆耶舞”可以视为其生活的本来形态的真实写照。“哆耶舞”的文化生态变迁是侗族地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缩影,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哆耶舞”的发展、传承又使人产生不少焦虑,因为当下多种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价值取向与审美标准在不断地变化,民族民间艺术生存和发展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1]黄守斌,周帆.侗族戏剧审美人类学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1(2):41-42.
[2]游俊,李汉林.湖南少数民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334.
[3]熊晓辉.湘西历史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670.
[4]杨彬修.探侗族民歌之源头——耶歌[J].中国音乐,2007(3):122-123.
[5]李雪梅.地域民间舞蹈文化的演变[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170.
[6]陈素娥.诗性的湘西——湘西审美文化阐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43.
[7]于平.舞蹈文化与审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
[8]郑英杰.文化的伦理剖析——湘西伦理文化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27.
[9]罗康隆.文化人类学论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60.
(责任编辑:刘英玲)
G127
:A
:1674-9014(2013)04-0124-06
2013-04-30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湘文化与地方民族音乐关系研究”(11YBB313);2011年湖南省民族学优势特色重点学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原生型民间音乐舞蹈研究”(HNYTZ014)。
熊晓辉,男,湖南凤凰人,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