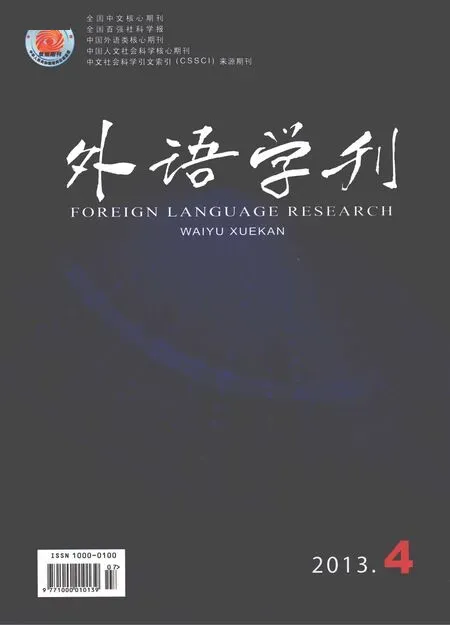言外转喻属性模式的语境操作层面分析
王明贝
(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150040)
1 引言
言外转喻是指言语行为的属性从意义上替代言语行为本身,言语行为指向其属性(Panther 2004:103-104)。鉴于目前的言外转喻研究没有深入考察语境的作用,本文对属性模式作语境等语用参数限定下的应用层面上的系统分析,重点阐述两个要点:(1)言外转喻X IS Y构式的属性操作描述;(2)其他模式的言外转喻操作。
2 X IS Y构式词义推理的认知语用解释
本文主要以Goldberg(1995)的理论为依据,将构式理解为一个基本单位序列,是形式和意义或用法的匹配体,是非模块化的,不是词素和句法规则互动的结果。其“构式”的定义如下: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结合体<Fi,Si>,且在形式Fi和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组成成分或先前已有其它构式中严格地推导出来时,C是一个构式(Goldberg 1995:4)。构式语法理论认为,语言系统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体系,X IS Y结构存在意义与形式的匹配,而且X IS Y结构有自己独特的整体构式意义和有别于其它相同结构的形式特征。X IS Y构式均为话语字面表达指向与之不同的语用功能,且话语指向其属性的形式具有相应独立性,这符合构式条件之一,即X IS Y话语表达形式是言外转喻属性加强联想操作模式下可以解释的构式(邹春玲2012:90)。
该构式的含意推理运作遵循属性归纳加强联想操作,构式语法研究基于体验的概念内容结构化、符号化为某特定形式的过程。这不是单纯的句法研究,体验是认知主体意向性下的能动体验,概念内容多为百科知识。这说明构式强调认知主体和多重语用因素的介入,话语意义是构式意义与词汇意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构式义与词汇义无冲突时,自然生成话语意义;当存在冲突时,构式义压制词汇义。
构式理论都是“基于说话人的情景建构”(Goldberg 1995:7),所以解读这些理论要受到一定理论和应用的限制。构式的研究对象是话语在特定社会文化和语境中长期使用而固化在句法层面上的结构。本文将结合语境,重新认识这些固化构式,努力从听话人解读的角度重新审视,通过剖析属性加强联想操作程序,以期获得某些新启示。研究须要明确构式义与词汇义各自的作用范围,也就是整体话语含意指向与具体含意指向之间是否存在彼此压制的过程。在分析和研究属性归纳加强联想推理过程中,我们发现构式和词汇义之间的压制关系相互影响,最终的解读要求构式含义由其突显性而压制词汇义的解读走向。具体地说,在“她的房子就是她的坟墓”(六六《蜗居》)这个典型的X IS Y构式中,当“坟墓”属性归于“死亡”,并且对前面目标域在实施加强联想过程中产生与目标域“房子”属性(居住)不相符的现象,造成构式义与词汇义不符。此时的推理策略是两个属性共同调整、整合、再归纳,再归纳得出的属性含意对整体构式义的解读产生影响。
鉴于篇幅有限,此处仅讨论属性操作在X IS Y的目标域词语层面和构式层面的应用。将言外转喻X IS Y构式的研究焦点定格在目标域的属性操作上,关涉对目标域词义的属性常规推理、词义在话语整体解读中的调整、充实性再归纳、两域结合解读的属性含意。这是以词汇层面为基础,结合语用机制、语境百科知识,对词汇未完全表述义、词义在使用中变化过程、运作机制、变化规律进行描写和理论阐释。言外转喻的目标域涉及词语属性提炼和含意解读,不存在零语境识解,必须结合各种语境因素和个人认知背景等阐释,强调词汇意义在语境中的动态性。
2.1 属性模式对目标域词义的收缩与扩充过程的完善
在言外转喻X IS Y构式中,词义收缩指词汇意义具有“目标域在源域”的局部操作,也就是词语在某话语特定语境中的属性指向是其所有属性之一;词义扩充指词汇意义是词汇在类-属联结过程中归纳出来的抽象属性含意的下位类结构,或者将某话语所有属性整合、归纳后的综合概念。(1)词义收缩:话语“她的房子,就是她的坟墓”(六六《蜗居》)的目标域为“坟墓”,通过对坟墓的属性归纳和随附加强源域“房子”理解整体话语。坟墓的属性之一是死亡,强加给“房子”作为临时属性,两域共用一个属性就是词义收缩,也是属性目标域在源域的常规性认知定位。(2)词义扩充:“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张爱玲《我看苏青》)。“同行”的认知常规属性有很多,如“同行相轻”、“同行是冤家”等。解读此例“同行”的步骤为:根据属性模式在生成空间中进行类属操作,同行为类,相妒为属,同行的属性随附给女人,产生类属二次联结的整合操作过程,扩大女人作为类的属性集合,这就是词义扩充的典型范例。
Panther对言外转喻属性指向的分析充分体现其推理的话语意图视角,如“疑问指向请求”。这在现代语言应用中有时与话语解读机制的运作完全脱钩,如在“What's the smell?”中的宏观属性解读归纳未必就是关门,即使补充场境推理过程中涉及的社会、权利、损益等因素也未必知道听话人究竟怎么解读,因为解读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认知。这时,单纯说是疑问指向请求就未免片面,多重因素决定解读的属性指向具有一定范围内的语境操控性,语境检验过程在属性加强联想模式中叫做评估空间,评估空间是听话人解读话语时主观认知的操作空间。原言外转喻宏观属性指向是具有逻辑规律的认知本质属性,这是说话人的视角。而言外转喻解读中的属性指向同时是推理手段,是听话人的视角。听话人根据自身主体性认知获取话语含意,有时与话语本身的意图契合,有时则不然。解读是听话人角度发生的动态运作,这就是本文在原整合理论图示上加入评估空间,强调听话人主体认知的必要性所在。
属性加强联想模式以其生成空间和评估空间的操作,在原言外转喻理论宏观指向的基础上调整推理焦点目标域中的各类具体词义,探究原言外转喻用于推理过程中应该描写和解决的问题,证实言外转喻在词义中是自然推理的观点。汉语言文化的话语解读都存在目标域具体词义在属性方面的收缩和扩充,其具体引发性因素各不相同,但可以用属性运作模式描述和解释,包括通过属性生成机制解释词义自动归纳、归纳后的整合加强对比情况(第二次类属整合解读)和不契合情况的再归纳。通过评估空间语境等因素检验词义收缩与扩充后的属性,不但比其它扩充形式省力,而且与词语显义的关系最强。
2.2 属性模式对原言外转喻中未描述的语境中含意变化现象的解释
这种含意变化多发生在目标域对源域的加强联想理解过程中。这对话语整体属性的定位有很大影响,对话语含意的释义产生与目标域和源域属性不相同的解读,主要原因是语境的作用。属性模式的解释力并不限于对己有解释的精细化,也可以解释原来未作深究的具体含意属性的调整操作现象。话语解读过程中含意的认知常规属性会产生语境中的突变现象,这是由听话人主体意向性激发,受部分源域联结过程中的具体语境制约,甚至感受制约。属性模式纳入对属性性质的考虑,描述推理也多从听话人解读视角出发。于是,这种突变现象可以纳入目标域属性操作的统一解释,突变现象的核心原因是加强过程的类属二次操作,形成与原属性不同乃至对立的含意。
本文的语境包括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其中,认知语境包括源域能提供的属性类信息、目标域属性常规性信息以及认知主体的自身认知背景。该类语境中的目标域属性操作并不限于上述收缩与扩充两大类,还可能出现词义的具体临时变化,前两者由目标域本身的认知常规属性归纳限制,这种临时的变化是在两域加强联想过程中产生的,因此,这种变化后的临时属性在意义上可以替代话语本身。语境影响分为以下4种:
第一,客观语境产生的突变现象。研究发现,原言外转喻中的宏观属性归纳并不能完全回答下面的问题:“What is she doing here?”是不是转喻,单就这句话本身很难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视客观语境而定。如果该句用在不知而问的情景中,表示询问,没有转喻思维;如果用在明知故问的语境中,也有可能表达感叹、不满等情绪。在后一种情形下,是间接言语行为,表征间接属性含意。某话语是否为言外转喻以及属性作何归纳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由语境决定。虽然认知语言学研究转喻,但目前对上句提到的语境因素对转喻的限制作用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这正是我们在本研究中所密切关注的一个部分。属性加强联想操作模式将语境因素考虑其中,因为如果离开具体客观语境的制约,解读“问题”不可能产生指向性归纳。
第二,主观语境产生的突变现象。熊学亮认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或思维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这种语用因素内在化、认知化的结果就是大脑中的认知语境”(熊学亮1999:125)。这样形成的知识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的结构化、抽象化的结果,原来的知识结构可以作为推理的逻辑部分,形成认知新事物时的种种关系。比如,一提到“医院”,就想到“打针”、“点滴”、“手术”、“痛苦”等种种知识结构,认知语境就是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在言外转喻具体话语中,由于可及性高而调用出来的认知语境首先是源域的属性含意,如“天下大事大抵如此——做成的蛋糕永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张爱玲《道路以目》)。“天下大事”的认知常规属性是“大-重要-成功”等类的属性,目标域(蛋糕)的常规认知属性关系是“过程”含意,两域加强联想后的类属操作是:过程重要,通过因果推理得出其属性含意:努力做事。努力这一属性和重要、过程等属性归纳不同,是二者加强联想操作后的另一属性归纳而产生的突变现象。这里,源域和目标域的属性有所矛盾,大事强调成功的结果,制造蛋糕强调成功的过程,只有在源域提供的属性认知语境中结合由此引发的对矛盾原因的寻找构成话语解读的一个部分,通过加强形成两域的矛盾统一,才会有突变属性的加盟解读。解读结果生成的另一属性,不但自身是一种属性归纳的认知效果,而且为上述两域属性解读的成立提供支持。可见,属性加强联想操作模式比原言外转喻理论的推理机制在解释力与可操作性上优越。
第三,主客观语境同时产生的突变现象。上面两种情况分别探讨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属性模式有时是在这两种语境共同作用下才能有效操作,如“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韩寒《零下一度》)。这里,客观语境是语篇提供的上下文:评价员工做事应该是常规还是超常规的风格,且内化为认知语境形成对做事风格指向性的铺垫。具体落实在话语中,野鸭也是列方阵飞的,源域属性是关于“野鸭会飞”的常规认知,目标域的属性列方阵指向不乱来、有章法等含意。这样,主客观语境共同得出一个属性的认识——规矩,而且与两域各自的属性不尽相同。此外,属性操作有时是各种语境综合作用下的突变现象。
第四,社会文化特定性产生的突变现象。属性操作过程中,社会文化的特定因素增加其复杂性。如“‘介绍蛋白质女孩给我认识!’,我以赎罪的心情大叫。我们相约去爬阳明山,张宝和我站在山下的超级商店等她。‘不过我得警告你’,张宝说,‘她是一个个性很好的女孩!’。我立刻了解了他的意思,‘没关系,我不注重外表’”(王文华《蛋白质女孩儿》)。按照Searl对言语行为的分类(Searl 1975:56),Panther和 Thornburg主要讨论指令类中的请求行为的转喻情况,没有深入分析其它言语行为(Panther&Thornburg 1998:755-769)。本例句就是对Panther言语行为理论的深入研究,揭示其中的“感叹”指向“阐释”、“警告”等的言外转喻类-属宏观推理关系。“个性很好”是属性加强的过程,其正常归纳应该激活“温柔”、“贤淑”等属性,但是这里却转喻性地指向同一类属范畴内的反向含意“不漂亮”。这就是汉语言文化下的特定转喻思维取向:文化因素导致的加强解读过程产生属性含意突变。礼貌原则要求,在表示与他人有损害的意思时需采取间接表达,久而久之,某些间接表达就成为其对立的属性的代名词,并在社会文化的沉淀中形成规约化的表达和认知方式。
综上所述,属性加强联想模式解释原言外转喻中未描述的语境含意变化现象,弥补原言外转喻对语境产生属性变化现象解释的苍白,不仅说明属性加强联想模式的可操作性强、解释力大,而且能加深对“属性加强”操作生成结果的语境指引方向性的理解。这样,就将语境中的属性突变现象纳入属性模式的统一框架中,列入“再归纳”过程的结果产生层面的考虑因素。
上文重新解释属性操作模式在X IS Y构式中的目标域词语与其属性的关系,论证属性推理应用于词汇层面的解释既具有宏观概括性也具有微观精细性,同时增强属性模式的解释力;另一方面,该模式为X IS Y等构式研究也提供新的视野,证明属性推理可能发挥的作用。
3 话语层面上的听话人解读推理应用
属性模式除对目标域及其属性关系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外,其在话语层面的操作也同样可以弥补原言外转喻推理视角单一的缺点:从听话人解读视角补充修正属性模式的言外转喻操作。话语层面的言外转喻应用分为常规转喻构式应用和非常规转喻的属性操作应用。常规性转喻的属性操作较为简单,可以一步到位地归纳话语属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然而,非常规转喻的属性操作比较复杂,因此重点予以讨论。
言外常规转喻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规约性,而非常规转喻的很多方面在推理释义过程中都不存在集体认同性,如“李燕: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刘震云《手机》)。“出轨”、“出门”和中年危机之间是纯粹的偶然邻近关系,所以叫做非常规转喻,有时是为了顺应语境和意向性而使用的经济性语用策略。“非”字体现在:目标域的本质属性不是源域的本质属性,而是其现象或临时属性,设目标域为Y,属性为Y1,源域为X,属性为X1,“非”的解读为Y1=X2,可以发现存在语境绝对可取消性。非常规转喻的解读过程有时容易使人们无法当机立断地明确解读该类话语的含意,该解读在生成空间内通过类属联结归纳得出的属性指向被偶然性地用来指向整体行为含意,具有间接性大、非必然邻近等特点,给确切解读带来困难。非常规转喻的应用频率在现代语言表达中越来越高,这是认知进化对语言经济性表达的要求。大部分转喻模式实际上是个体主观认知生成的推理和解读模式,而不是集体模式(Lakoff 1987:84-90),这种个体意向性语言表达的强势使我们不得不将其提上研究日程。
转喻的常规化和非常规化可以从其解读和认知效果看,话语理解时不仅要恪守传统研究路向“对方的话是什么意思”,更要追问“对方对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中国长期文化沉淀形成的含蓄思维造成语言表达较之西方语言的间接程度要大得多。话语解读时,人们不断思考“这话什么意思?”这样,探讨非常规性话语含意似乎更为重要。具体分析表明,转喻是常规还是非常规的,可以从5个方面考虑:(1)邻近的远近;(2)推理力度的高低;(3)解读努力的大小;(4)认知效果的强弱;(5)属性的本质还是现象。
研究言外转喻基本上都是话语与属性的对应性研究,对于各种条件限制下产生的宏观属性没有专门的讨论。因此,本文讨论宏观属性的不确定性,从而修补原言外转喻中对属性操作的片面看法,说明属性操作的归纳和加强过程发生在各个不同层面上。上文叙述过言外转喻X IS Y构式的情况,这里,继续探讨言外转喻的另一种情况——多域操作的复杂性,如“可是吃沙拉的时候,小静突然吃出了一根铁丝!简直太过分了!小静(招手):服务生,叫你们经理来。经理: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小静(用筷子夹起铁丝):这是什么?经理(弯下腰看):呃,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一份。小静:这是换一份的事情吗?经理(犹豫):这样吧,我再送您一份油焖大虾。小静:这是送一份油焖大虾的事情吗?经理(一咬牙一跺脚):小姐,您提出个解决方法,如果行得通,咱就按您说的办。小静:我们这桌免单”。(苏小懒《全是爱》)。该例中存在多个源域对应同一目标域的情况,其中,源域包括:(1)这是什么;(2)这是换一份的事情吗;(3)这是送一份油焖大虾的事情吗?若干源域共同对应同一个目标域,充分说明转喻多域操作的复杂性。多域操作的意思是涉及不止源域和目的域两个域,而是多个认知域。在不同语言现象中,多域操作方式不一定相同,会有不少变体形式,如同一目标域对多个源域,同一源域对多个目标域等。
上例中小静的问话“这是什么?”可当做构式转喻“What's N”看待,表达质疑的属性指向,确切含意的识解绝非只做到从话语类别推理到宏观属性这么简单,且推理出的属性含意也不止一个:该话语除了质疑外,更多表示不满。从经理的回答也可以看出这点,他把小静的话既当质疑,也当不满理解,所以先回答“对不起”是对不满的回应,后回答“我给您换一份”是对质疑的解答。这里,“这是什么”激活与之相关的认知域:“菜里的铁丝”,在饭店的菜里出现铁丝的情景下,也就是说在通常不该发生的情景作用下,进一步激活“饭店菜里的铁丝”的整体言外ICM.这里,存在从因到果的合情因果推导,经由属性归纳操作直接指向其含意“不应该”。经理的回答说明,他已经从小静的话语中识别出言外转喻属性归纳的两种情况,他的回答已经表明对小静的质疑和不满在个人认知背景下的理解,但是小静的进一步质疑否定了这个理解“这是送一份油焖大虾的事情吗?”,这是双方认知语境达不成契合造成的结果,再次表明质疑和不满,再次进入类属空间二次属性归纳加强的操作形成转喻思维。可见,在该句的转喻多域操作中,源域和目标域受认知语境的影响极大。除了多域操作外,间接言语行为的言语类型和功能不一致,转喻就是要为这个现象提供认知理据。因此,转喻的复杂性还体现在言语类型和功能不一致产生的多域操作和意义偏离,以往的言外转喻研究只限于“疑问代请求”层面上,只用为数不多的例句,如“C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分析有限的言语类型。本文力图综合分析间接言语行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对言语类型的转喻分析进行扩展。我们认为陈述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意义偏离,因此产生言语类型和功能不一致,这不仅是语用偏离,也是言外转喻属性归纳过程操作造成的问题,这种意义偏离离不开语境的制约。
4 结束语
本文意在说明言外转喻属性模式在语境中的应用操作,将言外转喻操作中涉及的方方面面统一在属性模式之下。文章主要阐述属性模式在两大层面的应用:(1)通过该模式解释和丰富言外转喻已有的属性操作的研究对象——间接言语行为,尤其是X IS Y构式中的词汇操作,加强属性模式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力度,实现属性模式用于言外转喻解释过程的精细性和概括性并存,拓宽其在本领域的解释范围和解释内容。(2)同时,属性模式对构式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这说明属性模式在言外转喻先前未涉足的语言研究领域内同样可以发挥作用。现有的言外转喻研究只能描写社会文化常规性强的构式,而基于属性操作的模式却可以将其逐步拓展,统一分析非常规转喻的操作。现有的构式分析对同一个句子形式体现不同构式,尤其是指向不同属性的分析还没有展开,本文分析言语行为类型与其功能的不一致弥补了这一缺陷,属性操作模式本身可对不同构式进行解读。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邹春玲.X IS Y言外转喻构式论证[J].外语学刊,2012(5).
Goldberg,A.E.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Panther,K.-U.& L.Thornburg.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1998(30).
Searle,J.R.Indirect Speech Acts[A].In P.Cole & J.Morgan(eds.).Syntax and Semantics:Speech Acts[C].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Thornburg,P.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