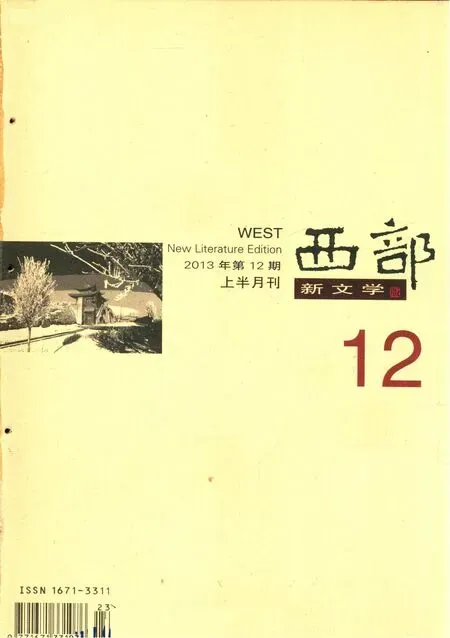十字路口的旅行
周雅薇
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神奇的作家,在与之相遇前,我还未曾发现一位作家能如此深情地抒写对一座城市的记忆。他笔下的帝国曾雄霸地中海,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土耳其的先祖西突厥人征驰于小亚细亚,他们是草原勇士,发迹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终而攻取博斯普鲁斯海岸城市君士坦丁堡——爱尔兰诗人叶芝为之歌唱的“拜占庭”。十七世纪后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的牺牲品,文艺复兴之星冉冉升起之日,就是奥斯曼帝国落日西坠之时。
十六世纪苏丹统治下的伊斯坦布尔人崇尚奢侈,贪图享乐。从波斯流传下来的细密画技巧经过反复锤炼,逐渐成为以鲜艳色彩和精美镶边著称的贵族收藏艺术品。它曾镶嵌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物件之内,绘制于为埃及法老陪葬的古卷之中,出现在祈祷书《古兰经》的边饰图案之上。以昂贵的象牙、羊皮卷为画纸,珍珠、蓝宝石磨粉作颜料,大师们创作的细密画插图手抄本,辗转流传于不同的宝库。一代又一代的细密画家群体聚集于君王设立的画坊,靠几十年如一日的临摹、重复前辈的经典作品来维系传统,以达到大师的尊崇地位。
奥尔罕·帕慕克对细密画颇有研究,在写作前,曾学习过绘画,后来,他以此为素材创作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并于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这部作品中,代号“橄榄”的凶手是画坊一名杰出的细密画家。他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感知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倾颓,这座城市终将成为废都。他不能任凭传承百年的艺术在他手中断绝,他知道当时细密画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它的图画既能表达宗教信仰,又满足了当时贵族们收藏的嗜好。一旦西方以达芬奇为代表的透视画法引进,细密画再无出路。这群早已被人遗忘的彩绘大师们,只能身陷画笔和颜料堆中相拥而泣,在入侵者围城之日,全世界只剩下这座城池,画坊是他们的坟墓,他们亲手绘制的细密画是他们的陪葬品。细密画家只能临摹前辈大师们的作品,不能在绘画中得到真正的精神满足。这使渴望获得自我风格的橄榄更加痛苦。融入血液的宗教意识使他不能完全丧失自我,颓靡的大环境却加剧了他的折堕。
进行艺术创作是人类释放欲望的途径之一,因宗教而产生的细密画却是为安拉服务的工具。画家之所见所闻都是创世者所赐予的,摒弃自我,皈依于安拉,细密画家们的绘画皆是透过安拉之眼看到的,“就像诗人描述他‘倾听’从心灵深处浮现出来的诗文一样,而神秘的是,这些诗文的权威性与完整性似乎自成一格,而与他无关。用华兹华斯的话说,就是以‘智慧的被动性’来倾听”。他们以终身为安拉绘画、年老失明为荣耀,失明并不是一种苦难,反而是褒奖终生为真主奉献的绘画家们而赐予他们的最终幸福。他们在晚年失明中获得心灵的宁静,达到绘画的最高境界,抛开尘世间的纷扰,画出安拉眼中至纯的世界。
橄榄迫切要求自我风格的形成,无疑成了保守派细密画家的攻击对象。谋杀保守派镀金师高雅先生,完全是橄榄预想筹谋多次的场景。整个谋杀过程超脱了恐惧,仿佛谋杀者不是他自己,艺术家独有的灵感和快感却被谋杀的阴暗情绪所激发。作为一名伊斯兰教徒,他对自我内心“恶”的觉醒产生了病态的自得。他渴望风格,如果拥有自我风格即是罪孽,那么橄榄为了使自我风格达成,不惜犯下真正的罪过——杀人。
帕慕克对于色彩所选取的欣赏角度是残忍的,他用谋杀来刺激感官,取悦艺术,达到一种高潮般的极致效果。“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与共。”所谓的震撼之美并不在于谋杀的具体景象,因为观看真正的谋杀之时,正常人不管是在视觉效果还是心理承受方面,都无法直接与美感取得联系。帕慕克所营造的氛围是从丑恶的主角中脱离出来的背景之美、暴力之美,这种美自成一体,与丑陋的现实世界毫无关系。
橄榄又是一名伊斯兰教徒,出于宗教信仰憎恨着西方文明。“橄榄”这个名字本身即是一种象征,象征和平神圣,是真主的盟誓之物,为真主的明灯而燃烧。他心系西方文明,却不堪忍受民族传统艺术被架空,渴望表现自我,却为伊斯兰宗教信仰所困,艺术和信仰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横亘在橄榄面前,“他对西方有多么热爱,就有多么轻视,他不能将自己看成西方人,却又为西方的文明而眩目,他感到自己被夹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他的灵魂从此被割裂成两半,一半是一千只翅膀覆盖东西方世界的天使阿兹拉尔,一半是因高傲堕落,分隔东西方、最先说出“我”的撒旦。法兰克西方画派背后是缓缓上升的文艺复兴,这浩瀚的人文主义光辉令为真主服务的细密画家们渴望自我,正如文艺复兴时期要求人性的回归,而艺术,则是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东方与西方、荣耀与罪孽的并存体,这些因素极致交汇、迅速碰撞而产生质变后,才能产出艺术。
橄榄的悲剧在于,作为向西方运动看齐的一部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持深刻批判的态度,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毫无价值。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耻辱。橄榄天才桀骜和冷酷疯狂的矛盾气质在少年时期就已形成,他在个人风格初步觉醒和宗教节制中饱受撕裂之痛,他是奥斯曼帝国大环境下培育出的真正艺术守护者,也是被大环境决然抛弃的时代受难儿。
这不是橄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历史的缩影。面对新兴的西方文明,细密画这种与宗教紧密相依的艺术形式根基开始动摇,橄榄的目光投递得很远,却看不到民族的未来,渴望将东西方文化同时接纳融合却找不到出口,这也并非他一人或几人之力所能达成。在任何时代,陷入困境的天才都是东西方永恒的话题。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本人的理想即是成为画家,当他怀揣理想,挣扎于伊斯坦布尔这座绘画艺术滑向边缘的城市时,他笔下那些细密画师结局悲惨的命运似乎就要重现眼前。即使在欧洲,梵高和高更都发了疯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更遑论这个曾经强大一时的国度已在漫长的岁月中衰朽,其子民亦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再也无法以曾经辉煌的艺术为荣。
帕慕克青年时期饱受此类困扰,家人告诉他:“如果不想成为建筑师或找其他谋生方式,你将成为那些神经兮兮的土耳其穷画家之一,只能看有钱有势者的脸色过活,别无选择。你懂吗?你当然懂。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光靠画画过日子。你会绝望无助,人们会瞧不起你,你的内心将饱受种种情结、焦虑、愤恨的煎熬,直到死去。”他同自己小说中的橄榄一样,在进行一场战争,尽管他几乎一开始就已明白,他不可能赢。他是一个人在进行战争,而且对手是隐形的、不可战胜的。这个沉迷在忧郁中的城市令他眷恋又使他痛苦,没有人捕捉到这座城市的情调、风格和灵魂,而他曾经无数次漫游其中,如此爱恋,如此寒冷。

但当帕慕克不遗余力地描写这座城市的大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天际线,甚至展示出一张张老旧的黑白照片,讲述这座被西方当作客体的东方城市时,请相信他是爱它的。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是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我”。帕慕克的忧伤并非源于他怀念奥斯曼曾经的荣光,并非惋惜帝国四个世纪的霸主地位。他忧伤是因为他明白,伊斯坦布尔从此辉煌不再,他只能通过呼愁来缅怀帝国的曾经,呼愁已经成为了他一生的宿命,他既没有办法摆脱,也丝毫不想摆脱,因为这种忧伤正是他真正的食粮。
与《看不见的城市》不同,卡尔维诺的大脑更加松快机智,语言之间充满着可圈可点的机锋,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则如实得像素描一样精细,他所描写的每个细节就像一张网状物中的一颗颗粒子,阅读时不用费一丝一毫的精力琢磨,只需透过一粒一粒的叙述点,随着他的笔触,去观察他为我们构建的伊斯坦布尔。每一粒叙述点串联起来时,就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在合上书的瞬间直接喷洒在视网膜上。帕慕克字里行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不解构,亦不重建,他安详的眼睛看遍了伊斯坦布尔曾经的荒芜和繁盛,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和交融。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一个古老帝国的轴心被迫朝反方向吱呀扭转时发出的悲鸣。也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在西方人眼中作为客体的东方是多么被动地忧伤着,正如他明白人们盛赞废墟之美,却无人愿意为废墟长久停留。
加缪说,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无非是了解这座城市里的人怎样活着,怎样相爱,又怎样死去。
此言不虚。
每当帕慕克的呼愁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扩散开来时,这种巨大的心灵之声就会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声音并非宗教性的召唤,而是身处伊斯兰文化中所具有的共鸣。“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转头再次望向窗外前,有一刹那深深望入我的眼睛——后来我也曾经如此看别人。他凄怆的眼神只有一个含义:如果你不做梦,时光就不会流逝。”
帕慕克借一个关于细密画的故事,动手解剖土耳其这个古老民族的灵魂,代表土耳其人述说着文明被割裂和架空的痛苦。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着苍凉的氛围,文化杂合令他们内心漂泊无根。他层出不穷地发掘这个城市的各种声音讲述这所城池,这些独特的音色被他错落有致地编排,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华丽乐章,为小说呼愁的忧郁灵魂包裹上一层鲜艳的颜色,无声无息地缅怀着帝国逝去的辉煌。这种苍凉是奥斯曼帝国文明逝去的忧伤,文化历史渐渐逝去的忧伤,西化改革失败之后再也无法重塑憧憬对象的忧伤。痛苦是文明碰撞的必然代价。这种巨大的呼愁和感伤,体现在帕慕克小说和现实中的每一个土耳其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