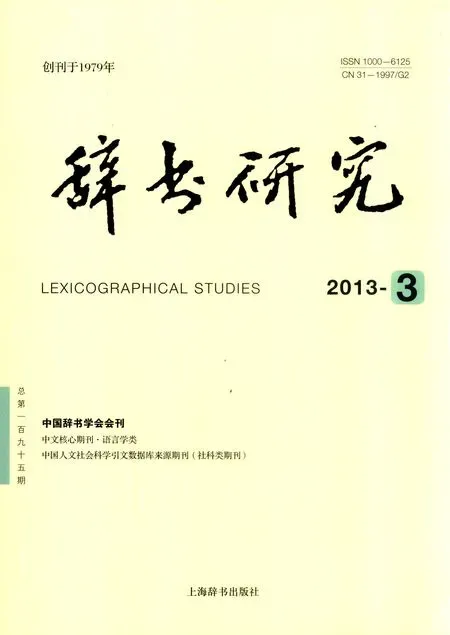义项界说综论
尹 洁
一、关于“义项”的普遍观点
提及词义的单位,人们通常会想到两个概念:一是义位,二是义项,并认为义位在词典中即表现为义项,甚至认为是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指称。
1908年,瑞典语言学家诺伦首先提出“义位(sememe)”这一名称,布龙菲尔德把它作为结构语言学的一个意义单位。1949年后,美国奈达沿用布氏的义位,认为是“一组语义上相关的义素”、“诸义素的总和”。张志毅、张庆云(2001)对义位的大中小三种概念进行区分,认为义位应是一个中观概念,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并从多个视角对义位进行界定:(1)直观定义:义位相当于义项;(2)操作性定义:义位是自由的、语义系统的最小单位;(3)属性定义:义位是最基本的语义单位;(4)分析性定义:义位是义素的综合体;(5)系统性定义:义位是语义系统中的抽象常体;(6)结构性定义:义位是由义值和义域组成的。苏宝荣(2008)对词义单位划分出义系、义点、义位与义项几个层次,指出:“一个词语在特定语境中所表达的与其基本意义相近、相关,而又有这样或那样区别的话语意义,就是这个词的义点”,并指出“义位是人们头脑对词语义点进行加工的产物……它具有主观和客观双重属性”。因单音节词在古代汉语中占绝对优势,蒋绍愚(2005)认为义位就大概等同于词典所列的义项,在讨论词义的发展变化时,要以义位为单位,以便消除传统训诂学中的一些认识模糊之处。
可见,义位是由义素组成的,既客观反映词义存在,又需要经过人为归纳和加工的词义的基本单位。然而,义位等于义项吗?关于义项,存在以下一些认识:
(1)邹鄷(1980):“义项就是辞书中按字义源流纵横的发展,对一个字的全部涵义分别进行训释,它是辞书表述字义的条目,是辞书特有的释义方式。”
(2)张清源(1980):“义项就是词典中词义的分项。一个词有多少个固定的理性意义,就应列多少义项。”
(3)胡明扬(1982):“义项指的是多义词中相对独立的意义项目,在词典中一般用数字分项注释。”
(4)潘竟翰(2000)界定义项的标准为三条:“①义项是语义的最小运用单位;②多义词的外部关系是对立的,各有区别性义素相分别,相互之间不能有重合、包容、交叉关系;③义项的内部有同一关系,有共同义素相维系。”
(5)符淮青(2006)认为狭义的义项是:“词义最小单位的名称,它在词典中有形式的标志。它区别于词典中广义理解的义项,是经过细致分析后所得到的最小的词义单位。”
(6)《语言学百科词典》:“义项指同一个词的每个词义。只有一个义项的词为单义词,具有两个以上义项的词为多义词。”
综观以上论述,学者们在对“义项”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这也成为我们立论的根据:
①义项是词义学概念还是辞书学概念?②义项解释的对象是字还是词?③若承认义项的对象是词,是否仅为多义词,义项的内部有无共同义素,在词典中仅有一个意义的词的解释单位是什么?④义项若指向同一个词的每个意义,通假义所记录的不是同一个词,通假义列在该词下,该怎样指称?⑤是否将义项解释的内容限于理性意义,语法意义是否为义项建立的根据?⑥义项有哪些特性,能否“分合”?以下我们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二、义项界说
(一)义项产生的历史
中国辞书的编纂出版历史源远流长,《史籀篇》应该是见于著录的最早字书,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尚算不得辞书。至汉代,出现了在汉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几部小学专书。有人将《尔雅》前三篇视为最早的“同义词典”,实际上,它属于同训纂集,是具有相同训释的词语汇编。从其体例来看,每一训条是将具有相同训释语的各词汇集在一起,后用一个训释语解释,一条之中的各词不全是同义关系。受其编纂体例之限,在单一训条之中无法直接体现各词的多种词义关系,而是采用重出的方式,把一个词的多个意义分别归到不同的训条之中,被训词多次出现,或出于同篇,或出于异篇,服从义类的需要。如[1]:
本义 +引申义。《释诂》:“永,长也。”又:“永,远也。”
基本义 +假借义。《释诂》:“来,至也。”又:“来,勤也。”
引申义 +假借义。《释言》:“干,扞也。”又:“干,求也。”
语法义 +假借义。《释诂》:“哉,间也。”又:“哉,始也。”
本义+近引申义+远引申义。《释言》:“济,渡也。济,成也。济,益也。”
这应该算是辞书史上较早的词义编排方式,后世产生的系列“雅书”也继承了《尔雅》的这种方式。如《小尔雅·广诂》:“弥,久也。”又:“弥,盖也。”其优点是以训为纲,便于查检者找到同训词,但不利于掌握整个词的意义系统,难以把握词义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脉络。
许慎所著的《说文》被公认为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字典,主要解释与字形密切相关的字的本义。《说文》所释字义通常具有单一性,若另有他说,许慎则以“一曰”、“又曰”、“或曰”标明。如:
《玉部》:“莹,玉色。……一曰石之次玉者。”
《马部》:“驸,副马也。……一曰近也。一曰疾也。”
有人认为:“这实际上已是‘分项’释义了,而且有的别义与本义之间还有引申关系,这便是义项的滥觞。”(王粤汉1991)我们认为《说文》的“一曰”尚不完全具备后代辞书义项的性质,它是许慎对字的本义难以决断时将他说列出备考,但在客观上却向人们展示了有些字不止一个词义(不超过三个)。
其他的小学训诂专书都有类似的编排,如《玉篇·糸部》:“绳,索也。直也。度也。”《广韵·上平声八·微韵》:“非,不是也。责也。违也。亦姓。”这类训诂专书的训释大都采自前代各种训诂材料,故多纂集之功而乏解释之力。
至宋朝,从戴侗《六书故》一书词的释义及编排方式来看,先释本义(正义),再释引申义(引之、因之、引而申之等),后假借(借),这种有意识的词义分条排列可以算作义项的早期形式,为后世的辞书编纂所借鉴。如“张”[2]:
菑良切 弓施弦也(绷弦于弓)。
张之满曰张(布满、充满),去声(证略)。
张帷幕亦曰张(张开)(证略),别作“帐”。
水张盛亦曰张(涨),别作“涨”。
而明朝梅膺祚的《字汇》则“采取多种措施,使以字义为中心的形音义项体系定型化”,他指出:“大抵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后之修辞者,每借实字为虚字,用以达其意。”(转引自邹酆1983)编者正是以对语义学的粗略认识为基础来完成每个字的语义体系的。在编纂方式上,按不同音切分列不同音义项,并用“〇”作为划界的标志。如[3]:
盖 居太切 该去声 覆也,掩也,苦也,车盖也,又发语端也。
〇又古杳切 甘入声姓也,又齐邑名。盖大夫王驩。
〇又胡閤切 音合 与盍同 何不也。(证略)
〇又叶居气切 音记。(证略)
这就较前人在词义编纂的方式上有大大的进步。而《康熙字典》的产生可以说是汉语传统辞书在词义编排上的最终成熟,其对释义模式的精心设计是建立在一定的编纂体例基础之上的:“字有正音,先载正义,再于一音之下,详引经史数条,以为证据。其或音同义异,则于每音之下分列训义。其或音异义同,则于训义之后又云某韵书作某切,义同。庶几引据确切,展卷了然。”如[4]:
殆 【唐韵】徒亥切 【集韵】【韵会】【正韵】荡亥切 并骀上声 【说文】危也。又近也。又始也。又将也,几也。又贾谊《新书》……又与怠通。又叶养里切,音以。(每义均有书证,略)
至此,辞书的分项解释体例已完全成熟,并为后世辞书所继承。由此可见,辞书对词义的分项解释是义项产生的基础,最初是为解决词的多个意义(训释)在工具书中的呈现而采取的编纂方式。
(二)义项的实质
由义项演进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义项自产生起,出现的环境就是各类辞书。虽然它是为解释意义而创制的一种辞书编排方式,并且是以单个词义为解释的内容,但绝不等同于词义。也就是说,词义的基本单位“义位”在辞书中可以表现为义项的形式,但不能逆推,说义项就是义位在辞书中的表现。
义位是词义的基本单位,是词义学中的一个理论概念。而义项是辞书学(或词典学)中的一个术语,它完全属于一个操作概念。在辞书出现之前,人们就有了义位的朴素认识,但义项却是伴随着辞书发展的进程而出现的。《辞书编纂基本术语》中明确指出:义项就是字、词典中“按一个字头、词头的不同含义分列的注释项目”。也就是说,只要是在字、词典中对意义的解释条目就是义项,若数量超过一,则按数目分项排列,既便于编纂者编排,也便于使用者查检。
在辞书中,义项的形式也不是单一的,符淮青(2006)对此分出三类:
1.一个义项是一个意义。包括:
(1)单义词的义项。如:
光压 射在物体上的光所产生的压力。
(2)经过细致分析确定的多义词的义项。如:
浅 ①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小。②浅显。③浅薄。④(感情)不深厚。⑤(颜色)不浓。⑥(时间)短。
2.一个义项是几个相近意义的集合。如:
轻 ③数量少;程度浅。
3.一个义项是某几个方面意义的概括,其下细分为不同的意义。如“打”,《新华字典》处理为:
③指某种动作。例打(捉)鱼|打(买)酒|打(收)粮食|打(织)毛衣|打(画)格子|打(捆)行李|打(发)电报|打(做)短工。
这三种类型的义项所包含的意义内容是不一样的。符淮青将第一种称为“义项(狭义的义项)”,第二种称为“义项组”,第三种称为“义项目”。应该说,只有第一种义项才和义位对应。而义项组是由几个相近的意义排列在一起形成的,它们之间有相同之处,但在上下文语境中又会产生差异,于是,这个义项组中的几个意义就分别称为“义项变体”(蒋绍愚2005),因其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不同,高频者称为“中心变体”,其余称为“非中心变体”,而中心变体就是这个义项的中心意义。
由此可知,义项与义位并非同一概念,两者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义位属于词义学的范围,是词义的基本单位,而义项属于辞书学的范围,是释义的基本单位。但二者并非截然无关,词义义项的建立要以义位为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即使明确了义项的概念和实质,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因为义项虽为辞书学的概念,却因解释的内容是语言中最复杂的意义,于是又与语义学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全面认识义项,就要从语义学和辞书学两个角度加以研究。
(三)义项解释的对象
中国古代长期字词不分的传统,导致人们常常将语言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混为一谈。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形体是根本,其本身并无意义可言,它的意义是其所记录的词语的意义。由此可知,义项解释的直接对象不是字。
古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使得人们过去在研究汉语词义,尤其是古汉语词义时,无须考虑语素这一概念,认为义项就相当于义位,就是词义的运用或表达单位。如《辞源》对“常”的解释,每一义项都可独立使用,故解释的均为词义。
①恒久,经常。②法典,伦常。③普通,平庸。④古代长度单位名。⑤古代绘日月圆形的旗帜。⑥树木名。常棣的简称。⑦副词。(1)常常。(2)曾经。通“尝”。⑧姓。
然而,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早已成为词语构成的主趋势,古汉语中大量的单音节词已降格成为单音节语素,即使就多义词而言,情况也有区别。符淮青(2004)从义项的角度对现代汉语多义词进行分类:(1)全部义项是词义的多义词;(2)一个义项是词义,其余义项是语素义的多义词;(3)词义义项多,又带有语素义义项的多义词;(4)多义不成词语素。如《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常”的解释:
①一般;普通;平常。②不变的;固定的。③副时常;常常。④指伦常。⑤名姓。
除了明确标注词性的义项③和义项⑤以外,其余均非词义,但仍需列项说解,故属于义项的范围。这样,作为音义结合体的单位,无论是词还是语素,只要是出现在辞书中的对其意义进行解释的分项,都属于义项。甚至对大于词的单位,如成语、歇后语、固定词组等的解释分项,也称为义项。如《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词组“舍生取义”、“常用对数”等,为此进行的专门解释同样也作为义项而存在。可见,义项的解释对象范围已经扩大,只要是辞书中对语素、词、词组的意义的解释都属于义项。
(四)义项解释的内容
义项既为辞书按字头、词头的不同含义分列的注释项目,那其解释的内容自然就是意义。人们常将义项与词的义位对应起来,认为义项是词义在辞书中的分项解释,是义位在辞书中的表现。但这个“词义”是否仅表现为词的理性意义?对于这一点,要先从词义说起。
符淮青(2006)曾列举了众多学者对意义的说解,并提出了自己对词义的看法:布龙菲尔德给意义的定义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起的反应”,但没有认识到“词义是一种同词的语音形式联系的思想意识形态”,没有看到“语言对词义的表述的性质和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维特根斯坦从“操作论”的角度看待意义,认为“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应用”,他这种企图用“用法”来代替“意义”的做法同样是欠妥的。“词的意义指词所反映的有关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点,词的用法指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能同哪些词搭配,能出现在哪些语境中”,应称为“功能、分布”,不能混淆两者的界限。最后符淮青陈述了一个事实:人们是在考察词的各种用例中分出不同的意义,借助于生活经验和科学认识去概括说明各个词义所表示的各种事物现象的一般本质的特点。据上说,词义的定义可以归纳为:在词汇系统内,一个词在构成句子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过程中所承担的意义。蒋绍愚(2005)结合古汉语词汇将词义分为六类:理性意义、隐含意义、社会意义、感情意义、联带意义、搭配意义。张志毅、张庆云(2001)用基义和陪义对词义进行分类,大概相当于理性意义和附属意义。李运富(2010)认为对词义应从词的语义属性和使用属性两方面加以认识,语义属性是针对词的理性意义而言,使用属性包括词的使用语境(语法功能、语义搭配),使用语体(书面、口语、文言、白话),使用语义(附加义、修辞义),使用范围(地域、时代),使用频率等方面。
我们赞同李运富的观点。对于实词而言,其语义属性占据主要地位,它是义位之间相互区别的基础,必然也就是义项区别的根据。如《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均将“典章法度”与“纲常、伦常”两个义项区分开来,就在于二者的理性意义有明显差异,我们列表来分析其理性意义。

义项 类别 属别 功用 产生 内容 特征典章法度 名物法律制度规范约束,维持社会稳定、正义国家政府涉及国家和个人一切行为的制度稳定、公正、约束力纲常、伦常道德标准规范约束,维系人际关系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 稳定、约束力
除了理性意义对义项具有决定性作用外,还要考虑使用属性对其产生的影响。如《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常性”条的解释“一定的习性”标明了“〈书〉”,以此指明其使用的语体为书面语;《辞源》对“常山蛇”的解释“喻一种阵法”,则指明了其修辞意义。对于虚词来说,理性意义已经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其功能和分布即在语境中表现出的语法意义则起着决定作用。如《汉语大字典》“从”:
⑰介词。(1)表示起点,相当于“自”、“由”。(2)表示对象,相当于“向”。(3)表示原因、途径,相当于“因”、“由”。(4)表示任凭。
这一类语义空灵的虚词义项,就必须从功能和分布上加以注释。
可见,义项所解释的内容就是意义,对词而言,部分与义位相等。因此,解释的内容就不单限于理性意义一端,尤其对于虚词,对其语法意义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义项的解释内容包括被释对象的语义和语用两方面。
(五)义项所释内容的范围
由于义项出现的典型环境是多义词,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谈及义项时首先想到的是多义词的义项。关于多义词,通常认为是指“包含互有一定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多种意义的词”(胡明扬等1982)。也正因如此,使人们误认为义项是多义词的专属,义项的内部要有“共同义素相维系”。这里由于混淆了义位和义项的概念,出现了两个认识上的误区:(1)义位由义素组成。义项中没有义素,故无须用“共同义素相维系”;(2)义项之间互有关联。义项是辞书对所释内容的处理手段,对于词义的解释而言,引申义列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故除要参照词义的引申义列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汉语的词义发展是一个连续统,属于一个泛时的概念,在一个词的引申义列之中,既有依托于同一词形的多义词的各个义位,也有不同形(包括不同音和不同字)的同源派生词,如上举《六书故》中“张”的各同源派生词。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庞杂的微观词义系统。然而语文辞书编纂通常以词形(或字形)为纲,若将一个个微观词义系统纳入,会给编纂和使用造成很大的不便。
因此,作为一个操作概念,义项是辞书编纂者对被释对象意义的一种技术处理。在建立义项时,并不将其内部语义联系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义项的解释对象打破了多义词引申义列的限制,只需将与该词形(字形)有关系的意义一并纳入,那么就不必受制于意义间的关联。本义(包括词的本义和字的本义)、基本义、引申义(包括比喻义)、假借义,以至于在共时层面难以建立联系的姓氏名、地名、专科名等都属于义项的解释对象。否则,对于不在基本引申义列中的意义,如《汉语大字典》所列的“常”的首项为字的本义“衣裳”,该如何指称;对于通假义的解释,如《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对“常”通“尝”的解释项及“姓”义,又该如何指称?
义项虽最先作为对多义词意义的分项解释,但是后来所指范围有所扩大。若被释对象(语素、词、固定词组等)是单义,或是辞书中只列出的一项释义,也应称为义项。如《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对单义词“常识”的释义“普通知识”,是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对“常数”只列出一个释义“表示常量的数”,也是义项。由此,我们认为义项不是多义词的专属,而是超越引申的界限,即对于没有引申意义的单义语言单位及不限于引申意义,还具有假借意义的语言单位的释义项目都归于义项。
(六)义项的性质
义项是在辞书中对注释对象的不同意义的注释项目。然而,我们看到不同辞书对同一被释单位所列出的义项却并不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原因何在?这就需要对义项的性质进行讨论。
1.义项的概括性与区别性
首先,义项的概括性不等同于意义(词义)的概括性,这需要从语义(词义)学和辞书学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从词义学角度来看义项的概括性,有两方面:(1)词义反映概念。概念的形成是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词义内容是在概括某类客观存在的普遍特征,并舍弃那些个性化的具体特征之后形成的。如对“人”的解释,在不同的辞书中表现不同。
《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辞源》:①人类。能创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改造自然的动物。
《现代汉语词典》:①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汉语大词典》:①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用语言进行思维的高等动物。
可见,不同的辞书在解释“人”时,力图排除民族、性别、年龄等属性,仅表现能概括“人”这个概念的本质属性,从而揭示“人”这个词的概念内涵,使读者获得关于人的正确认识。
(2)词义抽象语境义。语言中的词处于两种状态,一是使用状态,一是贮存状态。前者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使用的意义,它是具体的、灵活的、单一的;而后者则是收录在辞书中的词义,它具有相对的概括性、稳定性和丰富性。因此在参考古代训诂材料为辞书建立义项时,一定要将词义注释和文意注释区分开来,防止语境义的阑入。
从辞书学角度来看义项的概括性,实际上是在编纂过程中根据辞书的规模、属性等对义项进行的加工处理,即以客观意义为基础,将相邻的或意义相近的义项进行减省和归并。如“常”条在《辞源》和《汉语大字典》中义项的数量就有较大区别:
《辞源》例见本文第三节。
《汉语大字典》:
①同“裳”。裙子。②常规;常法。③纲常;伦常。④规律。⑤本质。⑥古旗帜名。上绘日月图形,为天子之旗。⑦车上所树之戟。⑧永久的;固定不变的。⑨一般的;普通的。⑩日常的。⑪副词。经常;常常。⑫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两寻为常。⑬木名。指棠棣。⑭通“長”。⑮通“尝”。副词。曾经。⑯通“尚(shàng)”。⑰通“祥(xiáng)”。⑱用同“嫦”。⑲古地名。在今山东省微山县东南。⑳水名。指常水。㉑姓。
两部辞书性质不同,《辞源》重源不重流,故无须将所有义项全数列出,只需选取典型或常用的义项,并且尽量增强每一义项的概括度。如义项②就包括了《汉语大字典》中的义项②③,这也是概括性的表现。
义项在体现概括性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其区别性。即义项与义项之间,一定存在某方面的根本差别,或体现在语义上,或体现在语用上,通过意义分析和语感都能获得的差异。在同一语境中,所对应的义项不能出现或此或彼、可此可彼的情况。应该说,“义项的概括性与可区分性,义项的概括与区分过程,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汪耀楠1982)。
2.义项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意义是客观的,由此推导义项也应该表现出客观性。这已成为共识,无须赘述。
然而,义项又是主观的,这与词典编纂者对意义的主观认识和表述直接相关。换句话说,义项的存在具有客观性,而义项的呈现却具有主观性。这一方面受到编纂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即在语义学层面对意义的认识和分析;另一方面,义项既然是出现在辞书中的语义解释,就必然要契合辞书的编纂需要。关于义项解释的对象、内容,我们已经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由此归纳和整理得出的应是义项的应然状态。也就是说,针对义项的解释对象(语素、词、词组),应该将以其为“字头”、“词头”的所有意义一并列出,包括本义、基本义、引申义、假借义等。然而,每部辞书会根据自己的规模、属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取舍或归并,这属于义项在辞书编纂中技术处理的不同。
事实上,对义项的研究要在三个层面进行,一是存在层面,二是表述层面,三是呈现层面。“存在”考虑的是义项的有无,即义项的应然状态;“表述”考虑的是将存在的意义转化为语词形式;“呈现”考虑的是选择哪些表现“存在”的“表述”示人。这分別涉及义项的建立和释义问题,关于这些,我们将另文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义项作出较为全面的界定:义项是字典、词典中的一个基本释义单位,是字典、词典中收录的作为字头、词头的语言单位的不同含义分列解释的词义项目。区别于义位,义项是释义单位;以字、词典收录的语言单位为对象;以字头、词头为统领,以不同含义为指归。
附 注
[1]例引自管锡华:从《尔雅》的多义项谈到辞书多义项的起源和性质.辞书研究,1988(4).
[2]例取自邹酆:中国辞书学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3]例取自邹酆:《字汇》在字典编纂法上的创新.辞书研究,1983(5).
[4]例取自丰逢奉:《康熙字典》编纂理论初探.辞书研究,1988(2).
1.《辞书编纂基本术语·第一部分》国家标准发布·辞书研究,1996(2).
2.辞源修订组.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丰逢奉.《康熙字典》编纂理论初探.辞书研究,1988(2).
4.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管锡华.从《尔雅》的多义项谈到辞书多义项的起源和性质.辞书研究,1988(4).
7.汉语大词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8.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
9.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10.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李运富.汉语词汇意义系统的分析与描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潘竟翰.义项的属性与界定.辞书研究,2000(5).
13.戚雨村.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14.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汪耀楠.多义词义项的概括与区分.辞书研究,1982(2).
16.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17.王粤汉.关于“义项”认识的歧异.湖北大学学报,1991(2).
18.许慎(东汉).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
19.张清源.谈义项的建立与分合.词典研究丛刊,1980(1).
20.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2.邹酆.论义项的概括与“分合”.辞书研究,1980(4).
23.邹酆.《字汇》在字典编纂法上的创新.辞书研究,1983(5).
24.邹酆.中国辞书学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