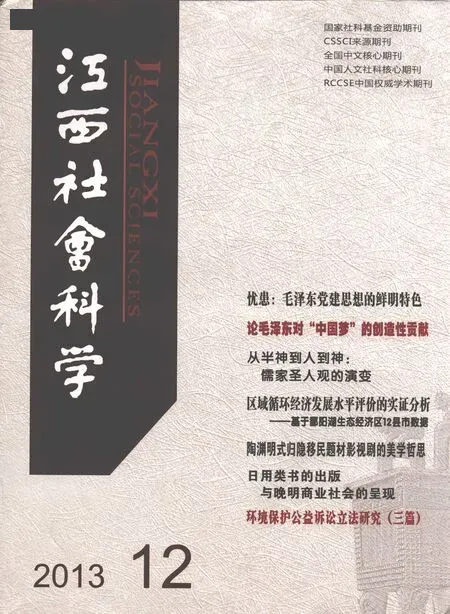我国公共生活的嬗变
——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论述为视角
熊 涛 陈付龙
我国公共生活的嬗变
——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论述为视角
熊 涛 陈付龙
审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下公共生活嬗变的中国图式,是找寻公共生活现代应然样式的有效切入。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论述来看,我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呈现出人的依赖性存在下的蛰伏异化、人的独立性存在下的虚热畸变、人的共生性存在下的公意确证的图式变奏。这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运用,也是分析我国社会公共生活图式的科学切入。
公共生活;蛰伏异化;虚热畸变;公意确证
熊 涛,南昌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副教授;
陈付龙,南昌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99)
公共生活是指人们在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内展开的各种活动,是具有规避国家或市场吞没社会之功能的一种介体生活运行的实践状态。公共生活是有“主体”的公共生活,与人的存在生态密切相关,审视人的不同存在状态下公共生活嬗变的中国图式,是找寻公共生活现代应然样式的有效切入点。本文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三个阶段的论述,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1](P104),来管窥我国社会公共生活的表征,这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代运用,也是分析我国社会公共生活图式的科学切入。
一、人的依赖性存在:公共生活的蛰伏异化
人的依赖性存在是以传统社会为蓝本,以血缘、宗法为基础,以家庭为经、土地为纬的前主体性存在。在传统中国社会,“向土里讨生活”[2](P6)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内涵和表征,个体并未呈现现代意义上的 “自我”、“独立”观念,而是呈现血缘、宗法逻辑下“差序格局”式的“依赖性存在”。
人的依赖性存在下公共生活呈现的蛰伏异化图式,一是公共生活的蛰伏。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权力介入的有限性使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间出现了权力 “真空”,也即出现了所谓的“士绅社会”。“国家—士绅—民众”的架构正好与人的依赖性存在相契合,满足“皇权不下县”的乡里民众依附的心理诉求。“士绅”阶层在其中担当着政府与社会的“润滑剂”,既维护着国家的权威统治,又主持地方公共事务,成为连接“官治秩序”与“乡土秩序”的支撑点。二是公共生活的异化。人的依赖性存在下现代意义上的“公”并未彰显,作为介体生活运行的实践状态,公共生活也并未以现代公共利益为旨归。“公共性”的本真被褫夺,公益并未得到有效确证,进而呈现公共生活的异化与偏失。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枢纽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但其与当时体制相抗衡的现代功能阙如,“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3](P272)。统治者的意志常左右着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且把自己当作子民福利的关怀者来操纵或运用民众的公共理性。
人的依赖性存在下社会公共生活呈现的蛰伏异化的图式,主要由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君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理念的文化观念三者共同作用而成的。
首先,传统中国“向土里讨生活”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一是狭隘封闭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可摆脱地受土地和生育的自然发展约束的关系,在时间上表现为血缘性的,在空间上表现为地缘性的约束关系。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民生活世界的坐标。 ”[4](P33-34)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下缺乏广泛的交往,商品交换和商业贸易无法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场域的经度和纬度严重受限。二是熟人社会为主的公共生活场域。个体的生活格局以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展开,公共生活场域亦基本是以“差序格局”不断推展,公共生活不是运用公共理性来关注与投入公共事务,而是以血缘、亲情为标杆在熟人社会中展开,“公共生活基本上是基于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5]。熟人社会中的公共生活与现代意义上的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公共生活存有某种程度的偏差。三是血缘宗法为主的公共生活纽带。“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概延续极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产生在这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 ”[6](P237)宗法主义的面纱笼罩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公共交往常常是血缘宗法关系思维的外延,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更多是血缘基础上的情感、直观等自然因素的推动。
其次,传统中国“君权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是公共参与与“君权至上”的不匹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公共参与既被界定为 “与君争位”、“与君争权”、“与君争利”,也被界定为“不必要的恶”,公共参与的虚空、政治系统的封闭性使社会权力难以得到制度性介入,民众参与公务事务的意愿和行为常常受到掣肘。二是以监督与制约君主权力为取向的公共理性的不正当。公共理性以“正义”为准则,以监督与制约君主权力为取向,是公共生活中的理性运用。然而在“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公共理性之“正义”取向难以为继,其对君权的制衡、制约也会被定义为不正当,由此公共理性只是异化为无病呻吟的哀怜或是虚设的“花瓶”。三是公共生活空间的窒息。“君权至上”即权力集中于 “皇帝”一人,普通大众在“皇帝”权力的施予下求得生存与发展。公共生活空间是在权力与权利统一的主体互动中建构的,被施予权力的普通大众既非合格的公共生活主体,也无法建构公共生活空间,公共生活空间在单向权力导致的权力与权利失衡的体系格局中难以逃脱窒息的宿命。
最后,传统中国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理念的文化观念。一是主体性的退隐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无以探寻。传统社会个体在“君臣”、“父子”、“三纲”的伦理教化下成为非独立人格的 “顺民”,而公共生活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基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而开展的生活,“顺民”式的主体性退隐与人的依赖性存在使得公共交往与公共生活难以凭借公共理性而进行。二是纲常伦理文化下独立意识的缺失。传统社会以直观、感性的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对自然、神和社会依赖极大,在独立意识普遍缺失、纲常奴性人格被美化的背景下,基于现代公共理性的公共生活自然无以开展。三是礼教文化下实则没有 “公众的公共”。中国传统社会以“礼”治教,孝道礼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涵,在孝道礼教文化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因官员的以国当家而被剥夺。尽管有因道义而舍生取义,因族际伦理而修建土木、组织捐款和兴建公共工程,因人际情义而组织公共事务、捍卫公共福利等公共生活的胚芽,但以现代公共生活的应然样态审视,它们都不是以公共理性的运用和公众的公共利益获得为取向,因而没有 “公众的公共”,只是打着“公共”幌子的家族式生活。
二、人的独立性存在:公共生活的虚热畸变
人的独立性存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业缘为经、职业为纬的主体性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个体从封建秩序的禁锢中脱嵌,成为独立的主体,谱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篇章。然而由于基本承袭了苏联模式,政治化和行政化成为当时整个社会生活运行的轴心。从某种程度而言,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错位,以高度的政治整合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以政治逻辑主导社会生活为样态是这一时期人的独立性存在的社会表征,造就了我国公共生活在某些范畴和层面上出现了虚热与畸变。
一是公共生活的虚热。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的解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获得了解放,人们的公共交往空间得以重构和拓展,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高涨。为了尽快兑现社会主义的庄严承诺,通向共产主义的幸福彼岸,政治逻辑异化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主宰力量,人们豪情万丈地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公共生活如同洪水猛兽,以排山倒海之势呈现出追求公共利益的道德虚热,“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乃为最佳诠释。二是公共生活的畸变。在我国“越革命越进步、越破坏越革命”的极 “左”思维循环“怪圈”中,极力否定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人的独立性逐渐异化,导致公共生活缺乏、公共理性的运用偏离现代性轨道。这期间的社会公共生活几乎是在“权力指令”中走上舞台,成为政治斗争的装饰品和权力疯狂运转的替代品,个体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受到抬举的奴隶”(马尔库塞语),尤其是在十年“文革”中,社会历史步入一种主体性退隐的“无主体”阶段,公共生活更是沦落为被政治逻辑主宰的日常生活政治化运动,呈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畸变。
人的独立性存在下社会公共生活呈现的虚热畸变的图式,主要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型文化模式三者共同作用而成的。
首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是资源的国有垄断使社会发育不良。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和偏差,“私”被视为“恶”的“同义词”,“公”被奉为“善”的“同义词”,公私之间的张力被严重扭曲。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引导下,资源被国家全面垄断,人们基本无资源可直接支配,国家与社会之间基本处于一种 “零和”博弈状态,整个社会发育程度极低。二是经济的内卷化使自由空间流动不足。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造成了人们“市场选择”的“缺席”,造成了经济能力的单位化、公社化等内卷化表征,而且强化了 “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和国家对社会的全方位统摄,在“单位人”、“公社人”的符号下,个体的自由流动空间被极大束缚。三是计划式指令使公共生活动因缺失。在经济运行机制中,指令执行成为经济管理的重要表征,“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7](P78)。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挤压至极限,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属于国家权力范畴,正如列宁所言:“我们不承认任何 ‘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私法范围。 ”[8](P587)由此,直接从事生产和管理的个体只是大机器中的小零件,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扼杀,公共生活的物质动因脱嵌,呈现出物质基础脱嵌的道德虚热与畸变。
其次,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一是权力魔棒的渗透使公共场域难觅。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党、国家、社会形成一体化格局,权力触角无处不在,生活世界异化为权力窠臼,主体意志沦为权力指令的自动表达,人们被动或主动地安眠于“权力”的母体怀抱中。公共场域相对封闭、公共空间或公众领地亦往往演化为政治场地,公共生活难以寻得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在公共场域展现的公共话题、公共活动等也往往是权力重新编码的缩影和对权力存在的确认。二是 “单位人”、“公社人”下公共生活的难以为继。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的“单位制”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把人们严格束缚在其所在的区域中,人成为“单位人”、“公社人”,身份认同与党政组织紧紧拴在一起,具有与公权抗衡性质的公共领域皆难以为继。公共空间异化为单位空间,公共生活异化为政治宣泄的渠道。三是泛政治化下公共生活的无奈与无助。在社会主义运行偏轨的机制下,泛政治化萦绕生活的每个空间,社会生活常被贴上 “政治标签”,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实则是群众缺乏自主的、非民主式的一种狂躁表现,每个人均是主动或被动地绑在“政治逻辑”主宰的社会生活中,他们的意识和行为都是按照政治逻辑的特殊要求而被加以整合。
最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型文化模式。一是革命政治伦理教育膨胀下公民身份认同的萎缩。“公民”异化为 “人民”,“公民”身份认同异化为 “人民”身份认同,是当时人们身份认同的主要表征。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是 “把对集体和权威的铁的纪律与竞争化的顺从行为作为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9](P21)。 教育的内容、方式、手段都被严格控制,无产阶级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内涵,公民教育的内涵严重式微,并异化为一个凸显革命政治伦理取向的特定政治符号,陷入“泛政治化”误区。二是政治主宰一切文化形态下公共观念的虚无。政治成为一切活动的主旋律,文化生活主题不再是精神家园的耕耘,而是演绎政治逻辑的炫目舞台。人们看似是政治生活的主人,实则更多是政治逻辑叙事的“奴隶”或“革命”逻辑叙事的“附庸”,个体利益的正当性诉求也被当作是 “自私”替代品的政治思维方式,由此社会诸多领域呈现公私两无的尴尬局面。三是意识形态泛化下“公”的异化与偏失。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某些别有用心之徒扛着“公”的大旗,企图规范、控制人民群众的思想世界。这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和大功告成,实则执行着一条 “彰显主体性→消解主体性→使人成为纯粹客体”的软权力指令,在执行这个指令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被自己镜中的形象迷住了”[10](P216),成为权力的盲从者或追随者。公共理性被掳掠和操纵,公共生活的公共性本质发生偏离与异化。
三、人的共生性存在:公共生活的公意确证
人的共生性存在即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人格为基础,以权利为经、共生为纬的主体间性存在。随着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建设全面展开,主体间性取代了狭隘的、极端的主体性,个体之间的主客二分关系转向“主体—客体(文本)—主体”的新型交互主体性,共生性存在成为人的生存样态的主要表征。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那种反对公共权力的强制以促进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文化群体,而是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错用与滥用的同时反对资本和市场的强制,以保证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文化群体。
人的共生性存在下社会公共生活走向公益确证。一是公共生活趋于理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权责对等观念渐趋生成,民族视域与全球视域的交融,公共生活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私下议论、私密窥探、政治调侃、政治新闻等,而更多是现代公民个体或公民群体自由、正规、合法地向国家或社会进行的 “价值输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二是公共生活寻求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公共权力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一方面,规避了公共权力向私人领域的扩张,避免“公民”成为虚幻的服从主体;另一方面,也规避了私人领域向公共权力的渗透,防止“公民”成为无聊的作秀主体,这不仅体现公民应有的“公共精神”,而且体现着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公共责任和公共关怀。
人的共生性存在下社会公共生活呈现的趋向公意确证的图式,主要由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主动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三者共同作用而成的。
首先,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不仅促进了以独立、自由、平等、公正等人格为基础的现代性观念谱系的建立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逐步走向完善,为现代公共生活的发展提供客观前提。一是政府角色的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政府充当 “服务者”和“裁判员”之角色的进一步确证,从管理型职能转向服务型职能,从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政府不再全面垄断经济社会资源,也不再是资源和利益配置的唯一主体,其主要职能是强化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产品和发展公共事业,从而为社会的良好发育创造前提和基础。二是公共生活场域的拓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市场和社会提供“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空间”也开始渐趋形成和拓展,公共生活的场所也得以健康发展。三是公民精神的生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传统的 “臣民”、“私民”、“人民”、“顺民”等角色逐渐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市民”与“公民”的双重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较好的统一,“商赋人权”与“法赋人权”得到了较好结合,有认同、有批判、有质疑、有责任等现代公共生活所诉求的现代公民精神得以生成。
其次,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揭示了我国民主政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 “民主政治、和谐政治和合作政治”的有序发展,为现代公共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土壤。一是国家权威性和社会自主性在我国公共生活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更加突显。公共生活从过去以“党政权威”或社会转型期以“社会权威”为中心的单向建构转向以 “国家权威和社会权威”为中心的双向建构,各社会群体、政党、阶层和大众等在公共生活参与中能够互动、合作,推动公共生活的现代转型。二是权利与权力的有效对接更加突显。权利更多地指向价值理性的肯定,权力更多地指向工具理性的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为权利尊重、权利服务和公共权力运用、公共利益服务提供良好的政治保证,使公共生活能够以法治为导向而展开。三是公共生活参与主体的多元互动更加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社会群体、政党、阶层和大众等共同合作的多元一体的政治。为此,交往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等不再是“劣势话语的沉默”和“强势话语的压制”,而是“劣势话语”与“强势话语”之间的交融、互渗等,公共生活不再是精英独唱、大众喧闹、强权压制和私利表达等,而更多是精英与大众相互呼应、共生共在的有序参与。
最后,主动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公共关怀、公共服务、公共参与等公共理念的塑造,为现代公共生活的发展提供文化动力。一是公共理性运用的文化土壤生成。“嘈杂”中浮现的许多当下公共舆论,不再是一种事实或信息的简单辩论或裁剪,而更多是情感投入与理性诘问的统一,从感性升华为理性,有序、理性、法制成为人们解决社会公共性问题的主要特点,人们更加注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统一,历史叙事与逻辑叙事的统一,开放宽容与理性精神的统一,等等。二是思想共识的价值引领。面对文化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既定事实,在“价值输入”与“价值输出”的博弈中,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从而为公共生活发展奠定思想共识。三是公共生活的主体基础形成。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是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义和现实使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公民主体不再是海德格尔笔下的一个互动符号,而是一个具有公共人格特质的概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同时代公民公共生活性质和范围不同,当代公民不仅生活在民族国家内,还生活在公民社会和全球社会中,因此,当代公民应当是权利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四重身份的统一。 ”[11]
总之,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论述为视角,考察我国社会公共生活的嬗变图式,不难发现,作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公共生活展现的样态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使然,从而呈现出人的依赖性存在下的蛰伏异化、人的独立性存在下的虚热畸变、人的共生性存在的公益确证的图式变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4]廖申白.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晏辉.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传统伦理的现代境遇[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
[6]李泽厚.探寻语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7]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9](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M].史继平,等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10](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冯建军.公民教育目标的当代建构[J].教育学报,2011,(3).
【责任编辑:赵 伟】
C911
A
1004-518X(2013)12-0230-0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生活建设研究”(12CKS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