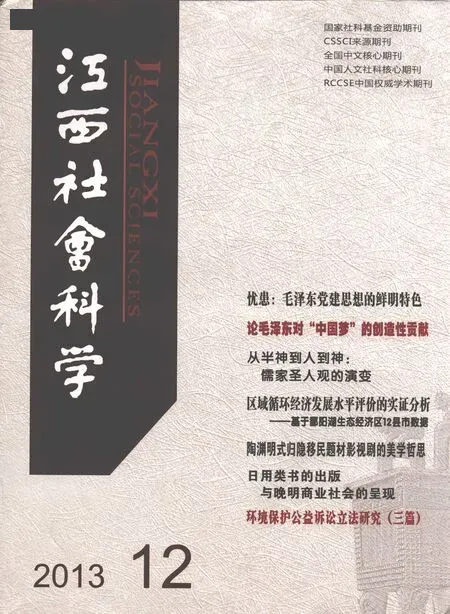论清代诗学思想的建构——以清代四大诗学流派为主要考察对象
■梁结玲
清人并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代之文学”。在入世的情怀倍受打击的情形之下,清人接受了丰富文学遗产的馈赠,他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了理论的支撑点,希冀为新时代贡献新经验。清代诗学理论的思辨性、集成性较前代更加明显。郭绍虞认为:“一到清代,由于受当时学风的影响,遂使清诗话的特点,更重在系统性、专门性和正确性,比以前各时代的诗话,可说更广更深,而成就也更高。”[1](P4)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诗文批评是清代的“一代之文学”。清代诗学思想是清人文学实践与反思的结果,其总结、集成的特征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人们只是注意到清代诗学对多元价值的兼容,忽略了他们在构建上的努力。有的论者甚至用目的论的社会史观直接标示清代诗学,认为清代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诗学必然是集成的。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忽视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过程性,没有认识到清人在价值判断上做出的艰难选择。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基本上代表了清代诗学理论的成就,本文以他们为考察对象,对清代诗学思想的集成性进行剖析。
一、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清朝以武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面对人口数十倍于自己的汉民族,统治阶级认识到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康熙宣布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将治统与道统合一:“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2](P899)明代心学的放荡并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程朱理学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纲纪。康熙说道:“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3](P239)乾嘉以后,程朱理学遭到了时人的批判,他们将目光放到了汉唐。有清一代的学人对明代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越过明代,试图在传统中找到儒学的真义。赵翼说道:“高青丘后,有明一代,竟无诗人。李西涯虽雅驯清澈,而才力尚小。前、后七子,当时风行海内,迄今优孟衣冠,笑齿已冷。”[4](P130)整体上来看,清人对明代文学评价并不高,认为明代的门户之争和盲目复古限制了文学的发展,他们自信能够从文学的传统中寻找到诗文发展的康庄大道,弥补明代文学的暗淡无光。正是鉴于明代文学的局限,清人对历代文学遗产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能够相对理性地批评各个时期的文学得失,汲取各时期文学的营养,结合时代的需要对文学进行权衡性的选择。纵观清代的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清代各个时期主流的诗学思想一方面都反映了传统诗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
王士祯批评了明末清初不良的门户诗风,“三十年前予初出交当世名辈,见称诗者无一人不为乐府,乐府必汉《铙歌》,非是者弗屑也;无一人不为古选,古选必《十九首》、《公宴》,非是者弗屑也。予窃惑之:是何能为汉魏者之多也?历六朝、唐、宋,以诗名其家者甚众,岂其才尽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尝著论以为唐有诗,不必建安、黄初也;元和以后有诗,不必神龙、开元也;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来,海内贤知之流,矫枉过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于汉魏乐府古选之遗音,荡然无复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识者惧焉。”[5](P74-75)王士祯对文学遗产进行了梳理,辑有《古诗选》、《五言诗》、《七言诗》、《五言今体诗》、《七言今体诗》等选本,对文学史的发展、得失有深入的了解。王士祯最终以“神韵”标举诗学是他个人的爱好和时代的需要。王士祯早年辑有唐诗选本《神韵集》,入仕后“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6](P203),晚岁再订《唐贤三昧集》。神韵诗派能够成为康熙年间主流的诗派,与历史的选择也是分不开的。清初宋诗曾风行一时,这股诗风是遗民思绪在诗歌上的反映,这与蒸蒸日上的帝国并不匹配。毛奇龄说道:“益都师相尝率同馆官集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谓开国全盛,自有气象,顿惊此佻凉鄙弇之习,无论格有升降,即国运盛杀,于此系之,不可不饬也。”[7](P2185)康熙喜好唐诗,认为:“诗至唐而众体皆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8](P163)王士祯受知康熙,成为诗坛盟主,这有其历史必然性。
沈德潜早年也钟情于唐诗,“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9](P1)。他辑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宋金元三家诗选》、《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通过这些诗歌选本,沈德潜构建起了中国文学发展史,而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也蕴含于史的构建之中。他在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古诗源》的序中说道:“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犹观海者由逆河上之以溯昆仑之源,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10](序页)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也说道:“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也。自陆士衡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奉以为宗,要惟恐失温柔敦厚之旨。……选中体制各殊,要惟恐失温柔敦厚之旨。”[11](序页)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打通了古今诗歌,找到了诗学发展的指南。格调说重诗教,宗唐而不废宋,与蒸蒸日上的帝国交相辉映,深受乾隆的推崇,成为乾隆前期主流的诗学流派。
袁枚和翁方纲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辑选历代诗歌,但他们对文学史有充分的认识,主张兼取各种风格。袁枚对沈德潜过度注重诗教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说:“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诣之所极,原不必兼众体。而论诗者,则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题之所宜。……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12](P1505)袁枚反对狭隘论诗,认为艳诗也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并不违背言志的传统,应该给予尊重。抓住了诗歌抒情的特点,袁枚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13](P146),“性灵”成了袁枚解读文学史的最终注脚。郭绍虞先生将“性灵说”当作中国传统诗学的集成。他说:“《虞书》言‘诗言志’,《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凡一切言诗以言志的论调,都可以是性灵说的滥觞,《诗序》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赋》言‘诗缘情而绮靡’,凡一切言诗以宜情者,也都可说是性灵说的滥觞。”[14](P441)因此,他对袁枚的“性灵说”评价很高:“所以公安、竟陵之诗论,犹易为人所诟病,而随园之诗论,虽建筑在性灵上面,却是千门万户,无所不备。假使仅就诗论而言,随园的主张却是无可非难的。”[14](P470)袁枚以“性灵”总结了文学的基本经验,他将“言志”、“缘情”的诗学传统都纳入自己的诗学思想中,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开启了乾嘉抒写真我的性灵时代,完成了诗歌平民化、大众化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翁方纲论诗具有开阔的视野,他以“理”沟通了经学与文学:“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15](P210-211)因此,在他看来,诗言志其实就是阐发义理,“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15](P211)。翁方纲的肌理说从本质上而言与理学家的诗论并无太大的区别,然而,在乾嘉考据学鼎盛之际,肌理说印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翁方纲认为:“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15](P211)用经史考据弥补诗文的空疏,从而将“理”落到实处,这就将诗文与时代学术融合在一起。
明代文学给了清人一个直接的教训,以致清人在诗学理论构建的时候不断地回顾整个文学史,用先典来为自己的理论作注脚。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中土以前,清人的诗学理论其实是用阐释的眼光把历史当代化了,清代各个时期的诗学思想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学术文化、经济生活等现实问题有紧密的联系。
二、传统审美范畴的融汇与提升
中国的诗学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许多审美范畴,这些审美范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涵,日趋成熟。清代诗学思想虽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但都能够在汲取历史营养的同时进行融汇、提升,使传统的诗学范畴更显精致、完满。
王士祯对严羽、司空徒等人“别裁”、“别趣”、“味外味”的诗论赞赏不已,并以此为审美取向,厘定了《唐贤三昧集》。王士祯虽然论诗多捏出“神韵”二字,但他的神韵说却不止于妙悟论,而是一个以妙悟、韵味、禅趣为主,同时兼容多种风格的诗学理论。《唐贤三昧集》不选李杜,人多以为神韵仅为平淡闲远的诗风,王士祯对此回答道:“严仪卿所谓‘如镜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盐味,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皆以禅喻诗,内典所云‘不即不离,不粘不脱’,曹洞所云‘参活句’是也,熟看拙选《唐贤三昧集》自当知之矣。至于议论、叙事,自别是一体,故仆尝云:五七言诗有二体,田园邱壑当学陶韦,叙铺感慨当学杜子美《北征》等篇也。”[5](P836)可见,神韵说并非只有一种风格。其在评论唐宋大家的时候说道:“余偶论唐宋大家七言歌行,譬之宗门,李杜如来禅,苏黄祖师禅也。……七言歌行,至子美、子瞻二公,无以加矣。而子美同时,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剙闢经奇;子瞻同时,又有黄太史之奇特。正如太华之有少华,太室之有少室。”[5](P41)王士祯对“鲸鱼碧海”的诗风并不排斥,神韵说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其内涵是丰富的。翁方纲评论说:“渔洋先生所讲神韵,则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此道至于先生,谓之集大成可也。”[16](P1427)
沈德潜感慨诗歌政教传统的失落,认为只有“仰溯风雅,诗道始尊”[17](P186)。他提倡温柔敦厚的格调,以挽救颓败的世风。沈德潜追求诗歌的教化功用,但他与道学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他充分尊重人的合理情感,主张用诗歌表现人性美好的地方,“窃谓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风格者,本乎气骨者也;神韵者,流于才思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18](序页)。这样,沈德潜便把“理”与“情”糅合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沈德潜的教化是建立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应该以艺术的方式感染人,“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讬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17](P186-187)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而且把两者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这是正统诗论的最好总结,也是格调说的不朽之处。
如果说沈德潜是“诗言志”传统诗论的总结,那么袁枚便是“诗缘情”理论的集成了。性灵说首重性情,但这性情不是“万古之性情”,而更多的是“一时之性情”、“一人之性情”,关注个体的个性情感。袁枚对理学多持怀疑的态度。他说:“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过敬邻叟,而忘其祖父之在前,可乎?夫尊古人者,非尊其名也。其所以当尊之故,必有昭昭然不能已于心者矣。”[12](P1563)袁枚不满于理学的空洞说教,他所说的“昭昭然不能已于心者”其实便是人的基本情感,诗歌要表现的便是这种情感。“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13](P2)将个人情感置于诗歌创作的首要位置,这是性灵说超越传统诗论之处。明代公安派也重个人情感,他们强调诗歌要表现日常的生活情感。袁宏道说道:“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口而出,信口而谈。”[19](P217)袁枚对这种俗化的创作感到不满:“诗如言也,口齿不清,拉杂万语,愈多愈厌。口齿清矣,又须言之有味,听之可爱,方妙。若村妇絮谈,武夫作闹,无名贵气,又何藉乎?”[13](P82)强调情感的雅与诗的韵味,这是袁枚与公安派的分野之一。同时,袁枚论诗重个体的才性。他说:“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诗,脱口能吟;其人之天无诗,虽吟而不如其无吟。”[13](P187)注重才性其实是注重个性的深层表现,它回答了个人内在因素对文学的影响,这就比一般的“缘情论”要深刻得多。袁枚性灵说具有现代个性解放的色彩,朱自清认为袁枚的“‘言志’的诗倒跟我们现代译语的‘抒情诗’同义了”[20](P35)。
翁方纲的肌理说为清代所特有,然而,这一学说却遭受了前人“影响的焦虑”。翁方纲将王士祯的神韵说当作诗歌的本质,“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着之也。神韵者,非风致情韵之谓也。吾谓神韵即格调者,特专就渔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其实神韵无所不该,有于格调见神韵者,有于音节见神韵者,亦有于字句见神韵者,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情致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此其所以然,在善学者自领之,本不必讲也。”[15](P346)既然神韵是诗学的圭臬,翁方纲为什么还要另外标举“肌理”呢?他自己说道:“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15](P341)以“肌理”充实神韵其实是以学问补充诗歌的空灵不实,这已经远离了神韵的精髓,翁方纲硬将“肌理”说成神韵,其实是为了兜售他的诗学。翁方纲的肌理说其实是学问诗论,是乾嘉学术在诗学上的反映,这一审美范畴反映了乾嘉学人在诗歌上的审美兴趣。翁方纲的诗集刊行时,深受学人推崇,“今闻其及门王君实斋、吴君兰雪诸子,编次其古今体诗为若干卷,一时之博学有文者争为序之”[21](序页)。翁方纲对苏轼、黄庭坚等人推崇备至,肌理说在内涵上与江西诗派是一致的,但肌理说梳理了神韵诗论,是在乾嘉“智知”主义的背景之下发生,这一范畴较江西诗派的理论更具宏大性。
三、辩证的文学观
主导明代诗坛的前后七子祖唐祧宋,门户习气很重,对文学史的发展往往缺乏辩证的眼光。清王朝虽然在政治上沿承明制,但对明代的学术文化却不认可。清人认为游谈不学是明代误国的原因之一,对明代的批判与反思一直是清人入思的基点。清人满怀信心对明代诗学思想进行了清算,他们对文学的发展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复变、唐宋取舍、古今等文学价值与方法的判断上更具辩证的眼光,避免了偏颇的倾向。
叶燮将文学发展史归结为正——变——复的循环过程。纪昀更是认为:“夫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22](卷九)文学的正变发展在清代基本上成了共识,简单的复古或否定传统都很难赢得市场。王士祯虽然对唐诗情有独钟,但他对宗唐而祧宋的做法很不满:“近人言诗,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如蛮觸氏之斗于蜗角,而不自知其陋也。”[5](P754)对于不同的表现方式,王士祯也能够兼取:“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5](P78)神韵说突破了门户之见,能够比较辩证地估量不同诗风的价值,理论上圆润丰满,没有留下太大的破绽。
沈德潜继承了传统的诗教理论,但重古而不轻今,重阴柔之美而不废阳刚之美,往往能够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中思索文学,不偏废一方。“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家之文,春华也。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亦即无舍春华而求秋实者。亦即无舍春华而求秋实者,惟从事于韩、柳以下之文而熟复焉,而深造焉,将怪怪奇奇,浑涵变化,与夫纡馀深厚,清陗遒折,悉融会于一心一手之间,以是上窥贾、董、匡、刘、马、班,几可纵横贯穿而摩其垒者。夫而后去华就实,归根返约,宋五子之学行且徐驱而轥其庭矣。”[23](卷十一)“春华”与“秋实”两者相依相存,不可舍此求彼,沈德潜的辨析富于辩证色彩,难怪袁枚说他有“褒衣大袑气象”。
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强调文学的发展变化,反对因循守旧。袁枚说道:“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12](P1502)辩证地辨析古今,防止了尊古卑今的情绪,这对促进文学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赵翼更是对当代充满了自信:“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24](P630)李杜诗篇经万口传诵已无新意,能够开创一代新风的只能期待新人,这种强烈的当代意识与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简单的复变论,显示了清人的自信。
翁方纲接过王士祯的理论,对唐宋均持肯定的态度,对各个时期文学的成就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孔子于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于韶、武之音,岂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节奏乎?抑且勿远稽三百篇,即以唐音最盛之际,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属,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谢、颜之作者乎?宋诗盛于熙、丰之际,苏、黄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直至明朝,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后,乃有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之说,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选体之说,五言不效选体,则谓之唐无五言古诗。然则七古亦将必以盛唐为正矣,则何不云宋言古
诗?而彼不敢也。”[15](P334-335)继承传统而更重创新,这给文学的发展注入强心剂,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肌理说虽然继承了江西诗派重学问的诗论,但翁方纲对学问与性情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人之为志,有不必繁言以含蓄为正者,亦有必以发抒详实为正者;所谓言岂一端而已,达而已矣,各指其所之而已矣。”[15](P291)正是对性情的重视,翁方纲反对“诗穷而后工”的说法,认为诗歌表现感情应当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得以穷达论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问诗论的不足。
四、结语
清代诗歌创作繁盛,诗歌创作数量远超前代,诗人遍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单是乾隆皇帝一人的诗歌数量就抵得上《全唐诗》。然而,清代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是对前代的延续,清人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诗歌样式。但清人在诗歌理论的构建上更具集成性,也更富成效。明代文学实践是清代最直接的文学经验,清人在反思明代文学中对文学史的发展、得失进行了辨析,表现出开阔的历史视野。清人在接受前人理论资源的同时进行了修复,避免了理论单一取向的偏颇,形成了浑厚、整一的集成风格。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面临着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马列文论、现当代文论等丰富的理论资源,如何整取合一,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是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清代的理论或许能够给我们以启示。
[1](清)王夫之,等.清诗话 [M].丁福葆,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清)朱轼,等.圣祖仁皇帝实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章梫.康熙政要[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4](清)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清)王士祯.渔洋诗话[A].历代诗话统编(四)[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7](清)毛奇龄.西河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8](清)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3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9](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清)沈德潜.古诗源[M].长沙:岳麓书社,1998.
[11](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3](清)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4]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5](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
[16](清)翁方纲.石洲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清)沈德潜,等.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8](清)沈德潜,辑.七子诗选[M].乾隆十八年刻本.
[19](清)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0]朱自清.诗言志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1](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2](清)纪昀.纪文达公遗集[M].嘉庆十七年纪树馨刻本.
[23](清)沈德潜.归愚文钞[M].乾隆年间教忠堂刻本.
[24](清)赵翼.瓯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翁方纲定武《兰亭》的收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