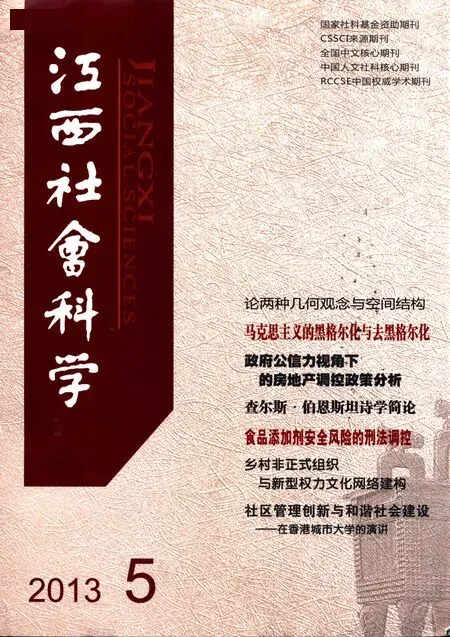山志编纂与古代庐山旅游活动
■龚志强
山志是传统舆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实用与增长见闻的功能而备受历代学者与各级官吏的重视。[1]我国众多风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的名山多有专志记载。庐山是我国第一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开发历史久远,既是一座文化名山,也是一座旅游名山,历代不乏专志记载。从笔者掌握的多种古代庐山志来看,其编纂、重修乃至发展演变均与旅游活动存在密切的关联互动,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古代庐山志的编纂与流传
古代庐山志的编纂与山区开发进程相适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庐山人文勃兴始于东晋,自高僧慧远而后,众多文化名流先后来到庐山,带来了地域文化的繁荣,一批专记庐山之作由此应运而生。其中,慧远所作的《庐山略记》(一作《庐山纪略》)被方志界认为是我国山志之始。[2]此外,东晋的王彪之、张野、刘遗民以及南北朝的宗测、周景式等人也分别著有《庐山记》。这些文献是庐山早期志书的代表,但可惜均已失传。
承东晋发展之余绪,唐宋时期庐山的宗教文化尤为繁盛。北宋晁补之有诗为证:“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缀蜜脾。”[3](卷十五《艺文下》,P218)宗教的繁荣助推了隐逸风气的发展,众多文人来到庐山隐居,对庐山知名度的提升大有裨益。同时,许多文人来庐山游览后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使庐山的文化底蕴不断积累,由此吸引了更多游人接踵而至。北宋王光远来庐山有诗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话胜游。”[4](卷二《地理类》,P29)在此背景下,宋元时期庐山出现一个修志高潮,先后有北宋陈舜俞的《庐山记》(五卷)、李常的《续庐山记》、马玕的《续庐山记》、释法琳的《庐山记》以及佚名的《庐山事迹》。稍后,元代的鲜于枢也著有《庐山志》。不过,由于年久失传,这批山志中仅有陈舜俞的《庐山记》流传于世。[5]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志书的重视使各地修志活动空前活跃,名山修志也掀起一轮高潮。这一时期,庐山开发进程也在国家政治、地方人口和旅游活动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不断深入发展。[6]明清时期出现的庐山志先后有明嘉靖四十年(1561)桑乔的《庐山纪事》(十二卷),清顺治年间释定的《庐山通志》(十二卷)、范礽的《续庐山纪事》,康熙七年(1668)吴炜的《庐山志》(十五卷)、康熙三十年查慎行的《庐山志》(八卷)、康熙五十九年毛德琦的《庐山志》(十五卷)和道光四年(1824)蔡瀛的《庐山小志》(二十四卷)等七部。可见,这一时期是庐山志书发展的高峰阶段。这些山志流传至今的有桑乔的《庐山纪事》、释定暠的《庐山通志》、吴炜的《庐山志》、毛德琦的《庐山志》和蔡瀛的《庐山小志》等五部,其中以桑乔的《庐山纪事》和毛德琦的《庐山志》流传最广,有记载的补订、重刊便分别达到四次和六次之多。
二、山志作者的服务游人意识
现存七部古代庐山志中,慧远的《庐山略记》、陈舜俞的《庐山记》、桑乔的《庐山纪事》和释定暠的《庐山通志》、蔡瀛的《庐山小志》为文人或僧人私修。另两部庐山志则分别是康熙初年江西提学佥事吴炜和康熙末年星子县令毛德琦主持编纂的,当属官修。无论私修或是官修,从编纂山志的动机来看,作者大多抱有明确的服务游人意识。陈舜俞的《庐山记》就是作者在遍游庐山的基础上编纂的,可谓因旅游而成。作者在书中写道:
余始游庐山,问山中塔庙兴废及水石之名,无能为予言者。虽言之,往往袭谬失实,因取九江图经,前人杂录,稽之本史,或亲至其处考验铭志,参订耆老,作《庐山记》。[7](卷二《叙山南篇第三》)
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北宋熙宁三年(1070)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王安石主持变法,“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责监南康军盐酒税”[8](卷三三一《陈舜俞传》,P10663-10664)。陈舜俞贬官南康后,在庐山周游穷览,寄兴于山水之间,但苦于山中诸多名胜无人能作介绍。有鉴于此,陈舜俞便着手编纂了《庐山记》。显然,编纂这部山志一方面是出于作者嗜古好游的个人兴趣,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传诸后世,以飨游人。
明清时期旅游风气盛行,庐山志作者服务游人的意识更趋明显。桑乔的《庐山纪事》是庐山志书中较重要的一部,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桑乔,字子木,曾任监察御史,因上书弹劾权臣严嵩遭陷害谪戍九江,时间长达二十六年。桑乔寓居九江期间,“往来庐山游憩,几诸名胜无不历览,所著有《庐山纪事》,简而核”[9](卷四十《流寓》,P4373)。可见,这部山志也是在作者亲身游历基础上编纂而成。尽管作者曾很自谦地说,编纂此书最初只是“聊以事娱,非敢传之作者也”,但他又转述朋友的话说明了刊刻书稿的缘由:“夫庐山亚于五岳而图记弗备,好古者有遗憾矣!是作虽芜秽,然姑以备览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订正焉。”[10](卷首《自序》,P1)所谓“好古者”,当然指的就是那些嗜古好游的文人士大夫。刊刻书稿供好古者“以备览考”,充分显现了该山志服务游人的目的。
至清代,庐山志的作者们几乎都明确表达了编纂山志服务游人的初衷。顺治年间,释定暠在其《庐山通志》中就曾说:“匡庐峰峦横溃四出,竞秀争奇,各为尊高,故峰峰有径,径径达岭,亦不可不告于游者也。”[11](卷二《山川分纪一·总论登山道路》,P53)这说明,该志的读者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游者”。其实,山志作者本人往往就是嗜古好游之人。康熙初年,吴炜主持重修庐山志时曾说:“自通籍以来,山水泉石之嗜未尝以剧。自挠兹抵豫章,□以匡庐志事自任,征购群籍,不惮僻远。”[11](卷首《凡例》,P7)这说明,吴炜主持重修山志也与其个人喜好“山水泉石”有关。同时,他又说:“今之志匡庐,大约广搜博访,务裒集古今瑰异,以补苴见闻之所不逮,使远在数千里外者,可以神游而心会。”[3](卷首《吴炜旧序》,P552)可见,作者在编纂山志时希望穷其详尽,以使人们即便不能亲来亦可持卷神游。康熙末年,毛德琦重修庐山志时更是明确表示,其主要目的就是使“庶几谢公之屐、卢生之杖不致迷途,即身未能至者,亦可挟册而当卧游”[3](卷首《自序》,P550)。由此看来,旅游需求正是推动山志编纂或重修的重要力量。
三、山志的旅行导览功能
山志作者服务游人的意识落到实处,便是山志旅行导览功能的实现。从篇目设置和内容编排来看,北宋陈舜俞《庐山记》的旅行导览功能已经比较突出。这部山志共分五卷八篇,分别为卷一《总叙山水篇第一》、《叙山北第二》,卷二《叙山南篇第三》,卷三《山行易览第四》、《十八贤传第五》,卷四《古人留题篇第六》,卷五《古碑目第七》、《古人题名篇第八》。作者首先对庐山地理形势和历史文化进行了概括,然后以游览线路为序对山中景观名胜展开介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卷三《山行易览第四》实际上是当时庐山的游览线路简介,人们照此即可畅游庐山南北。换言之,卷三就是作者为方便游人而特设的内容。最后,作者以较大篇幅辑录了有关庐山的各类历史文献以飨读者。
明代桑乔的《庐山纪事》是一部纂辑体山志,其特点是广收毕弋,类聚群分,集历代有关庐山的遗文旧志、游记图经、诗赋碑铭为十二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这部山志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旅行导览功能在前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加强。《庐山纪事》卷首配有插图,详细标明了庐山的地理形势及山中景观名胜等信息,游人可以按图索骥,更为方便地在山中游览。全志共十二卷,卷一《通志》分列山纪、品汇、隐逸、仙释、杂志、灾祥、怪异和艺文等目,卷二亦名《通志》下列登山道路及数十处名胜。作者介绍庐山名胜时首推山上的天池寺、御碑亭等处,原因在于明太祖曾在天池寺祭祀所谓的“周颠仙人”,使天池寺及其周边地带逐渐成为游人到访的中心地域。[12]作者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有意凸显天池寺在庐山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迎合了人们游庐山首选天池寺的需要。该志卷三至卷十二则按先山南后山北的顺序,以游线为纲对山中名胜进行介绍,上下连贯便是一条完整的游览线路。可见,这部山志就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旅游指南,一册在手便可畅游庐山。康熙四年,淮南人李滢“历览庐阜南北”,便“实赖兹编为向导”[11](卷首《李滢序》,P4)。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应用型院校的毕业生,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多。但与此同时,这些就业岗位对毕业生在职业素养方面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所以这也是高校面临的一个新的教育问题,大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体系能够为我校乃至吉林省同类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操作方案,切实增强大学生职业素养水平。
康熙初年,江西提学佥事吴炜主持重修的《庐山志》是庐山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山志,其体例严谨,克服了以往私修山志的某些随意性,卷首除序言和插图外,又分列凡例、重修庐山志爵里姓氏、诗文爵里姓氏考以及引用书目等内容。作为主持江西学政的官员,吴炜在修志时调集人力、财力及文献资料的力度空前。因而,这部山志博洽详明,刻板精良,总成洋洋十五卷。该志纲目在《庐山纪事》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卷一分列星野、舆地、祀典、隐逸、仙释、物产、杂志和灾祥等目,卷二至卷十三分别为山川分纪一至山川分纪十二,仍以游线为序介绍山中名胜,卷十四、十五分别为艺文上和艺文下。显然,吴炜《庐山志》的条理更为清晰,内容亦更趋详尽,其旅行导览功能较前志又有进一步提升。
康熙末年,星子县令毛德琦再次重修庐山志。这次重修山志,除少部分内容有所增补外,结构体例较吴炜的《庐山志》并无明显变化。毛德琦在序言中写道:
曲径不传,幽壑莫辨,则探奇猎胜者每多歧路之感。故必登峰有途,秒赏斯人。兹编面山南而背山北,以桑纪之勾采和吴志之考实,纵横备载,远近区分,挟册而求了若指掌,游山指南于是在乎。[3](卷首《凡例》,P571)
可见,作者编纂这部山志时兼采前志之优长,为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部实用的“游山指南”。当时,广饶九南道台龚嵘对这部山志极为赞赏:“(毛志)分是山为径者四,各祥所从入之途,某山水,某洞刹,就方位颠址,而挈其纲、条其目,俾游陟者不迷于向往,而群可搜殚其胜。”[3](卷首《龚嵘序》,P548)龚嵘的话说明,毛德琦《庐山志》在介绍登山道路和景观名胜时条分缕析,是一部非常实用的旅游指南。与此同时,江西按察使石文焯对这部山志亦给予了较高评价,其文曰:
世之蹑游屐随樵径极其所止,不裹粮涉月不能穷其奥。即穷之,以足之所经,目之所睹,而于庐山博大雄奇,求其犁然有当也,能乎哉?是殆游乎庐山之内,而未游乎志书之中也,志之为重于庐山有如此。[3](卷首《石文焯序》,P545-546)
由上文可知,庐山博大雄奇,要在山中穷搜博览实属不易,而山志却可以帮助游人全面深入地了解庐山。显然,石文焯的话也是从旅行导览功能的角度表达了对毛德琦《庐山志》的赞赏。
四、旅游对山志发展演变的促动
山志是一种实用功能突出的书籍,其编纂和重修往往体现了一种社会需求态势。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需求的变化也将对山志提出新的要求,由此促进山志的发展演变。清人李滢在参与吴炜《庐山志》的编纂工作时就曾说;
桑纪之成距今百年矣。其间事迹撰述颇增益于往昔,惜多散佚,无从稽考。且子木先生以旅寓浔阳,无由备典籍以稽往躅,其见于自序者常反复有遗憾。[11](卷首《李滢序》,P4-5)
这说明,尽管《庐山纪事》有不少优点,但由于作者条件有限,难免各种遗漏较多,加之已过百余年,一些内容已然不合时宜,重修山志实属必要。而毛德琦在重修庐山志时也曾说:
明侍御桑子木谪居九江,遍历博稽,仿《水经注》作《庐山纪事》,去今百六十年,书虽传而板蠹。向琦选都门,得吴粲叟山志,博洽详明,惜版亦不存,其书罕觏。今之通志为僧定暠所订,割裂旧本,文不雅驯,不足观也。[3](卷首《自序》,P549-550)
可知,当时桑乔《庐山纪事》和吴炜的《庐山志》已不容易得到,而释定暠的《庐山通志》又过于粗劣,不堪观览,所以毛德琦决心重修山志。李滢和毛德琦的话反映了一个共同问题,即重修山志是为了更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由于作者们编纂山志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服务游人,因此,正是旅游需求推动了古代庐山志的发展演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庐山志书的体例日趋完备,内容亦日渐丰富。作者们除不断收录有关庐山的各种文献资料外,还针对山区现实增加了不少描述性和考证性的内容。图文并茂、考订周详的山志固然可以更好地为游人释疑解惑,但山志内容过于浩繁厚重,又使人们登山游览时携带多有不便。清道光年间,九江文人蔡瀛游庐山,便深刻感受到“日检较毛志,秩累文繁,证以耳目,所经类多同异”。于是,他在毛德琦《庐山志》的基础上重修山志,“删补汇为若干卷,颜曰《庐山小志》”[13](卷首《自序》,P113)。蔡瀛的《庐山小志》尽管分列二十四卷,但实际篇幅较前志大为缩减,不及其三分之一。体例也有明显变化,卷首分列自序、插图、凡例、征引书目及方舆纂要、祀典纂要、登山道路等目,卷一至卷十二则仿《庐山纪事》以游线为纲、名胜为目展开介绍,其余各卷分列历代诗词碑记等内容。《庐山小志》简明精要,有效解决了山志中资料堆积过多的问题,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集中专纪名胜,嗜古者便于携带”[13](卷首《凡例》,P114)。可见,在旅游需求的推动下,山志已逐渐具备了现代旅游手册的明显特征。
此后,人们在旅游活动中对山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28年春,胡适与高梦旦、沈昆山等人同游庐山。当时,高梦旦带了一部吴炜的《庐山志》作为旅途参考,但胡适认为这部山志“篇幅太多,编辑又没有条理,一二百年前的路径是不能用作今日游览程序的”,因而“借得陈云章、陈夏常合编的《庐山指南》(商务出版社,十四年增订四版)作帮助”[14](P28)。如此看来,胡适即便得到蔡瀛的《庐山小志》也是不会满意的。因为,清末民初庐山经历大规模避暑地开发后,山上的牯岭成为人们在庐山的活动中心,山中游线也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了适应旅游需要,当时便出现了一批庐山旅游手册。这些旅游手册通常“以牯岭为游山中心,分叙山川胜迹”[15](P479),同时附有地图和照片,内容精炼生动,便于携带,能够更好地服务游人。1947年,方志学家吴宗慈便对吴子羽编写的《庐山卧游集》颇为赞赏,其文曰:
兹集以科学技术之摄影为之,可谓传其神而不遗其貌者矣。其取材约而精,其取携轻而便。游兹山者,得此一编,值天清气爽,固可伴游筇而作先导。[16](卷五下《艺文· <庐山卧游集> 序》,P949)
从旅游实用的角度来看,现代旅游手册的诸多优点是古代山志所无法比拟的。不过,古代山志仍然发挥着服务旅游活动的功用。仔细翻检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批庐山旅游手册便可发现,其体例和不少内容都是在古代山志的基础上采编而成的。可见,古代山志是编写现代旅游手册的重要资料来源。
由上可知,古代庐山志的编纂、重修乃至发展演变均与旅游活动密切关联。山志作者们大多抱有明确的服务游人意识,因此山志的旅行导览功能十分突出。同时,旅游需求的变化对山志的发展演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更好地满足游人需要,庐山志曾一度向图文并茂、考订周详的方向发展,但浩繁厚重的山志最终成为人们的旅游负累。清末,在旅游新需求推动下,庐山志转而变得简明精要,逐渐具备了现代旅游手册的明显特征。至民国,脱胎于古代山志的庐山旅游手册内容精炼,便于携带,很快成为游人的新宠,山志的旅行导览功能渐趋弱化,但山志具有体例严谨、内容丰富、信息量大等优点,仍然为旅游活动发挥着重要资料库的作用。
[1]石光明.明清时期山水志书的学术价值研究[J].农业考古,2006,(1).
[2]伍常安.历代江西山志述要[J].文献,1991,(2).
[3](清)毛德琦.庐山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明)单宇.菊坡丛话[M].续修四库全书本.
[5]李勤合.陈舜俞《庐山记》版本述略[J].图书馆杂志,2010,(10).
[6]龚志强,刘正刚.明清时期庐山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变化[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2).
[7](宋)陈舜俞.庐山记[A].罗振玉.殷礼在斯堂丛书(第9册)[C].北京:东方学会,1928.
[8](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康熙江西通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0](清)桑乔.庐山纪事[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1](清)吴炜.庐山志[A].石觉明,等.中华山水志丛刊(第25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12]龚志强,刘正刚.从明初庐山佛教信仰嬗变看国家宗教政策取向[J].宗教学研究,2010,(3).
[13](清)蔡瀛.庐山小志[A].故宫珍本丛刊(第260册)[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4]胡适.胡适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5]朱偰.庐山新导游[A].石觉明,等.中华山水志丛刊(第25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4.
[16]吴宗慈.庐山续志稿[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