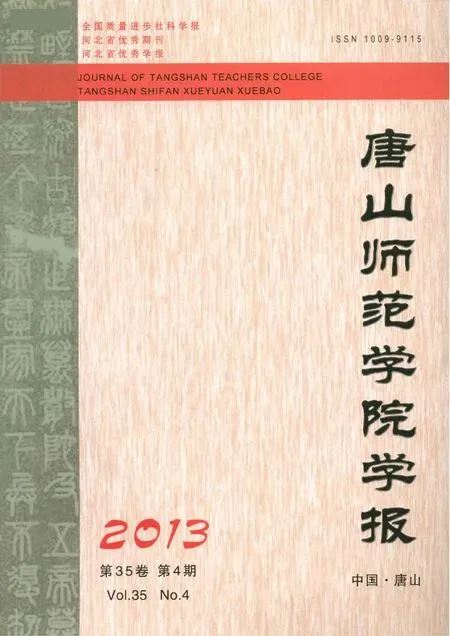激情源自孤独:论茨维塔耶娃抒情诗
刘 臻
(周口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南 周口 466001)
在茨维塔耶娃的抒情诗中,生活、爱情和死亡向来是贯穿诗人创作的永恒主题。在诗人涉足文坛之初,这些线索便已极其鲜明、且极富个性地交织出现在作品之中。“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祈祷》)诗人对死亡、爱情、自然,以及瞬息万变的生活的热衷仿佛是她一生写作的预言,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她狂热、敏感的诗人气质,对死生一致的彼岸的信念以及对超验的自然力的推崇。在近30年的创作生涯中,茨维塔耶娃一直执着于对生活与存在、世俗之爱与崇高之爱、现下与永恒的关系的思考,这些思考让她痛苦,但也推动了她绝然属我的创作个性的形成。
一
叶甫图申科曾评价茨维塔耶娃的诗是“男人的气魄,女人的心灵”。在不可遏止的激情的风暴中,诗人一直致力于以她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直觉来体察生活的细节,抒发心灵深处的感受。她擅长在对日常生活的诗性描述中捕捉瞬间、寻求发现,使原本庸常的一幕充满新奇的审美体验和微妙的情绪跃动。如果说,一般的诗人往往需要足够的等待,使自身关于诗的经验去将就诗歌的实际创作,那么,茨维塔耶娃无与伦比的充沛激情以及与激情同步的艺术技巧得以让她幸运地避免了这一创作滞后的缪斯陷阱,轻松自如地用女诗人特有的敏锐和细腻表现生活的种种复杂、微妙和延宕之处。而这种对生活细节的陌生化处理在茨维塔耶娃这里则主要体现为一连串的暗喻和换喻,她在塑造某一抒情主人公形象时,往往喜欢用不断变幻的比喻来界定形象并使之确切化。在著名的组诗《致勃洛克》中的第一节里,诗人这样写道:“你的名字是手中的小鸟,/你的名字是舌尖上的冰块。/嘴唇绝无仅有的一个动作。/你的名字是五个字母。/是被在飞行中接住的小球,/是口中银质的铃铛。”在这里,诗人使用了诗歌写作中“躲避真实”的小技巧,即对说出对方名字的禁忌,而我们也从中感受到诗人卓绝的直感和细致入微的敏锐:她用隐喻和通感说明她对勃洛克的推崇——手中的小鸟、舌尖的冰块、飞行的小球、银质的铃铛,以及独特的嘴唇动作和五个字母——这些因素虽迥然不同,但却在感觉上达成了质的和谐,给人以清脆、晶莹、颇具穿透力的印象。声响、外形、动作和语词在一段诗中相互应和,形成了悠长的回声,回荡于字里行间。
诗人臧棣曾在《绝不自然:我这样理解诗》中指出,如何理解诗的原型是每一代诗人所要做的最基本的工作之一[1]。在相当长的古典历史时期,自然不仅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主题、意象和内涵,而且成为评判诗歌高下的理想性标准。基于此,诗人阐述了自身的理解:“诗才是诗的唯一场所,而且,这个场所绝不是自然的。它和人的洞察力有关,和人的审美冲动有关,和人的创造天赋有关,它和人的生存体验有关。”[2]对语言的遵守使得茨维塔耶娃笔下对事物的描写总是超脱于事物的客观存在之上。事实上,由于茨维塔耶娃对譬喻的热衷和精通,比喻在她的笔下已逐渐摆脱了装饰的嫌疑,而成为一种感觉的本体,它可以是“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是巨大的叹息,/它向一个无名的深渊掉下去”(《致阿赫玛托娃》之一);可以是“敏慧的夜,漆黑如瞳孔,像吮吸/光明的瞳孔——我爱你”(《敏慧的夜,漆黑如瞳孔》);也可以是“在少女温柔的茸毛上——/死亡抹上一道银子的黝黑”(《在少女温柔的茸毛上》)。正是有了这些极具张力的譬喻,才使茨维塔耶娃的抒情诗大放异彩,充满了瞬间情感的眩惑和诗性致命的吸引力,并在非纯粹的抒情中揭示出诗人与我们、诗人与时代之间所存在的如同神启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除了极富女性直感的细节抒情之外,人们往往也能从茨维塔耶娃的诗中感受到奔腾而下、跌宕起伏的大气与无羁。诗人曾说,“我深知自己不会写出软弱有力的诗句,直到最后一句诗行我的诗都是强劲有力的。”叶甫图申科则如是评价她的创作:“她的诗仿佛是由激情、痛苦、隐喻、音乐所汇成的雄伟的尼亚加拉瀑布……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文学的圣处女——女皇。”[3]这种坚硬凌厉的诗风既与她同一切都不调和、不屈服的性格有关,也同她诗歌中大胆使用破折号进行断句、偏爱超浓缩的语词与警句、大量使用排比和叠句的写作手法有关。
茨维塔耶娃诗中大量使用破折号、删节号和断句,由此形成的思维跳跃性和片断性使人们感受到诗人急切的情感风暴。如《亲吻额头——拭去忧愁》:“亲吻额头——拭去忧愁。/我亲吻额头。/亲吻眼睛——抹去失眠。/我亲吻眼睛。/亲吻嘴唇——充满了水意。/我亲吻嘴唇。/亲吻额头——拭去记忆。/我亲吻额头。”(《亲吻额头——拭去忧愁》)在这里,诗人先是利用四个破折号营造出句与句之间铿锵有力的节奏感,然后又通过同一词语和相近词义的重复和对位来断句移行,在使肯定语气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使诗歌的层次感更加分明,从而产生了一种充满力度的、阶梯式的美感。
茨维塔耶娃诗中的超浓缩性往往体现在重点词的重复和平易语词的删除上,从而使语句具有穿透内心的震撼力。与此同时,形式虽然精炼,却又不失包容整个存在形态的复杂性和情绪发展的细微、曲折和延伸等多重可能。例如诗人的《峡谷》:“饮吧!纯粹的——/黑!上帝——/是无偿的:仿佛贴近深渊。……夜——就像偷儿,/夜——就像山峦。”(《峡谷》)不要过渡,而要重复;不要延展,而要突兀,就如同强有力的脉搏或异峰突起的奏鸣曲,给人以尖锐、跃动的美感。
茨维塔耶娃冲破了传统诗歌创作中认为排比和判断句缺乏诗意的樊篱,恣意酣畅地进行排比和判断句的叠用,从而彰显出诗句的回顾性和诗人喷涌而出、瞬息万变的激情,使人耳目一新。在《致拜伦》一诗的重重叠句中,拜伦的名字对诗人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僵死的、固定的抽象符号,而是戴着哥特式宝石戒指的“纤长的手指”,是林阴道和客厅里“所有渴盼的眼睛”,是“半明半暗的大厅”和“天鹅绒的花边”,是“从嘴唇和眼睛掉落的尘土”(《致拜伦》),是一系列转瞬即逝的、鲜活生动的形象在潜意识里急速旋转。又如《战争,战争》:“可是,王室的开支和民族的争端/跟我都没有关系。/在似乎有裂口的钢丝绳上,/我是小小的舞蹈者。/我是影子的影子。我/是两个黑月亮的梦游症患者。”(《战争,战争》),面对外面纷乱吵闹的世界,诗人通过“小小的舞蹈者”、“影子的影子”和“两个黑月亮的梦游症患者”等判断句的叠用不留痕迹地建构起多重感觉的过渡,并在情感阶梯不断向上回旋攀升、孤独感不断向外强烈辐射的同时,更为深刻地折射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特立独行和桀骜不驯。
可以说,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不仅描述对象,也描述语言自身,对语言的拆分和重组使诗人在解构现实和传统意义的同时,也新建了诗歌语言的实验性气质。
三
就整体的创作风格而言,茨维塔耶娃的抒情诗则极具时空上的延续性。要把握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精神,就必须把诗人的所有诗歌连贯起来,渐次阅读。由于她的很多诗都与先前的作品、先前的情感息息相关,从而使她的抒情诗在整体上兼具了一种广阔的时空上的张力,仿佛是向世人展示女诗人一生情感的传记。动荡不堪的时代背景,再加上诗人幼年丧母的孤单、成年后游离于所有文化团体之外的独立不羁、以及她对爱的执著和失落,都把她向孤傲、激烈、极端的性格越推越远,并在诗歌中有了相应的反映。
茨维塔耶娃热烈地歌颂姊妹之间的相互依靠:“我们是国王最后的/希望。/我们在古老的杯子的底层,/看呀:/那里面有你的霞光,和我们的/两道霞光”(《阿霞》);而对于诗人永恒的精神家园——莫斯科,无论是安于日常生活还是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浪,她都抱着最为纯真炽烈的心情歌唱着它:“赞美声‘阿利路亚’/流向黝黑的土地。/我亲吻你的胸口/莫斯科的大地!”(《莫斯科》之八)爱情更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重要助推力。除了与谢尔盖·艾伏隆并不幸福的婚恋之外,历数诗人一生,既有与诗人普卢采尔·萨尔纳、兰恩、曼德尔斯塔姆、格伦斯基、施泰格尔、塔尔科夫斯基的交往,以及著名的三诗人之间鸿雁传书式的精神恋爱;也有与女诗人索非亚·帕尔诺克,女演员索非亚·戈利代之间刻骨铭心的同性爱恋;在这些主要情感事件的间隙,也不乏仅仅出于情感的莫名孤单或对名誉、权力的欣赏而擦出的形形色色的爱情火花。茨维塔耶娃对爱情的追寻有一种几近病态的狂热,她的情感太过丰富和充沛,永远处于沸腾的顶点,面临漫溢的危险。然而,对于感情的迷恋或许只能说明诗人内心里深深根植的孤独和不安定感。她一直渴求心灵的交集,在焦灼不安中寻觅和等待,“一切,所有灼人的欲望/蜷缩成一个欲望!/在我的头发中,所有的色彩/都引起战争。”(《疯狂也就是理智》)可叹世间却无人能承受得起诗人奋不顾身、肆意燃烧的情爱,诗人所经历的也尽是从幻觉产生到幻觉破灭的过程。即便如此,情感的饥渴症和深刻的孤独感仍促使诗人怀着巨大的、预知的绝望对种种新恋情做出飞蛾扑火般的举动。在茨维塔耶娃面前,爱情蒙上了面纱。她越是看不清面纱后的轮廓,越是得不到期望的回应,就越是怀着更大的渴求伸手去抓——爱情对她而言,是一种狂热的错觉,也是一个横亘她一生的巨大的手势。
然而,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伤痛,促使她写出了《致谢尔盖·艾伏隆》、《女友》、《那里来的这般温柔》、《贝壳》、《剑刃》、《距离:里程表,海里》等瑰丽璀璨的爱情篇章。这些爱情诗和与此相近的诗篇构成了诗人辉煌成就的底色,昭示了诗人一生以恋爱的心情去写作的姿态,正如诗人自己所言:“每一行诗都是爱情之子,/都是贫穷的私生子。/它是心灵的地狱和祭坛,/它是心灵的天堂和耻辱。”(《每一行诗都是爱情之子》),即便如此,诗人仍“独自一人,对自己的灵魂,/满怀着巨大的爱情”(《脉管里注满了阳光》)。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诗人抒情诗中所体现出的“日记体”倾向,才能更清晰地明白诗人所说过的“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而“人在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是忠实于自己,真诗人总是她们自己的囚徒”。
诗人从十几岁的年纪起,就吟诵着自己的诗行:“我的诗赞美青春,歌唱死亡。”步入诗坛,死亡、爱情与存在的影子伴随了她的一生。另一方面,随着她后半生的背井离乡和颠沛潦倒,她诗歌中的孤独浓度也在不断上升,正是这种孤独使她写出了“离群索居:走进你的/内心,像祖先走进自己的领地。/离群索居:走吧/生命。”(《离群索居:走进你的内心》)之类饱含着原始的回归意向和死生一致信念的诗句。她的苦难意识与生俱来,到了她创作的晚期,更是“深埋在胸中的痛苦——/比爱情更古老,比爱情更古老。”(《时辰已到!对这把火而言》)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她的激情和痛苦伴随着心灵磨难的漫长过程已渐至诗人精神和肉体所能忍受的最高点,即便是在歌唱,也已蕴含着一种深入骨髓的绝望。就像伊·爱伦堡后来所评价的:“孤独,确切地说,离群索居,犹如符咒一样一生都笼罩着她……她觉得她的世界是一座孤岛,而对于他人来说,她常常是孤岛上的一个居民。”[4]而对于一生寻求爱而不得的茨维塔耶娃来说,写作,成了她在尘世间的唯一栖息之地。
米兰·昆德拉曾说,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茨维塔耶娃即是如此。她的近乎惨烈的激情决定了她只能借助于诗歌来拯救自己的孤独。读茨维塔耶娃的诗,仿佛能感受到她情感的粘稠血液在诗歌抒情的脉管中汩汩流动。她在诗中时而祈祷时而祝福,但紧接着的又是尖锐的嘲讽和诅咒,一切都显得那么狂热而合乎情理,一切都向我们展示着一个本能地、甚至可说是无节制地去爱、去倾泻激情的茨维塔耶娃。无怪乎诗人会以“我的饥渴无法满足,/那对忧伤、激情和死亡的饥渴”(《胸口别着一朵小花》)来自况,也正是基于那无法穿越的、巨大的孤独,才成就了茨维塔耶娃抒情诗在俄罗斯文学中无可取代的恒久魅力和独特价值。
[1] 臧棣.绝不自然:我这样理解诗[EB/OL].http://wenku.yiran.poemlife.com/thread-58226-1-1.html,2004-8-2.
[2] 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1-232.
[3] 荣洁.走近茨维塔耶娃[J].俄罗斯文艺,2001(2):21-24.
[4] 王守仁.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6: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