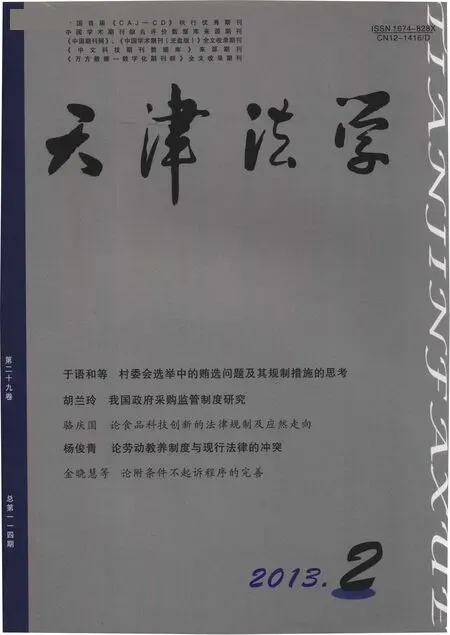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批评”述论——兼谈历史人物评价的正确路径
李继华
(滨州学院 政法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则是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在1924年前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二人互相敬重,精诚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二人相互关系的这种主导方面,特别是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赞扬,许多论著都做了介绍和探讨。但是对二人相互关系的另一方面,特别是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批评”,有关论著则注意不够,甚至不愿意承认。
在发表于1923年10月20日的《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中,李大钊讲到“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1]。对李大钊评价孙中山的这句话,《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加了一个注释,说明“此处应是记者的文误。”其根据是:“此处文字,不仅与孙中山的实际状况不合,而且与李大钊当时的实际认识也不合。”“李大钊当时不可能对孙中山有如此偏谬的判断”[2]。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未必妥当。
一、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态度来看
早在1919年12月7日发表的随感录《“裤子”》中,李大钊就讲到“中国的无裤党魁,却要和那武装戴鸡毛的人一路走,不知他那裤子是几时穿上的”[3]?对这种比较尖锐的讽刺,《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倒是给予了客观的肯定:“文中‘中国的无裤党魁’,隐喻孙中山;‘和那武装戴鸡毛的人一路走’,指孙中山当时多借助军阀势力”[4]。
在1923年4月18日发表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中,李大钊写到: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5]。
1923年6月25日,李大钊和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人联名致信孙中山:“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即令我们用一切办法把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那么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而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6]。
1924年7月1日,在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李大钊指出:“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7]。
同年9月13日,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中,李大钊讲到:“应当说孙中山在南方的政策至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就在不久以前,他甚至打算在‘纸老虎’的军队中寻求支持,他出席了他们的阅兵式,并且还向他们献了旗”[8]。
李大钊对国民党孙中山的上述批评,大体上是一贯的;与他在《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中对孙中山的批评,也并不矛盾。《李大钊全集》注释本,肯定了李大钊在1919年12月对孙中山的批评,却否认了他在1923年10月间对孙中山的批评,令人有前后不一之感。
二、从中共中央文献和其它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批评来看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趋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是,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9]。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指出:“若是国民党看不见国民的势力,在此重大时机不能遂行他的历史工作,仍旧号召四个实力派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其结果只(是)军阀互战或产生各派军阀大结合的政局”[10]。
早在1923年1月31日,蔡和森在《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中,就明确反对“国民党离开革命的地位而以周旋于四派军阀间的调人自处”,“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和”,“局促于局部的军事行动而疲于奔命,对于基本的革命宣传工夫一点没有做”,“专门是做与军阀相周旋的危险工夫”[11]。在7月11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上,蔡和森在《北京政变与各派系》中又指出:“国民党若是仍要参与这样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唐继尧等)及无赖政客(南政北安等)的大团结,结果只有仍如从前一样的上当无结果”[12]!
同在《向导》周报第31、32期上,陈独秀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中写到:“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在《北京政变与学生》中,他告诫学生“万不可象各派政客们只知结合奉、段等反抗直系,造成军阀对于军阀的战争”[13]!
6月13日,张太雷发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署名“春木”)。其中讲到:“国民现在所以怕国民党的名字因为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14]。
8月29日,在《粤局与革命运动》中,陈独秀批评“现在的国民党为了广州这一块土地,为种种环境所拘囚,对内对外不得不降心妥协背着主义而行,日夜忙着为非革命的军队筹饷拉夫,那有片刻空闲在社会上制造革命的空气”[15]。
此后的1927年9月,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回忆说:“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在其创刊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对国民党及其领袖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态度,几乎每期都刊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在宣传上采取独立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利用右派的反对,想把中共组织和一切政治工作都置于国民党的管理和监督之下,从而解决‘党内有党’的问题。很明显这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组织,限制其行动和批评自由”[16]。
国共合作建立后,一些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孙中山的批评仍然很尖锐。
1924年9月10日,蔡和森在《商团事件的教训》中指出:“广东政权之取得,并不由于革命势力之完成,但(而)是由于利用根本与革命相反的军阀财阀的势力,所以广东政府不仅不是革命的工具,适足成为雇佣军阀、交通系、政客、买办阶级以及升官发财的右派之狐城鼠社。”“雇佣军阀以养寇纵敌为长久敲诈军饷之法宝,军役不停,苛税繁重,因而引起人民对于革命之反感与不信任”[17]。在10月22日发表的《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中,蔡和森进一步总结了商团事件的教训,指出:“迄双十节为止,广州政府对于操纵商团的少数买办阶级委曲迁就,坐令反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扩大紧张”。“这种反革命之所以潜生滋长却是国民党雇佣军阀的武力革命方法之必然的结果。由这种方法产生的革命政府,不仅不能给广东人民以好处,不仅不能实现平日所宣传的抽象的主义,反而只能如军阀政府一样——苛税杂捐,重苦人民以养那一批一批的军阀头领及浩大的土匪式军队”[18]。
9月23日,署名“巨缘”的“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中指出:“从前广州政府对于列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实质上也和奉张浙卢湘赵差不多的一个所谓独立的地方政府罢了。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国民党中渗入了左派革命分子,无论左派还怎样微弱,始终已经不是从前的国民党”[19]。
10月1日,陈独秀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到:“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20]。
12月27日,陈潭秋在《国民党底分析》中写到:在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又走上了第四条错路——与军阀妥协,利用甲派军阀打倒乙派军阀。此时党内握有兵柄的党员,也多是与军阀的行径一样;致中国的政局,终只能成为军阀嬗递的局面,这是第四次的错误”[21]。
这些批评,或许有片面、过激之处,却反映了当时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真实看法,也反映了李大钊在对国民党孙中山的看法上与其他共产党人的一致性。对李大钊的看法,可以分析其是否有不当之处,但显然不能轻易否定它的真实性,不能轻易断言这些看法是“记者的文误”。
三、从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其在华代表对孙中山的评价来看
1922年11月8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署名孙铎)一文中指出:“国民运动领袖人物的观念上,必有许多错误。他们历来单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或者是一个大错误。他们的方法只是要获得一块地盘,树立他们的势力,再练一支革命军来实行他们的计划。跟着中国革命鼻祖孙中山的真实的国民运动者们,确实只见着革命的活动就是组织军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军事行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却极坚信: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义的宣传普及全国,比天天与军事领袖周旋结合,更为重要”。“听说吴佩孚还在他的兵士中做了一些宣传功夫。他的兵整队游行的时候,高唱爱国歌;这件事算是不错”[22]。
1923年3月8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指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而继续在以军阀派系之一的身份活动……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派系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23]。
同年4月4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就1923年第一季度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讲道:“孙逸仙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指望跟最反动的北方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结盟。国民党由于这一结盟使自己在中国各界自由派人士的眼里威信扫地”[24]。
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部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这种勾结有使国民党的运动堕落为军阀混战的危险”[25]。与这个指示相一致,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其出席中共三大的代表的指示草案中也指出:“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在国民党内部,反对孙逸仙同以英美和日本资本为靠山的军阀们的军事结盟,因为这种结盟有可能使国民党的运动蜕化为一个军阀集团反对另一个军阀集团的运动”[26]。
6月25日前后,马林在委托李大钊带给李汉俊的信中指出:“国民党绝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政治战斗团体,甚至最进步的国民党员,也怀疑建立一个民族革命性质的群众党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坚持封建办法,采用北方军阀相同的手段”[27]。
7月2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致廖仲恺的信中写到:国民党“只依靠军阀,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烽火连绵迫使党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28]。同在7月间,马林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署名孙铎)中指出:“在民党领袖的意见,中国革命是纯粹中国的事情,可以由中国人自己采用封建式的北方军阀的方法来解决的……这种观念居然能支配民党,令人难解”[29]。
8月25日,华俄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30]。11月25日,斯列帕克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又指出:国民党在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今天夺取广州,明天将它交回去,后天再夺回来,而后再交出去,等等。这对谁有利呢?对各种各样的将军有利,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大发横财。“所以很多人看不出国民党组织和其他军阀集团之间的区别”[31]。“对于许多人来说,国民党与中国其他军阀集团没有区别,或者在最好情况下没有多大区别”[32]。
11月27日,时任苏俄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在同国民党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33]。
12月上旬,鲍罗廷在《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中指出:“南方最优秀的国民党人对群众组织失去信心后,完全投身于军事工作,而在军事工作中,事物发展逻辑本身使他们变得更像所谓的军阀,在人民群众看来,不知道这些军阀在为什么打仗”[34]。
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其在华代表对孙中山的这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既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上述批评相吻合,也对李大钊关于孙中山的认识有较大的影响。
四、从孙中山自己关于国民党的失败教训及原因的论述来看
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开诚布公地指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之唯一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他列举倡导革命以来的许多史实,来证明“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35]。
12月9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重申:“吾党经过十余年来,或胜或败,已历许多次数。就以胜败成绩观察之,则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此点党员须首先明白。”“今后首当将企望以军队谋革命成功的观念打破”[36]。
12月30日,《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再次指出:“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做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起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37]。
这些论述表明,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的批评帮助下,孙中山对依靠封建军阀进行革命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大钊对孙中山所作批评的正确性。
当然,孙中山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并不是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主要是想利用苏联和中共来发展国民党。因而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并没有像过去一些论著所宣扬的那么真诚和单纯。他既不可能完全承认自己“最近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可能真正抛弃与其他军阀相联合的政策。与其他军阀的这种联合,既有统战策略的需要,也是当时的孙中山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即使在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前后,孙中山也没有停止同奉系和皖系军阀的联合。
1922年9月22日,在《复张作霖函》中,孙中山写道:“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对于所拟方略,极为一致,复经卢督办子嘉参加意见与以赞成,尚希卓见定夺为荷”[38]。几天之后,在9月27日《与郭泰祺的谈话》中,出于宣传方面的需要,孙中山否认了与张作霖的联合:“至关外张作霖,向不知护法二字为何物,更谈不到与我有所接洽。惟彼等形同土匪,招集乌合之众,占几个地盘,遂张牙舞爪,以疆吏自居,在予目之,殊不值一笑也”[39]。但是到11月30日《复张作霖函》中,孙中山又表示:“文前与公书,让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40]。这里所表现出的对张作霖的不同评价,固然有公开宣传与秘密联系的区别,恐怕也反映出孙中山对张作霖的两面认识。
1923年1月26日,在《致段祺瑞函》中,孙中山写道:“芝泉先生惠鉴:兹特派于右任晋商要事,即祈赐予接洽。至文对于时局意见,已于今日电达,想邀英览矣”[41]。
2月22日,在《与东方通讯社记者的谈话》中,孙中山公开表示:“余与张、段之三角联盟,现正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42]。
6月29日,在《致□□电》中,孙中山指出:“自兄行后,我已将中国大局长为考虑,觉得与段合作不过比较上或善耳,仍不能彻底以行吾党之主义。故对段之事只有十分水到渠成,毫无障碍方可允之”[43]。但在1924年2月《与日人某君的谈话》中,孙中山又讲道:“我军已有成竹在胸,一旦将长江占领后,即暂时出持久态度,谋与北方同志之段祺瑞同志一派提携,徐徐再打开统一的局面”[44]。
这些论述表明,孙中山对奉系、皖系军阀的联合,既有统战策略的需要,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既有对军阀本质的认识不清,也有某些清醒的认识。在种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比较激烈批评,则既有立场、观点的不同,也有对孙中山局限性的一针见血。
五、从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变化来看
如前所述,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并没有像过去一些论著所宣扬的那么真诚和单纯,而是经历了一个时有变化的过程。对此,陈独秀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回忆说:中共二大“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决议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推动下,中共西湖会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庭,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民国13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45]。
这段话中提到的马林垂头丧气回莫斯科,应在1923年8、9月间[46]。继他而来的鲍罗廷则在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47]。李大钊发表上述谈话的1923年10月20日,正是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由消极到开始积极起来的时候。对这种变化,远在北京的李大钊自然不可能马上知悉。这样,他说“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正是反映了孙中山在鲍罗廷来华之前对国共合作比较消极的状态。
六、从孙中山“嘱孙伯兰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的时间来看
《李大钊全集》注释本中《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一文的注释4还讲到:“1923年10月19日,即实际上在古庄此次采访的前几天,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嘱孙伯兰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48]。这句话的意思似为:孙伯兰密电李大钊赴沪,是在古庄采访李大钊的“前几天”;到古庄采访李大钊时,李大钊已经知道了密电的内容,因而不可能说出“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之类的话。实际上,古庄对李大钊的“此次采访”,即李大钊的《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发表于1923年10月20日[49],采访于前一天(19日)或更早。这与孙中山致电孙伯兰密电李大钊赴沪,最早也就是同一天(19日),更可能比李大钊接到孙伯兰密电的时间还早一些(因为要经历孙中山致电孙伯兰——孙伯兰发密电到北京——密电送交李大钊的过程,李大钊不太可能在19日就看到密电)。也就是说,古庄采访李大钊在前,李大钊接到孙伯兰密电的时间很可能要晚一到几天。《李大钊全集》注释本却把先后时间颠倒了。退一步说,即使确系李大钊收到密电在先,接受古庄采访在后,也没有证据说明李大钊对孙中山没有上述看法,或有此种看法而不讲。
综上所述,李大钊在1923年10月所说“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既符合李大钊自己对国民党孙中山的认识轨迹,也与中共中央文献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有关认识相一致,更与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及其在华代表对孙中山的评价相吻合。孙中山自己关于国民党的失败教训及原因的论述,和他对国共合作的复杂态度,实际上也证明了李大钊所作批评的合理性。全面分析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态度,他对孙中山既有赞扬,也有批评。今天的人们不能只注意前者,而不注意后者。更不能把后者简单地看作“偏谬的判断”和报刊的“文误”。
长期以来,一些论著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对所谓正面人物,特别是伟人,往往只宣扬其历史贡献,不谈或很少谈及其失误和局限性;对伟人之间的交往,也往往只谈其相互敬重和赞扬,而不谈或很少谈及他们的分歧和批评。笔者以为,这种“神化”趋向,恰恰是历史人物研究中的一种“偏谬”和“文误”;客观、适当地注意和肯定伟人之间的分歧和批评,倒是值得提倡和培养的良好学风,也是史学研究者应该努力培育的学术品格。
[1][2][5][48][49]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7.516.170.516.346,348.
[3][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8.370.
[6][7][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5,386.3.13.
[9][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29.133.
[11]《向导》周报(18).1923-01-31.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8.
[12]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21.
[1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320,322.
[14]《向导》周报(29).1923-06-13.
[15]《向导》周报(38).1923-08-29.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330.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9,80.
[17]《向导》周报(82).1924-09-10.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42.
[18]《向导》周报(88).1924-10-22.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63,664.
[19]《向导》周报(85).1924-10-01.
[20]《向导》周报(85).1924-10-0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588-589.
[21]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7.
[22][25][28][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338—339.457.431.525.
[23][24][26][30][31][32][33][3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29.240.252.267.320.323.340.370.
[27]田子渝,李汉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49.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2.
[35][36][37]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8)[M].北京:中华书局,1986.430,435.500—501,503.565,566.
[38][39][40]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6)[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8.562.627.
[41][42][4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6.54.130.576.
[4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9)[M].北京:中华书局,1986.535.
[45]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42—243.
[46]李玉贞,马林传[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52.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76.
[47]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92.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