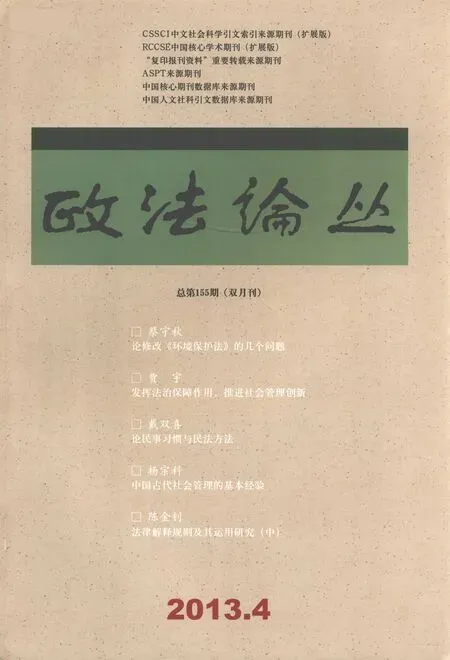法律解释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
李 可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法律解释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
李 可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由于缺乏一个元规则而颇受非议。对这些异议的回应迫使我们检讨影响法律解释方法位序的种种因素,并进而探寻隐藏在解释方法位序表背后的元规则。研究表明,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可以作为法律解释方法排序的始基,并在法律解释中担当起类似法学研究逻辑起点的各项功能。
法律解释方法 位序表 元规则 可接受性
一、对一些异议的反驳及问题的提出
在法理学界,一些人指责,由于缺乏选择解释方法适用效力的元规则,法律解释方法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位序[1]。但是,我们拟定解释方法的位序表不正是为了确定这么一个方法适用的效力规则么?因而,这一指责实质上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诡辩,对于解释方法位序表之存在不具有任何理论上的否证力量。而且解释方法的选择也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任意的。正如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所言:“在诠释学上的合理范围内一旦选择了某一解释或漏洞填补,即不应在没有重大理由的情况下放弃这一选择。”[2]P119因为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和法的安定性原则要求法官尊重前例的选择。即便有重大理由要求偏离前例的选择,法官也必须对于此种选择加以论证。同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前例选择的信赖和对新案选择的合理预期也要求法官尊重前例的选择。
确实,我们承认,对于解释方法位序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任何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之产生,但是不要忘了,方法位序表与方法一样,都只是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它在性质上近似于一种办事指南,是通向正确解释结果乃至司法判决的较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同于规则、原则和标准等规范性范畴。对于法官而言,解释方法位序表更像“菜单”而非“诊单”。就像雷德大法官(Lord Reid)所说的:“在每一个案件中,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相关情况,然后根据任何特定规则的分量作出实际的判断。”[3]应该说,需要权衡、比较和综合是解释方法位序表的根本特征,并无丝毫可指摘之处。
同时,解释方法位序表的拟定本身就是为了应对从简单案件到复杂案件以至疑难案件这么一个“由简至繁”序列上的法律问题,因而,位序表前面的方法简单而后面的方法复杂这么一种排列顺序也完全因应上述“由简至繁”的法则。“以简应简、以繁应繁、疑难之处应多加说明”这本身既是一种生活常识,也是一种使解释结果获得更多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必行之举。因为相比于简单案件,当事人要求解释者对复杂案件和疑难案件的解释也更复杂、更精致。与之相对应,前位的方法体现了更多的形式理性,而后位的方法则体现了更多的实质理性,这么一种“由表及里”的排序方法也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和思维特点。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方法位序表不单单是对形式规则的罗列,也是对实质规则(例如表后的论理解释、目的解释)的考量。
而且法律解释学也从来也没有声称过它只为法律操作问题提供一个程序性的指令,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做。难道位序表后的那些方法(例如论理解释、目的解释)不正是一些实质性的指令吗?同时它也从来没有声称过只需考虑法律内部因素就可以解决疑难案件[4]。多数方法位序表的倡导者突出论理解释和目的解释在各自位序表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试图在解释乃至裁判活动中引入法外因素和实质性判断。其实有人早就提出了一些法律解释应当考虑的价值,它们是:三权分立的宪政结构、法的统一性、公平正义、利益最大化[2]P69。
国内外所有方法位序表的制定者也从来没有声称过其位序表是绝对永恒、固定不变的。自然,前位的方法比后位的方法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并且解释者相应负担的论证义务也更轻。在没有干扰因素(例如事实不清、法律不明)的情况下,人们更易理解前位的解释方法及其相关方案,但是当干扰因素一出现,前位的解释方法就失去了明确的解释对象而不得不让位于后位的解释方法。而人们通常更难理解后位的解释方法,故而需要解释者负担更多的论证义务。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各自建构的方法位序表都只具有假说的性质,它们能否在诉讼情境中最终胜出,得看哪一方能从规范、事实、价值和理论中寻求到最佳的论证资源。
在法律解释中,“先定结果再找方法”的执果索因式解释模式并不是解释的特例,而是解释的常态,司法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先进行法律发现、后予以法律论证的二阶过程[5]P254。法官在综合考察个案并结合以往类似判例的基础上,先提出一个“规范假说”,然后再从制定法、判例、逻辑和伦理等多个维度予以验证[6]P120,152,204。诚然,如人们所言,法律解释的最终目的乃是为择定的判决提供有根据且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7]P32。司法判决与法律政策的联系即便是在奉行严格解释的刑法中也是稀松平常的。我们不能因为法律判决要考虑社会后果和社会目标就否定它的自足性和自主性。法律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系统,人们从法律中所能捕获的确定性也只能是一种“流动的确定性”。
二、影响解释方法位序的因素
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对方法位序表影响最大的是人们对文义、体系和目的等关键词的理解。由于词语的多义性及外延的弹性,同样的一个词,人们既可以对它进行广义上的理解,也可以对它进行狭义上的理解,既可以扩张其外延,也可以缩小其外延。例如,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理解文义一词,那么在利格斯诉帕尔默(又译为埃尔默)案(Riggs v. Palmer)中[8],我们可以说帕尔默的律师、格雷法官和厄尔法官都是从文义的角度对纽约州的遗嘱法进行解释,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一般情况下,法条的字面含义、字中含义和字外含义之间具有单向外推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区别:字面含义是人们单从法条文字本身即可看出的含义;字中含义是人们需要将法条与所处法律体系中的其他法条联系起来才能体会出的含义;字外含义则是人们需要将法条与所处社会的主流价值联系起来才能发掘出的含义。帕尔默的律师是从“字面”的角度理解纽约州遗嘱法,因而得出结论说帕尔默享有继承权;格雷法官是从“字中”的角度理解相关法律,认为该遗嘱法与刑法之间的界限清晰,没有必要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理解,从而支持了帕尔默律师的辩解;而厄尔法官则是从“字外”的角度理解遗嘱法及与相关法律的联系,认为遗嘱法的字外含义在该案中与字面及字中含义发生了分裂,需要将该法条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联系起来才能释明该法条的个案含义,并从而得出帕尔默不能享有继承权的结论。当然,在该案中,厄尔法官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也即个案情境下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说成是“立法者的意图”。换一个角度讲,在厄尔法官看来,在通常情况下,法条的真义与其字面含义、字中含义是重合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分裂,前者可能逸出字面和字中,因而需要到具体个案情境中去捕捉此种含义。在此,法官必须根据一般法律原理从过往的类似判例中提炼出一个“规范假说”,并对之予以逻辑、规范和价值上的验证。这可以视为一个找寻法条本体的过程,一个字面、字中和字外三种含义发生分裂,而且这种分裂为人们所觉察并被有意识地予以突显,而不得不迫使当事人、律师和法官去找寻丢失的意义的过程。
仅从对文义解释的广、中、狭三义的理解即可发现,上述理解实质上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论辩,即借助什么方法去发现法条之本体。借助不同的方法事实上可以发现至少表面上有理的法条本体。同时,借助不同的方法也可以突显或淡化个案事实的某些部分,从而使案件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来。例如在上述利格斯诉帕尔默案中,律师采取字面含义的方法尽量淡化帕尔默毒杀其祖父与其享有遗产继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该案保持简单案件的面目;而厄尔法官则突显这种内在联系,从而使该案呈现出疑难案件的面目。因而,一个案件是否是疑难案件,往往与观察该案的视角、方法有关。这样看来,方法类似于一盏探照灯,它投射到案件的不同侧面,将使个案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乃至性质。同时,观察案件的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也将影响个案中解释方法的位序。例如,如果从广义上理解文义一词,那么帕尔默案中解释方法的位序将简化成:文义解释、历史解释和合宪性解释三种。
其次,解释者的价值观和价值目标对于解释方法的排序也有着重要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解释方法的位序受到该国的法制规划、司法政策和国际国内的人权运动等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在1997年刑法之前,类推解释在我国刑法解释方法的位序表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文义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等无法解决问题时,类推解释就被派上用场。在国内法治建设和国际人权运动的推动下,1997年刑法废除了类推,从此类推解释就从刑法解释方法的位序表上被剔除。在理论研究中,解释方法的位序受到解释者的价值观和解释目标的影响。例如,目的刑论者注重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因而在解释方法的排序中往往突出目的解释,将之作为整个位序表之核心。可见,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诸解释方法之间的位序往往受制于解释者的价值观。在长期的解释实践中,某一个学派乃至某一个法律体系下的法律人通常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解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拥有大致相似的法律价值观和相对一致的解释位序取向。例如,受法教义学影响较深的大陆法系法官在法律解释时,一般倾向于优先采取文义解释、逻辑解释和体系解释等形式性解释方法;而在受法社会学影响较深的英美法系法官在法律解释时,往往喜欢抛开形式性解释的羁绊而直接运用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等实质性解释,以直扑预定的裁判主题。
再次,法律解释所发生的部门和领域对于解释方法的位序也有较大影响。例如发生在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法律解释要受到公法致力于保障人权、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价值取向和偏重于法之安定性、可预期性等形式价值的影响,因而较多地采取文义、体系和历史等形式性解释方法,而较少地采取目的、意图和合宪性等实质性解释方法。这一点亦得到公法领域的主流观念的认同[4]。同时,出于形式法治之需要,公法领域的法律解释亦有致力于发现立法者的真正意旨之努力。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是形式性解释还是实质性解释,皆为发现立法者之真意,以抑制法官的恣意裁量,保障被告人和相对人的权利。尤其是在对待公法中的不确定性条款上,学者无不强调对立法资料的诉求,因而历史解释在公法领域的解释方法位序表上往往占有重要地位,个别学者甚至将之作为“初始解释方法”对待[9]。可以说,在公法领域,一直以来偏向于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观,无论是在刑法还是行政法的解释中,人们都非常强调解释的谦抑性。
最后,在解释方法位序表中,一些方法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先后顺序。因而,情形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方法本身不能为方法的选择和排序提供任何有用信息[10]P92。例如文本是规范、事实、价值和现象之载体,是解释客体之具现,构成了解释方法诸要素中的客体要素①。解释者只有基于对文本进行形式与意义之展开,才能为其他解释方法确定一个方法上的“锚”。因而,文义解释不得不位于所有解释方法之首。当然,如前所示,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文义,那么它的包摄力是惊人的:所有形式性解释方法都有理由被它收编,甚至一些实质性解释方法(例如目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对文义解释的展开。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人们才断言:“文义不仅是一切解释的出发点,更应是一切解释的终点。”[11]故而,在此我们只能对文义解释予以常义理解,方能恰当地确定它与其他解释方法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与文义解释有密切联系的是体系解释。从内在结构上看,体系解释包含一个先在的方法论假定,即任何体系在逻辑上都是自洽的、无矛盾的意义网络,而法条之文义乃是此网上之“结”。因而,如果逻辑解释可以单独成为一种解释方法的话,那么它必须位于文义解释之后、体系解释之前。同时,只有先对法条作体系解释,才能确定该法条在适用范围上是否封闭,因而体系解释必须位于反对解释之前。此外,只有先发现法条的立法目的,才能确定该法条的规范逻辑外延,因而发现法条的目的必须位于反对解释之前。
三、方法位序表上的元规则
方法位序表的异议者否认有一个解决方法适用之先后次序的“元规则”存在,即使有也并不具有与法律规则对解释者一样的拘束力。但是,即便是在常理意义上,各解释方法之间难道就没有一个作为排序之始基并统摄全局的元规则存在吗?假使有这么一个元规则存在,那么它应当具备什么的性质呢?对此,有人提出“良法原则”是解释方法的元规则,而且认为符合良法原则的法律原则还构成了一个元规则系统[12]。但是,原则是解决规则之间冲突的元规则,而方法与规则毕竟在性质上不尽相同,适用于规则的元规则未必适用于方法;而该论者从法律选择角度对良法原则的论证与方法选择的元规则问题相去甚远,因而未能说服人心。在此,笔者想借助法学方法论上逻辑起点的若干性质对解释方法的元规则予以说明,或许能够给我们若干启发。
法学方法论上的逻辑起点是指法学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它构成了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分析单元。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一般而言,逻辑起点必须具备下述四个条件:首先,它凝结了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次,它构成了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再次,它贯穿于理论发展的全过程;最后,它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②。那么,在诸解释方法之间有没有这样一个类似法学方法论上的逻辑起点存在呢?换言之,我们能否从诸解释方法之间提炼出这么一个起始范畴以作为方法位序表之元规则呢?如果我们从规范与事实、效力与实效、价值与现象、形式与实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立场出发,认真审视字义/文理解释、逻辑/体系解释、意图/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之间的内在关系,完全可以发现或提炼出这么一个元规则。根据形式与实质之间对立统一的规律,我们可以把上述解释方法压缩为偏向形式的解释和偏向实质的解释两大类。字义解释、逻辑解释属于偏向形式的解释,意图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属于偏向实质的解释。方法位序表从根本上讲是要解决诸解释方法的适用在效力上相互冲突时,究竟应选择何种方法的适用效力之问题。这样看来,偏向形式的解释是要解决方法适用的内在效力问题,而偏向实质的解释是要解决方法适用的外在效力问题。内在效力指向规范,而外在效力指向价值;内在效力以实定法的位阶为根据,外在效力以事实在伦理上的评价为根据。那么,内在效力与外在效力的契合点在哪里呢?或言之,实定法的位阶与事实在伦理上的评价能够找到结合之处吗?
我们认为能够找到,那就是当事人的“可接受性”。什么叫做可接受性?这在词典上没有明确的定义,我在此假定可接受性是指解释结果虽然给了当事人以限制,但是当事人认为这种限制并没有违背其自由意志,相反为其自由意志之行使创造了制度和伦理上的积极条件。例如,解释结果对败诉方不利,但是这种不利与其先前的意志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可识别的;解释结果对胜诉方只有有限的利益(即这种利益可能没有达致其预期目标),但是此种有限的利益与其先前的意志行为之间的联系也是可识别的。简言之,解释结果与当事人先前的意志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包容性但是不具有可操纵性。解释结果不能根据实定法的位阶、事实在伦理上的评价以外的因素被人为地操纵。具体地讲,解释者必须在规范与价值、事实与现象这两类因素中寻找解释的标准或根据,而这些根据均潜在地指向当事人的可接受性这一目标。
以上述逻辑起点的四个条件观之,“可接受性”可以作为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首先,法律的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就是其作用对象的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性,即便是主张“法即规则”的实证主义者对此也不予否认[13]P52-63。其次,不论是社会法学还是规范法学,不论是历史法学还是自然法学,它们对法律的研究都是从“该法是为们所接受的”(即可接受性)这一最基本单位开始的。再次,法的可接受性贯穿于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提出并验证理论假说和修改、完善理论体系这一系列程序之中。最后,可接受性有助于克服武断地将法学研究之逻辑起点定于自然理性、上帝意志、统治者的命令、基础规范等诸理论体系之缺陷,从而可以架构起一个逻辑、规范和价值上自洽的理论体系。
以可接受性的元规则观之,按照可接受性程度的高低排序,在上述诸解释方法中,当事人最容易接受字义/文理解释,次之是逻辑/体系解释,较难接受意图/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这是因为前两种解释是偏向形式的解释,而后两种解释是偏向实质的解释,而常人的认识通常是由形式到实质、由现象到价值这么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当然有人可能说,合宪性解释不是一种形式性很强的解释吗?为什么它的可接受性却最低呢?这一质问颇有道理。但是在当下中国的解释语境下,宪法虽是最高的、最根本的“母法”,不过同时也是最抽象、最模糊、最偏向实质(价值)的“大法”和最缺乏可操作性、可适用性的“虚法”。宪法是一国人权的宣言,也是一国法制价值的宣言。如此看来,合宪性解释岂不是最偏向于实质和最难为当事人所接受的解释?
四、可接受性元规则的展开
可接受性的元规则是依据前述形式与实质之间对立统一的规律,从诸解释方法中提炼出来的,因而它必然考虑到了法律解释方法的形式维度、价值维度和事实维度等对立统一的解释因素,可以有效防止解释者选择方法时的恣意裁量。因而,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程序性指令,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性描述,而是一个综合了规范与事实、效力与实效、价值与现象等多种解释因素的方法论上的基本范畴或起始范畴。如果我们考虑到“解释是体系化的前提,体系是解释的结果”之经验事实,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解释方法之元规则的可接受性概念可以成为法律体系的起始范畴③。可以说,解释方法的元规则的操作功能和价值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它既可以为人们解释规范、理解事实提供一个方法论上的出发点,也可以为人们解决诸解释方法适用效力上的冲突提供一个价值上的基点,还可以在具体的司法裁判过程中调节效力与实效、价值与现象、形式与实质等目标之间的冲突。因而从形式上看,解释方法的元规则确实担当了类似法学研究上的逻辑起点之功能。
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并没有否认传统合法性和合理性判准对解释方法之选择的制约作用,相反,它是在尊重上述判准的基础上所设立的具有解纷性质的方法论判准。详言之,当实定法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发生冲突时,人们可以借助该元规则加以解决,以最终克服解释方案的内在冲突及由此导致的解释结果之多样性等难题。从方法论策略上看,可接受性的元规则试图具体地而非抽象的、个案地而非一般地解决当下人们所面对的解释难题。“在原本的法律职业群体正当化的基础之上,社会成员对正当化的接受都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4]可接受性的元规则无论对于方法位序表前位的形式性解释方法还是后位的实质性解释方法的意义都是重大的。与方法位序表前位的形式性解释方法相比,后位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对于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渴求更大更急切。因为这些解释方法在作为法续造的工具时往往缺乏实定法规范的支持,所以更加需要人们的内心认同和情理上的依据。后位的实质性解释方法——例如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主要是作为法律续造的工具,其在法律上的正当在于,它必须为法律职业共同体(首先是法官)和社会公众(首先是当事人)所接受。当然,这种接受通常只是以缓慢甚至是不易觉察的速度进行的,与司法职业伦理和社会主流价值相契合的续造为人们接受的速度较快,但也得有个过程。其如有人所描述的:“在法律发展的一定阶段,某种解释的可能性、某项一般法律原则或者某一漏洞填补的做法会被提出讨论,并缓慢地获得其效力;也就是说,它们被司法/执法机关所接受的或然性不断增大。”[2]P12
在实践中,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对于习惯法解释也有较强的说服力。相比于制定法,习惯法更体现了人们对于一种秩序的可接受性程度。“因为一项行为秩序只有在能被接受为是关于特定生活关系的公正的、且符合主流法感受(即法律共同体的opinio juris)的秩序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习惯法得以贯彻。”[2]P15在同时存在数个适用于个案的习惯法解释的情况下,解释者应采用最能为当事人所接受的解释。
处理解释结果适用效力上的冲突问题与处理一般正义问题一样,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可接受性”为标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无法以传统的甚至是唯理论的权威束缚人们的思想,在法律问题上,每个人实质上都坚守内心的道德律,并以之作为评判一种解释方案正当与否的标准。当然,正当的解释方案也是融会了集体共识的方案,同时也是坚守了某些贯彻于诸解释方法始终的一般原则的方案。因而,正当的解释方案是建立在宽容歧见,反对价值专制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的解释方案才是可接受的。
在个案当中,可接受性的元规则之具体展开要更为复杂些。具体个案是不同利益、价值和目标“厮杀的战场”,是“通常情况”(常规情形)与“特殊情况”(例外情形)角逐的领域。尽管如此,解释方案要取得上述共识和原则的支持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正是在这样纷杂的情境下,解释方案应符合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就更加重要。当然我们可以讲,可接受的理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解释的程序、原则和原理却可以将它们引上理性的轨道和公平的竞技场。
在陈述了可接受性的元规则在具体社会和个案中遭遇的复杂情势后,我们就可以明白当今占主流地位的方法位序表为何要将合宪性解释作为“压轴式的解释方法”了。如前所述,宪法是一国法制价值的宣言,它凝练了该国国民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进言之,宪法不仅是法制价值之宣示,更是法律伦理、法律原则和法律传统之汇聚。不过,从前述形式性解释方法过渡到合宪性等实质性解释方法,解释者的自由度不断扩大。为了防止法官解释的裁量恣意,解释者必须负担更多的论证义务,必须更加小心求证,因为前行的道路上布满了文本与史料、规范与意志之间因断裂而形成的陷阱。
注释:
① 解释方法的其他要素是主体、目标和程序。参见李可:《法学方法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208、214-215页。
② 参见李可:《法学方法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67页; 胡平仁:《当代中国法理学范式及其逻辑起点批判》,载胡平仁主编:《湘江法律评论》(第7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③ 当然,方法位序表的元规则能否作为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它与本文主题相去甚远,故只能另文详述。
[1] 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J].法学研究,2004,5.
[2]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M].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 See Maunsell v. Olins [1975] 1 All ER 16. Cited by Legal Method, by Ian Mcleod, 6th edtion, 2007, Palgrave Macmillan.
[4] 梁根林.罪刑法定视域中的刑法适用解释[J].中国法学,2004,3.
[5] [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6] 李可.法学方法论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7] 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解释方法的追问[A].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 Riggs v. Palmer, 115N. Y. 506, 22N. E. 188(1889). Cf: Re Sigsworth [1934] All ER Rep 113. Cited by Legal Method, by Ian Mcleod, 6th edtion, 2007, Palgrave Macmillan.
[9] 孙晋琪,蒋涛.论刑法司法解释方法[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4.
[10] 梁治平.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A].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 苏彩霞.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J].中国法学,2008,5.
[12] 雷绍玲.论法律解释元规则[J].广东社会科学,2009,3.
[13]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4] 孙光宁.法律解释的评价标准:从合法性、合理性到可接受性[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5.
Meta-ruleoftheOrderTableofLegalInterpretationMethods
LiKe
(Law Schoo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The ord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is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lack of a meta-rule, the response to which forces us to review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rd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metal-rule behind an order table of legal explana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eta-rule of acceptability can serve as a sorting arch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which can undertake all kinds of functions similar to jurisprudential logic starting point in 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order table; meta-rule; acceptability
DF0-051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本文系作者参与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意沟通与司法调审制度改革研究”(10YJA820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 可(1975-),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方法、法律方法。
1002—6274(2013)04—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