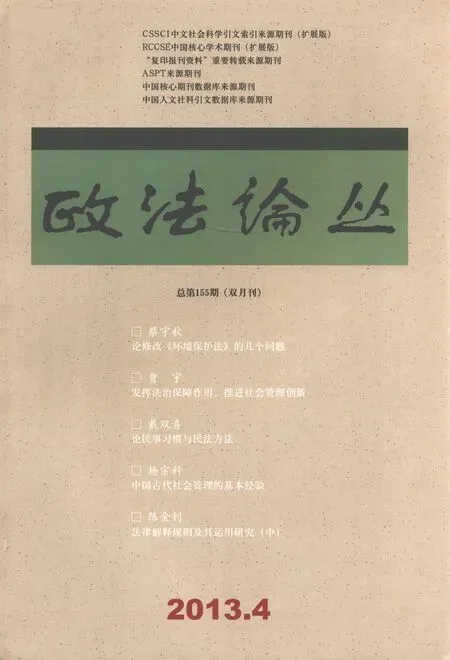“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孙曙生
(江苏行政学院法学部,南京 210013)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孙曙生
(江苏行政学院法学部,南京 210013)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法治 法治国 继受 普通法
一、问题的提出
史学大家陈寅恪1927年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把清末已降的中国的变迁,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1]P5此一宏论,与李鸿章19世纪70年代初“三千余年一大变局”[2]P119的言说,颇为相似。皆谓“大变局”背后的创巨而深痛,揭晓在一个民族劫难结束之际,必然迎来历史性的复兴与巨变。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8年,标志着新中国法制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1978年后的中国,开始从“人治”走向“法治”了,这对于具有数千年徒具“人治”和有限“法制”历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不可不谓“一大变局”。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法学家所开展的关于“法治”与“人治”的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第一个人权报告到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把这一治国方略载入宪法;从2001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到2011年3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法治的精神归纳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2011年,全国人大终于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一词已经成为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从国家的报刊到偏僻村镇的围墙上,随处都能看到“法治”的字样。在“法治”已经成为国人常识的今日,我们想追问的是:“法治”概念在今日的中国,除了前述象征脱离“人治”的意义之外,在法理学的意义是否能找到一个脉络清晰的概念界定?通过对我国法治建设现状的实证的考察,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天天在使用的“法治”并非英美国家的“法治” (rule of law),而是继受于大陆法系德国法传统的“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从当代中国法治概念所具有的法条主义、法律实证主义、法律保留原则、法治技术的理性主义、法治主义的方法论等方面的特征都让我们看到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的痕迹,“法治国”概念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从比较法的角度,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对法治概念继受本身的不足。
二、当代中国对“法治国”概念的继受的现状:一个来自比较法观点的考察
传统中国社会固然早已有“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3]对“国家”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描述,但现代意义上“法治”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缺失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法治”概念无疑是对本土外的该概念的继受。由于受当今世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影响,“法治”的概念也区分为来自德国的“法治国”与源自英美法系的“法治”。是以下因素促成了当代中国对“法治国”概念的继受:其一,历史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经历了数千年历史演进,该历史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而大陆法系与中国的传统法律均属于成文法的范畴;其二,清末法制变革。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缘起于清末的法制变革,“仿照大陆法系的构架建立了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4]P448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宣誓废除了一切所谓的反动法律,但大陆法系的理念已经融进了国民的精神世界;其三,地缘因素。日本为中国的近邻,其法制变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作为其近邻的中国,在效仿日本法律的同时,不自觉地继受了法律的概念,“法治”的概念也不例外,“德语的法治国随同其他德国的法律制度及用语,先传日本,再由日本传至中国”。[5]P52所以,尽管在中国大陆没有哪一本教科书或官方的命令要求选用大陆法系的德国“法治国”的概念,但该概念在政治及学术的话语中不知不觉地被使用了。
作为欧陆法传统发展典型的德国来说,在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思潮影响下,其“法治国”的概念当然地将立法机关的关键性角色凸现出来,国会具有的保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功能以及我们熟悉的“法律保留原则”与“法治国”的思想紧密相连;在“依法而治”思想观念的引领下,尽管今日德国的“法治国”概念已转向“实质意义法治国”,但其“实质意义”的法治主义仍具有浓重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特征。德国“法治国”概念所具有的这些形式化的特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法治”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其一、最低限度意义上的法治国——有法可依。
对于作为欧陆法传统发展典型的德国来说,有着重视法律作为一般性规范的背景,国会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部门。具体而言,由于德国十九世纪之“法治国(Rechtsstaat)”正是要在君主专政的政治背景之下,对抗彼时的君主王权,抵御来自掌握行政权力的君主官僚对人民无限度的侵害,从而要求君主王权若侵犯人民的自由与财产,不能没有国会的同意。因此,在这个“政府侵犯人民须有国会制定之法律作为依据的” 诉求之下,制定明确具体的“成文法”成为实现“法治国”的前提。尽管Rule of Law在英国法的传统中,基于英国法中所谓“国会至上”的理念,固然也重视国会与国会立法,但是在普通法的制度背景下,“所谓法治既然指向司法部门借由裁判活动来确保个案实质正义的功能,则个人权利保护的关键仍然被认为应该寄望于法院所提供正当程序的保障。”[6]P287因此,尽管德国的“法治国”与英美国家的“Rule of Law”都强调国会至上,但实现法治的路径截然不同,前者奉行“立法中心主义”,后者贯彻“司法中心主义”原则。
正是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概念的影响下,中国政府以完善立法作为实现法治国家的切入点。从建国60年特别是近30年以来的中国法治实践看,“法”居于突出地位。具体表现为:其一、立法至上。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中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先行者董必武提出了法制的主题思想是“有法可依”,在此精神的指引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立法的高潮,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另一次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法律的制定成为整个中国法治实践的中心,中央层面的人大立法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相辉映,地方人大与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更是如雨后春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在2010年终于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二、普法教育。在立法机关努力立法的同时,对公民进行普法教育同步进行,从1986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到2011年已经开始实施第六个五年普法规划。“立法”与“普法”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时代强音,也是中国“法治”追求的目标,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国”。其三、 法治国技术理性主义——追求法的确定性。立法机关不仅追求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面立法,而且努力实现法的确定性,其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法律出台后,各种司法解释随后出台,而且达到非常精细的程度。[7]国家通过立法、普法使法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法治即法律的思想成为人们理解法治的普遍观念。
其二、法治国家的真实特性——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原则。
“作为欧陆法治国传统的重要产物之一的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位原则(Vorrang und Vobehalt des Gesetes),并不能从英美背景下的法治基础上导出,也因此在英语世界中找不到足以完全相应的概念。”[6]P288其重要性与“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在普通法发展脉络中的重要性相似,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原则为大陆法系法治概念的最重要的内涵。堪称为德国古典行政法学始祖的奥拓·麦耶于1886年出版的《法国行政法原理》提出了法律保留的概念,他认为“自法国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以来,对于人民及财产的限制,必须保留在法律方可。”[8]P4在讨论行政及立法的关系时,麦耶提出了行政对法律的依赖关系的理论:“行政不能表达任何违反法律的国家意志,行政只能执行法律的意志,此即法律优位原则”。[5]P112在其十年后出版的《德国行政法》中对上述法治国的原则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在德国波恩大学担任公法教授的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在其出版的《宪法学》(Verfassungslehre)中对于法治国的概念有进一步的介绍,特别指出“法治国概念应包含法律保留原则,即:在国民主权统治下,唯有国民整体才可以对国民自由权利设限与作任何决定,所以法律所代表的是限制或涉及到人民自由权利的规定。如无法律规定,而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均是违法,且所有国家权力的行使不得抵触法律均形成市民法治国理念。”[5]P121德国基本法第二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个人自由不可侵犯。对这些权利之限制,只能根据法律才能加以实现”。
作为法治国概念真实特性的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原则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款及第九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该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在我国其他的法律如《行政强制法》等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中无不贯彻上述的法治国原则,在法律的层面上使我国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受到法律的保障。
其三、法治国家的具体实践——法律实证主义。
从德国法治国概念的萌芽及兴起的历史看,几乎所有的学者在提出法治国的概念时,皆强调使用法律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工具。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如毛鲁斯、格耐斯特、贝尔等明确提及,法律外尚有“法”(Recht)可以拘束国家权力,但这些所谓的“法”,并非指由法律更上位的法规,如宪法或自然法所引导出的法理念,毋宁是法律所衍生出的“法秩序”之谓。因此,整个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法学界在使用“法治国”的概念时,对国家的法律的不法的评价至多从立法的程序是否完备作为出发点,很少由公平正义及宪法理念来评定。“立法上不法”在德国的公法学界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才有著名的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提出,而成为讨论、批评一个实证法效力的重要用语。
德国的法律思想,到了施塔姆勒(R·Stammler),其法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完美结合,既关注法律的纯哲学意义的探讨,更注意法律的实效。著名的民国法学家吴经熊评价其导师施塔姆勒的法哲学思想时指出:“斯氏法律哲学,非幻想也,非凿空之论也;其一生精力,为欲解决近代德国法律及经济生活之实在与切要问题也”。[9]P248施塔姆勒的法哲学思想与美国法学家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思想具有极大的相近之处,庞德本人评价施塔姆勒的法哲学思想时说,“厥惟斯氏之法律哲学,不期然与社会学派之法律哲学同一结果也,斯氏与社会学派之法学,殊途同归”。[9]P262可以说,以施塔姆勒为代表的注重实证的德国法哲学思想及大地影响了吴经熊、王宠惠、居正等中华民国的法学家、法律家,当然影响了其后的中国的法制实践。
德国“形式意义法治国”概念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国家的具体实践,这种法律实证主义的特征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表现的最为明显。首先,对于“立法上的不法”,我国的宪法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制度的缺失,使法治的品质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其次、执法的目标上,“稳定”压倒一切,即追求“法的安定性”成为行政执法的终极目标,而法律理念的另外两层“正义、合目的性”[10]P73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三、在法治的具体实践方式上,“以运动式的执法模式为主。”[11]从全国范围看,以“严打”为主要方式,从1981年中央政法委布置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严打”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国家都要实施类似这样的集中执法行动。这些执法特征带有极为浓重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特征,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的情形极为相似。
第四、法治主义方法论——学者对法治概念形成的贡献。
英美普通法中,法律家们包括律师和法官对法治概念的形成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法治内涵的阐释也主要由法律家们来承担。纵观德国法治国概念形成的历史,与英美普通法相反的是,德国的学者们对“法治国”概念的形成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对于国家的概念,康德定义为:“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12]P138,康德这种结合国家与实证法律成为其国家观的立场,清晰地将国家统治与法律连在一起。因此,康德是“形式主义法治概念”的最早概括者。比康德迟生一代的政治学及哲学家威廉·洪堡(Wilhelm V. Humbolt,1967-1835)也是建构德国法治概念的早期人物,在其撰写的《一个尝试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意见》中表达了“自由主义式的实质意义的法治国”观念。自洪堡以后,哲学家普拉西度斯(J.W.Placidus)、浪漫派学者米勒(Adam Muller)、主张自由主义的魏克(Carl Theodor Welcker)、法学家莫耳(Robert Von Mohl)、法哲学家史塔尔(Friedrich Jujius Stahl)、法学家贝尔(Otto Bahr)、格耐斯特(Rudolf von Gneist)、毛鲁斯(Herinrich Maurus)、奥拓·麦耶(Otto Mayer)等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法治概念应有的内涵,推动了法治国的概念不断地走向成熟。可以说,德国之所以有19、20世纪法学的繁荣,从而成为世界大陆法系的翘楚,影响19、20世纪世界法学甚巨,其最主要的贡献由学者们创造。
中国之所以能继受法治国的概念,与德国极为相似的是亦应归功于中国法学者的贡献。其表现为,其一,学者们开启了当代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 的讨论。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学者进行了“人治”与“法治”的讨论,通过激烈的“概念之争”,主张法治的学者们“以深邃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时代透视力,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必须实行法治’的正确论断”。[13]P75其二、法学者们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从孙志刚事件导致中国收容条例的废除;从物权法的制定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入宪;从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阐释到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中国的法学者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为推动中国法治国家的实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三、学者们讨论法治的方法。中国的法学者坚持以纯粹法学的方式来解释法治的内涵,而非以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此一问题。其四、讨论法治国的概念皆由学者承担,法治国的讨论成为宪法学及宪法解释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当代中国对“法治国”概念的继受的积极意义
当代中国对“法治国”概念的继受无疑对中国的治国方略产生了积极意义。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改变,更是我国走向法治文明的标志,它亦是数千年来的中国的大变局之一,对我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起到奠基的作用。其积极的意义表现为:
第一、 治国方略的现代性的转换——实现中国法治的形式主义。
“法治”一词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是陌生的,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动走向开放算起,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已经走过160多年的风雨路程,但由于新中国从建国之初对法治的误读,到文化大革命所经历的十年浩劫,使中国的法治之路比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充满着更多的艰辛。自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开放,“法治”的概念无疑也被引进我国,一系列的因素使我国“继受”了德国的“法治国”概念,而该概念的最基本的特征是“有法可依”,正是在该概念的指引下,我国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立法运动,第一次以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为标志,后一次以我国加入WTO为契机,两次的立法运动使中国快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使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到2011年,我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我国变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律国”,实现了德国法治国的第一阶段——“形式主义的法治”。
第二、法律文化的开放——法律文化建设的多元主义。
“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究竟往何处去?”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面对这个历史课题,国人进行了四条出路的探寻:“原状复古;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摘取精华,自己创造”。[14]P3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一直到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中国走的是第二条道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的一声令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在大陆被彻底废除,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亦随之断裂,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法律文化在“一元主义”的主导下畸形地发展。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从接受经济的“多元主义”,到逐步接受法治文化的多元主义,此一继受的典型就是承认法治的价值,把这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变为自己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对“法治”概念的继受,实质是发展法律文化的多元主义,使中国的法律文化从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一般来说,追求单一的主流价值,无论代价是什么,都会导致片面性的后果。”[15]P169中国已经深深认识到这一点,这对发展中国的法律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第三、放宽中国法治的视界——法治发展的历史理性主义。
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集中地表达了历史理性主义的观念:“人类理性的自觉使人类历史不断地走向完美之境”。[16]P45历史是理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场由坏而好、由恶而善的不断进步。历史理性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历史的道路多么的曲折,但其向上、向善的历史趋势不可改变,人类的历史是从较低文明不断地走向高级文明的过程。中国尽管有着长时期的封建专制而无法治的历史,但法治作为当代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不应该成为西方国家的专利而被独享,亦应成为作为当代世界主要成员之一的中国所继受。中国走向法治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理性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展示。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果敢地摒弃“人治”的治国手段,与传统社会中的专制历史彻底决裂,大胆地继受完全出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使“法治”、“法治国家”等变为普通民众耳熟能详的语汇;其二,国家倡言法治并付诸实践。国家通过实施依法行政、司法改革并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全民普法等进行具体的法治实践活动,积极探索适合于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在继受西方法治概念的基础上,努力探寻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法治内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追求法治发展的历史理性主义的道路。
四、当代中国对“法治国”概念的继受的消极意义
当代中国对来自德国的“法治国”概念的继受固然有着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固守“规范论”的法律思维模式。
德国的“法治国”概念以法律的完善为其基础目标,在此目标的引领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运动,这对有着许多法律空白的中国无疑有着上述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其负面的影响,在此概念的影响下,“所有宣称‘法治国’(Rechtsstaat)的人,到头来其实是在追求‘法律国’(Gesetztaat),也就是说,‘法治国’在规范论思维取向下,已然质变为‘法律国’”。[17]P13在这种规范论的法律思维导向下,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第一、在法观念上,法律工具主义盛行。在这种“法律国”概念的影响下,使普通的民众认为,法律等于秩序,有了法律就有了法治。其实,规范与规则的思维,只是在法学任务与活动的完善整体中,从他处引导出来的有限的一部分。规范和规则无法创造秩序,它们只能在现存秩序的框架中、在现存秩序的基础上,拥有效力规模较小,且独立无涉于事物状态的——某程度的管制功能而已;其二、对法治之法应有品质的忽略。在“仅以法律为依归”的思维模式主导下,以制定法为中心所形成的“合法性”概念遂成为法实证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以“合法性”思想取代一切正当性的依据,从而忽略了法治之法应有的品质,使某些“恶法”成为司法、行政执法的依据,从而走向了现代法治的反面;其三、忽略了某些法律制度的构建。由于立法以“有法可依”为追求的目标,使建设法治国家应有的制度缺失,最典型的例子是,虽然在我国宪法的条款经常被修改,但作为法治国家标志之一的“违宪审查制度”却一直缺失,致使“立法上的不法”行为得不到遏制。
第二、在“我者”与“他者”之间——不能形成中国法治概念的独立品格。
来源于德国的“法治国”概念无疑使法治概念的本身带着浓重的西方色彩,对中国法治建设最典型的影响表现在法学的领域。“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中国的法学者研究法治的最主要的范式。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与对象,假定一概取之于西洋,其奈历史基础没法转换,主体的多数是中国人,这就使中国的法治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为此,庞德早已指出,“中国法典应该由中国的法学家发展成中国法律,并由中国的法官加以解释与适用;并且适用于中国人,以管理中国生活。如此,中国法律解释与适用始能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质与色彩。”[18]P191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处理好法治概念的“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形成如下的格局,其一、“我”与“他”的分离。这里的“我”指的是中国的问题,这里的“他”指的是我们继受来的法治概念。来自大陆法系的“法治”概念作为中国问题的“处方”在缺乏共同历史基础的前提下并没能针对性地解决中国的法治的病症;其二、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分离。当代的中国法学者以研究西方“法治”为己任,而中国的“法律家们”以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为其终极目标,造成法学界与法实务界的分离,其结果是:“法学界内部法学话语的分裂;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的分裂;法学家话语与法律家话语的分裂。”[19]其三、法治主体与法治客体的分离。西方的法治的客体是政府的权力,法治的主体为普通的民众,是以民众的权利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作为法治的客体政府却变为法治的主体,中国法制的发展明显带有由政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性质,如每一次大的立法活动都由政府唱主角,每一次大的普法活动也都有政府发起,等等,这使中国的法治建设陷入了康德的“二律背反”的境地,这种法治的主体与法治的客体颠倒的格局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所在。
第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忽略了传统法治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由于法治概念浓重的西方色彩加之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整体的反传统主义的流行,使中国的法治研究与法治实践呈现为反传统的现代性特征,即脱离本土的传统的法治文化来谈现代的法治主义,忽略了传统法治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庞德指出:“一项成熟的法律制度必须具备三项条件:‘法则’(precepts)以外,须有‘技术’(technique)以解释及适用法则,更需要有该制度所属社会里一般人‘已接受的理想’(received ideals)以为解释与适用法则时最后的根据。”[18]P191庞德所谓“已接受的理想”主要指一个民族传统的法治文化,任何民族的法治建设与一个民族之法制历史传统不可分。因此,庞德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习惯或许可发展成为一套现在社会“已接受的理想”,借以为调整关系及管理行为之准则。因此,传统伦理习惯与传统法律制度不应该因系过去的传统或因与西方制度不合,而即加以放弃;但也不应该因系历史上证明的传统,即作为解释与适用法典之根据;必须视其是否能帮助使法典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保持关系而定。“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20]P119这是在中国实行法治的困难所在,同时也是在中国实行法治的前途所在。若单纯靠立法的数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其结果是法律愈多,漏洞愈大,因为再严密的法律也不可能包罗万象。没有落实到每个人观念和行动中的尊重法治的法治文化的支持,任何法治都不能横空独行。在今日的中国,继受西方“法治国“概念无疑是快速建设法治国家的一条捷径,但是如果忽略了把本民族的传统法制文化作为继受“法治”的文化底盘,那么中国所继受的法治是悬空的,是“漂浮的法治”。[21]P167因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22]P7
结语
当代中国对西法的法治概念的继受总体上而言是来自大陆法系的德国“法治国”概念的某些形式上的“拷贝”,如今的德国“早已进入了强调以法正义与人权保障为最高理念的实质主义的法治国时代,法治国原则成为宪法原则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的是法治国体系的精细化与完整化。”[23]P593作为法品质保障的违宪审查制度及法治国理念骨架的三权分立的制度我们都是拒斥的。从与普通法比较看,我们使用频次最多的“法治”亦不是英美的“Rule of Law”,因为,在普通法背景下,法治指向司法部门藉由裁判活动来确保个案实质正义的功能,个人权利保障的关键被认为应该寄望于法院所提供的正当程序的保障。而居于英美法治概念核心的“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在中国还处于口号的阶段,远远没有化作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未来的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的法治应该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追求法律数量的“法律国”向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司法国”的转变;由“形式主义的法治”向“实质主义法治”的转变;由追求“实证主义的法治”向倡言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法治”转变;由追求仅是消极地保护人民免于危险的“消极法治”向积极谨慎地促进与支持个别国民的发展“积极法治”的转变;由追求继受西方法治概念的“外向型法治”向继承与超越本民族法治文化传统的“内向型法治”转变,等等。
中国的法治任重而道远,问题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到底要使用“法治”、“法治国”或者“法治国家”的概念用语,而在于这些概念用语的背后,我们到底是站在何等基础上、又透过何等方式,来理解与诠释当代中国法秩序中“取代人治的法治”落实的途径。对于这一点共识,才是促使中国走出对西方法治概念的继受使我国法秩序步入健全轨道的关键。
[1]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 李建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 《管子·明法》.
[4]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5] 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中)[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6] 黄舒凡.变迁社会中的法学方法[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9.
[7] 仅以刑法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对《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试点。具体规定了量刑基准、量刑要素、量刑适用规则、量刑方法,决定被告人的刑罚,是我国法律追求法的确定性的典型范例。
[8] O.Mayer,Theorie des Franzasischen Verwaltungsrecht,1886.
[9]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0] [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1] 孙曙生.对中国专项式法治治理模式的理性思[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6.
[12]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3] 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4] 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5] [美]威廉·A·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M].佟德志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2005.
[16] 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5.
[17] [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M].苏慧婕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18] 马汉保.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9] 孙曙生.中国现代性的法学话语的分裂及其意义[J].法商研究,2007,6.
[20] 刘军宁.从法治国到法治[M].公共论丛第三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7.
[21] 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2]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北京三联书,2011.
[23] 陈慈阳.法治国理念之理论与实践——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之德国国家法理论与政治现实为研究范围.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上)[M].台湾: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
TheSuccessionandSignificanceofConceptsofRuleofLawinContemporaryChina
SunShu-sheng
(Law Department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Nanjing Jiangsu 210013)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whether in academia or legal practice Department, although we all use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 it is actually a succession of country of Rule of Law or doctrine of Rule of Law in civil law system. It has brought a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also brought some negative effects. It has become a bounden mission in front of us how to come out of the succession and construct legal-order models of our own personality of development.
the rule of law; country of rule of law; succession; common law
DF044
A
(责任编辑:黄春燕)
江苏省人事厅2011年度“江苏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现代性与中国法治”(1101098C)阶段性成果。
孙曙生(1969-),男,江苏宿迁人,法学博士、博士后,江苏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治理论。
1002—6274(2013)04—0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