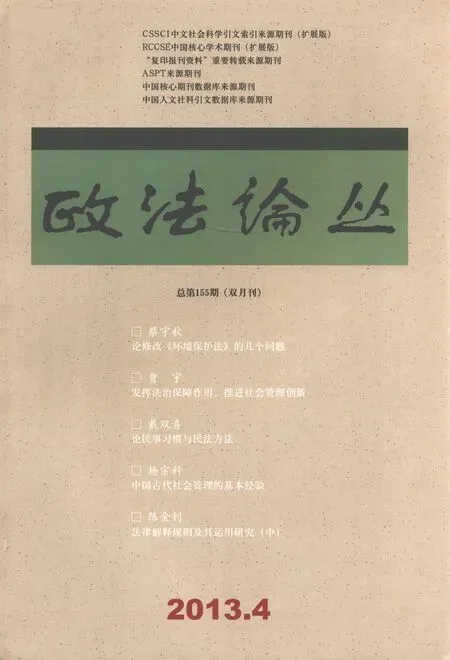彭州乌木事件的法解释学思考
王永霞
(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山东 济南 250100)
彭州乌木事件的法解释学思考
王永霞
(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山东 济南 250100)
彭州乌木事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讨论,针对乌木的法律属性和归属,形成了埋藏物、天然孳息、无主物等几种主要观点。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由于不具备埋藏物和天然孳息的核心要素,乌木不可能归属这两个范畴之内。我国法律并未确立无主物的先占规则,从解释论的角度观察,不论采取国家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都存在难以破解的困境,因此只能转向立法论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从立法论角度观察,国家本位主义立场需要的制度环境建设远远难于个人本位主义,同时个人本位主义对当前中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应是较优选择。除对实体性法律问题本身的思考外,这一事件中反映出的法学研究问题也值得反思和认真对待。
乌木事件 无主物 先占 法解释学
引言
乌木,学名阴沉木,由于地震、洪水、泥石流等原因将楠木、红椿等地上树木埋入古河床等低洼处,在缺氧、高压的状态下以及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经过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炭化过程形成。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以及收藏市场的推动,近年来市场价格非常高,一般每吨价值几千至几万元,其中以金丝楠乌木最为名贵。
2012年春节期间,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村民吴高亮在田里闲逛的时候,发现了地里埋藏的乌木。2月9日,吴高亮组织挖掘,当晚被通济镇政府阻止。次日,镇政府将情况上报市级相关部门。2月12日至23日期间,镇政府组织对乌木进行挖掘,共挖出7根金丝楠乌木,最长的达34米,市场价值超过千万元人民币。吴高亮与通济镇政府就乌木归属问题产生争议,7月3日,彭州市国资办召集文管、林业、司法、水务、国土等部门,对吴高亮作出正式答复:依据《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乌木属于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同时依据该条规定,决定给予吴高亮总计7万元的奖励。对于这个结果,吴高亮并不认可。2012年7月26日,吴高亮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乌木归自己所有。
这一事件见诸媒体后,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也引起法学界的激烈讨论,对于乌木的法律属性及其归属,论者众说纷纭。不仅事件本身的法律问题,即乌木的法律属性和归属需要进一步厘清,而且这些争论中凸显出的法解释学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乌木是什么?
彭州市政府在给吴高亮的答复中认为乌木属于埋藏物,吴高亮一方起初认为乌木属于无主物,起诉时主张乌木属于天然孳息。法学界对乌木的法律属性也存在诸多观点,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三种:(1)埋藏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宪忠教授持此观点,并认为埋藏物应归国家所有。(2)天然孳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龙卫球教授均持此观点,但是梁慧星教授以乌木是在河道中发现为前提认为河道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乌木的所有权应归国家,龙卫球教授以乌木是在吴高亮的承包地中发现为前提,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乌木是土地的孳息,应归用益物权人吴高亮所有。①(3)无主物。中国政法大学柳经纬教授和李显冬教授认为乌木属于无主物,应根据先占原则归发现人吴高亮所有,武汉大学孟勤国教授虽然也认为乌木属于无主物,但是主张应按惯例归国家所有。②确认乌木的法律属性,亦即回答“乌木是什么”的问题,需要首先对相关法律概念作出解释,只有在明确法律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前提下,才能确定乌木是否归属这一范畴。
我国法律对埋藏物的含义未明确界定,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对埋藏物的规制并不一致。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1款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同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由该条规定可知,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区别规制埋藏物和遗失物相同,《民法通则》将埋藏物界定为一般是所有人不明的物,③将遗失物界定为一般可以查明所有人的有主物,并据此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直接归国家所有。我国《物权法》改变了这种区分规制的立场,规定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并且规定了比较详尽的遗失物制度。立场的不同反映了对埋藏物性质认识的不同,我国《物权法》并不把埋藏物界定为所有人不明的物,而是将其认定为与遗失物相似的一般可以查明权利人的有主物。因此参照遗失物的规定,能够判定埋藏人的,发现人应告知或交还埋藏人,不能判定埋藏人的,发现人应告知或交给有关部门。[1]P252
基于我国《物权法》将二者等同对待的做法可知,埋藏物与遗失物这两个法律概念应在核心要素上相同或相似。遗失物的核心要素是其在被遗失前有所有权人,所有权人也没有抛弃该物以消灭所有权的意思,而是由于疏忽等原因暂时丧失占有。基于保护所有权的需要,我国《物权法》规定拾得人负有返还遗失物的义务,确实找不到失主的,经法定程序后归国家所有。埋藏物也应具备这些核心要素,即埋藏物在被埋藏之前有所有权人,所有权人没有抛弃所有权的意思,只是在该物被埋藏后由于各种原因丧失占有(例如遗忘、埋藏人死亡而继承人不知情)。为保护埋藏人或其权利承继人的所有权,我国《物权法》规定埋藏物准用遗失物的规定。埋藏物一般应是人为埋藏之物,由于自然原因埋藏于他物之中,所有权人并不知情的是否属于埋藏物,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实际上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并不像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具有现实法律意义:埋藏物是埋藏于包藏物之中的物,有些国家和地区规定埋藏物由发现人和包藏物所有人各取得一半所有权,有的国家规定埋藏物归包藏物所有人所有,但发现人可以请求包藏物所有人支付一定报酬。而对于遗失物,很多国家和地区均规定超过认领期限的,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严格区分埋藏物和遗失物意义重大,但是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和埋藏物的规制相同,因此由于自然原因埋藏于他物中的物是属于埋藏物还是遗失物,区分的意义不大。但是不论是人为原因还是自然原因,埋藏物在被埋藏之前都应当是有主物,不能是未曾归属任何人所有的物,这是我国《物权法》上的埋藏物的核心要素。乌木的形成至少需要上千年,即使这些古树被埋进古河床之前有“所有权人”, 也不是现代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人,更不是我国当前法律体系承认的所有权人,质言之,形成乌木的树木在被埋藏前不是现代法意义上的有主物,因此不能归于埋藏物,当然也不需要适用我国《物权法》的程序性规定,例如发现人报告有关部门,并由有关部门公告等。④
我国现行法律同样对孳息及天然孳息的含义没有明确界定,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物权法释义将天然孳息界定为依物的自然属性所产生的物,主要来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例如耕作土地获得的粮食和其他出产物,果树的果实、养殖牲畜获得的子畜和奶产品等。[1]P254这一解释将天然孳息限定于依物的自然性质获得的有机出产物。与之不同,学者们大多借鉴德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或法学理论确定天然孳息的范围。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对天然孳息的界定大致相同:包括依物的自然性质获得的有机出产物和依物的用途获得的无机出产物,前者如鸡蛋、水果,后者如矿山的矿物、采石场的石头。⑤虽然对于作为孳息的收益是否具有相当的定期性存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天然孳息的核心要素上没有多少异议:依据自然性质或物的用途一般可以从原物中获得的天然派生物。在天然孳息的归属上有“分离主义”和“生产主义”两种立法例,前者被大陆法系物权法广泛采用,规定孳息归属于原物权人,包括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等,后者被英美法系财产法接受,确认孳息系劳动所得,归属于投入劳动的人所有。[2]P86我国《物权法》第116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物权法释义中说明《物权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劳动的保护,这一解释揭示了我国《物权法》实际上采纳的是“生产主义”内核。同时,这一解释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土地出产物都是我国《物权法》上的天然孳息,一般应是人们通过劳动获得的原物的出产物才能被认定为天然孳息。
乌木是由于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界的异常原因将树木埋入古河床经过几千年上万年形成,并且只有少数品种的树木最终可以形成乌木。这一形成过程表示乌木并不是依据自然性质一般可以从河床或土地中生成的出产物,其形成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并且乌木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对于耕作人来说,不可能为获得作为天然孳息的土地出产物等待如此漫长的时间。同时,乌木的形成完全是由于自然的原因和时间的累积,并没有加入人的劳动,因此依据我国《物权法》,乌木不是土地的天然孳息。⑥
在关于乌木法律属性的争论中,还存在矿产资源说、古生物化石说、文物说等观点。如果对矿产资源、古生物化石、文物依照相关法律的定义或界定进行文义解释,乌木均不属于这些范畴。例如我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规定矿产资源的矿种和分类见《矿产资源分类细目》,乌木不在该细目之内。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规定古生物化石是指地质历史时期形成并赋存于地层中的动物和植物的实体化石及其遗迹化石。地质历史时期至少应距今260万年,而乌木的形成时间最长不过几万年。我国《文物保护法》虽然未对文物的含义作出解释,但是根据其列举的受国家保护的文物范围可知,除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外,文物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人类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遗物、遗迹,乌木作为自然形成的炭化树木,其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是人类和社会发展史上的遗物,所以不能归于文物范畴。
当然,法律适用的解释不能只采用文义解释一种方法,还有目的解释等其他方法,并且如果存在法律漏洞,还需要通过类推、目的论限缩等方法进行法律补充。首先,《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未将乌木列入其中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呢?即使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或地区,也大多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原因是矿产资源是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只有将其所有权收归国家,才能保障对其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我国《物权法》及《矿产资源法》均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时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了详细的勘探、开采制度以及法律责任。乌木近年来市场价格蹿升主要是由收藏市场推动,虽然其本身具有科研价值,但是对工业生产以及经济发展并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国家未将其列入矿产资源不存在法律漏洞。其次,是否可以采用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将乌木列入古生物化石范畴呢?古生物化石是鉴定和对比地层、了解地球历史的重要根据,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起源、发展历史及规律的珍贵材料,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这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规定古生物化石归国家所有并予以特别保护的原因。乌木并不具备作为古生物化石核心要素的特殊科研价值,因此不应归属于后者范畴。最后,是否可以采用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将乌木归入文物呢?文物的核心要素是其在人类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乌木在被加工成工艺品之前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文化价值,所以乌木不可能是文物。
那么乌木是无主物吗?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无主物这一法律概念,仅在《提存公证规则》中涉及到“无主财产”一词。大陆法系物权法一般认为无主物须为无主动产,包括两种情形:一为未曾归属任何人所有的动产,例如海洋里的鱼贝,山野中的禽兽;二为原是有主物,后被抛弃的动产。[3]P124如果我们借鉴大陆法系物权法的传统,乌木似乎应该属于第一种情形的无主物,适用先占规则由最先占有的人取得所有权。但是,我国承认这种情形的无主物以及先占规则吗?
二、乌木归谁所有?
我国《物权法》详细列举了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这些财产对于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或者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规定宣示了这些财产只能由国家所有,私人不能成为其所有权主体。除我国《物权法》外,还有一些特别法对国有财产作了规定。其中在自然资源类财产的归属和利用上,除前文提及的我国《矿产资源法》、《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外,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以及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归国家所有;我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规定国家保护珍贵野生植物和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野生植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采集或者破坏其生长环境;我国《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禁止采猎一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采猎二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必须持有采药证;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受保护自然资源类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保护范围之外的普通自然资源以及类似财产归谁所有?
对于这一问题,一种解决方案是凡是集体或私人不能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一律归国家所有。这一立场意味着在我国不存在真正的无主财产,国家保护范围之外的普通自然资源以及类似财产均属于国家所有。可以将这一立场称为“国家本位主义”。另一种解决方案是除非现行法律明确规定某类财产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否则应作为无主物,适用先占规则由最先占有的人取得其所有权。可以将这一立场称为“个人本位主义”。
所有权的归属不是权利人的目的,对财产的实际控制和利用才是其根本目的。国家所有权的实际行使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设定用益物权,例如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矿权、渔业权、狩猎权等,由用益物权人对国有财产实际使用和收益,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向用益物权人收取费用。自然资源类财产一般采取这种方式。二是由国家机关、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三是国家以国有财产作为出资设立或投资企业,通过享有出资人权益获取收益。如果将不属于国家保护范围的普通自然资源或类似财产的所有权一律直接归于国家,一个现实的困境是不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国家都无力实际控制和利用此类财产,因为现实生活中此类财产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并且非常分散,而上述三种模式都是将某类财产的所有权或用益物权集中归属于少数权利主体,这导致发现或者收集的成本巨大,而获得的实际利益可能较小。因此要实现这一国家所有权,防止资源浪费,可能唯一的方式就是由单位或个人发现、收集这些财产后上交给国家。但是单位和个人并不负有主动发现、收集的义务,单纯依靠个人自觉只能是国家或政府的一厢情愿,因此这种方式能够顺利运行的有效方法是对发现者或收集者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报酬或物质奖励。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在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有学者建议确立遗失物及漂流物拾得人、埋藏物及隐藏物发现人的报酬请求权,立法者最终并未采纳。由此可以推知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如果将国家保护范围之外的自然资源以及类似财产的所有权归于国家,发现人或收集人也不享有报酬请求权。这种处理方式只能导致很多人发现或收集这些财产后隐瞒不报、据为己有,或者不予理会、任其弃置。
任何一种调和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的制度安排,都需要追问其正当性。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最大困境在于极度扩张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范围会直接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例如我国《物权法》规定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我国《渔业法》规定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除生产经营性的捕捞业之外,如果采取国家本位主义立场,水流、海域中的所有原生水产品、海产品均属于国家所有,个人出于休闲娱乐目的的野钓将成为侵害国家所有权的违法行为。同样地,如果普通野生动植物资源均属国家所有,个人在荒山上采摘蘑菇,抓取蝴蝶、套取野兔也都属于侵害国家所有权的行为。但是这些休闲娱乐活动具有正当的也是必需的娱乐价值,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禁止这些活动。再者,如果所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都归于国家所有可能会侵害个人的生存利益。例如有人以采猎野生中药材为生,有人以在河沙中淘金为生,如果采取国家本位主义立场,采猎野生中药材和沙里淘金都应被界定为侵害国家所有权的行为,但是这一做法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国家为了微薄的经济利益损及的是个人的生存利益。
实际上,前面列举的野钓、采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为国家禁止。除此之外,更为常见的是对于被所有权人抛弃的废弃物品,国家并不主张所有权,而是由最先占有者自由处分。这一现实也导致我国民法学界一个通行的观点:虽然法律未明确规定先占规则,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先占规则的适用。但是这一观点只是对现状的描述,如果采取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是在现行制度体系下先占规则是否正当。有论者认为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有权放弃其所有权,现实生活中实际适用先占规则的财产就是国家放弃了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国家所有并不是政府所有,而是全民所有,作为全民的代表,国家是否有权放弃属于全民的所有权?是否需要经过法定程序,例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对先占规则的适用范围以及适用条件作出明确界定,否则国家放任先占是否损害了全民利益,更重要的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会导致现实生活中政府执法的任意和专断。乌木事件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以前,乌木并不值钱,维持在每立方米几百元钱的价格,对于个人挖掘乌木并出售的行为,地方政府并不干涉。近十年来,乌木价格从几百块钱每立方米窜升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每立方米,地方政府就开始主张对乌木的国家所有权。虽然地方政府大多以乌木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为由执法,避谈经济价值,但是政府依据市场价格选择性执法的事实显然会让人合理的怀疑那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托词,这也是彭州乌木事件中民众对地方政府发出“与民争利”、“疏于管理”、“选择性执法”的诘问的原因。
个人本位主义立场将这些财产作为无主物,必然需要借助先占规则以确立第一个占有人的所有权,因此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论证在我国确立先占规则的正当性。论者大多在介绍罗马法以及现代发达国家的先占规则及理论之后,提出我国也应予以借鉴。虽然这是我国法学界经常使用的论证方法,但是这是一种非常简单武断的方法。物权法具有浓厚的固有法色彩,其必然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前设,发达国家的制度并不能成为我国制度设计的当然理由。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权法或财产法中,先占不仅是一项规则或制度,它还作为一种理论是物权法或财产法的法理基础之一。西方学者大多以先占理论解释私有财产权利如何从无主自然资源中产生,虽然有观点认为先占会产生鼓励自然资源浪费行为的反效果,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是被西方国家广泛接受的财产法法理基础,并被认为先占规则已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习惯,如果抛弃这一规则,将会破坏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稳定状态。[4]P13-14我国借鉴西方国家的物权或财产权制度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是,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设计其规则及制度,而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正当性当然不能依据私有制国家的法理基础进行论证,而私人所有权的根据也不能通过先占理论予以解释。劳动报酬理论是我国个人取得私人所有权的法理基础,即个人对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的财产享有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我国《物权法》规定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我国《合同法》规定超过5年未领取的提存物归国家所有;包括前文所述的天然孳息的归属都体现了公有制这一制度环境以及所有权取得的劳动报酬理论:个人对不是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的财产不能享有所有权,只能收归国家所有。
法律的价值判断应该具有融贯性,因此无主物的归属也应体现劳动报酬理论这一法理基础。依据劳动报酬理论,经济价值小的无主物适用先占制度大多没有障碍,因为发现或者取得这些财产付出的时间和劳动的成本可以等同财产本身的经济价值,例如野钓、采蘑菇、捡拾垃圾等,赋予第一个现实占有财产的人以所有权可以认为是对其付出劳动的报偿。有些无主物虽然经济价值较大,但是取得这些财产的劳动成本也非常大,例如沙里淘金,采摘悬崖上生长的名贵野生中药材,将获取的黄金和药材的所有权归属淘金人和采药人也不违背劳动报酬理论。但是有些财产的经济价值较大甚至巨大,而发现或取得这些财产的劳动成本大大低于其经济价值,例如乌木,对这些财产适用先占规则就难以用劳动报酬理论予以正当化。在彭州乌木事件中,不少人当然地认为乌木不应归属吴高亮,包括法学界的不少学者,产生这一反应大多是由于用劳动报酬理论衡量取得私人所有权的正当性,即使很多人没有明确的意识到或者不能清晰的表达。
前文的论述似乎只能得到一个悲观的结论: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语境下,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和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都有难以破解的困境。但是这些困境是从解释论的角度观察而来,在解释论难以给出合理答案之时,我们需要转向立法论的角度重新进行制度设计。
如果坚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内核,需要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以及法治建设进程中对西方发达国家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的介绍和借鉴,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等客观情况,决定了极端的国家本位主义在我国已经丧失生存的土壤,任何一种国家本位主义都只能是有限的国家本位主义。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应首先承认无主物的存在,而不能采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或个人的财产均归国家所有这一极端做法。其次应承认适用于无主物的先占规则,并且划定先占规则的适用范围或者设定其适用条件。在将找不到权利人的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收归国有这一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先占规则应与劳动报酬理论相结合,只有无主财产的价值与先占人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本不过分悬殊的情况下才能赋予先占人以所有权。最后,依据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逻辑,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先占规则,不能以现实生活中可以依据习惯适用先占为由不予规定。当然,鉴于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和法律的抽象性特点,立法不可能对先占规则规定的非常详细,但是应尽量为行政执法和司法提供明确的标准。依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设计,对于无主财产的价值与先占人付出的劳动成本过于悬殊的情形,不能适用先占,这些无主财产应归国家所有。为了防止资源浪费,鼓励单位和个人积极上交财产,应规定发现人或取得人上交国家的,国家按照一定比例给予报酬。同时,为了防止法律价值判断的悖反,也应规定遗失物及漂流物的拾得人、埋藏物及隐藏物的发现人的报酬请求权。
如果采取个人本位主义立场,根据经济、文化、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扩张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范围,例如如果经过科学论证,乌木的科研价值巨大,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将乌木的所有权收归国有,禁止私人采挖。但是,未通过法律明确列入国家所有权客体范围的财产,不应归国家所有,这意味着不在国家保护范围之内的普通自然资源及类似财产都属于无主物,适用先占规则。至于无主财产价值与发现或取得的劳动成本过于悬殊的也归先占人所有的处理方式,可能与很多人的感情相悖,但是就像花很少的钱买彩票获得巨奖一样,可以将其归于个人的“好运气”。每个人在自然中生存,在社会中生活,都可能有好运气,也可能有坏运气,既然坏运气的后果需要自己承受,好运气带来的利益归于个人也并不违背正义。况且,当代社会有价值的财产大多已有所属,这种情形的先占不过是少数例外,对社会的基本秩序不会产生冲击。当然,就像买彩票中奖所得需要缴纳较高的偶然所得税一样,也应通过税收对超过一定价值的先占所得进行调整和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先占规则可能会鼓励自然资源的浪费行为。例如如果明确乌木属于无主物,个人可以适用先占规则取得所有权,在乌木价格节节攀升的当前,可能会催生大量破坏土地或河道的乱采乱挖行为。这就需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无主财产的先占行为不得侵害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等其他相关权利人的权利,也不得损害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实际上彭州乌木事件中有一个被媒体和公众包括法学界忽视的问题:如果乌木埋藏在吴高亮的承包地中,地方政府主张归国家所有,其挖掘乌木的行为损害了吴高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吴高亮无权拒绝挖掘行为,地方政府也应对吴高亮的损失予以补偿;这一挖掘行为同时损害了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地方政府也应对村集体予以补偿。如果主张乌木归吴高亮所有,挖掘行为如对土地或河道破坏过大,则吴高亮无权挖掘,如果破坏不大或者可以恢复原状,吴高亮有权挖掘的话,也应对村集体或国家予以补偿。
法律的价值判断必须具有融贯性,如果依据个人本位主义设立先占规则,现行的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和隐藏物制度都须修订,应规定所有人不明的,或者超过一定期限无所有人认领的,归拾得人或发现人所有,并同时通过税收对财产价值过高的情形进行调整。如果法律重新设计这些制度,埋藏物和隐藏物制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发现人和包藏物所有人各按一半比例共有埋藏物。无主物如果系埋藏于地下或其他财产之下的,可以直接或类推适用埋藏物制度。
任何一个法律制度设计都仅仅是纸面上的法,检视这一设计是否妥当,不仅需要看其是否能够顺利实施,还要评价其施行的社会效果。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先占规则设计如果能够顺利实施,有关国家机关不仅需要主动发现、取得价值较大的不适用先占规则的财产,防止资源浪费或者被侵占,还需要主动查处违法侵占行为。由于此类财产的类型多种多样,鉴于我国国家机关职责划分以及行使的现状,这一制度设计的最大困难可能在于体制障碍。⑦此外,民众对这些财产归国家所有的最大疑虑在于其不能真正实现国家所有权的本质——全民所有,而只是有关单位攫取利益的手段。彭州乌木事件发生后,不少网站做了调查,腾讯网的调查中高达98%的网民认为乌木应归个人所有,新华网和新浪微博的调查中也都有7成以上的网民认为应归个人所有。⑧除公众将对公权力极度挤压私人利益空间的不满情绪投射到这一事件之外,担心甚至确信乌木归属地方政府后将沦为政府部门的私利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国有财产的利用情况比较透明,政府能够真正将国有财产用于全民,相信大多数公众会认为价值如此巨大的乌木应归国家(全民)所有。因此如果将这些财产的所有权归于国家,这一根本性问题不解决,仍然会受到政府与民争利以及公权力任意专断的诟病。
相对于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制度设计实施的困难,个人本位主义立场制度设计的实施要容易得多。除现实困难这一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考虑外,基于个人本位主义立场进行制度设计在当前之我国具有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打着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侵害个人权益的事件屡见不鲜,公权力的行使常常任意专断的现状下,在私法中宣示个人本位主义立场不仅可以遏止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和任意行使,也对公众私权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而后者是建设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
结语:关于法解释学的思考
截止到本文结稿时间,吴高亮提起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确认乌木所有权的诉讼请求,由于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驳回,吴高亮表示将继续提起民事诉讼直接起诉镇政府索要乌木。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乌木到底归国家还是个人,依据现行法律,从解释论的角度观察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而立法论角度论证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法律的完善,在价值判断、规则及制度的设计上都可能对现行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变动甚至颠覆,并且常常有一家之言之嫌,难以作为处理当前案件的依据。因此吴高亮如提起民事诉讼,案件最后的判决将主要依靠法官自己的价值判断。
但是,作为法学工作者,法学界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显现出来的法解释学问题值得我们反思。适用法律解决乌木事件的逻辑应当是:乌木的法律属性→乌木的归属,而不应当是乌木的归属→乌木的法律属性。但是在这一事件的讨论中,很多人实际上预设结论,即首先确信乌木归属于谁,基于这一结论再去寻找法律规范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从法律规范出发得出结论。当然,如果预设结论是将相关法律规范以及法理内化的结果无可厚非,甚至值得钦佩。遗憾的是,很多人预设结论更多的是出于与普通公众并无二致的个人直觉或感情,借以论证的法律规范不过是对个人感情的伪装。实际上即使是依据个人直觉或感情所得的结论,也可以挖掘形成这一观点的深层次原因,并论证其合理或正当与否,但是在这一事件的讨论中鲜有学者作这一工作。而缺少了真正的分析和论证过程,法学研究将丧失其专业性,与普通民众依靠直觉、感情或者粗略的正义感进行评价并无本质的区别。例如在这一事件的讨论中,很多论者预设结论,认为价值如此巨大的乌木不应归个人所有,应归国家所有,并据以寻找支持自己结论的法律规定。有人寻找到了矿产资源,有人寻找到了文物,还有人寻找到了埋藏物,由于有关矿产资源和文物的现行法律规定比较明确,将乌木归入其中困难较大,因此更多的人将其归入埋藏物。在是否是埋藏物的争论中,否定方认为埋藏物需要是人为埋藏,肯定方坚持不论人为还是自然原因埋藏的物都应归属埋藏物以消除这一障碍。但是,即使可以用埋藏物规则来解决乌木归于国家的问题,如果将来面对与乌木类似但是不是埋藏于地下的财产,又将根据什么将其归于国家呢?例如陨石,由于其是人类直接认识各星体的实物标本当然具有科研价值,但是其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收藏上,国内现在收藏的人较少,没有受到过多关注,政府部门对一般的陨石买卖也并不干涉,如果陨石成为收藏界的新宠,价格蹿升,某人在荒无人烟之处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天价陨石,政府如果主张对陨石的所有权,又将寻找什么法律依据呢?因此将乌木认定为埋藏物与其说是适用埋藏物的法律规范必然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要将乌木认定为国有的手段,不过这个手段采用了法律的伪装而已。
在这一讨论过程中,还有一种典型的论证方式是列举境外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指出境外有这种法律制度或规则,即简单的推出结论:我国也应确立这种制度。虽然我国的民法制度包括理念不是从我国的制度及文化土壤中原生而成,大多系移植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移植或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必须充分论证其是否能在本国土壤顺利生长,不会产生排异现象。并且,除了“拿来主义”外,是否可以尝试考查在本国的固有环境下通过完善自身的制度(当然不局限于法律制度,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其他制度)或体制达到相同的甚至更好的社会效果?即使最后的结论是仍需移植或借鉴,这一研究过程本身也是有益的。尤其对于物权法这种固有法色彩浓厚的法律,更应该将研究的目光投射到本国制度、文化、历史以及民众意识的特殊性上,抛弃法学具有自足性的想象和法律的自负。
注释:
① 梁慧星教授认为乌木归国家所有建立在乌木在河道中发现这一前提之上,如果乌木确定是在吴高亮的承包地中发现,或许梁慧星教授最后的结论会有所改变。
② 参见雍兴中:《身价暴涨,地下乌木变国有?》《南方周末》2012年5月31日;徐霄桐、李丽:《民法专家激辩天价乌木归国家还是归发现者》,《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7日;龙卫球:《乌木权属纷争折射中国法理变迁》,载中评网http://www.china-review.com/sbao.asp?id=4422&aid=30456,最后登录时间2012年12月10日。
③ 针对埋藏物、隐藏物可能有所有权人的情形,《民通意见》第93条做了补充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
④ 彭州市和通济镇政府主张乌木属于国家所有的法律根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但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基本原则,埋藏物的规制应适用我国《物权法》的规定。
⑤ 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7页;[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⑥ 我国现行法律并不像德国法传统一样将树木作为土地的组成部分,而是将树木作为独立物对待,乌木是树木的直接转化形式,因此依据我国法律,乌木应仍属于树木所有权人,而不能作为土地的天然孳息。我国法律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未遵从德国法传统,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物权法的基础是公有制,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不可能将建筑物以及树木等地上定着物都作为土地的组成部分一体归国家所有,而德国法传统的物权法以私有制为基础,并不存在这一障碍。
⑦ 2010年安徽安庆打捞出150余根,总重2000多吨的乌木,被收归安庆市政府所有,除42棵作为安徽省博物馆的观赏树外,剩下的乌木在两年间并未得到妥善保护,放置在乡村菜地无人看管,安庆市林业局、国土资源局、博物馆均认为无职责或无权管理。参见张火旺:《安徽安庆2千吨天价乌木被弃 百棵去向成谜》,载人民网,http://energy.people.com.cn/BIG5/n/2012/1128/c71661-19721223.html.
⑧ 参见:腾讯网http://view.news.qq.com/zt2012/wumu/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7/10/c_123392826.htm;新浪网:http://topic.weibo.com/areahot/25272?pos=0&lable_t=tips最后登录时间:2012年12月10日。
[1] 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 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3] 史尚宽.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 [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M].钟书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ThoughtsonPengzhouDarkWoodEventinLawHermeneutics
WangYong-xia
(Post-doctoral Station in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Pengzhou dark wood event stirred up much debate in our legal research cirde. There are several leading opinions about dark wood’s legal nature and its attribution, which include buried property, natural fruit and unclaimed property theories. According to our current law, dark wood doesn’t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buried property or natural fruit because of its lack of the core elenents. There is no legal regulation about unclaimed property and occupation in China, and it will be got trapped in difficult position either to take nation oriented standpoint or citizen oriented one. Consequently, we should design new legal rules by ourselv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citizen oriented standpoint is proved to be much better than the nation oriented one. In addition, we ought to think of those defects in our legal research appeared from the debate deeply.
dark wood event; unclaimed property; occupation; law hermeneutics
DF521
A
(责任编辑:张保芬)
1002—6274(2013)04—114—08
王永霞(1975-),女,山东枣庄人,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讲师,山东省民商事法律与民生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