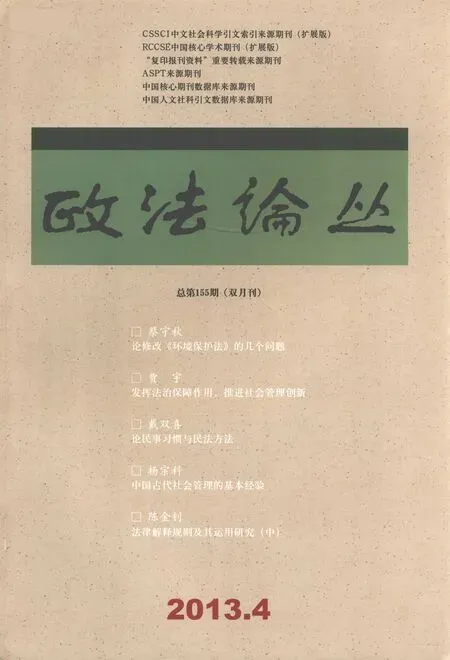法律论证与裁判智慧
徐梦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一、法律论证需要面对现实的复杂情形
(一)法律论证有效性需要依循特定语境
“法律论证”一词来源英文单词的“legal argument”。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法律论证分为不同的类型,最通常的划分就是分为形式法律论证与实质法律论证,其中前者通常是指形式逻辑中所说的演绎论证、归纳论证和类比论证 。在分析评价时,前者只关注论证形式,而不管论证内容,即只从狭义逻辑观出发,仅从语形和语义角度讨论法律论证的评价问题;后者则是需要结合论证的内容来进行论证分析与评价,即主要从语用维度讨论法律论证有效性。
关于法律论证的界定,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从最低限度的共识上来分析,可以说法律论证主要是对于某种立法意见、法律表述、法律学说等的确定性与正当性提出理由、意见或根据来予以证明。归结起来,就是对于法律命题证立的过程。法律论证的理论源流、确证标准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陈述策略、话语情境来确立不同的论证模式,这样也注定了法律论证是一个开放性的、能够容纳多种语境认同的界定与归纳。另一方面,揭示一种为多数人认可的结论的合理性这一目的,使法律论证总体的发展趋势扮演的主要是方法论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一方法论又以开放的态度将更多的可能依循可接受性原则的理论框架纳入其讨论范围之中。所以,法律论证是一种以提供正当化理由为特征的非形式论证。在结构上,法律论证是法律语境中一个结论和若干个支持结论的前提组成的陈述句序列。这一定义展现了法律论证的形式特征:一个法律论证只有一个结论;一个法律论证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前提;法律论证中基本的语句只能是陈述句;前提必须在证据上支持结论。
法律论证通过相关性、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对论证有效性进行评价。这些评判标准离不开相关语境要素的关联性参照和推进,从而确保论辩进程中命题相关性、依据充足性和定识体系、预设图景以及诉诸根据与对象性质的融贯性。这些目的的达成不但需要通过形式逻辑思维的进路予以推导,更需要融入法律人的以专业智识为基础的技艺展现、公正考量和有效判断。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案件,因而一定程度上,他们面对的都是独一无二的问题。况且“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中的人,其需要及其需要的满足状况存在差异,”[1]因此,很多情况下,法律人必须在对由于资料的不充分、问题的不协调性和核心问题的凌乱性过程中,以及无法逐步分析特定法律问题的时候,通过内在的感知迅速地对可能的答案进行猜想、设想与判断。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试图寻找顿悟和灵感,这种思维主要是直觉性的。
(二)法律论证思维中直觉因素的渗透
许多司法裁判实例中都体现出来某种直觉性反思,或者裁判智慧或许并没有直接体现为特定的演绎推理过程,甚至有可能许多裁判就是根据直觉性的正义观念而得出。之后的合理性论证或许并没有真正地反映法官思维中的跳跃性和灵感。有学者就认为“正义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们心里的直觉法。”[2]P241并且,能够通过正义与否进行判断的主体及其行为主要是“看似对行为有自由选择权的相关主体,该主体不是在必须、强制或他人权威命令的压力下行为。”[2]P243在这里,正义成为一种表征伦理冲动的心理现象。进一步说,无论是行为合理性的论证还是规则针对的行为类型的选择,都离不开对行为主体的内在动机甚至个性的探究。“仅凭人陈述的逻辑性是无法弄清理由是否是合理的,还必须考虑到作用于人内部的心理动机。”[3]P132在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看来,越是涉及伦理、哲学、政治、心理或者社会问题,而不是考察具体对象的经验操作,就越是依赖思想者的人格结构。“不但成套的学说或理论体系如此,就连像爱、正义、平等、理性之类的单个概念也是如此。”[3]P188基于主体性格模式的分析有助于探索法律行为的动机要素,挖掘深层的利益协调方法;借鉴心理分析有利于促进纠纷的解决、正义的实现。这种观点从内在层面和精神层面将司法审判作为特殊的心理过程,强调主体单方面的体验与理念,固然有其独特的视角以及片面性,但这种观点也从侧面证明了法律以及法律论证思维的心理本质,以及灵感与直觉要素存在的合理性。
二、案件的特殊性与问题化——对“例外”的探寻
(一)例外的普遍性
正如上文所言,不同心理动机以及理念指向的多样化与独特性决定了每一个案件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面对普遍性原则与规范的对应时,发现例外情形表现为一种常态。例外指向的是一种关于规则与论证的可批判性与可反思性。任何原则都有例外,而这些例外本身可能又根据某种相关性准则连接到一起,形成新的原则。因而原则和例外之间的关系很难从线性的、单纯纵向地推断下去,否则最终会走向一种对原则自身的毁灭以及观念本身的重复论证与自我证明。如果能够从网状的、互动性的以及对话性的角度,用开放的、商谈的和语用的视角来俯瞰这种悖论性状态,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解开例外悖论死结的方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分析将从例外本身的互动性与对其得以延伸性反思的关于特定范畴、原则、规则与关于其他法律观点的论证的可反驳性的分析当中,找到一个得以洞悉被直觉性思维掩盖的法官裁决智慧的机理及其得以培养与提升的空间与可能性。
(二)裁判原则及其例外的语境依赖
法律论证思路并不总是严格地将法条作为大前提,有时需要通过具体案件抽象出来的道德评价原则作为大前提进行判断。这个过程更多地作为裁判智慧深刻体现在案件中。然而现实的裁决或许包含了更多法官的直觉要素,例如经典的所罗门王在两母争子案中的判断。在基督教的《旧约全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住在一栋房子当中的两位妇女都有一个儿子并且年龄相当。一天夜晚其中一个孩子被他母亲在睡梦中压到口腔,窒息而死,这位母亲就把另一个孩子换了过来,后来这两位母亲由于对活着的孩子的争夺到所罗门王那里寻求裁判。由于双方争执不下,所罗门王说他决定用剑将这个孩子劈成两半,每个母亲分得一半。孩子的亲生母亲听闻该判决立即下跪要求将孩子给予另一方,不要伤害孩子,而另一位母亲则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接受。此时,所罗门王相信那位疼惜孩子的妇女才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应当享有抚养权。显然,这个故事主要是为了彰显案件裁判过程当中所罗门王的直觉性智识以及高明的智慧。在当下社会,任何法官都不允许通过这个有损生命权利的裁决方式断案,更何况通过DNA的鉴定方法完全可以解决类似问题。那么是否意味着这种基于灵感的、直觉的、充满智慧的并且是特定的纠纷解决方法在寻求程序正义和法治的稳定性的当下社会中无法适用了呢?或者即使可以适用,也只能运用于调解等除司法审判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
关于特定裁决的公正性,需要通过理性论证的方式,并对法律推理过程中的大小前提的合法性、有效性、正确性与正当性进行解释和说明。即使是类似于所罗门断案中的智慧也可以进行理性分析。针对该案裁决的合理性依据,人们通常倾向于指出,孩子的抚养权理应由亲生母亲享有。亦即,任何基于良善的原则判断道德标准的理性主体,在面对这样的命题,即因为X是Y的母亲,所以X应当照顾和抚养Y的时候,都很难予以否认这一命题基于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类型的逻辑普遍性。这项规则在该案当中可以作为有效依据,并且在我国的《婚姻法》中就有该项依据,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因而所罗门的思维在因果逻辑层面上也可以转变成演绎推理的过程:
大前提:亲生母亲应当是他的孩子的理所当然的抚养人。
小前提:不忍心将孩子劈成两半的妇女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结论:应当将孩子交给不忍心将孩子劈成两半的妇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例外的或许对于所罗门所在的时代无法预料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些情形,例如:
情形A:两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后,双方父母认领错误,将对方的孩子抱回家并抚养长大,并且父母和其非亲生的孩子之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情形B:孩子的亲生母亲由于吸毒或者其他情况不具有抚养孩子长大能力;
情形C:某女性由于意外的原因怀孕并产子,她不具有抚养孩子的意愿,并且她所处的社会对于孩子的收养规定完善,需求很大;
情形D:特定社会情境中如果借腹生子是合法的,某妇女甲由于和不具备生育能力的主体乙签订合同,她就应当履行怀孕并生子的义务,并获取一定报酬的情况下,孩子的抚养权由乙方享有,等等。
以上这些情形都使人们在面对之前确立的“孩子的抚养权理应由亲生母亲享有”这项规则的时候产生怀疑和顾虑。毫不夸张地说,上述列举的几种情况在当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多清晰对应的相似甚至相同的现实案例。法官在面对诸如此类的案例时,就需要慎重考虑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博弈,以及规范的例外情形对于特定主体利益保护的倾向性。例如,我国《婚姻法》关于抚养权的规定主要就是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这样的原则,该原则引导的裁决指向在上述情形中就可以找到合法的依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特殊情况都可以找到无可辩驳的理由,因为很难证明在情形A中打破规则界限的理由单纯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在亲生父母的家庭孩子可能受到更加良好的照顾和教育,因而法律体系当中不同规范对于例外的考察并不像以上提到的例子那么完善。更何况这些规范有可能仅仅来源于生活常识、文化传统、政策理念、乡规民约,甚至偏见、误解与潜意识,这些造成论辩进程的谬误难以避免。再加上“证据证明所用的论证也不是演绎推理,只是合情论证。”[4]因而,对于案件裁决中的规范指引就需要法官以及其他法庭主体在理性商谈与论辩过程中予以辨识、探寻、分析以及确立。
(三)扩展发挥裁判智慧的空间
法官在规则设定的空间能够施展自由裁量权,例如在规则的例外情形中,在数额(如赔偿、补偿、抚恤等)、时段(如合同期限、有期徒刑的年限等)、方式(责任承担方式能够选择的情形下)和理解方式(特定法律规范的抽象程度可以产生多种解释和解读)等的选择中,在法律规则缺漏的填补中,甚至在寻找法律规范体系以外的裁判根据的过程中,法官都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的公正理念、创造性思维甚至直觉要素渗透其中。在规则自身的逻辑结构层面,有学者指出,所有法律规则都在内在层面上具有可反驳性与可废止性[5]P68-355。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无法避免,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现实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世界的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所有的解释肯定是暂时的,我们最好在对实际问题作结论时十分谨慎。”[6]P6由于不同法律原则的相互作用,以及规则针对现象和主体特征的多重可能性,规则当中存在广泛的操作性空间和体系性的各种例外情况的现象普遍存在,这里不仅涉及价值判断体系的不稳定性,如效率和公平的博弈、秩序与正义的较量等,还涉及到在特定论证在探寻可普遍化的依据过程中与现存法律规则的协调、摩擦与弥合等。即使是在同等类型的不同案件中,特定情形特征的考察也有可能使规则发生大相径庭的例外考量①,这也决定了法官创造性思维的谨慎性和理性前提。
现实案件当中,不仅应当给予法官,也要给与法庭情境当中的其他法律人甚至当事人更多的创造力展现、创新性思维甚至直觉性反思的空间。这种空间或许不仅仅是平等、真诚和理性的商谈情境能够解决的,因为其提供的主要是程序性保障,而没有实质性促进。并且这种程序性要件的合理性没有扩展到关于创造性反思的范围、对象类别以及推进方法的限制的层面,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显性的功能性运作,只是作为一种程序性批判的依据。在一个缺少诸如所罗门王智慧的法庭情境当中,即使每个法律主体都极尽态度和表达的真诚性、确保依据和凭证的正确性和前提的真实性,也都很难有效地将裁判论证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在最大化程度上实现。
三、不同向度的论证思维——普遍化与抽象概括
(一)普遍化对应情境可能的特殊要素
普遍性具有可普遍化特点的规则或者理念性原则对于演绎推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一般化原则或规则本身的绝对化程度或者对其他可能性的包容范围决定了结论本身走向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各种逻辑推理的前提都依赖于各种不同的抽象性原则作为大前提或者是归纳依据。理解这一术语对于法律论证的思维性引导作用可以从可废止性论证的分析入手。可废止性论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普遍性前提或大前提中的“例外”存有包容性,或者对于和论证结论本身相悖,或者难以与该结论相融贯的情形存有开放态度的一种论证。也正是因此,这种论证方法充满了判准性的争议,因而,与纯粹的归纳和演绎思维不同。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种通过举例的论证类型中分析出来②:
论证A:
普遍性前提:证人的证言总是为真。
附加前提:证人说现在外面有雾。
结论:现在外面有雾。
该论证结论通过一种典型的基于证人证言的演绎推理过程得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种可以直接找到反例证明该普遍性前提的可反驳性。但这并不妨碍这种演绎推理的逻辑有效性,即预设前提普遍性的绝对化,当前提为真的时候,结论不可能为假。事实上,这种推理的大前提通常的理解可以在论证B中得以理解。
论证B:
普遍性前提:证人的证言具有为真的可能性。
附加前提:证人说现在外面有雾。
结论:现在外面有雾。
尽管不具有演绎有效性,但现实生活中这种思维进程普遍存在。前提对于预设的普遍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或者说前提涵盖的多重语境已经为目标合理性的探讨留下了可兹商谈的空间。这种思维和归纳推理类似,虽然表现为通过个例来验证前提的科学性,但这里主要侧重的还是论证结论正确性的思维进程与依据序列(各种证据类型或者其他证成依据)。论证C中的普遍性前提或原则可以说就是上述可废止性前提的表述方式。
论证C:
普遍性前提:如果没有例外,证人的证言可以视为是真的。
附加前提:证人说现在外面有雾。
结论:可以暂时(试验性或可预期的)将现在外面有雾视为真的。
对于论证结论的确信如果建立在可兹反驳的认同基础之上,那么这种论证就属于可废止论证。其前提的依据并非建立在归属于其可普遍性的个例的数量上,而是认同一种情景类别和该前提存在不一致处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把结论作为通过各种情景要素予以衡量的结果。该结果也需要其他例外性或者反驳解释或理由的验证。或许在特定情境下附加前提中的某种事实或观念性内涵极具特殊性从而无法满足普遍性前提的预设,那么该结论就要被推翻。
论证D:
普遍性前提:如果没有例外,证人的证言可以视为是真的。
附加前提:证人说现在外面有雾。
结论:可以暂时(试验性或可预期的)将现在外面有雾视为真的。
存在新的依据或前提:证人在法庭内,且法庭所在的房间没有窗户。
得出新的结论:外面有雾这一证言不能再视为真。
显然,新的证据指明了一种情境,使证人的证言无法为真。这种情况是具有说服力和反驳力的理由。新的信息总是能够使先前已经被认同的或者被确信的情形被推翻。这种新的信息又有可能基于各种来源而使说者预期的论辩走向陷入始料未及的被动境地。正如麦考密克所言,人际情境的多样化使预见到所有可能性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因而保有一种现实性的,对意料之外的情况保持一种开放态度,并且随时准备明确地回应这种意外情况的智慧是必不可少的。[7]P94大法官卡多佐也用具有象征性的语言描绘了例外情形以及溢出规范预设可能性的选择对于法律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为提升思辨魅力具有的价值。“法学的胜利在于煽动心灵的反叛之火,而不是用陈词滥调来平息它。”[8]P85因而,仅仅认同法律论证本身的可废止性只是提升论证合理性与可接受性的第一步,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通常情况下对可普遍性原则与规则的依赖,以及普遍化对个例的倚重与概括性对于规则抽象程度之间的关系识别。
(二)横向的或语境的关联和纵向的抽象程度的关联
裁判智慧的关键不仅在于裁决结论依循的原则的普遍性与抽象层次,还在于界分与借助不同原则与理念之间的关系。裁判者在推理思维当中往往会形成一种连贯的或者可以作为相互支持的原则体系。例如在所罗门所断的亲子关系案中,他的智慧主要体现在通过“将孩子劈成两半”这种方法形成一种貌似公平的结果,而他事实上依循的却是这样的观念:“亲生母亲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尤其是肉体上的。”姑且将这个观念视为支持性观念B。
普遍性前提:亲生母亲不会容忍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尤其是肉体上的。
附加前提:该妇女祈求所罗门不要伤害孩子。
结论:该妇女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观念B的支持性解释可以表示为“亲生父母对孩子的爱护”(姑且成为观念A),那么他们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同时,观念B本身又可以成为前述探讨“孩子的抚养权理应由亲生母亲享有”(姑且其成为观念C)观念的支持性原则。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逐步抽象或者逐步解释的逻辑链条:

该思维如果建立在法律目的的约束范围之内,就可以将某种对于观念C具有双重论证力的原则附加到这一链条当中,即我们可以假定法律目的或者通常的道德理念都将特定关系类型当中孩子利益的保护放在首位。即可以确定观念D:通常的道德理念和规范目的都会将孩子的利益放在相对重要的位置,基于孩子的年龄以及其和家人的关系状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B和D两个要件如果有一项不满足就有可能影响结论C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例如上文所述的关于所罗门案的几种例外情形。即观念B在未曾预期对各种例外情形的有效解释与避免就有可能面临风险。这种考虑不但影响法庭主体互动进程中交往理性与策略理性之间的平衡,也对包括法官在内的诸多法律人的认知参照与智慧提出挑战。
四、裁判智慧的理解与整合——关联性分析
关联原则意图在明示的对话互动者之间形成尽可能最大化的共识性理解与认同。而法庭情境中的话语交往通常都是明示性的。法官作为说者(作出审判结论的主体)首先要作为当事人及其他法律人的听者,这个过程是一个主体间的商谈进程。而对于法官个人来说,他就要秉持一种对话语或其他信息(如通过证据获取的)理解的开放态度。否则就有可能陷入逻辑悖论的怪圈、无限抽象化依据探寻的困境和循环论证的泥淖,从而导致认知层面上的识别错误与偏差以及公正理念的判准与运用隔阂,最终造成不公裁判的结果。
关联理论依赖于案件本身信息丛的语用性或语境依赖性。法官与其他法律人为了实现最终的具有可接受性的裁判结果,通常会尽可能地寻找案情表面意义之外的额外信息,并通过这些提示为大小前提细节的树立和弥补找到线索以及对应的核心问题。这些额外意义主要就是“预设、寓义和命题态度”[9]P3,这些额外的信息不但从不同指向将语境转换的可能选择与预测进行了归纳性总结,而且对原有命题本身的逻辑性、完整性、可信度和有效性等进行检验、修改和补强。这种效果有时甚至不是法官或者其他法律人刻意为之或者通过严谨的逻辑形式推理得出的,有可能正是特定要素的启发性与融贯性使特定问题的解决突然或者逐渐有了头绪和线索,甚至指向一个直通最具普遍可接受性的结果预期。因而就产生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在不违背“法和法律的精神意识、规范制度、行为方式等”[10]前提性涉及的情况下,使裁决效果的现实评价与影响远远超出法官或其他法庭主体的预期和理解范围,尽管有时会存在并非“喜出望外”而是负面效应的风险。而对这种风险的判断往往和特定语境以及背景当中的裁判文化与传统有关(更强调实体或程序等)。③
在著名的马伯利诉麦迪逊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巧妙地回避了和时任总统麦迪逊的正面冲突,同时也通过诉诸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欠缺以及原告诉诸的法律和宪法相抵牾驳回了马伯利的诉讼请求。该案在策略性和技巧性上体现了法官的问题指向和游刃有余的精明,但该判决能够成为日后树立著名的违宪审查制度的依据及其重大意义是马歇尔法官未曾预料的。尽管如此,这种审判智慧仍应属于司法理性的部分,“司法理性属于一种专业理性,”[11]这种理性还可在许多例证中表明④,当下情境中产生的欲求甚至激情是引发人们具体行动的关键要素,“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对遥远的未来进行总体反思后的选择;相反,理性指示这种欲求、这种激情的努力。因此,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来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们也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12]苏力对于法律裁决情境化要素的强调本身蕴含了一种对于裁决效果难以预期的强调,以及当时当下情境要素对于裁决本身的走向和影响力的决定性效果。
结论:裁判规则对多重可能性的容纳
任何规则都很难照顾到不同案件的当事人的细节与特点。世界上不存在专门为了法条的参照框架而发生的案件,恰恰相反,社会情境的分门别类以及不同案件的关系模式形构了法律规则的安排与体系。规则的确立总是建立在对特定行为的选择范围限定及其激励与惩处基础之上。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刑法当中对各种犯罪行为类型的架构与情节体系的确立,从而对不同情节的行为处以不同层次的处罚。在其他部门法当中这种特点也是普遍存在的。规则本身的线性思维总是将执着于一种现象到一种结果,但忽视了各种可能性的存在,甚至忘却了规则本身的意图恰恰根源于违法或者悖逆规则的基础。如果法律单纯通过激励和处罚将萝卜加大棒的方法用到极致,单纯强调审判技艺的司法体制则将这些方案在现实中体现出来。然而,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往往也基于行为结果本身的利害权衡。在两种能够带来同等收益的违法结果中,相对无法用更高的付出成本或代价来弥补这种对违法收益的渴求的情况就很难实现规则的意图,更何况现实生活中有诸多狂热的铤而走险者。此外,即使法律通过极为严格的补缺性或惩罚性后果阻却了特定情况下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很难阻止行为人用五花八门的更加隐秘、复杂、巧妙甚至掩盖着良善外衣的手段达到目标,并带来更加恶劣的社会效应,⑤这就是遵循线性思维规则本身以及司法体制无法预见和避免的情况。“很多不公都源自于概念上的专制。当人们将概念视为真实的存在,鲁莽地运用它们而无视逻辑对结果的限制时,它们与其说是人们的工具,毋宁说是专横的主人。”[8]P129这些不公忽略了规则的例外、忽视了溢出制度和司法程序以外的刺激性要素、忘却了人类拥有提升、改进、扩展和发掘各种可能空间从而达到目的⑥的能力,甚至无视来源于经验的智慧以及针对上述规则的悖论能够灵活地依情况而定,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启发性方案。“制度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类行动所构成的。这些行动中有许多是习惯使然,很难说有什么目的。对于那些有目的的行动来说,行动者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对于那些参与制度创制过程的人们来说,他们对于自己所造制度的目的和功能也可能有着相当多样化的理解。”[13]P170规则与激励绝不是智慧的最佳替代品,实践智慧也绝离不开做出正确、公平之事的意愿与动机。
总的来说,具备深厚裁判经验以及相关实践智慧的法官通常能够熟稔规则涵盖的要件、构成以及范畴体系在对应案件事实中的关键点与核心问题。他们未必一定要寻求裁决依据的无限抽象性证明,“当抽象出来的东西仅仅能够适用于法律思维时,就已经不错了,没有必要要求它一定还要普遍适用于人类一切思维,也就是说,关于专业思维的逻辑抽象未必一定追求顶级抽象。”[14]因为,他们能够做到知晓案件本身固守规则预期可能带来的社会效果,知晓如何寻获可能的溢出规则要件本身的更佳的解决办法,是借助于其他社会规范,还是在可能的基于正确性、合理性、有效性以及面临可批判性检验的信心来平衡案件独特性对规范评价抽象等级层面上的论证,并且在此基础上发掘更佳的可能性选择。纯粹进行逻辑探寻而忽视酌情要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墨守陈规都可能在审判中带来严重的毁灭正义的结果。
注释:
① 例如前文所述的不同的关于生母对孩子的抚养权判断。
② 这里不再采用大小前提的说法,为了和通常情况下以规则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区分开来,并且说明通过某种依据得出的某项结论具有可普遍化的特征。
③ 例如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在按照严格的按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和程序主义原则的之后做出的无罪判决引起了包括本案检查官、诸多专家学者甚至公众对美国司法体制公正性的怀疑与批判。
④ 例如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妯娌二人在争夺一个陶罐难分上下,并且没有明确依据证明该陶罐应当归属那个人的时候,法官一怒之下将陶罐摔碎,并自己出钱分别补偿了该二人。在效果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结果。这和本文关于裁决智慧的理念似有偏差,但主要是为了说明语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有时导致结果效力可接受性超出预期。
⑤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仅举一个比较细节化的例子,见“中国新闻网”:组图:走私毒品藏匿方式五花八门 伪装成巧克力:“今年以来,福州海关已查获毒品走私案件15起,其中邮递渠道10起,旅检渠道5起,缴获毒品海洛因、K粉、冰毒10479.25克。查获毒品的藏匿方式日趋隐蔽,伪装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如夹藏在鞋底、画册、枕头里,伪装成巧克力、茶叶、嘉应子、咖啡等等。”http://www.chinanews.com/tp/news/2010/06-26/2364444.shtml,2010年06月26日。还有更加离奇的无法料想的此类案例,见http://www.tianjinwe.com/tianjin/tjsh/201007/t20100713_1219131.html,2010-07-1309:21:“胃里肛门藏毒品 罪犯运毒险丧命刚出监狱又被抓。”
⑥ 无论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道德或不道德的,合法还是违法的目的。
[1]何士青.论法治与公民幸福[J].政法论丛,2012,1.
[2]Petrazycki,Law and Morality,trans 1,H.W.Babb,Cambridge,Mass,1955.
[3][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4]武宏志.论式:法律逻辑研究的新方向[J].政法论丛,2011,6.
[5]See Richard H.S.Tur,‘Defeasibilism’,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1(2001)
[6][美]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M].王昺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7]Neil MacChormick,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A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9][法]丹·斯珀波,[英]迪埃珏·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M].蒋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蒋晓伟.论我国的法律文化[J].政法论丛,2012,5.
[11]江国华.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J].政法论丛,2012,3.
[12]朱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关于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的故事[J].比较法研究,1998,1.
[13][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4]孙培福,黄春燕.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J].齐鲁学刊,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