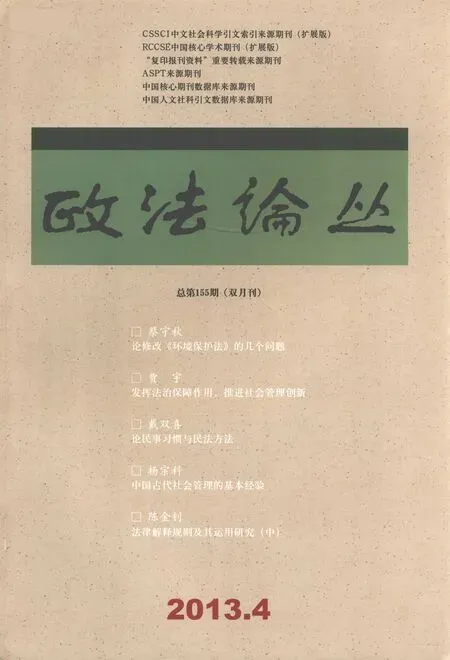论民事习惯与民法方法
——以《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经验为例
戴双喜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论民事习惯与民法方法
——以《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经验为例
戴双喜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中国未来民法典与其传统伦理、传统法文化的重要渊源——民事习惯之关系问题在民法学界基本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日本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民事习惯所采取的从排斥到吸纳甚至给予极高地位的反复经验对中国未来民法典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可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日本民法典有关民事习惯的制度安排及其后续遗留问题的处理模式对中国未来民法典民事习惯位置的讨论提供了生动的个案。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程度需要将来的民法典必需慎重对待中国固有民事习惯,以便保障民法典的伦理基础和惯行定式。
“法典之争” 民事习惯 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当代法律人乃至前辈们半个多世纪的凤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走入市场经济,调整民事关系的主要法律陆续被制定出来。现已初步形成以民法通则为主体,包括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以及大量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在内的庞大的民事法律规则体系。但立法时间跨度大,其间中国社会变革急剧,各种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严重。于是,制定统一的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虽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但被强大的制定民法典的呼声所淹没。[1]中国民法学界对未来民法典以何为本的问题上意见尚不统一,基本的态势是对外国先进民法制度的借鉴和移植比较充分,而对作为中国本土资源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传统习惯的研究则做得相当不够。[2]尤其是作为传统伦理、传统法文化的重要渊源——民事习惯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的讨论基本没有深入展开。纵观亚洲各国现代民法典制定之背景就会发现,各国在制定民法典之前无一例外做了如下几项重要的工作:一是翻译和研究外国民法典;二是成立专门的法典编纂机构;三是成立负责机构,调查本国民商事习惯。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法典的制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绝非易事。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也应当依循上述足迹。笔者以近邻——日本民法典制定经验为蓝本,探讨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民法典制定中的民事习惯问题。
一、日本近代史上的“法典之争”
在日本,任何研究和探讨日本民法史的论著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非“法典之争”莫属。1890 年日本旧民法公布于世,日本法学界以法学学派为分界点,围绕民法典的“延期”和“断行”以及旧民法是否反映了日本社会伦理和民俗基础为核心,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争论,法律史上称之为“法典之争”。“法典之争”所产生的影响从法学波及到政治,反映日本社会伦理基础和民事惯行定式的民事习惯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争论,彻底改变了民事习惯在日本民法典中的命运,也给出台一部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法典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日本法律史上的“法典之争”应当以法学学派的脉络谈起,因为法学学派的不同立场、观点是“法典之争”的重要起因。近代日本法学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渊源: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自然法学说。在明治初期,法国学者博瓦索纳德被当时的日本司法省邀请作顾问,并作为司法省法学校的教师,讲授自然法。[3]P175所以,日本早期民法学说深受法国的影响。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学派,根据法国经验,主张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也可以称之为法典派。日本近代另一重要法学学说发祥地为东京开成学校。开成学校虽然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但最初讲授英国法。英国法学派信奉以奥斯丁所限定的法律学领域,即现行法主义。英国法学派认为奥斯丁的学说是19世纪新型学说,并以日本习惯法国粹论和以法典主义要以法国法律代替日本法律为理由,强烈反对法国法典派,[3]P190-191从而,这个学派又称之为非法典派。两种法学学说在当时的日本,观点相对,争论非常激烈,互不相容,二者的分歧很快集中到明治政府所计划制定统一民法典问题上。在法国学者博瓦索纳德和日本国内深受法国法学说影响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日本旧民法公布于世。但日本旧民法公布后立即遭到了国内英国法学派的强烈抵制。英国法学派的毕业生团体法学士会发表了延期意见。[3]P192延期派认为民法典亲属法部分的规定与日本的传统家族惯行相脱离,甚至出现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论断。[4]P16围绕法典制定以何为本以及“延期”还是“断行”为核心的两个问题,延期派与断行派之间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即“法典论争”。当初断行派占优势,但最终,延期派战胜了断行派,日本旧民法典被迫延期。这种法学学派的争论虽然推延了日本民法典的诞生,但对后期成熟而稳健的民法典的出台发挥了巨大作用。它的意义至少应该有三个方面:一是学派争论过程造就了一大批民法学家,推进了日本民法学的科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二是催生了第三学派,即德国法学派,对潘特克吞体系的引入功不可没;三是促使日本民法典重视民事习惯,为日本民法典与日本社会的契合,奠定了基础。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明治七年(1874年),法国学者博瓦索纳德在司法省讲授自然法、参与起草日本旧民法典之始,东京开成学校也开始教授英国法律。趁着民法典的起草,日本法学教育蓬勃发展。伴随“法典之争”,代表两大学派的毕业生从各自立场,成立学术组织、著书立说,促进了法学研究和教学。“法典之争”还造就了如梅谦次郎、穗积陈重、富井政章等起草日本民法典的法学家。这些法学家给日本培养了法学中坚力量,如我妻荣等民法学家。可以说,日本民法典立法工作是以翻译法国民法典为起始点的。[5]P1但经过“法典之争”成长起来的法学家,改变了简单“翻译”法国民法典的立法思路。日本民法典起草者们深厚的比较民法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础。[6]
“法典之争”的第二个贡献是催生了第三法学派——德国法学派。明治十八年,原属于文部省管辖的司法省法学校与法科大学合并,成为法科大学法兰西法学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明治十九年(1886年),日本颁布了帝国大学令,次年,在法科大学原有的英法法科之外,设立了德法科。[3]P200德国学派在明治初期,与强大的法兰西学派相比较而言,地位甚弱,还不能称之为独立的学派。但随着明治初年,日本学者翻译德国民法学家著作开始,德国法学派逐渐崭露头角,其中有三位学者可称之为日本德国法学派的启蒙者。他们是中江笃介、山胁玄、平田东助三个人,尤其后两位学者,当时出版了(德)温德沙德(Beruhard Windscheid——笔者注)的《独逸民法通论》,德国民法学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注意。以此之始,温德沙德的影响波及日本,非比寻常。后来德国法学派兴起时刻,此宗法律学派整体转向潘特克吞体系。[3]P200日本新民法起草之始,日本法学界法国法学派逐渐衰落,与此相对立的英国法学派也因失去对手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而德国法学派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如日本民法典起草者梅谦次郎、穗积陈重、富井政章三人中后两者均是德国法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支持延期派的核心力量之一。穗积陈重博士在“法典争论”中发表文章,支持“法典” 延期的同时,在议会,从延期派立场广泛呼吁,延期日本旧民商法典的施行。[7]P37日本德国法学派兴起后,重新审视民法典制定思路,对日本新民法典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日本新民法时代就是德国法学派蓬勃的时期,日本民法学也进入了注释法学时代。[7]P199-200于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所建立的历史法学派的新学说占据了日本自然法学说。法律是民族精神的发现、历史的产物等观点,被大部分法律学者所信奉,而且这一思想和学说支配了后续明治时期,一直到大正初期。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对日本新民法典的起草产生了重大影响。民法典起草人之一,与梅谦次郎一同在法国理昂大学留学的富井政章博士,抛弃自然法的观点,融入到历史法学派,其结果成为日本民法学界德国法学派的鼻祖,对日本民法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7]P206虽然说日本新民法是平等参考了法德两国法,但其形式完全是德国式的,其内容也大量参考了德国民法第一草案,与旧民法纯粹的法兰西风格相对,新民法顿时增添了很多德意志色彩。[3]P200因此,可以讲,“法典之争”造就了德国法学派,德国法学派以新颖的法律观点和学说占据了当时日本的主流法学学说——自然法学说,成为日后日本新民法典起草的主要理论工具之一。[4]P10
“法典之争”第三个贡献是日本传统民事习惯的价值重新被发现。日本旧民法典起草之时,面对实力强大的西方列强,明治政府为了达到废除治外法权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编纂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程,其中也包括民事习惯调查。日本民事习惯调查工作早在旧民法典起草之时就已经开始。明治九年(1876年)为民法编纂提供材料,在司法省成立地方民事习惯调查局,并任命生田精为主任[8]P10。日本全国性民事习惯调查进行了两次,准确时间在日本近代法制史上存在争议,日本学者据各种档案材料考证,第一次是在明治九年5-11月,并在明治十年(1877年)出版了第一次调查资料——《民事惯例类集》(简称十年版)。[8]P27第二次民事习惯调查是在明治十一年(1878年)1-12月,调查辑录在明治十三年(1880年)出版(简称十三年版)。[8]P57由于战乱,当前保留下来的是明治十三年版的《民事惯例类集》。为何出现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其中的原因不是非常的清楚。根据学者考证,第一次民事习惯调查可能因客观原因被中断,调查材料不充分,因此,为了补充材料,到更多的郡做调查变得非常必要。[8] P54-55日本民事习惯调查并不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法国法学派起草人所倡导,而是一位被日本司法省所雇用的美国人赫利(Geoge W.Hill)①提出的建议。赫利认为,民法典编纂之际,以原样继受西欧“近代法律”是错误的,仿照六世纪东罗马皇帝尤士丁尼的立法经验,强调有必要对日本旧法律制度进行集成。并且他作为英美法学者,从重视判例的立场提出,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募集“昔时裁判官所作出的各种诉讼裁决录”,“掌握昔时惯习,也就是普通法”是最紧急和必要的任务。[8]P11-12明治九年5月2日(1876年),赫利作为司法省所聘请顾问,向司法卿提交了《关于日本民法及其习惯法编纂意见书》,提出了上述民事习惯调查和募集诉讼判决录的意见。②赫利的意见被当时的司法省采纳,司法省成立专门调查机构,着手进行民事习惯调查。这是日本近代史上,为民法典的制定而开展民事习惯调查的最初缘起。
日本近代史上,两次的民事习惯调查均以“为了给民法典编纂提供材料”为目的。在司法省的组织下,以生田精为代表的调查组耗费一年半时间,走遍日本全国收集和调查,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这对旧民法编纂而言,是否就意味着当时起草民法典之时,两本《民事惯例类集》应被评价为必要或不可欠缺的呢?答案是否定的。[8]P8其中的缘由非常复杂,后来的学者作了很多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起草民法典的学者急于制定一部“日本版”的法国民法典而“故意”忽视了民事习惯调查辑录,甚至存在蔑视民事习惯调查辑录的现象,这纯粹是当时政治和学派偏见导致的;二是认为,以当时日本法学研究水准和立法技术,无法使民事习惯调查辑录转换成近代意义的民事规范;三是重视民事习惯调查辑录的学者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还没有进入核心层或被边缘化。[8]P82-89这是日本近代民事习惯调查被排除日本旧民法的主要因素。日本旧民法的体例是按照法国民法典的章节编排方式安排,对民事习惯法律渊源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陈涉及家庭、继承和婚姻领域极少数条款采用固有民事习惯之外,民事习惯的影响微乎其微。
日本近代民事习惯调查虽然对旧民法的起草没有发挥作用,但随后展开的“法典之争”中却成为延期派对断行派发难的主要材料,尤其是参与新民法典起草者以及“延期派”学者,频繁引用民事习惯调查辑录,批评断行派制定出来的脱离日本社会实际的民法典。
二、日本民事习惯调查与日本民法典的制定
“法典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是,日本近代以儒教思想为支撑点的旧武士阶层的家族道德与西欧近代民法中的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进行协调,脱离日本“家族制度”的民法典能否被有效推行?如后来学者总结:晚辈身份的妻或子对长辈身份的夫或父享有权利,况且,允许晚辈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向裁判所提起诉讼,控告长辈,这对保守派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5]P17这对以维护传统道德为立场的延期派来讲,对断行派发动攻击的最好武器之一就是反映传统家族制度,维系“家父长”制度的民事习惯调查资料。因此,延期派的学者纷纷引用民事习惯调查辑录的内容,批判断行派。延期派在引用民事习惯之时,不仅限于婚姻、继承和亲属制度方面,如物权习惯、债权习惯也在其例。如穗积陈重的《隐居论》、穗积重远的《离婚制度研究》、奥田义人的《民法继承论》和田守菊次郎的《法典修正实施先后论》等等。[8]P7上述学者均是延期派的代表人物。民事习惯调查辑录的价值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中重新被挖掘出来,对后来民法典吸收民事习惯、民事习惯位置安排提供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首先,民事习惯调查辑录对抛弃不符合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相关规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旧民法基本是法国民法典的抄袭版。在旧民法起草过程中,法典取调委员会认为:“本邦固有习惯多,外国人起草此法甚难,如财产取得篇的继承、赠与以及夫妇之财产契约等与人事之关系密切,亦委任外国人起草甚难,故,人事篇以及继承、赠与、夫妻财产契约诸章任命本邦之人起草。”[9]P122似乎旧民法的起草充分尊重了日本固有之民之习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旧民法的起草是在法国人博瓦索纳德的主持下展开,对亲属篇的起草不可能不征求博氏的意见。另外,不是夫妻财产契约、继承、赠与、亲属部分符合日本传统就能够避免旧民法脱离日本社会实际。如日本旧民法草案中根据法国民法典的内容,制定了用益权制度。③用益权制度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共有的具有深厚习惯因素的制度。如法国民法典以此为契机,保留了与农业经济相适应的诸多民事习惯,“用益物权还受到历史传统、民众生活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表现出强烈的固有性的特点。”[10]P412德国民法典正是以“习惯法”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的态度对待各邦民事习惯的,通过用益权制度,吸收了诸多民事习惯。归纳德国民法典用益物权种类就会发现,其复杂程度是任何其它国家民法所不及。对此学者们解释为:其所以如此复杂,系德国民法制定于德国统一之后(1896年制定,1900年施行),必须顾及各地的习惯。④因此,可以说,用益权制度是德法民法典所共有的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在1898年实施的、参考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日本民法典却排除了“用益权”制度。
大陆法系民法的体例和法典化运动影响了当时亚洲主要两个国家——日本和中国。但大陆法系民法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用益权制度在“东进”过程中却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在西法东进中,用益权却“消失”了。用益权在罗马法中是“为了给寡妇提供生活供给”[11]为目的而出现,故可视为现今德国所谓用益供给的直接起源。用益权制度是西方国家早期与养老、扶养有关的重要物权制度。日本和中国民法排斥用益权,究其具体情况,学者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养老之方面历来以家族赡养为主要形式,没有形成类似大陆法系的相关养老习惯。因此,民法典如何适应一个社会实际,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去理解习惯仅仅集中在婚姻、家庭和继承等领域。日本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无疑民事习惯调查在这一方面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显现的。
其次,日本民事习惯调查辑录对日本民法典如何在宏观上安排民事习惯法律渊源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这是民法典获得活力的重要因素。日本旧民法是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起草的,由于体例以及制定民法典心情急切,对民事习惯法律渊源地位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法国民法典和和德国民法典在总则中均不承认民事习惯的法源地位。“《法国民法典》即有否认民事习惯效力的倾向”[12]P6。“《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习惯的效力未作一般性规定,仅在第157条和242条(交易习惯——笔者注)规定,解释契约和履行契约应顾及交易上之习惯。”[13]日本民法典虽然以德国民法典作为最主要的参考资料起草和制定,但在民事习惯法律渊源位置安排上并没有学习德国的经验。《日本民法典》第92条规定:“习惯与法令中有关公共秩序规定之外其他条款相异的,能够认定法律行为当事者有依其习惯意思表示的,遵循其习惯。”日本民法典有关民事习惯法律渊源地位的认可,实属来之不易。日本旧民法起草之时,1876年,法典编纂局下设四个课,其中以生田精为主任的第四课负责民事习惯的收集和调查,到1898年,日本民法公布实施,经过22年,中间经“法典之争”的洗礼,民事习惯成为日本民法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日本民法典认可民事习惯法律渊源地位是因为,一方面延期派在“法典之争”中呼吁日本民法典应当以体现和反映日本社会实际为理由,给日后民法典吸收和承认民事习惯提供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受到了现代民法鼻祖——瑞士民法典的影响。
1897年制定,1907年12月实施的《瑞士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审判官依习惯,无习惯者自居于立法者地位所应行制定之法规判断之。”⑤瑞士民法的做法被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例如,土耳其民法、泰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等等。民事习惯从近代民法典中被排斥的厄运中解脱出来,大有回归之态势。学者对其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时指出:极端理性主义的动摇、成文法局限性被人们所体认,绝对法制统一的动摇以及积极全能国家观念被抛弃是主要的原因。[13]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制定法“化石化”,给民法典适应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张力,因此,法典本身给法官解释法典、吸收习惯、创制新的民事规则,就变得非常重要。日本民法典是世纪之交各种政治力量、经济转型和学术思想相互妥协的产物,其对称之为现代民法之先河的瑞士民法典的经验,不可能无动于衷。很快,在日本法例中认可了民事习惯的重要法律地位,日本《法例》第2条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的习惯,对依据法令有规定的事项或无法令规定事项,与法律有同等的效力。”
第三,日本民法典吸收了部分民事习惯作为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民法典的内容与社会民众民事生活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日本民法大量吸收民事习惯是在法典的亲属和继承两篇。后续学者总结日本民法典特征时讲到:“民法典的亲属、继承两编中尊重‘家’,牺牲个人的尊严,无视父与母、夫与妻、子与女之间的实质平等的规定颇多。”[14]P11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尤其二战之后,日本确立了西方个人主义的观点,人格尊严平等观深入人心,日本民法中的有关亲属和继承两篇也被全面修正。有学者认为,这是对日本民法个人主义法思想不彻底的一次历史清算。[14]P11但当时日本社会的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很大,民法典不得不做出妥协,这是历史的选择。日本民法典不仅在亲属和继承两篇中大量吸收了当时日本各类民事习惯,在被后续学者认为的彻底体现西方个人主义的财产篇里实际上也吸收了具体的民事习惯。如《日本民法》第217条、219条、228条和236条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第263条、294条的入会惯行;第268条、269条地上权的规定;第277条、278条279条有关永小作权的规定等,都是来源于民事习惯。[4]P31日本民法上述民事习惯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法明文规定的民事习惯在其调整范围之内优先于国家制定法。如《日本民法》第236条规定:“如果存在相异的习惯,前二条的规定遵循其习惯”。这里指的“前二条”是指日本民法典第234条和第235条。实质上,前面两条的法律适用秩序上民事习惯优先于国家制定法,如果把类似条款算作日本民法有关民事习惯条款,民事习惯在民法典的比例是很大的。除此之外,根据日本法例的规定,民事习惯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与制定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司法裁判中被认可的民事习惯也可以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通过这一渠道被认可的民事习惯有立木交易习惯、温泉惯行和水利惯行等等。日本民法典除以具体法律条文认可民事习惯之外,还通过交易习惯条款,吸纳民众所遵循的旧民事习惯或者新产生的民事习惯不断进入民事法律,使民法的内容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因此,日本法学界对民事习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日本民法学家我妻荣认为,民法从渊源上而言,应当存在四种民法:一是普通民法,即成文法民法典;二是民法典之外的成文的民事特别法律;三是惯习民法;四是判例民法四部分构成。[14]P19因此,日本民法对本国民事习惯非常重视,认为民事习惯是日本民法典适应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也是民事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渊源。
三、日本民法经验的中国启示
现代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给予民事习惯评价时总结到:“因为社会生活是流动的,习惯法会自然而然不断产生,成文法再完备也无法永久阻止其产生,这是社会事实。无论学说上如何占有优势,习惯法还是作为事实存在下去。”[14]P19因此,作为民法典,在技术上绝对不能无视民事习惯的存在。基于上述理由,我妻荣教授认为,习惯法终究会达到废改成文法的目的。[14]P19从日本学者站在本国民法学立场,对日本民法中的民事习惯所做的评价中可以轻易推测出,民法典如何对待民事习惯是民法学中的重要实践课题和理论问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在日本法学界,对民事习惯的调查和更新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制定法的僵化以及新的民事习惯或旧民事习惯不断地逼迫制定法做出必要的调整。日本民法典实施之后,第一次修改就是因为永小作权习惯的规定不符合社会实际而被迫做出修改。日本学者总结到,“当时倍受到批评的入会权和农村水利权的规定,没有理会学说和判例的努力,没有做出修改,今天依然留下很多问题。”[14]P13日本民法中的民事习惯后遗症的根源就在于因条约修改的政治目的而匆忙起草和制定民法典,没有足够时间充分调查农村存在的民法惯行,即民事习惯。因此,只要修改民法就会引来一个民事习惯的再调查,每次立法中有关借地权或永小作权等都在被重复调查。[8]P84日本民法中的民事习惯命运、波折以及后世学者的警示,对今天中国民法典中的民事习惯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1.不能轻视民事习惯,重蹈日本覆辙,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日本民法典起草之始,主要目的在于废除治外法权,夺回国家主权。在这种政治目的下,民法典的起草过于匆忙,以致在“法典之争”中被迫延期。这一背景使得反映日本社会伦理、民俗和法律惯行的民事习惯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后来重新起草民法典,涉及财产权的民事习惯虽然一定程度上被民法所吸收,但不成熟,最终不断被修改和补正,这是从日本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必需吸取的一个教训。
1949年2月,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在大陆被废止。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现过两次制定民法典的动议,但由于各种运动、人治思想、经济基础之不适而被放止;在20世纪80年代末制定《民法通则》之始,市场经济制度还刚刚开始,也没有人主张对民事习惯进行调查,如何使民事立法更多地体现国家民众之风俗习惯等问题未被纳入议事规程。致使民事习惯长期徘徊于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民法学家也没有倾注必要的经历研究民事习惯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5]P29当下民法典起草活动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少有人提及民事习惯。到今天为止,立法过程中,我们很难发现习惯的影子,没有系统的习惯调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很少表现出对民间习惯一类社会实践的‘同情和了解’,遑论重视和尊重;也不曾组织和进行类似清末和民国时期规模可观的习惯调查。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当重复当年的习惯调查,而在于如何认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16]曾经为学者提倡的“有法律时从法律,无法律时从习惯”的语句,在全国人大正式公布的草案中,也无踪影。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有严重轻视民事习惯的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将来的民法典如果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不能与中国民俗、伦理相衔接,那将是中国法治历程上最大败笔。我们在理论上过多地强调了民法与市场经济的关联性,而对作为民法本体的伦理性则表现出不应有的冷漠。[17]有学者总结到:“民法虽然主要是调整财产(经济)关系的,但就其产生和演变来说,对人(其中特别是公民)自身的价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权利的关注远胜于对财产的关注。这也是民法区别于商法的表现之一。”[2]而笔者认为,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也带有很强的社会伦理和惯行特点。如在文章前面谈到的,在法德等西方国家民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用益权制度在东方国家民法典中并没有出现。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东方,并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家庭制度,即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家庭观念,没有西方式的设定用益权的养老制度、扶养制度。用益权制度虽然作为调整财产用益关系的规则,被西方国家民法中普遍得到认可,但它不适合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家庭伦理和处理财产关系的惯行。因此,民法规定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均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和惯行定式。就制度资源理论而言,直接反映社会伦理和惯行的规则体系,毫无疑问是民众有意识无意识遵循的习惯体系,对民法而言,就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民事习惯。中国将来的民法典如果不能反映社会伦理,不能与民众民事惯行之间找到契合点,那只能是空中阁楼。我们的近邻,同样是以儒教为主要思想体系的日本民法典就是最好的经验。其实,对立法中轻忽社会倾向的批评也来自民法学界内部。批评者以时效、不动产交易登记、农村承包等制度为例,说明立法者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够,更进一步指出,民法典应“与中国实际接轨”,而不是与“各国民法接轨”。[17]
2.民事习惯的流变性特质决定,民法典的制定必需考虑民事习惯因素。当下,很多人可能会问,中国有民事习惯吗?这个问题借助人类学语言,恐怕不能在“摇椅”上回答,只能靠扎实的实证研究。退一步讲,中国有民事习惯,但是否是不符合现代化的“陋习”?中国民法学界不止一两位学者有这样的疑问。日本学者我妻荣对自己提出的“惯习民法”时谈到:“如果不存在否定民事习惯法效力的法律条文,习惯法从正面直接被适用;如果反过来,不得已,习惯法会通过迂回的方式发挥作用。”[14]P19也就是说,如果在法律文本上不承认习惯法的法律效力,习惯法会以间接的方式依然发挥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这就是在中国社会看到的,国家制定法经常被习惯法“打败”的情形。因此,我妻荣认为:“结局只是形式或时间问题,习惯法最终会达到废改成文法的目的……。因此,着眼于习惯法上述终局效力,正面审视习惯法废改成文法这一事实,把惯习法提高到与成文法对等的位置。”[14]P19根据上述论断,民事习惯具有以下几个特质:一是从历史渊源而言,习惯法是成文法的源头;二是国家制定法不是民法的唯一渊源;三是民事习惯是终局效力的法律规范;四是习惯法是一种流变的知识体系。前三个论断在历史法学派的论著中颇多,在这里不再赘述。民事习惯第四个特点,对回答前面两个问题意义更大。首先,诚如“民间的习惯并不总是陋习,也并不是固定不变”,[18]民事习惯是一个不断流变的知识体系,它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变化的问题,这是关键。当然,当下中国社会到底有哪些民事习惯,这是超出笔者能力范围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搞全国范围内的民事习惯调查和司法调查。当然,“翻箱倒柜”是发掘和整理不出民事习惯的。“作为上层建筑之一部分的习惯一定会并总是会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随着社会制约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流变。”[18]其次,民事习惯流变性特质的主要动力是社会需求的变化。如果某个民事习惯社会不需求的时候,它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某民事习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它就会作出自我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如果社会需求,僵化的制定法又不能也不可能创设新规则情况下,人民大众会以自己的智慧创设新的交易规则,以满足社会生活的制度短缺问题。因此,民事习惯的流变性特质决定,否定其与时俱进是不恰当的,认为民事习惯都是“陋习”的论断更是以偏概全。习惯法的这一特质在历史法学派的著作中论述已达登峰造极的程度,这里不再赘述。
现代民法利用民事习惯流变的特质,可从三个方面防范成文法蜕变为“化石”的危险:一是通过民法总则部分,总体上认可民事习惯法律渊源地位,避免成文法的僵化,给司法吸收民事习惯创造条件;二是在具体民事法律条文中吸收稳定的民事习惯作为法律条文的组成部分,民事习惯成文化;三是部分涉及民事习惯较多的民事行为,允许行为人遵循民事习惯,援用秩序上民事习惯优先于国家制定法。如《日本民法典》总则92条、法例第2条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民事行为当事人双方依民事习惯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行为。日本民法不仅在总则部分规定了民事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而且还在具体条文中结合日本交易惯行,认可部分民事习惯,例如入会权、永小作权、地上权、相邻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民法典在涉及民事习惯的民事行为上,通常民事习惯优先于国家制定法。日本民法虽然是以德国民法典作为最主要蓝本加以借鉴,但非常灵活地创设了民事习惯法律渊源,在当时看来,已力所能及地照顾到了本国民事惯行。这是日本民法典被日本民众所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日本民法典不断获得活力的基础。
站在中国立场上,回顾日本民法的经验时,不得不对中国当前民法典制定的思路做出反思。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不是急于搞出几个版本的民法典,而是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事习惯调查和司法调查。这不是一两个学者所能完成的浩大工程,而应由全国人大或者司法部牵头,组织相关学者和人员有计划的进行民事习惯调查,在此基础上再组织相关专家起草民法典。否则,将来的中国民法典和中国社会成为两张皮,民法典有失去社会根基的危险。
3.中国社会结构特点要求民法典必需重视民事习惯。中国社会结构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展开描述。从纵向而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格局恐怕短时间之内还无法打破。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并不是说中国农业在世界上占有强势地位,而是世界上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城市化进程在加快进行,但城市化不是无止境的,因为城市必需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去养活。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8日发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当前城镇人口 59379万人,乡村人口72750万人。[19]实质上,近6亿城镇人口,其中包括小城镇城市人口,中国实际农业人口近9亿。这个庞大群体的交易惯行如果被排除在中国民法典之外或其法律诉求得不到满足时,我们将来的民法典还能剩下什么?因此,依据现代法治理念为基点的民法典,必需考虑中国广袤而人口众多的乡土社会的实际交易惯行和社会伦理基础。
以法国民法典制定的社会背景为例,法国民法典颁行之前的1800年,法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结构比例为35%左右的人口居住于城市,剩余65%的人口还在农村从事农业,[20]P20农业人口比重在整个法国占绝对多数。以德国为例,17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众多邦国的集合体,没有条件实行经济一体化,政治上也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社会的政治、经济上的整合。这种历史条件给德国民法典的制定带来了重要的命题,即对各邦的固有的民事习惯如何对待。在法学家们的鼓吹以及政治上的压力下,起草者不得不重视各邦传统民事习惯的作用。这种历史环境给德国民法典吸收各邦民事习惯创造了动力。以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观点,法律的发展表现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法,其法律渊源主要体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是学术法,法律既属于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又属于法学家手中一门技术;第三阶段是法典法,既以学术法为基础编纂法律家与民众共守的规范体系。[21]P52历史是具有继承性的,而且不能一刀切式的断开。德国民法典正是以“习惯法”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的态度对待各邦民事习惯的。在法国民法典,连牲畜粪便的归属在内都有规定,其法典散发着浓浓的“泥土的气息”和“牛粪的味道”。这一切均归功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民事习惯的重视、信任以及吸纳。
日本民法典制定之始,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近20年,产业革命刚刚开始,日本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但日本产业革命的深化并没有对日本社会结构产生实质影响。产业革命期,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但也留下了诸多后进性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残留了很多不完备的因素。[22]P4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本农村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是日本经济史达成的基本共识。虽然机械制造大工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日本广大农村社会并没有彻底地解体,更重要的是被扭曲为产业结构的一方,持续存在着。[22]P4日本民法典的制定不得不考虑这些广大农村地区的现实,必须尊重其伦理和法律惯行方式,这是日本社会接受民法典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日本民法典重视民事习惯的吸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社会从横向来讲,又存在土地广袤而人口相对稀少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不足全国人口13%,但其聚居区却占有中国64%的土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形态、文化氛围不同于汉族地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有权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其法律意识和传统上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未来的民法典还要考虑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化的特征,否则,通过法典,统一市场、促进国家的凝聚力等目标无法实现。对中国民法文化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中国民事立法进程对少数民族民事习惯的关注严重不足。清末民法法典化运动中虽然做了大量的民事习惯调查,但其调查范围在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有效展开。一方面,在清朝统治时期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很封闭的状态,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保持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还在旧有体制中运转。这一局面到了民国时期有所改观,但民国民事立法调查活动因内外各种复杂因素决定,未能对少数民族地区展开有效的民事习惯调查,少数民族民事习惯对中国民事立法进程的影响甚微。另一方面,清朝末期民事立法以“更符合西方民法的标准”为事实上的立法实质精神,《大清民律草案》并没有充分体现本国民事习惯,何况是少数民族的民事习惯乎。民国时期“民事习惯在民法典中直接体现极少”,[20]P218究其原因,“法律家关于民事习惯的基本观点就是:民事习惯多为地方性习惯,且不良习惯居多。”[20]P218新中国建立后,民事法律真正得到发展和引起重视还是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发展之后的事情,计划经济一刀切的传统思想当时没有彻底改变,为了急于赶上西方国家的法制进程,包括汉族地区的民事习惯在内统统被立法者所忽略,少数民族民事习惯更是无人问津。
因此,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必须慎重对待9亿农民以及占全国64%土地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广大基层民众的民事习惯。否则,我们所制定出来的民法典就是充斥着混凝土、钢筋、水泥的冰凉和冷漠,最需要贴近民众的民法典则可能与它理应产生的土壤相分离。
注释:
① 此人何时以何目的来日本不是很清楚,其在明治5年玛利亚·路斯号事件中担任法官,由于贡献突出,明治6年被司法省聘请为顾问。参见利光三津夫、手塚豊著:《民事慣例類集》,慶應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昭和44年第91頁。
② 学者利光三津夫、手塚豊的《民事慣例類集》一书中载有当时赫利提出的意见书全文,这里只摘录了部分内容,参见利光三津夫、手塚豊著:《民事慣例類集》,慶應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昭和44年第93-94頁。
③ 日本旧民法草案第二编,第一部第二章用收权、使用权以及居住权。参见前田達明著:《史料民法典著》,株式会社成文堂,2004年第764頁。
④ 德国民法上的用益物权可概括分为地上权、役权和土地负担。其中役权的人役权、用益权、居住权;其中用益权又有物上用益权、权利用益权及财产用益权。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⑤ 对此条还有其他的译法,如“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参见殷生根译,艾棠校:《瑞士民法典》,法律出社,1987年版第1页。
[1] 李凤章,郝磊.民法典法典化与习惯缺失之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1.
[2] 赵万一.论民法的伦理性价值[J].法商研究,2003,6.
[3] [日]岩田新.日本民法史-民法を通いじて見たる明治大正思想史[M].株式会社同文館行,1928.
[4] [日]吉田豊.民法総則講義[M].中央大学出版部,2000.
[5] [日]前田達明.史料民法典[M].株式会社成文堂,2004.
[6] 焦富民.论日本民法典的基本特点——兼及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7] [日]福島正夫.穗積陳重立法関係文書の研究[M].信山社,平成元年.
[8] [日]利光三津夫,手塚豊.民事慣例類集[M].慶應義塾大学法学研究会,昭和44年.
[9] [日]中村菊男.近代日本の法的成形―条約改正と法典編纂[M].有信堂昭和31年.
[10] 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大学出版社,2003.
[11] 米健.用益权的实质及其现实思考[J].政法论坛,1999,4.
[12] 史尚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 谢鸿飞.论民事习惯在近现代民法中的地位[J].法学,1998,3.
[14] [日]我妻荣.民法総則《民法講義Ⅰ》[M].岩波書店刊行,昭和41年.
[15] 戴双喜.游牧者的财产法——蒙古族苏鲁克民事习惯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16] 李凤章,郝磊.民法典法典化与习惯缺失之忧[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1.
[17] 梁治平.没有市民社会的市民法典[A].法学家茶座[C](3).山东人民出版,2003.
[18] 苏力.当代中国法律中的习惯——一个制定法的透视[J].法学评论,2001,3.
[19] 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gov.cn/test/2009-02/26/content 1243894.
[20] 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一九0一至一九四九[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1] 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22] [日]武田晴人,中林真幸.展望日本歴史18·近代の経済構造[M].東京東堂出版,2000.
OnCivilHabitsandCivilMethods——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Civil Code
DaiShuang-xi
(Law Schoo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1)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and its future Civil Code, traditional cultu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aw - Civil habits relations in civil law scholars basically no in-depth discussion. Japanese Civil Code making process adopted for civil customary exclusion to absorb even give a high position in the future of China's repeated experience of how to embod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ivil Code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Japanese Civil Code concerning civil customar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subsequent problems left over from processing mode for China's future habits of the Civil Code Civil provides a lively discussion of the location of the case. China's curr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in the future must be careful to treat China's civil code civil inherent habit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eth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es Civil lines established formula.
Codex Dispute; civil habit; Civil Code
DF03
A
(责任编辑:唐艳秋)
戴双喜(1972-),男,内蒙古科右前旗人,法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事习惯。
1002—6274(2013)04—019—09
——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失范与规制